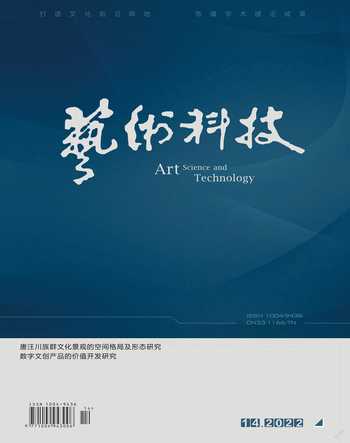新主流電影的轉型與創新
摘要:主旋律電影旨在表現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價值,新主流電影由主旋律電影發展而來,歷經多次變化,新主流電影應不斷完善自身以應對市場變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新主流電影開創電影生產的新模式。電影《狙擊手》給新主流電影的轉型與創新發展帶來重要的啟示。文章以電影《狙擊手》為例,分析新主流電影的界定與演變,探討新主流電影的轉型與創新。
關鍵詞:新主流電影;主旋律電影;《狙擊手》;轉型;創新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14-000-04
在我國,主旋律電影有重要的宣傳教育功能,在電影市場也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主旋律電影自誕生以來,就一直與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和民族英雄人物事跡緊密聯系。20世紀末,電影市場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早期刻板單一的主旋律電影在海外引進片的沖擊之下發生改變,積極吸收好萊塢商業類型片的元素加以創作,從主旋律電影逐漸過渡到了主流電影。主流電影進入21世紀之后又經歷了三次改變,才成為今天的新主流電影[1],可以把新主流電影看作主流電影在新時代自我嬗變的一種新形態[2]。
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探索,主旋律電影用影像講述中國故事,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塑造大國形象的主要目的延續到現在。而如何用專業的創作手法講好故事、傳遞好情感是如今新主流電影面臨的問題。電影《狙擊手》在2022年春節檔上映,既是一部有關抗美援朝戰爭的故事片,又是一部有重要意義的新主流電影,對當前身處創作困境的新主流電影實現創作的轉型與創新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1 新主流電影的界定與演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新主流電影的藝術表達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通過影像展現出中國力量和中國精神。新主流電影由主旋律電影發展而來,兼具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特點。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新主流電影成為一種展現國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電影,具有成熟的商業敘事特征[3]。
學者馬寧最早提出了新主流電影這一概念,原指那些低成本且有新意的國產電影[4]。早期的主旋律電影創作較為刻板,故事劇情單一缺乏自身特色,人物扁平缺少立體化的塑造,陷入一味表現正面人物的桎梏之中,在沒有海外引進片的時代仍很難得到觀眾的青睞,電影的市場表現極其慘淡。20世紀末,在社會經濟和大眾文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商業類型電影開始充斥電影市場,眾多優秀的海外引進片進入了國內觀眾的視野,觀眾的觀影訴求和審美取向變得多元,電影的類型表達在這一時期開始變得尤為重要,于是主旋律電影吸收了各種商業類型片的創作方法和理念,創新了主流價值和文化表達方式。1999年,中國青年電影作品研討會上提出了“新主流電影”這一概念,針對當時中國電影所處的困境,一群年輕導演開始改造中國電影,將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與當時的市場環境相結合,提出了“新主流電影”的思路[5]。
進入21世紀,關于新主流電影的真正界定眾說紛紜。馬寧認為新主流電影是從2000年正式起步的,并將新主流電影看作主流電影的一種補充之作[6]。學者張夢飛將主流電影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從1949年到1979年的主流時期;再到2009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衰落;2009年以后,主流電影在商業化轉型下迎來了復興[5]。而陳旭光教授則認為,直到21世紀以后,主流電影在三次轉變后才最終成為“新主流”。第一次轉變發生在“三建”系列電影中,即《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第二次轉變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深入后,出現了《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等在國際上宣傳中國形象的“外向型大片”;第三次轉變是在2019年之后,以《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等呈現平民化趨向的“內向型小片”為代表[1]。
盡管關于新主流電影的界定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但新主流電影是從主旋律電影發展而來的這一事實已經得到一致的認可。新主流電影的概念或許就是不斷變化的,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解讀,也有不同的發展,而當下所探討的新主流電影就是一種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結合商業類型片的敘事手法,并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展現國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電影。
2 轉型:細微處見證偉大,樸素中直面殘酷
2.1 小視角探討大問題
電影《建國大業》(2009)的出現開啟了主流電影大制作的時代,高投資、大規模、群星參演的制作模式影響了后續眾多主流電影的創作,《建黨偉業》(2011)、《建軍大業》(2017)、《我和我的祖國》(2019)等影片均延續了這種以重大歷史題材為藍本的大敘事的制作模式。2022年春節檔上映的兩部關于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影片——《長津湖之水門橋》和《狙擊手》,則分別代表了主流電影對這種大敘事制作模式的傳承與創新。作為續篇的《長津湖之水門橋》延續了前作的影片風格,全景式的戰爭場面,群像式的人物塑造,給觀眾制造了一種全知視角;電影《狙擊手》則將目光對準一場看似不起眼的戰場救援行動,在我方狙擊隊員與敵軍斗智斗勇的過程中,展現了志愿軍戰士們的英雄主義氣概和集體主義精神,從幾名狙擊隊員的小視角探討關于民族與國家的大問題。
《狙擊手》將目光聚焦在戰場上的一個特殊群體——狙擊手,他們被看作戰場上的神槍手,關于他們在朝鮮戰場上的故事民間早已廣為流傳,但在眾多以抗美援朝戰爭為題材的電影中鮮有表現他們事跡的,他們身處一條隱蔽的戰線,逐漸成了一個被忽視的群體。影片在表現我方與敵方狙擊手的較量時,我方的狙擊手沒有被一味神化,并非無所不能,摒棄了傳統的敵弱我強、敵小我大、完全丑化敵人的創作手法,而是通過一個個真實可信的細節展現整個斗智斗勇的驚險過程,敵我裝備差距的巨大和敵軍表現出的陰險毒辣也恰好反襯了我軍的英勇頑強。
影片中的鐵勺是一個輔助瞄準的工具,憑借這個不起眼的鐵勺,我方狙擊手完成了對敵人的擊殺,獲得了最終的勝利,表現了我軍戰士智勇雙全的品質。班長犧牲之后,鐵勺到了大永手中。與敵軍先進裝備的對比也體現出中美兩國精神文化的差異,先進的武器裝備不能遮蓋美國軍人個人主義至上、急功近利的本質。而通過不起眼的鐵勺,觀眾可在班長與大勇兩代狙擊手身上看到中華民族特有的英雄主義氣概和無私奉獻的集體主義精神。
“點名”這一儀式在片中出現三次。影片一開始的點名是為了執行任務,戰士們士氣高昂,整裝待發;第二次點名是班長念出寫有犧牲戰士名字的名單;第三次點名出現在影片結束時。一次次念出這些普通的名字,表明正是這些平民英雄的犧牲換來了戰爭的勝利。不同于以往的主流電影將目光僅對準那些早已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的做法,《狙擊手》意在通過平凡見證偉大。最后一次點名同時表達了一種傳承,電影的結束正是精神傳遞的開始,當影片最后再次響起已經犧牲的每一名戰士的名字時,是暗指他們的精神尚未消失,偉大的革命事業必然有后人去完成。點名既是對每一個無名英雄的隱喻,又是對他們犧牲精神的呼喚,這既推動了劇情發展,又象征著中華民族精神的代際傳承[7]。
以細小精深的選材表現偉大的家國精神,在故事的細節中表達對平民英雄的崇敬。《狙擊手》所要傳達的正是所有主流電影一直不遺余力表現的民族氣節和家國精神。
2.2 直面殘酷性,回歸原生態
直面殘酷性是商業類型片的一大特點,盡管進入21世紀以來,主流電影在不斷學習商業類型片的創作手法,但在直面殘酷性這一問題上始終做得不夠徹底。以往的大部分主流電影由于通常選擇社會歷史大事件作為創作題材,容易陷入說教的怪圈,故事戲劇性弱和人物形象扁平且不說,甚至不敢直面殘酷的現實。“三建”系列和后來的主流電影盡管已經開始直面殘酷的歷史現實和真相,但還只是流于表面。
在電影《戰狼2》(2017)和《紅海行動》(2018)中,通過高超的聲畫合成技術和人體化妝技術表現了真實的戰爭場面,讓觀眾直面現代戰爭中的殘酷場景,感受真實戰場帶給人的恐懼,其真實程度甚至超過了眾多槍戰類型片。而在《狙擊手》中,導演張藝謀通過現實和邏輯的真實營造了一個殘酷的戰爭世界,吸收了戰爭和槍戰類型片的元素,但又有別于此,回歸到一種原生態的類型片創作模式。
《狙擊手》的前半部分都圍繞班長劉文武這個角色展開,指揮隊友作戰、隱蔽、保護受傷隊友、與敵人談判等。在觀眾看來,這就是影片的男主角,是貫穿影片始終的重要人物。然而,影片剛剛過半之時,伴隨著一聲巨大的炮響,班長劉文武犧牲了,這不符合觀眾習慣的敘事邏輯。真實的戰場需要有領導大家作戰的英雄人物,需要一個核心人物帶領團隊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現實世界的英雄人物永遠沒有“主角光環”的庇護,他們也會隨時倒在殘酷的戰場上。當危險真正來臨之際,往往也沒有觀眾習以為常的“最后一分鐘營救”的奇跡時刻出現。
班長劉文武只是真實戰場上千千萬萬個戰士的縮影,主角的中途離場既是影片劇本的需要,又能凸顯戰爭的現實殘酷性。班長劉文武倒下了,尚未完成任務的狙擊小隊迅速有人勇敢地站了出來,接過班長小勺子的大永也接過了班長尚未完成的使命,帶領剩余的隊員繼續與敵人作戰。在巨大的裝備差距面前,除大永以外的隊員相繼倒下。在最后的決戰時刻,大永憑借自己的智謀終于擊斃敵人完成了任務,狙擊小隊雖然最終取得了戰斗的勝利,但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慘勝,而這場小規模戰斗的慘勝正是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一個縮影。狙擊小隊為取得勝利付出慘痛代價的情形在當時的朝鮮戰場上每天都在上演,對于沒有親歷過戰爭的當代觀眾來說,通過這樣一個側面展現戰爭最殘酷的一面,才是真正的直面殘酷。
影片含有現代戰爭和槍戰類型片的某些元素,如CG合成的子彈慢放特寫鏡頭。《狙擊手》既沒有濫用先進的電影技術,又沒有讓技術流于表面,而是努力營造邏輯與現實雙重真實的戰爭環境,以達到讓觀眾直面殘酷的效果。
2.3 樸素紀實的美學風格
在以往大制作的主流電影中,可以明顯感受到電影畫面帶給觀眾的視覺沖擊,主創團隊斥重金在電影的服化道、攝影美術等方面給電影披上一件華麗的“外衣”。“三建”系列電影為了塑造歷史的真實感,通過修復珍貴的影像資料、運用大量電腦CG合成鏡頭以及重建真實的場景來達到這一目標。《長津湖》系列電影在戰爭場面的還原上大做文章,通過虛擬技術還原了一個個宏大的戰爭場面,給觀眾帶來一場極佳的視覺盛宴。
《狙擊手》是由導演張藝謀和女兒張末聯手完成的。張藝謀的電影攝影風格是其身上的一個重要標簽,其以往的電影作品都體現了獨具特色的攝影美學風格。電影《狙擊手》中的風格轉變既是其個人的一次轉變,又預示了新主流電影在美學風格上的轉變,精湛的服化道配置和高超的攝影技巧能夠帶來不一樣的視覺享受,但漸漸丟失了主流電影的真實性。
主流電影一直追求真實的表達,而真實的表達來自對現實和邏輯的準確還原、對情感的合理抒發。狙擊戰場沒有正面戰場的激烈碰撞,那就呈現一個雪地應有的平靜;敵人的狡黠陰險并非一定要通過燈光的明暗去刻畫,情節的發展才能塑造一個更真實的敵人形象;我方戰士的英勇無畏也無須配合鏡頭的俯仰展現,在細節上與敵人斗智斗勇的戰斗英雄才最真實立體。《狙擊手》摒棄了眾多電影在形式上下功夫的習慣,而是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將鏡頭語言的作用發揮到極致,通過有效的對白傳遞隱藏在人物背后的個人情感和家國歷史,通過故事情節的推進促進人物成長和兩代人之間的精神傳遞,整個故事情節在一種自然的狀態中推進,沒有借助絢麗的場景搭建與虛擬華美的畫面來實現。
《狙擊手》的整個故事就在這樣一片雪地上展開,幾乎完全運用自然光拍攝,臺詞上大量使用方言對白,全片最具有現代科技感的畫面僅僅是對子彈的慢速特寫鏡頭,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樸素自然的美學風格。
3 創新:多元類型融合,可持續發展
3.1 創新敘事手法,追求極度真實
《狙擊手》的創新首先體現在敘事層面,其借鑒了美國好萊塢經典影片《正午》(1952)的敘事手法,使電影劇情發展的時間長度與真實世界的時間長度巧妙地達成一致,為觀眾制造一種沉浸式的觀影體驗。故事情節的發展也一反傳統戰爭片的漸進式發展邏輯,將整個故事的高潮前置,以此加快觀眾入戲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當下年輕觀眾偏好短平快視頻節目的習慣。此外,影片的敘事嚴格遵循西方古典戲劇理論——“三一律”的要求,讓故事劇情更加緊湊集中,提高了情節的強度。
在遵循傳統理論的基礎上,導演也在尋求新的變化。《狙擊手》敘事的最大亮點在于雙男主的演員設置,成長和犧牲作為貫穿影片的兩大主題,也串聯起了兩名狙擊手之間的傳承關系,通過鐵勺這一物件和點名這一細節巧妙地實現了任務交接和精神傳承的目標。在遵循傳統理論和借鑒經典影片的基礎上,導演找到了對影片極具意義的創新方式,讓主流電影力圖塑造民族英雄和表達集體主義精神的目標都得以實現。
3.2 多元類型融合,主流價值表達
主流電影向商業類型片借鑒創作元素和方法,將商業類型片的成功經驗與自身的創作需求相結合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狙擊手》則實現了多元類型的融合,這是導演張藝謀對此前的電影《懸崖之上》(2021)創作手法的一次延續,將懸疑、槍戰和動作片的元素類型融入一部電影的創作之中。《狙擊手》本身作為戰爭片的一個亞類型,在世界各國的電影創作中都不是主要的類型片創作對象。《兵臨城下》(2001)是一部經典的以二戰為背景的狙擊題材電影,但影片所傳達的是西方長期以來倡導的個人英雄主義理念。在我國的電影史上,關于狙擊手題材的優秀電影更是屈指可數,在主流電影的創作中也暫時無人涉及這一題材領域。《狙擊手》填補了這一領域創作的空白,同時創新了這一類型的電影,融合了現代槍戰片的特效場面、懸疑片的劇情推進方式和戰爭片的表現手段,成為一部具有主流電影特色的狙擊題材電影。
《狙擊手》既依托抗美援朝戰爭的宏大背景,又淡化了故事背景,憑借故事的傳奇性、電影的類型突破以及狙擊動作的真實場面等內部因素就已經頗具吸引力[7]。盡管其在某種程度上是張藝謀個人創作風格的一種延續,但同時為主流電影向新主流電影的創作轉變找到了突破口,從對商業類型片的元素吸收借鑒到如今的多元類型融合一部影片,主流電影所倡導的價值表達在表現手法上得到了發展與創新。
3.3 可持續發展的電影生產模式
《狙擊手》另一個方面的創新體現在對電影產業的貢獻上,為新主流電影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案例。自2020年以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全球電影產業遭遇前所未有的大縮水,電影主創團隊得到大投資和贊助變得愈發困難,曾經那些高投資、大制作的電影開始減少,新主流電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必須制訂契合自身發展的轉型計劃。可持續發展是如今新主流電影創作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旨在摒棄此前的高投資、大制作加上群星面孔的創作方式,回歸電影的本質,以故事吸引觀眾。
如果說《長津湖》之類的電影在中國特色的新主流電影中屬于重工業電影大片的范疇,那么《狙擊手》則為“中等工業美學”的主流電影提供了成功案例。“十四五”規劃中就曾提到,中國要有十部左右票房十幾億的電影,四五十億的票房成就固然振奮人心,但這種奇跡是可遇不可求的[7]。新主流電影所遵循的“中等工業美學”既不同于曾經高投資的制作方式,又并非要進行以小博大的賭博式創作嘗試,而是要合理利用和分配創作所需的資源,理性控制生產成本,以確保取得相應的收入。
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模式不僅在疫情時期具有特殊的含義,從長遠的角度看,也預示著新主流電影以后會進入的常態,甚至是整個電影生產將要形成的一個合理的創作環境。
4 結語
從主旋律電影到新主流電影,其間僅僅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但出現了多次重大變化,讓這個電影類型在電影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狙擊手》作為主流電影向新主流電影轉變的一個典型案例,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延續了傳統主流電影的價值表達與精神傳承,同時也在形式和內容上尋求創新,滿足了時代發展提出的新需求,并克服不同階段電影創作所面臨的新問題,代表了新主流電影的轉型與創新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 陳旭光,劉祎祎.論中國電影從“主旋律”到“新主流”的內在理路[J].編輯之友,2021(9):60-69.
[2] 韓風云.守正與創新:新主流電影的發展之思[J].電影文學,2019(12):19-22.
[3] 周星,喬潔瓊.主流電影的嬗變:寫在建黨百年之際[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4):5-12.
[4] 馬寧.新主流電影:對國產電影的一個建議[J].當代電影,1999(4):4-16.
[5] 黃夢昀.淺析新主流電影的藝術特色[J].中國文藝家,2022(5):10-12.
[6] 馬寧.? 2000年:新主流電影真正的起點[J].當代電影,2000(1):16-18.
[7] 薛精華,劉婉瑤.抗美援朝記憶的另類書寫與新主流電影的類型化敘事:電影《狙擊手》學術研討紀要[J].視聽理論與實踐,2022(2):86-96.
作者簡介:楊勝凇(1997—),男,貴州甕安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藝術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