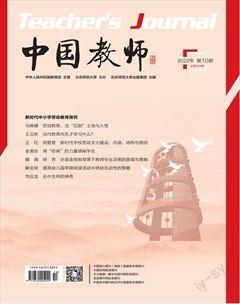勞動教育:當“見到”土地與人性
馬維娜
【摘 要】“土地”作為實描,強調的是其“純色”與“本色”;“土地”作為隱喻,寓意的是其“根性”與“實性”。土地上的勞動教育是有神圣感、儀式感的,是接地氣、扎根性的,應拒絕單一的走形式與作秀式的打卡。勞動教育是土地、勞動、勞動教育的交互相融,是體力流汗、腦力流汗、心靈流汗的實實在在,應摒棄不上心的參與、不經意的折扣、不在意的敷衍。勞動教育是體悟的、歷練的,是全方位的投入、全身心的體驗,須謹防讓位于學習的家庭替代、讓位于陳式的學校應對、讓位于他人和社會的目光短視。見得人、見得土地、見得人性,三者是相通的。與土地相通的人性,寓意相互引導、相互激發的關系存在,寓意人與土地的溫度和情感,寓意深層內里的相關品質。“見到”本真本色,“見到”美好人性,理應成為勞動教育的內在追求。
【關鍵詞】勞動教育 “見到” 土地 人性
伴隨2022年開年后國家多項勞動教育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義務教育課程方案(2022年版)》《義務教育勞動課程標準(2022年版)》)緊鑼密鼓的發布,“勞動教育”再次被熱議和關注。當勞動與勞動教育被進一步強調,當勞動教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理念與形態發生進一步變化時,是否意味著與勞動緊密相連的“土地”可能會被重新關注?與勞動教育相關的一些問題可能會被重新解讀?或者說,當土地變得越來越成為某種奢侈品時,學生借助勞動與勞動教育,是否可以與土地有更多相互觀看、相互觸摸、相互親近、相互引導的機會?成為學校必備課程和教育實踐的勞動教育,是否需要“見到”土地以及與土地相通的人性?
一、勞動教育:當體現土地的純色與本色、根性與實性
土地對于現代城市尤其對于現代城市中的中小學學生來說,已經變得越來越奢侈了。城市的快速拓展、高速公路的四通八達,不經意間使土地的原本空間越來越局促起來。城市中太多的土地被水泥、柏油、塑膠覆蓋著、呵護著,即使有幸聳立于林蔭之道的參天大樹,也只能在有限直徑的網狀式土地保護圈的縫隙間,有限度地享用來自泥土的清新自然和雨露的無私滲透。固然,學校的花圃里是有“土地”的,但孩子們見得更多的是覆蓋在土地上的姹紫嫣紅與四季翠綠,那些使姹紫嫣紅與四季翠綠有根可扎、有莖可展的土地本身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農村學校或許有所不同。學校的邊遠、簡陋給予土地更多自由敞開的空間,學校的一些實驗田地也總能拉近孩子們與土地之間的距離,也給土地包容溫和的博大胸襟得以彰顯的可能。
當然,在提及勞動教育的同時提及土地,倒并非對農耕時代的一種簡單回眸,也并非對“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勞動形象的一味眷念,而是想表明“土地”與勞動教育之間無法割舍的質性。土地,似乎總以質樸無華被人贊賞,質樸無華到只有純色而無雜色;土地,又總以厚實本真為人稱道,沒有調料,抵制摻假,是怎樣就是怎樣。盡管在這個五光十色的世界中,土地也會遭遇多種外在添加物的騷擾,但比起那些扎染布、混色物、調和油來,無雜色仍然是它的本色。這也許得力于土地的抗干擾應激反應,畢竟土地若被侵蝕,侵蝕者就會收獲土地的“無私回報”—或產量下降或顆粒無收。這樣的教訓不是沒有,而土地只為捍衛自身的一身正氣。“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既是一種人與土地之間的實描狀態,更是一種對土地本真本色應有的虔誠般敬畏。因此,強調勞動教育時提及土地,表明的是勞動教育當首先體現土地的“純色”與“本色”。
不可否認,現代社會進程中出現的土地稀缺現實,帶來學生們對土地感知的困難;隨時代變化而發生的勞動形式本身的多元多變,也使“土地”的原義發生更多的轉義和引申義。“土地”更多成為各種勞動類型的平臺、環境、載體的代名詞,“土地”也由此更成為某種隱喻,寓意來自土地“純色”與“本色”的土地的“根性”與“實性”。土地的“根性”說的是它那種能讓萬物扎根、伸展、蔓延的底氣,那種不畏風吹日曬、酷暑嚴寒的韌性;土地的“實性”說的則是它不浮夸、不虛華的地氣,那種一步一個腳印且順應大自然萬千變化的務實。有學者曾提出要“建立勞動教育的長效機制”,包括三個維度:一是要確保勞動教育的條件支撐,切實解決勞動教育到哪里“教”的問題;二是要確保勞動教育的評價驅動,著力解決“不愿意教”的問題;三是要喚醒勞動的內在自覺,促進學生個性潛能和勞動世界的相互調適與對接[1]。這正與此處所說土地的“根性”與“實性”有相通之意。
所有這些都表明,土地需要敬畏,土地上的勞動需要莊嚴,土地上的勞動教育是具有某種神圣感、儀式感的接地氣、扎根性的課程設置與實踐活動。任何在“土地”根基上的勞動教育,若僅僅只是單一的走形式,只是作秀式的打卡,都是對土地、對勞動、對勞動教育的褻瀆。與此同時,勞動教育是多方融通的,它需要土地、勞動、勞動教育的相互交融,這種相互交融既不是外人對土地對象化式的外加行動,也不是任意他者的隨便敘事,“動手實踐、出力流汗”,是自己身臨其境的親力親為,是體力流汗、腦力流汗、心靈流汗的實實在在,拒絕不上心的參與、不經意的折扣、不在意的敷衍。正因為如此,勞動教育是體悟的與歷練的,“接受鍛煉、磨煉意志”需要全方位地投入、全身心地體悟,既不是日常生活勞動讓位于學習的家庭替代,也不是生產勞動讓位于陳式的學校應對,更不是服務性勞動讓位于他人、社會的目光短視。勞動教育的所有環節之間要謹防一種習慣性割裂,不可以讓位,不可以隱身,不可以有缺席者。否則,與勞動教育緊密相連的類似需要、情感、意志這樣的潛在能量,或類似體力、認知能力、行為能力這樣的潛在能力,都可能處于一種休眠或未被真正激發的狀態。
二、勞動教育:當參透與土地相通的人性
有一句俗話這樣說:能見得人就能見得土地。言中之意似乎包含這樣的邏輯:見得土地的前提是先見得人,或者說,在見得著人的基礎上才能見得著土地。這表明土地與人之間存有相通靈性,有“人”的土地萬物茂盛、草木蔥蘢,肥沃廣袤的土地里必然蘊含著人的性情與本性。涂爾干指出,人性歸根結底是社會化的產物,具有社會屬性。人性的本質在于個體意識作為一種更高的精神生活形式,它不僅可以把集體精神內化在心靈之中,也可以內化在身體之中[2]。在這個意義上說,見得人、見得土地、見得人性,三者是相通的。布迪厄早就提醒人們關注農民與土地之間保持的一種神奇關系。他認為農民的全部實踐按照另一種方式實現了儀式顯示的客觀意圖:土地從來不被當作需要利用的原料,它是受人敬畏的對象;傳說它會“同你算賬”,會因為匆匆忙忙或笨手笨腳的農民對它的虐待而要求賠禮道歉。并且,若把人們不敢向其他人推薦的人“推薦”給土地,那就是對土地的不敬[3]183。可見,土地是有“人”的土地,“人性”是與土地相通的。土地容不得人對它的懶惰,勞動就是人與土地之間的相互善待,勞動教育只有在有“人”的土地中,才會有“汗滴禾下土”般的融為一體,也才會有“秋收萬顆子”般的默契回饋。換句話說,勞動教育當參透與土地相通的人性。
這種當參透的與土地相通的人性,寓意相互引導、相互激發的關系存在。
在農耕時代,土地與人相互依賴、相互引導。土地會根據自己的質性,引導面對她的人如何尊重自然時間里的耕犁、播種、發芽、生長、除草、殺蟲、果熟、收獲,如何摸透不同土質的習性,匹配合適的種源和類別,以達到最佳適配效果。而人在土地的引導下,也會有計劃、有節律地根據土地的特性,保證土地上的植物獲得最大收成。所以,有經驗的農民“見到”土地,采取的是對待一個人的和面對一個人的態度,也就是面對面,表現出一種親近和自信,就像對待一位受人尊敬的親屬[3]183。
在當今時代,土地發生著它的時代演化,成為與勞動教育相關的環境、平臺、載體代名詞的非實體性的“土地”,激發的是既與勞動教育相關又與高科技、人工智能、5G時代相關的多種想象、多種思維、多種形式。無論是分為日常生活勞動、生產勞動、服務性勞動3大類別的勞動課程內容,還是包括清潔與衛生、整理與收納、烹飪與營養等內容的10大任務群,都可能在這些相互激發中,借助實實在在的學習和實踐,通過認知、意志、情感、行為等有意識的活動,實現開發學生潛能的多種可能,實現人性達成的多種可能的現實努力。
與土地相通的人性不僅是關系的,而且是有情感、有溫度的。沒有來自人對土地發自內心的情與愛,就無法長久維系土地、勞動、勞動教育互融一體的關系存在。“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一特定歷史時代背景下的詩句情感,或許并不因時代的更迭進化而發生隱退。面對“土地”,只有心與土地貼近與親近,才能心見如火、入目成淚;反之,不入心的“土地”,即使面對也會冷若冰霜、視而不見。這或許也正是勞動教育中需要提防的勞動情感缺乏癥。勞動教育按課表上課,各類勞動按設計程序操作,本無可厚非,但若僅僅如此,沒有情感的投入,沒有發自內心的意愿,沒有能見到人性的勞動,勞動教育就可能成為工業生產中的流程,就可能發生實質性缺位的情形。這也是無論在中國古代思想家那里,還是在西方諸多社會學家的闡釋中,情感與人性總是不可或缺和不可分離的重要原因。中國的荀子就有“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4]的闡釋,西方的孔德也認為,感情是人類的靈魂、行為的動力。推動力總是來自感情,才智永遠只是一個指揮手段或控制手段。因此,情感構成人性的重要部分,是人行為的直接[5]。或許,這也正是“能見得人就能見得土地”的真正含義所在,也是人性與土地相通的實質意義所在。
與土地相通的人性還寓意深層內里的相關品質。畢竟,所有“有目的、有計劃地組織學生參加日常生活勞動、生產勞動和服務性勞動,讓學生動手實踐、出力流汗,接受鍛煉、磨煉意志”的最終旨歸,恰恰是能夠“培養學生正確勞動價值觀和良好勞動品質”[6],從而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所提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合格的社會成員。而在其中,崇尚勞動、熱愛勞動、辛勤勞動、誠實勞動的勞動精神,相互幫助、相互合作、相互啟迪的團隊精神,對家庭、對學校、對社會的公民責任感等,正是既抽象又可感、既個體又群體的深層內里品質的具體體現。而只有拋開了那些表層的膚淺的東西,才能凸顯與土地相通的人性的光輝。
三、勞動教育:多統感地立體“見到”
無論是勞動教育當體現土地的純色與本色、根性與實性,還是勞動教育當參透與土地相通的人性;無論是土地的各種質性,還是人性隱含的多種寓意,無法繞開的一個關鍵詞就是“見到”。這里的重點并非要做類似純語義學的辨析,只期待從簡單的比較中感悟到“見”與“見到”的個中差異,以使上述諸言具有“立足之地”。一是既然本文傾向使用的是“見到”,就不僅僅是、事實上也不會僅僅是“看”之意,而是表明身體多種感官的同時啟動與共同作用。單純的“見”,似乎更多借助某個感官—眼睛,就能“看”或者“觀”;而“見到”,除了“看”和“觀”,還具備了感知到、覺察到、注意到、意識到的意涵,需要多種感官的全力投入,需要生理、心理的齊心協力。在這個意義上,“見”與“看”可以互換,而“見到”卻不可。二是“見”更多是“看”的感官結果或直接畫面效應,“見到”則是一種帶有終極目標的達成期待,兩者顯然具有層次上、程度上的淺深之異。三是在時空上亦存有瞬時與延時之別。“見”更多是瞬時的,既是瞬時就很難賦予或獲取其他更多內里的東西;“見到”則更多是延時的,時間的延展可以給“見到”一種相遇的感覺,并進而可能生成有情感、有溫度、有內涵的相遇。
當真正“見到”時,那些經過勞動和勞動教育所形成的價值觀和良好品質才能漸漸植入內心、深入心底,也才能漸漸與美好社會相遇。到這個時候,有“魂”的勞動教育就會像馬斯洛所描述的那樣,內部要求與外部要求是很好配合的,“我需要”與“我必須”是彼此一致的,超越性動機是超越了基本需要激勵的。此時,人會更接近自我實現狀態,也更裨益于人性修煉的豐滿。總之,無論是原始意義上的本真土地,還是當今高科技時代非實體意義的“土地”,“見到”本真本色,“見到”美好人性,理應成為勞動教育的內在追求。當然,任何人為夸大或刻意矮化勞動教育的作為,都是不符合學生成長規律和教育教學規律的,抓住勞動教育的本色、本真,使其不走形、不變質,方是第一要義。
參考文獻
[1] 柳夕浪.推動建立勞動教育的長效機制[J].勞動教育評論,2021(1):22-29.
[2] 嚴懿.論涂爾干的人性兩重性——讀《人性的兩重性及其社會條件》[J].雞西大學學報,2012,12(4):132-133.
[3] 皮埃爾·布迪厄.實踐感[M].蔣梓驊,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4] 吳祖剛.《荀子》“性、情、欲”之關系分析[J].道德與文明,2013(6):52-57.
[5] 郭景萍.情感社會學:理論·歷史·現實[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232.
[6]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教育部關于印發《大中小學勞動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的通知[EB/OL]. (2020-07-09)[2022-06-2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2007/t20200715_472808.html.
(作者系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教育學博士)
責任編輯: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