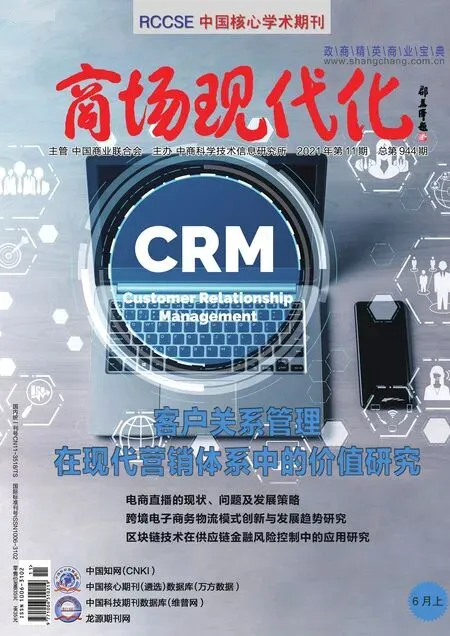從金融業集聚到經濟增長
摘 要: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以提供專業化和標準化服務為特征,另外作為一種信息密集型產業,金融產業在促進經濟本身增長和優化資源配置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點。由于金融產業本身就具有高流動性這一特點,并具備集聚的傾向,即有著區域集中的趨勢并經過一段時間形成金融集聚。因此,本綜述以金融集聚為出發點,對國內對此研究學者的結果進行總結,并試圖歸納目前從以金融集聚到區域經濟增長為重點和金融集聚的相關研究。
關鍵詞:產業集聚;經濟增長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狀況已經迅速發展,國內金融市場資源配置逐步完善,金融業顯示出區域聚集的趨勢,如上海陸家嘴金融城、北京金融街、深圳世界金融中心等,這些區域金融中心依托中心城市為當地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從區位角度分析同時也對當地城市-經濟圈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對金融集聚和區域經濟增長,目前的研究有從資源流動、技術創新、地區間差異、市場一體化、空間溢出和區域經濟增長效應等方面來探討;也有從環境資源、綠色發展角度來分析以及在金融集聚和其他產業相結合是否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而以往傳統對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包括:索洛新古典增長模型,由美國經濟學家索洛于20世紀50年代融合凱恩斯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理論;基礎——區域乘數理論;人力資本遷徙理論。
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成本可能解釋了金融集聚的現象,Zhao[1]等基于信息不對稱角度,信息不對稱造成在跨國公司總部地點選擇和金融中心發展的關鍵決定因素。考慮一個具有兩個部門的經濟,即金融部門和實體部門,有兩種商品:金融產品和實體經濟產品,資源分為勞動力和資本,由于物理距離上信息流的摩擦會導致成本。基于此提出了與傳統觀點相反的結論: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北京在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服務和金融中心方面比上海具有更多優勢,由于北京的地位可能對金融服務業具有吸引力。
金融集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理論上目前主要為兩種觀點:供給主導論(supply-leading view)和需求伴隨論(demand-following view)。而物理距離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成本導致集聚的出現,這往往涉及到距離問題。而集聚可能導致當地企業的生產率得到提高,進而對當地資源、環境和綠色發展方面產生影響。而金融集聚往往通過規模經濟效應、創新驅動效應、信息溢出效應和結構調整效應等途徑產生影響;此外集聚帶來的影響往往具有區域異質性,以我國為例,東中西部的影響和發展狀態一般不同。
對金融集聚和區域經濟增長,目前的研究主要從資源流動、技術創新、地區間差異、市場一體化、空間溢出和區域經濟增長效應等方面來探討。
在金融集群形成的原因方面,有人認為基于信息不對稱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以解決為什么金融活動存在著空間集聚這個問題。由于物理距離上信息流的摩擦會導致成本。Naresh和Gary[2]對英國三個地區(倫敦、愛丁堡和布里斯托)金融業集群分類做了細致的分類,并解釋了金融業集群之間的績效差異是由于集群的構成和集群內發生的流程的差異所致。其發現倫敦和南蘇格蘭,服務于許多市場的大公司的存在是活力的主要驅動力;而布里斯托的案例表明,集聚本身并不一定意味著優越的經濟表現,另外集聚的政策方面的進一步決定應該因不同的類型而做調整。
嚴圣艷等從金融集聚、技術創新和區域經濟增長方面著手,利用PVAR模型發現在全國,金融集聚和技術創新都能給區域經濟增長帶來正向刺激,然而這個影響時間有限;除此之外,在發達地區的沖擊效應有正有負,而在欠發達地區沖擊一直處于穩定的正向關系,這也給政策制定方面帶來了一定啟示。
此外,金融業集聚往往具有動態效果,金融集聚的前提是區域經濟發展,金融產業集聚帶來的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反過來會繼續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來看,金融行業的集聚不止帶來的集聚效應、輻射效應,集聚本身產生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和外溢效應也對區域經濟增長作用顯著,但遺憾的是有關具體模型對效應做出具體量化分析的研究相對較少。
在金融集聚與不同地區間地區差異以及經濟發展之間關系上,孫武軍等驗證不同地區間差異和經濟發展關系,并討論區域經濟增長和金融集聚程度之間的引導關系并基于此分析了效果,他們認為應加大對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金融債支持,擴大金融集聚的輻射作用以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胡國暉和鄭美美在同時考慮金融創新與金融集聚的協同作用的基礎上,利用區位熵和DEA模型對我國2006年-2017年間30省市集聚水平和創新效率進行了測算,通過SAR模型和空間效應分解模型實證檢驗了二者對區域經濟協同影響和空間溢出效應,除此之外還發現溢出效應較強,但是間接效應高于直接效應;在區域層面,金融集聚和金融創新是造成區域差異的重要原因,特別是沿海內陸存在著更加顯著的溢出效應。
關于金融集聚、市場一體化、區域經濟增長三者的關系上,將這些因素綜合考慮的研究相對較少,更重要的是缺少金融集聚通過市場一體化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經驗證據:僅分析金融集聚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關系,并不獲得集聚通過市場一體化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因果證據。金融行業企業可能傾向于選擇區域經濟增長高速的地區進行集聚,即區域經濟增長較快的地區會吸引更多金融企業產生集聚。如果能從通過尋找外生政策變化著手,通過構建因果分析模型也許能彌補這一領域的缺陷,獲得真實一致的因果關系。
在金融集聚、空間溢出與城市經濟增長方面,大多研究往往基于城市層面視角,采用改進權數的空間杜賓模型來檢驗金融集聚和空間溢出、城市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及背后的作用機制,雖然學者們認為人力資本、集聚規模與產出密度等因素不僅能顯著促進城市經濟增長,在一定范圍內的城市還可能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在溢出效應的影響路徑研究方面,可能由于金融集聚的規模加大帶來更大的空間溢出;也有可能來源于集聚效率的提升,加速產生空間溢出效應。如果將金融集聚和增長極理論聯系起來,不同地區應當采用不同模式以促進空間溢出加速區域經濟增長,不同地區是否可能存在某一城市為經濟增長極促進金融集聚,這一話題則更容易引起關注。
對城市圈金融集聚的研究大多采用金融業區位熵進行測算,并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對空間溢出效應進行研究,往往需要先驗證包括空間溢出效應,此外如果對這一行業進行細分,對區域的包括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聚集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效果和路徑的研究進行探索則能夠全方位評估分析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從微觀企業的視角著手,給出微觀企業視角下金融集聚和空間溢出影響城市經濟增長的證據則能為進一步研究金融集聚、空間溢出與城市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提供下一步研究的可行方案。而針對省份層面空間溢出效應的研究往往相對較多,這些研究的樣本量往往偏少,缺乏對區域統一角度的探索。值得一提的是,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地區GDP的變化上,能否帶動區域經濟高質量增長也是值得關注的話題。還有研究傾向于金融集聚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區域異質性:一般來說往往認為東部地區的金融集聚效應遠遠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區,這也是以往研究中指出出現金融集聚區域化變動的現象之一,另外從經濟直覺上中心城市或傳統意義上的金融中心、沿海省份、東部地區更傾向于吸引金融業企業的集聚。
在區域經濟增長效應的方法上,往往采用測算金融業下屬行業的區位熵來研究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所構建的模型大多是固定效應,以解決遺漏變量的問題。另外,以往研究大多提出銀行業集聚能夠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但證券業集聚帶來的卻是一系列的混合結論,為什么金融業細分的不同行業會出現如此差異?以往的研究缺少對此的進一步解釋。有學者對金融集聚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做了進一步研究:趙明惠用2003年-2013年省際面板數據構建面板門限PTR模型研究二者的非線性效應,雖然金融集聚測度采用消除價格因素影響后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但是發現金融集聚和區域經濟增長存在著倒U型,即金融集聚存在閾值轉化的特征:在某一范圍內起到正向促進作用,而超出這個范圍則是反向的抑制作用,但卻缺乏對背后原因的進一步分析。
金融集聚在引導經濟增長的路徑方面,有研究采用門限效應(張秀艷),其認為促進實體經濟增長的本質是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而知識資本外溢是否順暢是金融集聚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且從直接集聚效應和間接的溢出效應來看,前者集聚效應為正,而且是金融集聚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更容易形成規模經濟效應,吸收更多的資源;而后者即對地理鄰近的溢出效應影響來看則為負。劉紅以上海為例構建LS模型,將金融集聚對核心區增長效應分為“需求關聯效應”和“資本溢出效應”;集聚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具體來看分為兩種:即資源在條件滿足時對周邊產生補償效應,另一種是金融集聚的集聚程度提高以后,金融資源會通過鼓勵技術進步、增加資本積累以及刺激儲蓄投資轉化來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回顧以往研究,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不足和問題,以及有待進一步開展的方向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指標的選取方面。以往對金融集聚的衡量往往采用復合指標進行加權,如區位熵等,但這樣的指標也面臨一些問題:這些指標往往過于復雜,雖然考慮了諸多因素,但缺乏對金融集聚的簡潔描述,包含大量其他信息,而這些信息可能對研究結論產生不利影響,如果一個指標中包含有關經濟增長的因素,再用其解釋經濟增長,結果必然出現偏誤。另外,對短期金融集聚的衡量,并沒有反應集聚帶來的綜合效果;對金融集聚的指標選取應該是一個動態和靜態相結合的指標,傳統只是利用靜態的選擇對結果會有一定偏差的影響。
2.雖然金融集聚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這也進一步導致了地區間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盡管以往的研究發現了金融集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正面的關系,但究竟是區域經濟增長導致的集聚現象的出現還是金融集聚進一步加強了區域經濟增長?以往集聚和區域經濟之間內生性的關注并不足夠,大多數研究宣稱觀測到的溢出往往包含了反向因果的問題,這也是以往研究出現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以往研究大多往往基于地區和行業層面,從微觀企業層面著手的研究相對較少,如果能從微觀視角分析金融集聚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對金融集聚的影響的評估將會更加全面。
3.另外,對集聚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動態效應研究的關注缺乏一定重視,集聚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應當是綜合與復雜的,比如相互加速促進作用:區域經濟增長得到發展進而促進金融集聚,金融集聚進一步加快區域經濟增長。此外,集聚并不是簡單正向影響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增長還對金融集聚有一定支撐作用:雖然金融集聚理論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區域經濟增長對金融集聚卻沒有支撐作用,二者之間應該存在相互互動發展,若缺乏此類關系,則雙方的協同促進可能會產生消極作用。此外,以往研究大多關注經濟增長,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視卻并不足夠,缺乏金融集聚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有力證據。
4.將金融業細分為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后,前兩者都被證實對區域經濟增長有利,而證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效果不明顯著至是相反的作用呢?是否可能是我國證券市場發展仍不完善導致證券不能很好服務于實體經濟,進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或是不同行業間存在一定原因使行業出現某種差異,導致溢出效果的不一?如果能結合國內證券市場發展的綜合角度也許能回答行業異質性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效果,從此角度出發回答這一問題有助為未來的研究做進一步分析。
5.在金融集聚和區域經濟增長雖然已經達成了二者正相關關系,但是在分析方法上仍然有待創新,例如使用系統動力學SD模型模擬仿真和政策預測。此外,對金融業集聚的綜合影響缺乏全方位的評估:盡管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正向影響被廣為證實,但集聚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其他影響。比如金融業的高度集聚有可能導致區域的經濟發展更加虛擬化,降低其抵抗金融風險的能力,這可能會導致國內金融業企業面臨更大的國際金融風險、國內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國內經濟高質量增長放緩等問題,從這一角度出發或許也能為金融集聚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獲得新的成果。
參考文獻:
[1]Zhao S,Cai J,Li Z.Asymmetric Information as A Key Determinant for Locational Choice of MNC Headquar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enters:A Case for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5,16(3):308-331.
[2]Naresh R Pandit,Gary Cook.The Benefit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Insights from the British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t Three Loca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ing,2003,7(3):230-245.
[3]嚴圣艷,徐小君.金融產業集聚、技術創新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PVAR模型分析[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1):103-109.
[4]孫武軍,寧寧,崔亮.金融集聚、地區差異與經濟發展[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3):92-103.
[5]胡國暉,鄭美美.金融集聚、金融創新與區域經濟增長[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20,41(04):22-29.
[6]趙明惠.金融集聚對經濟增長的非線性效應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16(03):172-174.
[7]張秀艷.金融集聚引導下的經濟增長路徑——基于門限效應和空間效應的解析[J].財經問題研究,2019(11):47-54.
[8]劉紅.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的增長效應和輻射效應研究[J].上海金融,2008(06):14-19.
作者簡介:張昊淵(1997.01- ),男,漢族,杭州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產業集聚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