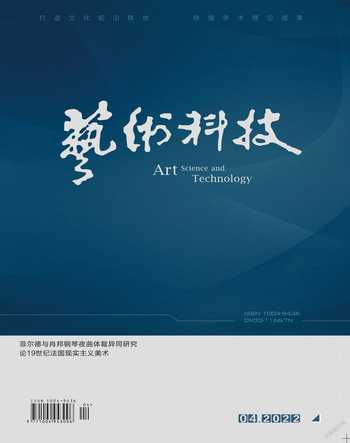拉康鏡像理論視域下《黑天鵝》主人公的自我建構
摘要:鏡像理論是拉康精神分析學說的奠基之論。《黑天鵝》中,妮娜經歷了從“虛幻自我”到“真實自我”的自我意識確立。從鏡像理論的維度分析《黑天鵝》,有助于從藝術領域延伸和拓展精神分析學說。
關鍵詞:拉康;鏡像理論;《黑天鵝》;自我建構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04-00-04
《黑天鵝》是美國導演達倫·阿倫諾夫斯基執導的一部有關芭蕾舞演員探索自身本質的超自然驚悚懸疑影片。28歲的芭蕾舞演員妮娜(娜塔莉·波特曼飾)與她的母親——一位有極強掌控欲、曾經擁有輝煌芭蕾舞事業卻因生女兒而被迫放棄事業的艾麗卡(芭芭拉·赫希飾)居住在一起。妮娜在媽媽的掌控下,她的生活只有芭蕾舞和野心勃勃的職業目標。舞團導演托馬斯(文森特·卡塞爾飾)決定為新一季《天鵝湖》挑選新演員,妮娜因為無可挑剔的舞技成為新的“天鵝皇后”,取代她一直以來的偶像貝斯。不過,妮娜的“天鵝皇后”地位時刻都在遭受挑釁,莉莉(米拉·庫妮絲飾)是托馬斯看好的替補“天鵝皇后”,因為新一季《天鵝湖》的主演需要一人分飾兩角,“天鵝皇后”不僅要能演出白天鵝的無辜與優雅,更要能演出黑天鵝的詭詐與淫蕩。漸漸地,妮娜為了更好地飾演黑天鵝,不斷經歷痛苦與掙扎,欲望、誘惑、邪惡撕扯著妮娜嬌弱的身體和脆弱的靈魂,人性深處的惡逐漸占據上風,她開始出現精神分裂癥狀。在巨大的精神拉扯下,妮娜獲得了空前的藝術成功,最終在《天鵝湖》首演上,妮娜釋放了真實的自己,以結束生命為代價,實現了真正的“完美演出”。
精神分析學說由弗洛伊德創立,之后經歷漫長的學說發展,在拉康手中又大放異彩,重新煥發生機。拉康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號,重新確立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學派中的重要地位,拂去了當時學界日漸機械腐朽地解讀弗洛伊德之風。但是拉康的這個口號卻名不副實,他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完全繼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志愿,而是在其基礎上對精神分析學展開了全新的闡釋,在“自我”概念的建立和發展、無意識主體理論、臨近學科之間的關系等各方面,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都大有不同。其中,闡釋建立“自我”歷程的鏡像理論作為拉康精神分析學說的起點和奠基之論,猶如杠桿一般,支撐起拉康的整個精神分析學世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拉康的鏡像理論對于自我意識的建構和發展有著獨特精妙的闡發,而電影《黑天鵝》主人公妮娜通過經歷擔任新“天鵝皇后”這一人生激勵事件,在眾多“他者”的推動之下,實現了從“虛幻自我”到“真實自我”的自我意識確立。從拉康鏡像理論的維度分析電影《黑天鵝》,有助于從藝術領域延伸和拓展拉康的精神分析學說。
1 自我的初識:鏡像之中的虛幻自我
所謂鏡像階段是指當還不會說話,步履蹣跚趔趄的幼兒看到自己在鏡中的映像時會歡欣雀躍、喜不自禁,并且這種對鏡中形象的興趣會持續好長時間[1]。幼兒在出生后很長一段時間,由于神經系統尚未成熟,沒有“自我”的概念,無法將自己與溫暖的子宮、母親的懷抱剝離,所以鏡像階段是自我的結構化和清晰化,是幼兒第一次將自我與混沌的世界區分開來。
康德指出,在鏡像階段,幼兒在鏡中看見了自我,印象鑄成了幼兒心中的“自我”,幼兒有了“這就是我”“我就是這個樣子”的想法[1]。
女主人公妮娜在28歲之前則處于拉康所說的鏡像階段,在舞蹈之外的世界并未長大。她穿著粉色睡衣,從充滿粉白色碎花元素的童話風格的臥室里醒來,臥室里擺滿了洋娃娃,母親像是照顧幼兒一樣給妮娜穿衣服、卸首飾,妮娜被母親悉心照料著衣食住行,日常服飾也是以粉白色為主,交友受到母親的監管,連鐘愛的舞蹈事業都是在繼承母親年輕時未完成的事業,永遠是在媽媽掌控下的小甜心、乖女兒。妮娜在生理年齡上早已脫離幼兒階段,看似是個具有社會關系的獨立個體,卻如同被牽線的木偶娃娃,以28歲之高齡仍處在拉康所說的鏡像階段,在鏡像前沉迷于“自我”的影像,并歡欣雀躍、理所當然地接受“自我”的現狀,處于一種“自戀”的狀態。但實際上妮娜所接收到的只是幻象和碎片的意識,她沒有成為真正且獨立的自我,也沒有真正意義上擁有掌控鏡像、掌控主體的能力。
拉康所創造的“鏡像”概念——盡管映照出“我”的整體形象,是保證自身連續性、統一性的心靈母體,但對“我”來說,卻是把自己的起源讓給別人,就像被人吞沒那樣寄托自身的命運[1]。這樣看來,人類自我意識形成的第一步其實是建立在虛妄和虛幻的基礎之上。
2 他者的推動:虛幻與現實的交織
拉康指出,精神分析學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它的顛覆性。幼兒不可能永遠處于鏡像階段的初始階段,被幻象所蒙蔽,自我的構建貫穿人的一生。拉康認為,“他者”在“自我”的形成與變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自我的認同總是借助于他者,自我是在與他者的關系中被構建的,自我即他者。”[2]所以,個體只有通過鏡像階段,只有將自己投射到外部世界的他人和自己、他人和他人的關系之中,才能在他人對自我的認識中認清自己,即“我”是在“他人”的認可下才能成為自我,“我”并不是自我本身的意識產物,而是他人、他者的意識產物,“我”之所以能建構自我,是在和他者之間的博弈關系中才成為的自我。
拉康認為,“他者”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分別為“大他者”和“小他者”。“大他者”涵蓋整個時代背景、社會形勢和規章制度等;“小他者”則具體指向如拉康所說的鏡像形象和周邊人物所造成的影響等。電影《黑天鵝》,恰恰很好地體現出了他者——無論是“大他者”,還是“小他者”,對主人公妮娜的自我構建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2.1 “大他者”:表現空間的壓縮
《黑天鵝》的時代背景為21世紀的美國紐約,整個電影對于大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形勢所花的筆墨很少,甚至有意回避,著重勾勒的是芭蕾舞團的規章制度。舞團成員對曾經的“天鵝皇后”、現在卻因年紀大被踢下臺的貝斯極盡辛辣嘲諷奚落,舞團導演托馬斯如獨裁者般決定每一位舞者的生死,導演特意將鏡頭表現空間壓縮至芭蕾舞團,營造出“芭蕾舞團即為整個世界,跳舞是生命的全部”的強壓窒息氛圍,芭蕾舞團這個“大他者”緊緊包裹著妮娜,裹挾妮娜前行,令人窒息。
2.2 “小他者”:對掠奪者的憎恨
奧古斯丁在《自白》中描寫過這樣一幅畫面:哥哥看見弟弟被母親抱著打盹兒而嫉妒得臉色發青。兩個人作為擁有共同愿望的競爭對手產生了劇烈的沖突,暴露出隱藏在鏡子前歡欣鼓舞背后的攻擊性。對于哥哥來說,弟弟是母親懷抱的掠奪者,對于成為“天鵝皇后”后舉步維艱的妮娜來說,莉莉、母親、導演……乃至妮娜本人,都是她成功的掠奪者。他們從不同的方面,成為妮娜的“小他者”,妮娜通過“小他者”對自身的確認與充實來填補自我本質,逐漸形成新的自我意識。
2.2.1 莉莉
莉莉是妮娜打破鏡像之中虛幻自我的最強力的推動者。妮娜偏好粉白,莉莉一襲黑衣;妮娜害羞教條,莉莉開放酷辣;妮娜怯懦嬌柔,莉莉復雜多變。妮娜是最純美無瑕的白天鵝的代名詞,莉莉則是性感魅惑的黑天鵝的最佳選擇。
妮娜和莉莉的初次見面并不是妮娜記憶之中的化妝間,而是在更早之前。妮娜在地鐵上看到的那個一襲黑衣、性感魅惑卻看不清面容的女子便是莉莉。妮娜將頭發挽至耳后,黑衣女子同一時間做同樣的動作,強烈的熟悉感使妮娜對其產生好感與好奇,這是妮娜心中隱藏的另一個希望成為的自己,而此時的她并不自知。如果說兩人的初次會面并沒有使妮娜成為“真正的自己”,那么莉莉帶妮娜去酒吧尋歡作樂后發生的一切,則清楚地向妮娜抑或是觀眾傳遞一個信息:妮娜記憶中醉酒后拉著莉莉狂奔回臥室,因此不惜和母親產生沖突,當晚在想象中和莉莉瘋狂發生性關系……這一切顛覆妮娜長久以來的乖乖女形象,打破長久以來的生活狀態,無異于是向母親宣戰的行為,實則全為假象,都是妮娜在高壓之下精神分裂產生的幻覺。從妮娜進門的身影出現在關鍵道具鏡子中,莉莉從妮娜背后如同鬼魅般閃出身影開始,到兩人激烈性愛結束后莉莉逐漸抬起的臉竟是妮娜自己的,到最后妮娜質問莉莉為什么在早上沒有喊她起床未果,反被莉莉猜出妮娜是不是幻想兩人發生性關系……這一切或明或暗的細節都表明妮娜已經完全被欲望所支配。她要成功,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黑天鵝,而不僅僅滿足于扮演。
所以,到最后首演當晚,妮娜在重壓之下,產生莉莉要替代自己的幻覺繼而殺死莉莉、冷靜處理化妝間滿是血水的謀殺現場的這場想象性謀殺,則成為理所應當和順其自然的敘事走向。
莉莉是妮娜的“小他者”,是妮娜的鏡像,是妮娜將欲望置于莉莉身上的映射。或許莉莉并不完美,也不是“天鵝皇后”的最佳人選,但是作為妮娜的理想之“我”——莉莉由妮娜所建構,在莉莉的推動下,妮娜發現“真實的自我”,并最終被推向死亡。
2.2.2 母親
母親是妮娜鏡像階段前期人格的最大創作者。“小寶貝”“乖女兒”是母親的口頭禪,這看似親密的母女關系的實質卻讓妮娜和觀眾不寒而栗。
母親發現妮娜背后的抓痕,不顧女兒的懇求和阻止也要態度強硬地扒掉女兒身上象征著尊嚴的衣服、每次都像照顧幼兒般幫28歲的妮娜穿衣服、想要時時刻刻陪伴女兒練舞、對女兒的所有物品了如指掌、清楚地知道女兒每一只耳環的樣式、和舞團辦公室老師蘇茜關系匪淺,第一時間就能掌握女兒面試主演的消息、對女兒所有的行程了若指掌、時常哭泣著在畫室中畫自己年輕時的絕美舞動風姿……這一切都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妮娜:母親為了生她,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母親這個“小他者”為妮娜量身定做了一個囚籠,和芭蕾舞團這個“大他者”共同產生作用,使得妮娜沒有喘息的機會,無處可逃。
隨著妮娜的成長和對黑天鵝角色的欲望,妮娜順從的慣性和平衡慢慢被打破,妮娜開始試探著反抗母親,主體的自我意識逐漸萌生。
母親這個“小他者”同樣具有多面和復雜之處。如果這種無孔不入的掌控欲出自怨恨女兒搶走了自己的事業而滋生出的嫉妒,那么這個人物的深度則會大大削弱,成為一個徹底的反派。實際上她不僅是個盡忠職守的媽媽,而且對女兒取得的成就發自內心的自豪和高興。她會像所有普通的母親一樣在女兒第一次面試失利時輕柔體貼地幫女兒摘掉耳飾,像哄嬰兒般在床頭細語安慰,一向作風強硬的她也不惜自嘲般地揭自己的傷疤只為了哄女兒展顏。
知女莫若母,母親從第一次發現妮娜背后的抓痕時就斷言妮娜會因為這個角色壓力過大而承受不了,所以她一直試圖阻止女兒出演這個終將毀掉她的角色,母親想要的是女兒而不是名利。但妮娜的自我意識已然覺醒,母親的干預反而加速了妮娜的叛逃,身體中一直被壓抑的黑色邪惡力量一旦迸發,將永不枯竭。母女關系是共生關系,可以說,妮娜從單純、迷茫到最終黑化,母親無疑是重要的“小他者”。
2.2.3 導演
在京劇中,京劇演員講究“亮相”,主要角色上、下場前有一個短促的停頓動作,以集中突出地展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狀態,電影同樣如此。托馬斯這個人物的第一次亮相使人印象深刻,上至舞蹈老師的緊張局促,下至舞團成員立刻脫衣服展示優美的身段希望吸引托馬斯的目光,整個舞團呈現出的逢迎之意,彰顯出托馬斯在舞團中當之無愧的皇帝般的地位,掌握著每一位舞者的生殺大權。
托馬斯的能力和他的地位是匹配的。他敏銳且具有掌控力,對于舞蹈有著苛刻到極致的要求,他一眼就看出妮娜具有黑天鵝的潛質,所以他誘惑、教導、挑釁、強吻、撫摸,帶妮娜去家中親自調教,和妮娜談論性愛,希望妮娜享受愛撫自己的身體,布置給妮娜的家庭作業是每天自慰……這并非職場性騷擾,而是嚴肅的舞者教學。他想要打破妮娜根深蒂固的自持冷靜,將體內黑天鵝的一面激發出來。他同時也是細心和藹的,在發現妮娜在為貝斯的車禍而自我埋怨時,敏銳地消除妮娜的愧疚并給予堅定的鼓勵。
在《黑天鵝》中,父親一角一直是缺席的。這一方面從側面豐富了母親的角色,母親這么多年都是一個人含辛茹苦地將妮娜養大,側面突出了母親這一角色的不易,對母親畸形的控制欲作出合理解釋;另一方面,導演托馬斯實際上扮演著父親的角色。整部影片沒有出現任何其他的男性角色,顯然在妮娜的成長過程中,缺失了以父親為代表的男性角色,而導演托馬斯則承擔了妮娜生活中不只是父親,包括所有男性角色的重任,間或承擔上級的嚴厲教導,間或表現父親的溫柔關懷,間或給予情人般的調教誘惑。
2.2.4 “我”是他者
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有過一番很出色的描寫,是關于自我意識的主奴辯證法。在主奴關系中,主人是支配者,而奴隸是被支配者,可是沒有了奴隸,主人也無法實現自己的愿望,主人反而成了奴隸,而奴隸同時一方面依賴于主人,另一方面面對對象的改造,意識到自己的力量。
影片最開始有一個片段是妮娜做的一個關于白天鵝被黑魔王擒住,整個畫面只充斥著黑與白兩種極致顏色的超現實主義夢境。夢境中的白天鵝象征著妮娜現在所處的狀態,而黑魔王則意味著脆弱敏感的白天鵝妮娜,其實在內心深處壓抑了一只想要釋放,想要叛逆的黑天鵝。而在進入夢境的更早片段中,有一陣陰森詭異的笑聲,仿佛意味著女主人公另外一重人格的覺醒,并終將釋放出黑天鵝那一面。
無獨有偶,影片前期有大量細節表明邪惡的力量一開始就自主生發在妮娜的靈魂之中。從鏡像階段初期妮娜就具有的象征黑天鵝翅膀的背后的傷疤,到第一次競演失敗后在狹窄通道中擦肩而過和妮娜擁有一模一樣的臉的黑衣魅惑女子,再到用貝斯的口紅去爭取出演主角的機會,都預示著早在一開始就已經有另一個正在從妮娜的身體中掙扎著想要破土而生的“真實自我”。拉康認為,生物對外在于自身的形象能以一種類似想象的方式占有[3]。就算沒有芭蕾舞團這個“大他者”,莉莉、母親、托馬斯這些“小他者”,也會有別的人、別的“他者”和別的激勵事件,以及最重要的是,“我”是他者。
3 自我的終建:尋找真實的自我
黑天鵝是妮娜內心壓抑激情的釋放,白天鵝則象征通過自我克制追求完美。邪魅、淫蕩、嫉妒、誘惑、詭詐等黑暗力量牽扯著妮娜,黑天鵝逐漸侵入妮娜的靈魂,她難以抗拒,無路可逃,但她卻并不是絕望被動地接受,相反,這一切她甘之如飴。黑白天鵝所代表的不只是善和惡,還有幻象與自我。自我建構的過程是追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實現和欲望滿足,自我建構一旦開始,就會沖破一切束縛,是自我無法控制的力量。
妮娜原來壓抑地處于虛幻鏡像中的世界,在“大他者”和“小他者”的推動之下,通過對莉莉的想象性謀殺這一高潮片段,主人公完成自我建構,實現了自我的升華。表演完之后妮娜發現,她并沒有真的殺死莉莉,謀殺現場是強壓之下精神分裂所產生的幻覺,妮娜殺死的是曾經壓抑的自己。“殺死自己”具有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寓意,心理上,妮娜殺死的是曾經潔白無瑕的自己,而生理上,妮娜刺向莉莉的兇器所對準的,其實是自己的腹部,妮娜死于演出獲得巨大成功的現場。拉康認為,認同的過程是引向死亡的過程。
妮娜逃出虛幻自我,建立真實自我,自我與他者對立消解,形成真正的自我認同。如果不背叛自我,就不會消除隔閡,只是把自我撕裂,而不把它的外殼撕得粉碎,我們就不會走上自由之路[2]。
4 結語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中,十分強調本能、欲望、壓力、沖動等生物學機制,以否認、壓抑等自我防衛機制為中心,是壓抑的、克制的。而拉康與此相反,拉康在其理論形成的初期就表現出一種對生物學傾向的反感,其創見則是相對排除了神秘的生物學力量,是撕裂的、突破的、是趨于毀滅和新生的。
在《黑天鵝》導演達倫·阿倫諾夫斯基看來,對“自我”的求索是他想探尋的根本性主題,個體自身的成長與重塑才是個體的一生事業追求和形成、發展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原因,《黑天鵝》對妮娜“真實自我”的探索過程與呈現方式十分精彩。回顧妮娜自我建構的過程,通過諸多“他者”的推動,自我與他者的對立消解,最終形成真正的自我認同。從鏡像階段開始,幼兒就確立了自我和他人的對立和共生關系,從意識到他人特質,到明確自己本質。把他人的目光當作鏡子,以為他人目光里的鏡像就是自己,然后從這個鏡像內化真正的自我。
參考文獻:
[1] 雅克·拉康.拉康選集[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1:6-7,45.
[2] 福原太平.拉康:鏡像階段[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19,56.
[3] 里德.拉康[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18-19.
作者簡介:張瑋瑜(1996—),女,江蘇徐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電影創作、廣播電視藝術、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