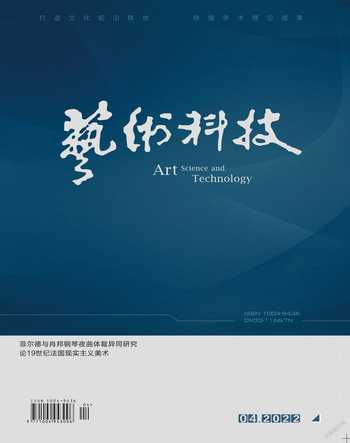鄉村文化治理的實現路徑與合理性研究
摘要: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基石在于鄉村治理,鄉村治理的根基在于汲取傳統文化中的治理精髓。在鄉村文化治理的視域下,因地制宜地促進當地文化產業的發展尤為重要,同時在發展中要繼承和創新當地傳統文化以推動鄉村振興。文章從花茂村的發展轉型中,找到其治理中主客體的相關掣肘因素,優化文化治理的實現路徑,探究鄉村文化治理的行動邏輯,對未來鄉村振興中鄉村文化治理的發展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鄉村振興;文化治理;鄉村文化;文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G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04-0-03
0 引言
黨的十八大全面部署了五位一體戰略總布局,并將文化建設視作整個有機整體的靈魂,之后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雖然兩者提出的時間不同,但相互之間聯系緊密、不可分割。千百年來優秀的農耕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騰飛的起點,而今天的鄉村文化振興同樣是未來鄉村全面振興的起點。鄉村文化的興衰不僅關系到鄉村的興衰,更關系到中華民族的興衰[1]。因此,在發展中如何促進鄉村優秀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怎樣全面統籌協調鄉村文化與產業、人才、生態、組織共同發展,是當前必須思考的問題。
1 鄉村文化治理的概念
鄉村文化治理是鄉村振興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中人是治理主體,人的思想觀念是治理的核心要素。文化治理是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社會人文領域的體現,也是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部分[2],在鄉村振興中,鄉村文化治理作為一種重要的治理手段,日益被學者們關注。
對鄉村文化治理的定義,學界還沒有統一的定論,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視角闡述鄉村文化治理。胡惠林教授將文化治理作為一種新時代呼應國家發展需要的治理手段,需要著力提升文化產業形態發展的現代化程度,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3]。俞可平教授認為國家治理體系分為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善治”是一種治理的理想狀態[4]。劉彥武從嵌入性理論的視角提出應使先行文化、鄉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并重視鄉村文化的獨特性、純潔性與傳承性[5]。
總體來看,對鄉村文化治理雖然沒有一致的論述,但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以更加多元和全面的角度進行理解[6]。鄉村文化治理不是指僅僅關注文化發展,而是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7],在發展傳統文化的過程中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鄉村文化振興賦予廣大鄉村地區更多文化自信,增強農民的幸福感、價值感、獲得感,縮小城鄉精神層次方面的差距。
2 花茂村大體介紹
2.1 發展現狀
花茂村位于貴州省遵義市楓香鎮的東北部。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來到花茂村考察時曾說“怪不得大家都來,在這里找到鄉愁了”[8],一句意味深長的“鄉愁”讓全國人民開始認識花茂村。曾經的花茂村貧困荒蕪,人口流出率非常高,但隨著精準扶貧政策的出臺,短短幾年間,花茂村一躍成為貴州省乃至全國的脫貧示范村。從花茂村的改變可以看到傳統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治理到文化治理的轉型帶給鄉村的巨大影響,通過發展以“美麗鄉愁”為文化特色的鄉村旅游,激發了花茂村自身發展的內生動力。
2.2 鄉村文化治理下的花茂村
實現鄉村振興,鄉村旅游是重要選項[9]。花茂村在鄉村振興的路上,將鄉村旅游、特色農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積極探索旅游、農業、文化一體式的發展模式,引導村民發展特色鮮明的鄉村旅游。花茂村從鄉村文化角度出發,摸索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文化旅游產業道路。
2.2.1 花茂村的文化資源
第一,紅色文化。距離花茂村僅10分鐘車程的茍壩,就是茍壩會議的召開地。作為革命老區的花茂村,被時代賦予了深厚的紅色烙印,使其在時間的長河中歷久彌新。謀求發展的花茂村將紅色文化嵌入鄉村旅游,把茍壩會議會址打造成鄉村旅游一個亮麗的文化標志。如今茍壩會議會址已經成為花茂村經濟、文化發展的優勢,也成為花茂村保護和傳承紅色文化的一種方式。
第二,非物質文化遺產。花茂村的底色不只是紅色,其還有貴州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花茂土陶。花茂村的制陶業有100多年的歷史[10]。但隨著時代發展,村里的人紛紛外流,加上交通不便、難以運輸,花茂土陶逐漸沒落,制陶技藝也被人們遺忘。同時,花茂村的另一項技藝——古法造紙,也面臨著和花茂土陶一樣的困境,構樹皮造紙是花茂傳承千百年的工藝[11],卻在風雨的洗禮中逐漸褪色。
如今在牢記優秀傳統文化的理念中,花茂村重新將幾近失傳的技藝發展起來,通過當地政府和花茂土陶第四代“非遺”傳承人母先才的共同努力,花茂土陶再一次成為花茂村的文化名片。除此之外,村里還建立了茍壩會議紀念館、紀念廣場、紅色之家、母氏陶藝館等文化傳承基地,成功帶動了村民發展鄉村旅游與特色文化產業,同時建立起的創客中心更是吸引著外面的年輕人加入本村文化振興的行列。
花茂村立足于本土文化,通過鄉村旅游發展有效保護和發展紅色文化及本地傳統文化,讓游客融入鄉村,在感受民風民俗、體會美麗鄉愁的同時,也保護了農民的文化權益,提高本村村民的自豪感,真正彰顯了鄉愁的現代價值。
2.2.2 各路產業積極融合
以前的花茂村以發展第一產業為主,通過治理轉型,現在的花茂村在主營鄉村旅游的同時帶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全面融合發展,讓村民的口袋越來越鼓。
當地農業引進山東九豐集團,利用“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發展模式[12],鼓勵全村種植露天、大棚蔬菜瓜果,讓游客可以深度體驗采摘、品嘗當地農作物。農家樂和電商也在花茂村蓬勃發展,村民在自家門口就能賺到錢,還能照顧家中的長輩和孩子,吸引了不少年輕人返鄉創業,更是讓以“鄉愁”為名片的大山特產走進了千家萬戶。
文化旅游和生態田園的融合,成功將以前的“荒茅田”打造成了遠近聞名的鄉村旅游度假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融合推動花茂村全方位發展,文化價值的持續輸出推進了花茂村的可持續發展。09B613B9-6D44-4542-91B1-A1F0EE71EE1A
3 花茂村在文化治理中的掣肘因素
3.1 鄉村文化的“褪色”與“亂序”
從鄉村文化治理的客體角度出發,可以看到不同村莊都有各自獨特的文化精華,這是幾千年來當地生活凝聚的結晶,體現著當地農民群眾的道德價值觀念和生活理念。尤其是在偏遠地區的村落、少數民族聚居的村寨以及一些充滿歷史遺跡的村莊等等,都蘊含著濃厚的獨特的傳統文化。但一方面,從花茂村這個案例中能夠看到鄉村文化的“褪色”,其中花茂土陶作為花茂村的“非遺”之一,到目前為止僅有一位傳承人,從100多年前的興盛到如今似乎只剩下土陶讓后人觀賞,其中的文化韻律及社會價值都讓人難以尋覓。另一方面,向鄉村地區過度輸入城市的理念和精神,使得優秀的傳統文化在城市影響下不斷萎靡,使得鄉村文化的價值受到質疑,村民對本村落文化的認同感下降。
3.2 鄉村治理主體的“消散”與“缺位”
鄉村治理的主體是當地農民和當地政府。一方面,參與度低使得農民難以置于文化建設的中心。年輕人外出上學、適齡勞動力外出務工已成常態,留在村子里的都是文化程度較低、缺乏勞動力的群體,這種情況下很少有人能夠參與鄉村治理。長期以來廣大農民群眾對政府習慣處于“依賴”與“跟隨”狀態。另一方面,在之前的發展階段中,政府主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忽略了從傳統文化尤其是農耕文化中汲取精髓,造成政府在文化發展中角色的缺位。
4 鄉村文化治理的實現路徑
4.1 建立多元的鄉村基層組織體系
農民作為主體,在文化建設過程中應處于決策地位。但由于信息不對稱,多數農民的參與意識不足以及多年以來形成的慣性思維,文化建設的發展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下達執行,農民的主體地位被淡化。要從多元維度構建鄉村基層組織,強調政府、農民和這種組織三種力量的互補與協調共治,尤其是突出農民群眾的意愿。鄉村振興的中堅力量是農民,最終受益者也是農民,要重點突出農民在鄉村文化發展中的主體作用,激發其主觀能動性,引導增強其“主人翁”意識與責任感。
4.2 創新數字化傳統文化保護機制
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一直以來就是人們不斷研究的內容。隨著大數據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數字博物館的建設漸成規模[13]。數字博物館能夠有效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傳統文化傳播得更加廣泛,凸顯其魅力。因此,不同地區的政府和社會組織應當加強數字文化的建設,將智慧治理的理念融入文化治理。
4.3 完善人才引進與資本投入機制
優秀的人才儲備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條件,也是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法寶,優秀的人才能帶領村莊找到新的機遇,幫助鄉村更有效地利用文化資源,挖掘不同鄉村治理的獨特方式,推動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資本的支持在各行各業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在這方面要發揮優勢,持續招商引資,發布惠企惠民政策,借助新型市場化手段,建設有嶄新面貌的美麗文化鄉村。
5 鄉村文化治理的合理性
5.1 鄉村文化治理的起點: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
切實保障農民的文化權益是鄉村文化治理中微觀層面的體現,也是基層政府在進行文化治理時要達到的最基本目標。如今我國的鄉村振興建設工作已全面推進,城鄉發展在物質方面的差距已大幅縮小,這就使得精神文化層面上的落差日益凸顯。
文化權益的實現程度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一大體現[14]。文化治理作為社會文明不斷進步的產物,是由政治治理到經濟治理演進而來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3]。目前鄉村治理中的首要任務不再是著眼于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而是重點關注如何激發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意識,鼓勵農民自發參與文化建設,突出農民群眾的決策地位。作為職能部門,政府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幫助農民群眾抓住建設重點,確保農民主體地位的落實到位,凝聚多方力量實現“文化興、鄉村興”,使之成為鄉村文化振興的內生動力。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建設,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鄉村文化治理既要充分重視農民的需求,又要考慮文化差異,在發展文化的過程中,要完善群眾的利益共享機制,讓農民群眾享有更多文化發展帶來的碩果。
5.2 鄉村文化治理的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4]
當前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地方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已呈現出新特征,因此治理模式亟待創新[15]。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這一論述指明了我國治理模式的創新與發展方向。鄉村文化治理的推動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治理的過程中引導農民繼承遵紀守法、誠實守信、扶危濟貧等優秀傳統文化,并不斷豐富其內涵,助力鄉村治理。
5.3 鄉村文化治理與鄉村振興戰略的耦合性
鄉村文化治理與鄉村振興戰略的耦合性是鄉村文化治理能夠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為解決現階段我國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提出的重要發展戰略,堅定文化自信是實現鄉村振興的現實動力和持守定力,也是鄉村文化繁盛的核心內容和重要條件[16]。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進入新時代,城鄉經濟差距的縮小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文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這意味著鄉村振興中“形”的問題已經得到初步解決,但是“魂”的問題依然存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擁有悠久的農耕文明,其背后蘊含著特有的農耕文化,文化自信歷來是一種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堅定信念,因此在鄉村文化治理中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不斷汲取我國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精髓,為當代鄉村塑造嶄新的精神風貌。鄉村文化治理的方式、內容和手段順應了時代和人民的要求,對穩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重要意義。
6 結語
不同鄉村所處的地域環境、經濟條件、民族文化等都有差異,在鄉村文化治理的路徑上不會完全相同,但大部分農村地區在人口流動、社會觀念的改變等方面存在普遍的共性問題。通過探究花茂村在文化治理上的成功經驗,讓其他地區的文化治理有了一定借鑒。鄉村文化治理之所以能得到支持和發展,是因為其順應了國家的發展趨勢,回應了民眾的時代呼聲,能夠有效推動鄉村振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09B613B9-6D44-4542-91B1-A1F0EE71EE1A
參考文獻:
[1] 楊華,范岳,杜天欣.鄉村文化的優勢內核、發展困境與振興策略[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2(3):23-31.
[2] 邢澤瑋.黑龍江省加強鄉村文化治理對策探賾[J].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20(4):54-58.
[3] 胡惠林.實現文化善治與國家文化安全的有機互動[J].探索與爭鳴,2014(5):11-12.
[4] 俞可平.論國家治理現代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3.
[5] 劉彥武.從嵌入到耦合:當代中國鄉村文化治理嬗變研究[J].中華文化論壇,2017(10):5-13,190.
[6] 葉鵬飛.秩序與活力:鄉村文化治理的問題與反思[J].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39(6):69-79.
[7] 范玉剛.在中華文明與全球化雙重視域中領悟鄉村文化復興的意義[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122-133.
[8] 張雷,汪海平.學思踐悟·十九大解碼特色產業精準扶貧的“花茂樣本”[EB/OL].百度,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5041320754706146&wfr=spider&for=pc,2017-11-25.
[9] 劉朝文,何文俊,向玉成.鄉村旅游視域下的鄉村振興[J].重慶社會科學,2018(9):94-103.
[10] 于海軍.花茂土陶,黔北鄉村文化名片[J].民生周刊,2021(7):32-34.
[11] 金一丹.一紙繁花千年古法造紙做活花茂鄉村振興[J].造紙裝備及材料,2021,50(4):4.
[12] 許峰.鄉村旅游“花茂樣本”的觀察和思考[J].當代貴州,2021(49):60-61.
[13] 張建國.數字博物館對文物保護與全球化傳播的保障策略研究[J].情報科學,2022,40(2):59-64.
[14] 張波,李群群.鄉村文化治理的行動邏輯與機制創新[J].山東社會科學,2022(3):110-117.
[15] 申樹欣.新時代地方治理的特征、問題與對策[J].理論學刊,2022(2):120-127.
[16] 林巖.鄉村振興背景下堅定文化自信:應然選擇,力量之源與現實路徑[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37(2):47-51.
作者簡介:陸思羽(1997—),女,陜西西安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行政管理。09B613B9-6D44-4542-91B1-A1F0EE71EE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