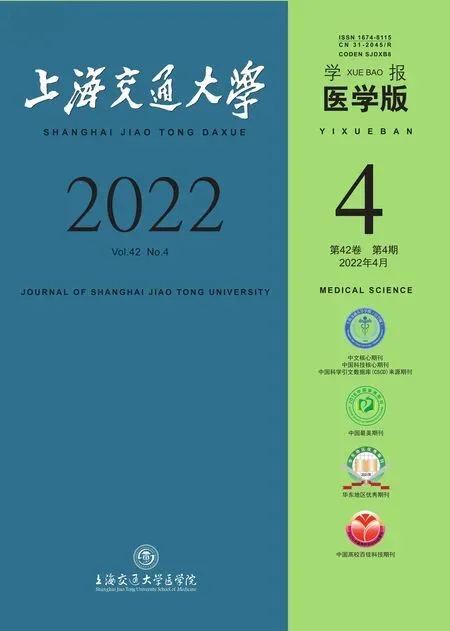難治性產后出血導致子宮切除的危險因素分析
胡佳寧,張錦文,劉曉瑞,陳彩蓮,林 羿
1.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中心實驗室,上海市胚胎源性疾病重點實驗室,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出生缺陷與罕見病臨床研究院,上海 200030;2.上海交通大學電子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院自動化系,系統控制與信息處理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240
難治性產后出血是一種經子宮收縮藥物、持續性子宮按摩或按壓等治療后仍無法止血,需行外科手術、介入治療甚至切除子宮的嚴重產后出血。研究[1]顯示,難治性產后出血是孕產婦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圍產期急癥子宮切除術是指因產科相關因素導致的在保守治療無效時,緊急采取的子宮切除手術。該手術是治療產后出血、搶救產婦生命的重要手段[2]。然而,對于患者來說,切除子宮將會使其永久地喪失生育能力及月經來潮等生理功能;對于醫生而言,這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此,在保證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如何降低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的子宮切除風險,已引起了臨床醫師和科研工作者的高度關注。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2014—2020 年間產科急癥子宮切除術的發生率以及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的臨床資料,探尋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發生子宮切除的臨床特點及相關高危因素,以期為臨床決策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及其分組
選擇2014 年1 月—2020 年12 月于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定期產檢并住院分娩的產婦110 934例。
1.1.1 2015—2020 年段產婦及其分組 基于時間隊列考慮,選擇2015—2017 年段(n=48 984)與2018—2020年段(n=45 262)的產婦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臨床資料完整。
1.1.2 難治性產后出血產婦及其分組 選擇其中發生難治性產后出血的產婦108 例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符合《產后出血預防與處理指南(2014)》[3]中有關難治性產后出血的診斷標準。②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合并重要臟器器質性損傷。②合并女性生殖系統惡性腫瘤。根據術式的不同,將該研究對象分為子宮切除組(n=22)和子宮保留組(n=86)。
1.2 臨床資料收集
1.2.1 2015—2020 年段產婦的資料收集 收集并整理2015—2017 年段及2018—2020 年段產婦是否行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情況及切除率。
1.2.2 難治性產后出血產婦的資料收集 收集并整理難治性產后出血產婦的臨床資料。①一般資料:年齡、孕前體質量、孕前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孕次、產次、既往流產史、孕周、胎兒數目、分娩方式、產后出血量、妊娠合并癥(前置胎盤、胎盤早剝、胎盤植入、瘢痕子宮、子癇前期、妊娠期糖尿病)、宮縮乏力、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羊水栓塞。②母嬰結局:住院時間、手術后發熱、產褥期發熱、產褥期感染、新生兒Apgar評分(肌張力、脈搏、刺激、膚色、呼吸)、低出生體質量兒、新生兒黃疸、新生兒濕肺。
1.3 統計學方法
利用Excel 2016 錄入數據,采用SPSS 20.0 軟件對研究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定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進行比較;定性資料以頻數(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檢驗進行比較。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獨立危險因素。以α=0.05 為檢驗水準,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同時期產婦的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率分析
采用χ2檢驗對2015—2017 年間與2018—2020 年間產婦的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率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在94 246 例產婦中共發生產科急癥子宮切除20 例。其中,2015—2017 年段發生15 例,切除率為30.6/10萬,2018—2020 年段發生5 例,切除率為11.0/10 萬;該2 個時段內未發生產婦死亡,且切除率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39)。
2.2 難治性產后出血產婦的一般資料比較
對2組產婦的一般資料進行比較分析,結果(表1)顯示與子宮保留組患者相比,子宮切除組患者的年齡較大,發生前置胎盤、胎盤植入、瘢痕子宮等妊娠合并癥的比例較高,孕次≥2次、胎兒數目<2及發生羊水栓塞者的占比亦較高,產后出血量更大(均P<0.05)。

表1 子宮切除組和子宮保留組產婦的一般資料比較Tab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uterine-removed group and the uterine-preserved group
2.3 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將是否行產科急癥子宮切除作為因變量,單因素分析獲得的影響因素設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2)顯示,年齡、產后出血量是導致患者行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獨立危險因素(均P<0.05);年齡每增加1 歲其子宮切除率增加39.1%,產后出血量每增加1 mL 其切除率增加0.2%(即每增加500 mL,子宮切除率增加272%)。

表2 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mergency peripartum hysterectomy in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postpartum hemorrhage
2.4 母嬰結局比較
對2 組患者的母嬰結局進行比較分析,結果(表3)顯示住院時間在組間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7)。此外,新生兒Apgar 評分是評估新生兒身體狀況的標準方法,在本研究中,雖然該指標的組間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5),但仍然可說明經切除子宮后的患者誕下的新生兒,其Apgar 評分具有下降的趨勢。

表3 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的母嬰結局比較Tab 3 Comparison of maternal-infant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postpartum hemorrhage
3 討論
3.1 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發生率
2005—2015 年間,全球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發生率為0.02%~1.01%,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地區,且近年來呈逐步下降的趨勢[3]。在本研究的數據庫中,2015—2017 年間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率為30.6/10 萬,2018—2020 年間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率為11.0/10 萬。分析其下降的原因,可能與2015 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考慮到生育高峰的再次出現,醫務工作者對存在高危妊娠危險因素(如高齡、瘢痕子宮等)的產婦進行了更為嚴密的孕期動態觀察,并采取了更加積極的干預措施有關;同時,由于人們再次生育的意愿增強,醫務工作者在搶救高危產婦時,進一步降低剖宮產、子宮切除等對子宮有創的操作,為妊娠再次成功創造了條件[4]。
3.2 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危險因素
本研究發現,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的年齡、孕次、產后出血量、胎兒數目、羊水栓塞以及發生前置胎盤、胎盤植入、瘢痕子宮等妊娠合并癥均為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影響因素。對不同地區的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發生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常見原因進行分析發現,結果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來自意大利的TRIUNFO 等[5]發現,產婦高齡、家庭收入低、產次多、具有既往剖宮產史是導致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主要危險因素。一項愛爾蘭的研究[6]表明,宮縮乏力、胎盤前置、胎盤植入是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主要原因。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內研究[7-8]發現,胎盤因素已取代宮縮乏力、子宮破裂等原因成為了影響我國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主要因素。在本研究中,為排除混雜因素的影響,設置了因變量及自變量后進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和產后出血量均是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的獨立危險因素。分析其深層次原因,可能如下:①隨著產婦年齡的不斷增加,其子宮動脈內壁的肌肉成分逐漸被膠原成分取代,使得管壁的彈性減弱、復原能力降低,易導致產后子宮動脈修復不足而持續出血[9]。②高齡產婦發生胎盤前置、胎盤植入、子癇前期、妊娠期糖尿病等妊娠合并癥的概率明顯高于非高齡人群,且這些妊娠合并癥均是其發生難治性產后大出血的高危因素[10]。③高齡產婦中經產婦的比例較高,而經產婦具有瘢痕子宮的可能性較大,因此也增加了高齡產婦發生兇險性前置胎盤(附著在子宮下段剖宮產瘢痕處的前置胎盤,伴或不伴胎盤植入)的風險[11]。且該疾病易導致胎盤供血不足,誘發胎盤粘連或植入,從而使胎盤不易剝離母體,進一步增加了發生難治性產后出血的概率[12]。綜上所述,高齡產婦一旦發生產后出血,出血量通常較大,搶治難度較高,往往會導致切除子宮的不良結局。此外,在本研究中,子宮切除組患者胎兒數目<2 個(即單胎妊娠)的占比較高,這與我們既往認為多胎妊娠會導致更多的妊娠合并癥從而增加子宮切除風險的認知不符。究其原因,可能由于在妊娠初期產科醫師通過B超等方式已明確了產婦為多胎妊娠,從而更加重視對產婦的健康宣教、孕期管理及監護等。
3.3 產科急癥子宮切除術后并發癥及預防
在本研究中,2015—2020 年間行產科急癥子宮切除術的患者均未發生死亡,證實子宮切除仍是挽救難治性產后出血產婦生命的有效手段。但通過后續比較子宮保留組與子宮切除組母嬰結局時,我們發現與子宮保留組相比,子宮切除組產婦的住院時間有顯著增加,發生手術后發熱等應激反應的比例雖有增加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些現象或可會增加產婦院內交叉感染、產褥期感染的發生風險,從而進一步增加其醫療費用,不利于產后的身心恢復。同時,產科急癥子宮切除也對新生兒健康亦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Apgar 評分有所下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難治性產后出血患者具有較多的妊娠合并癥(如前置胎盤、胎盤植入等),可導致胎兒早產、發育不成熟,或發生宮內窘迫、出生時嚴重缺氧等;另一方面,由于產后出血延長了產婦的恢復期,使得母嬰接觸、哺乳喂養等受到影響,從而降低了新生兒預后[13]。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醫務工作者在關注子宮切除產婦的身心健康的同時,還需加強對新生兒護理的規范管理。
綜上所述,產科急癥子宮切除對母嬰健康造成了諸多不良影響。針對如何降低產科急癥子宮切除率,我們考慮如下:①首先,需提高高危妊娠危險度評估的精準性,加強孕期全程管理。醫務工作者需合理掌握剖宮產指征,降低人工流產、引產率,從而進一步降低瘢痕子宮的發生率;而高危產婦也需針對其妊娠合并癥進行積極治療,包括前置胎盤、胎盤植入、子癇前期、妊娠期糖尿病等[14-15]。②其次,一旦發生產后大出血,在診斷明確的條件下,醫務工作者應積極干預,以避免因延誤搶救時機導致的產婦子宮切除甚至死亡的發生。
對于難治性產后出血導致子宮切除相關危險因素的分析,本研究納入的產婦例數較少,結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后續,尚需開展多中心、大樣本的隨機對照研究,對獲得的結果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論證。
利益沖突聲明/Conflict of Interests
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All authors disclose no relevant conflict of interests.
倫理批準和知情同意/Ethics Approval and Patient Consent
本研究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醫學科研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審批號:國科倫委(GKLW)2017-121]。因屬回顧性研究,未簽訂知情同意書。
All experimental protocols in this study were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e Medic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Maternity& Child Health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GKLW 2017-121),issued on 23/08/2018].No informed consent is required to the retrospective nature of the study.
作者貢獻/Authors'Contributions
林羿、陳彩蓮參與了課題規劃;張錦文參與了數據統計;劉曉瑞、胡佳寧參與了論文的寫作和修改。所有作者均閱讀并同意了最終稿件的提交。
The study was designed by LIN Yi and CHEN Cailian.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ZHANG Jinwen. The manuscript was drafted and revised by LIU Xiaorui and HU Jianing. All the authors have read the last version of paper and consented for submission.
·Received:2021-11-18
·Accepted:2022-01-10
·Published online:2022-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