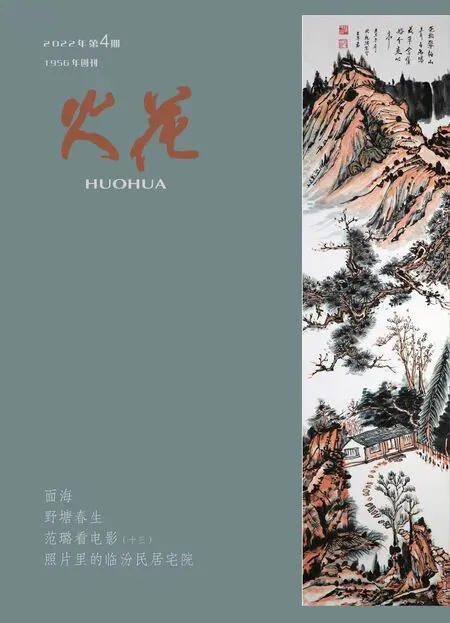你這個犢子
陶詩秀
一
周明笙是恢復高考后,進入S學院讀書的。大學沒畢業,他就考上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研究生,之后作為國際交流生赴美留學。
周明笙博士畢業,入職硅谷的網絡通信技術公司,此后的人生履歷與大多數留美學生相似——結婚、生子、安家、樂業。他慢慢等“翅膀”硬了,便在同行業的公司間跳槽,最終選擇與合伙人創業。
多年來,周明笙對工作恪盡職守,對家庭全身心地承擔起丈夫和父親的角色,在異國他鄉過著一種循規蹈矩的平靜生活。
不過,這一切最近都被打亂了——他接到北京來的電話,妹妹告訴他,她要去澳大利亞探望在那里工作的兒子,其實是背著老母親去辦移民。父親過世得早,癱瘓多年的母親身邊不能沒有親人。周明笙想都沒多想,倉促中把公司事務托付給合伙人鄭北北,安頓好家小,便馬不停蹄趕回北京。
他心里清楚——歲月催人老,自己兩鬢星斑畢露,早過了“知天命”的歲數,該在老人跟前盡盡孝了。
提起合伙人鄭北北,周明笙與他還真有點兒緣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周明笙從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市的華盛頓大學畢業,應聘到硅谷公司從事數據傳輸的研發工作。一天,在圣塔克拉拉谷地的公司洗手間,洗手臺前的周明笙發現身邊站著一張東方面孔,便有一搭沒一搭地打了個招呼:“來自中國?”
對方回答嘎嘣脆:“沒錯,北京的!您呢?”
周明笙慢條斯理地接話:“也是!知道學院路嗎?那兒有個S學院。”
對方的語氣顯然亢奮起來:“嗨!太知道了!我是G學院的,您上的哪所中學?”
“G學院附中七〇屆四班的,您呢?”周明笙受到鼓舞。
“太巧了!咱們是同校同屆,我是一班的鄭北北。”
“認識你很高興,我叫周明笙。”
萬里之遙一個幾平方米大小的空間,讓隔著千山萬水一所中學的倆同窗狹路相逢,說明什么?說明地球也就這么大點地兒。
兩人的人生軌跡經過短暫交集,各自又按照專業路徑的職場圈子,游走于硅谷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多年以后,周明笙與北北在一次通訊產品發布會上再次相遇,聊著聊著,雙方都意識到,不管從研究方向、技術路線,還是商業理念,兩人對通訊領域行業發展與技術的前瞻性看法都十分相近。
不久后,他們從各自公司辭職,共同組建了“風雨同舟”通訊技術公司。多年商海沉浮,公司業務有了長足的發展。
回到北京的這些日子里,周明笙整天忙忙碌碌的。他學會了給母親喂飯、服藥,也能熟練地給母親梳頭、按摩;就是協助保姆給母親擦身子、換衣服時,還有些縮手縮腳。不過,總算慢慢適應了北京的生活。
這天吃完晚飯,周明笙慵懶地倚在母親床邊的沙發上,按照母親的叮囑,把每天吃的藥量按照早、中、晚,分別用紙包好,同時有一搭沒一搭地與母親嘮著家長里短。
藥包完了,周明笙隨手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無意中調到某文藝頻道。映入眼簾的是電影《劉三姐》的女主角、七十三歲的黃婉秋步入演播大廳,迎接她的是暴風雨般的掌聲——也難怪,觀眾席上凈是中老年人。
黃婉秋深情地放聲高歌:
山頂有花山腳香,橋底有水橋面涼,
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
山歌好像泉水流,深山老林處處有,
若還有人來阻擋,沖破長堤泡九州……
周明笙好像一下子遭到電擊,產生一種時空轉換的錯覺,連母親問他話都沒聽到。他的腦海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二手錄放機——播放、卡帶、快進、回放,往昔歲月一幕幕情景從記憶中遲緩地流淌出來。
二
火車沿膠濟線的蒼茫大地爬行,穿過孤寂的冬夜,在京滬線迎來破曉的黎明。周明笙靠在車廂的硬木座位上,迷迷糊糊地打著瞌睡。
等他清醒過來,窗外,墨綠色的火車皮在微弱的晨曦下,閃爍著幽暗的光亮。蜿蜒的鐵軌在迷茫的目光下顯得飄忽不定,好像預示著人的命運跌宕起伏、悠遠漫長。
飛馳而過的景物在晨霧與蒸汽的襯托下時隱時現,仿佛象征著撲朔迷離的世間萬象……
周明笙十四歲跟隨父母所供職的大學,從北京遷往山東。周明笙初中畢業,分到魯北一個荒原上的油礦當工人。這次回京,他要與院里從小一塊長大的兩位兄長聚會。
周明笙終于抵達朝思暮想、離別三年的故鄉——北京。走出站臺,撲面而來的是漫天飛雪,街區樓宇銀裝素裹,大地樹木萬籟寂靜。無數細小的雪花,在灰暗的天空中輕盈飛舞,還未落地就像卑微的生靈一般悄然無蹤。他遲疑了片刻,拎著提包,徑直來到南城的一家浴池——清華池。
對這個浴池周明笙并不陌生,打小就常來。“澡膩子”是老北京人對那些泡澡有癮但無所事事的閑人的稱謂。
他們一早來到澡堂子,先砌上一壺釅茶,直喝得滿臉通紅、汗流浹背;隨后走進蒸汽彌漫的水池,泡他個皮囊粉嘟嘟,汗腺洞開,暢快淋漓。這時搓澡的師傅就會悄無聲息地出現在他身旁,熟練地搓掉客人身上每一個部位的污濁,還他一個清凈的皮囊。
到了中午,他們會叫上一匣外賣的點心,填飽肚皮后睡上一覺,醒后容光煥發,這就是“澡膩子”悠悠然的一天。
周明笙拍打著身上的雪花,掀開為防寒特制的毛氈子門簾,熱騰騰的水氣撲面而來。一個臉上長著細麻子的中年服務員迎面接客:“小孩兒,怎么這么早就來啦?”
周明笙含糊著嘟囔了一句,拎著提包徑直往里走。澡堂這兩年變化很大,現如今白天開澡堂子,晚上當客店。這會兒,剛好是浴池營業的時辰,周明笙選了個鋪位,先把提包塞進柜子,然后脫光衣服,鎖上柜門,搭上浴巾,走進浴池。
他沿著池子邊,緩緩將身體滑入水中。熱水擁抱了他疲憊的軀體,一夜的倦意仿佛在熱泡中消退、融化……老北京人講究泡澡;洗,是肢體動作;泡,是全身舒坦。一字之差,大相徑庭。
此時的清華池水氣氤氳,溫潤如春。熱池中的周明笙,小臉被水氣激得紅撲撲的,他愜意地自言自語:“水熱,人都泡活泛啦!”
三
肖群群終于出發了。他在屯里的知青點擔任“司務”——守護著知青們的錢糧,擔當著集體戶灶上的伙夫,兼給大伙兒記工分,還時不常地替補一下生產隊的車把式。就為這,他是今冬臘月里最后一個離開屯子的知青。
知道啥叫“并屯”嗎?按照知青政策,凡遇到招工、招生和參軍等可以改變前程的機會,城里來的知青優先。所以,用不了多久,屯子里的知青就會縮減;這時縣知青辦就會將遠近幾個屯子里的知青進行歸攏,名曰方便管理,俗稱“并屯”。肖群群遭遇過三次“并屯”,周明笙對群群面對苦難表現出來的堅強意志極為欽佩。他覺得,群群的內心磨礪得十分強大。
聽說群群要去北京,往來密切的車把式“二疙瘩”,非要送他一程。白城子地區使喚馬拉雪爬犁,這是生活在冰雪世界里的百姓犁地和運輸的工具。當地有句謎語,謎面是“前后沒轂轆,滿地亂出溜”,謎底就是“爬犁”。
馬拉的爬犁形狀為長方形,兩根又厚又硬的柞樹干做轅木,兩端翹起,遇到溝溝坎坎能順利通過。白城子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處于冰雪期,田野中的雪特別厚,往往淹沒了“道眼”。爬犁最大的好處就是不分道路,只要有冰雪,就能靠著牲口的牽引行走。
兩人駕著爬犁整整走了一宿。為了驅寒,一路上他們相互對著軍用水壺的嘴,往肚里灌老白干,就這樣風塵仆仆、醉醺醺地趕到白城子火車站。群群好不容易才在機務段,找到曾在一個知青點待過的霍果子。
果子兄弟辦事麻利,直接從停靠在站臺上一列南下的火車另一側,將群群塞進車廂;還遞給他一串客運列車專用的車廂門鑰匙和一大袋子熱騰騰的饅頭夾肉,讓囊中羞澀的群群心里涌出一股暖流。
上車沒多久,便開始查票了。乘務員先把車廂兩頭的門鎖上,然后從前往后一個坐席一個坐席地檢票。群群不慌不忙地靠在離門不遠的過道上,眼睛死盯著乘務員的一舉一動。趁乘務員低頭給一位老年婦女檢票時,他一個箭步跨到車廂門口,用鑰匙麻利地打開車門,然后反身鎖上,進入下一節車廂。他和乘務員玩起了藏貓貓……
四
這一陣陳巖心情不錯,父親陳樞民“結合”進S學院的領導班子,算是官復原職了。再就是學院設在北京的留守處,為方便父親來京開會辦事,在老校區給父親安排了一間單身宿舍。
這可是陳巖幾年來夢寐以求的,他從遠郊區的煤礦回城,終于有了落腳點。為此,他寫信邀請兩年沒見面的發小肖群群、周明笙一塊來京聚聚。
這一天,陳巖和礦上的工友汪小年一同下井。他與小年來自一〇一中學,一塊來到平西煤礦,分在一個掘進隊干活。下井時,陳巖堅持走在小年頭里,他自夸足球踢得好,奔跑時爆發力強;他嘲笑小年的體型是標準的“豆芽菜”。
礦上采用豎井與斜井相結合的開采方式,這會兒他們走在斜井的巷道里,離采掘點還有一段距離。越往前走,巷道里的空氣越稀薄,兩人走一會兒就得停下來,在巷道的送風口倒換口氣。
走著走著,突然,小年聽到頭頂上有一種木頭受擠壓、承受不住而發出的扭曲聲響。他眼明手快,上前一把抓住陳巖就往回拽,已經來不及了———從巷道支護架上“咣當、咣當”,連續落下幾根坑木來,近旁的一根正好砸在陳巖頭上。只聽得他“嗷呦”叫了一聲,便栽倒在地。
五
人頭攢動的學院路商場,周明笙一眼就認出肖群群來了——這位仁兄比旁人高出半個腦袋,扣了頂狗皮帽子,棉軍大衣半敞著懷,外頭斜挎個軍用水壺。原本的書卷氣蕩然無存,完全蛻變成一個標準的東北“老坦兒”。
見到周明笙,群群劈頭蓋臉就來了一句:“你這個犢子!”周明笙覺得很接近魯北農村長輩對后生常說的一句疼愛話——你個生瓜蛋子!
兩人邊走邊聊,一塊來到陳巖住處。進門就看見陳巖倚在床頭上,脖子上打著石膏、纏著繃帶,兩人這才知道陳巖受傷了!
一旁的汪小年告訴他們:“這小子命大,巷道上方土層塌陷,把幾根坑木擠崩下來,有一根砸中他的脖梗子。就差半步,小命就沒了。”
陳巖笑道:“虧得小年揪得快,要不這回真玩完了。閻王爺瞅了瞅,看我還沒娶媳婦,硬是不收,提溜著脖領子給退回來了!”
群群板著臉一本正經地說:“你的名字起得好,巖字命硬,土坷垃坍方不頂用。”大伙兒一起笑了起來。
陳巖說:“今晚都住這兒,打地鋪。”
吃著小年從門頭溝捎來的豬頭肉和火燒,喝著大缸子沏的釅茶,哥兒幾個熱烈地談論起各自的讀書心得。周明笙還是頭回感受到知青們對理想的執著追求,他們志趣廣泛,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屠格涅夫的《羅亭》,再到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沙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以及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間》、柯切托夫的《落角》——書中人物的命運、情懷以及對未來的憧憬,竟然與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如此貼近和契合。
周明笙朦朧中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人文氣息和哲學精神——這是一條綿長、悠遠的心路,令他流連忘返。他們在這間小屋里爭論著,時而面紅耳赤、時而開懷大笑,全然不顧天色已過午夜。
小年看周明笙歲數小,很關照他,也愛逗他玩。睡前他給周明笙出了個謎語,謎面是:面朝東,打一個人名。周明笙半天沒猜出來,就睡著了。
第二天,他發現枕邊放著一張紙條,拿來一瞧,上面寫著幾個字:謎底:樸正熙(瓢正西)。
小年有個弟弟叫汪小博,進入青春期后狂熱寫作。小年有時會帶些小博的習作來陳巖宿舍,大伙輪流傳著看。讓周明笙印象深刻的是一個短篇小說,叫《歪脖子老等》……
劉三姐用山歌贊美勞動、贊美大自然、贊美愛情,悅耳動聽的歌聲與秀麗的桂林山水,完美地融為一體。三姐的歌美,人應當更美。對山歌時,三姐斗笠上罩著面紗,從未有人見到過她的容貌,包括情哥哥阿牛。對完山歌,她會到漓江邊上浣水,確信近旁沒有生靈時,才會撩開自己的面紗。
有一種水禽叫蒼鷺,常愛駐足河流的淺灘,伺機捕魚。蒼鷺對三姐的長相充滿好奇心,它把捕魚的耐性用在窺測三姐的容貌上,一等就是十幾個小時。
終于有一天,三姐款款而來,當她除去面紗的那一刻,蒼鷺看到了一張天地間最丑陋的臉,上面布滿膿包和雀斑,嚇得蒼鷺猛地轉過頭去,再也沒有扭回來。從此,蒼鷺有了一個綽號——歪脖子老等。
周明笙被小博荒誕、幽默的表現手法震驚了,從來沒見過誰這么講故事的。他是在譏諷當下的審美觀念,還是嘗試對傳統敘事方式的反叛?周明笙不得其解,他沒有能力分辨出各種不同的寫作技巧。
周明笙和群群在陳巖宿舍沒待幾天,陳巖的父親聽說兒子工傷的消息后,放心不下,硬是找了個機會來京辦事,“順便”看看兒子。這讓周明笙和群群有些“發毛”,為了不讓陳巖為難,群群和周明笙商議各自找關系到外頭“刷夜”。
夜晚對周明笙來說,綜合起來就四個字——“膽戰心驚”。
那個年代在北京沒家、沒戶口,自降三等。周明笙住的最多的地方是同學在工廠的單身宿舍,每回碰上“查戶口”,都會有一番較量。
那天晚上剛睡下,就有人來敲門,同學“老樂”示意周明笙鉆到床底下去。工人糾察隊進門后強行要搜查床下,“老樂”死活不讓,還發生了口角,差點兒打起來。
幸好蹲下察看的是周明笙的另一位同學“包子”,他用手電筒一掃,燈下黑的周明笙目光炯炯。“包子”假模假樣地端詳一番,掉頭對門口的同伴說:“床底下就一摞破紙盒子,走人!”
到了白天,周明笙碰到“包子”。他奚落周明笙:“你丫眼睛里充斥著狼性,有撲上來撕咬的沖動。為什么不早打招呼?這樣我可以提前通知你,預先轉移個地方。”
周明笙反諷道:“兜這些圈子干嘛?直接住你家去不就得了!”
遇到同學和同屋人都不上夜班,沒有空閑床位,周明笙就沒轍了,只好厚著臉皮去“蹭”群群的“關系”。白日里,兩人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里“窮逛”,晚上到群群的“插友”家混一宿。
群群貓在屯子里的炕頭上讀了不少書,在寒風中,他哆哆嗦嗦地向周明笙大談別林斯基和托爾斯泰。群群告訴周明笙:描寫故事情節要置身于所處的年代,用那時的語言、表達方式和洞察力去塑造作品,刻畫人物要細膩傳神——如神態、表情、舉足之間的情感,以此勾勒出獨特的人物形象。那年群群二十歲,才氣已鋒芒畢露。
哥兒幾個抱團取暖,一起度過嚴寒的冬天。
六
京城書市。盡管是春日,周明笙腦門子還是沁出汗了。此時他正與一個書販討價還價:“這些書打幾折?”
“都是正版書,新書八五折,年代較遠的打五折。你找什么書?”
“有汪小博的短篇小說集嗎?”
“有!正版五折。”
“好!來一本。”
周明笙跑遍書攤,專程來買汪小博寫的《歪脖子老等》。他發現在《汪小博文集》里有三卷短篇小說,他要找的描寫劉三姐的那篇,改頭換面叫《仙歌》了。
周明笙回到家中翻閱《仙歌》,感覺情節寫得又臭又長,讓他大失所望。他懷疑是否有人背地里把小說的內容改了!汪小博已是享譽文壇的知名作家,可惜英年早逝。
周明笙經歷數十載,對這篇小說的理解歷久彌新,也有了更深刻的解讀。他體會到:小博試圖告訴人們——也許在世人眼里,我的確很丑陋;但是“老等”這些俗禽,安知我的鴻鵠之志。我將用歌唱去贊美生活和愛情,并以此為樂,不再受世俗眼光的擺布。
隨后,周明笙好像記起了什么。不大一會兒工夫,他從家里的書柜取出一本舊相冊來,翻找到一張照片,仔細端詳起來:這是陳巖、肖群群、汪小年、汪小博和周明笙在頤和園知春亭前的合影,這群年輕人的風采——“恰同學少年”。
據說,“知春”二字源于宋代詩句“春江水暖鴨先知”。每年春天,昆明湖的解凍由此處始,故名知春亭——1978年陳巖和汪小年拔得京西地區的高考文科狀元和榜眼,再次成為同學;只不過是從北邊的一〇一中學,換到了南面的中國人民大學。礦工們為慶賀他倆燃放起煙火,絢麗多彩的煙花在礦區騰空而起——綻放、湮滅,再次躍升、怒放……
周明笙從回憶中緩過神來,他發現這張照片背后還有字跡,仔細一看,上面寫著幾個俊朗的鋼筆字——“你這個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