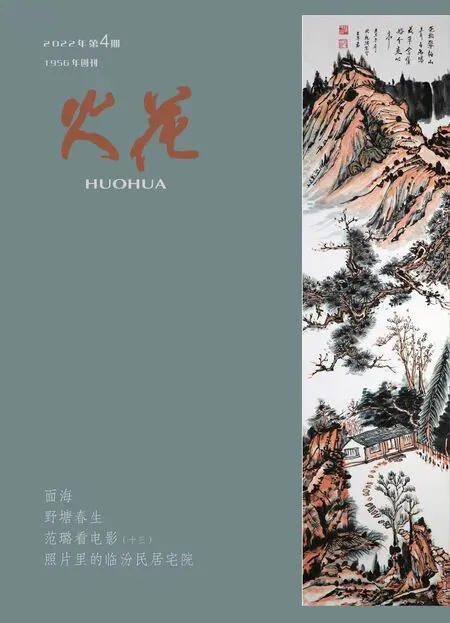雪事
高洪珍

北方的冬天,必定是有雪的。有雪的日子大多是有記憶的。
一
1978年家門前柳樹兒發芽,爺爺給我折一根柳枝做笛哨時,我忽然發現身材魁梧的爺爺直不起腰來了,整個身體跟一直塌陷的日子一樣,打開鍋蓋就是一鍋玉米碴子粥,稀稀拉拉一點精氣神也沒有。好在到了暮春,眼看著日子開始好起來,鍋里開始有了高高的白面饅頭,總算不用母親外出借米借面,日子緊巴可尚能過得去。母親在每次烀餅子的時候,就會在一圈金黃的餅子中間嵌上兩個白白胖胖的白面饅頭。那饅頭在蒸氣繚繞的朦朧中,像一對白白胖胖的娃娃,可愛又讓人食欲大振。每次掀鍋時,我都站在娘的身旁,恨不得一把抓來吃。娘把這對白白胖胖的饅頭,麻利地從鍋里提溜出來,放在一個干糧墊子里,晾好后,將皮剝去,掰成四塊,將其中一塊放進爺爺的手心里。我盯著爺爺將這四分之一的饅頭,掰成我指頭肚那樣大小放進嘴里,慢慢咀嚼。我嘴里的唾液跟著他下頜一動一動的白胡子在運動。之后,他閉著嘴,像是準備做一件大事一樣,使勁地往下咽。有時候饅頭像是一塊石頭堵住食道,咽不下吐不出,他背轉身子,我們裝作看不見,心揪得疼。
爺爺依舊跟往年一樣忙那些該忙的活兒。麥子該上糞了,該澆水了,該準備割麥子的家什兒了。找出掛在墻頭的鐮刀,找出去年剩下的草繩子。只是,爺爺氣力不足,割不動麥子了。爺爺的身子漸漸佝僂、瘦弱,但是,這場麥子,他是要在場的。
在生產隊那些年,哪場麥子不是他揚出的!那時候,他英武的樣子許多人都羨慕的,甚至在教育自家孩子時,都以學爺爺那樣把麥場揚成一彎甚至兩彎月亮才算好。打麥揚場,爺爺是可以左右開弓的。站在兩堆麥子中間,爺爺就像一位英勇無敵開弓射箭的將軍,斗志昂揚。每一堆麥子旁站著一名拿木锨的壯勞力,他們也是在眾人中挑選出來的精壯漢子。嚓,左邊的壯勞力已經把小麥上滿了锨,爺爺迅速將簸箕側斜給左邊,一送一接,爺爺順勢就將簸箕里的麥子隨風揚出左前方;緊接著,右邊壯漢的木锨上的小麥已經來到,爺爺的簸箕迅速側斜給右邊,又是一個天女散花般的飛揚,簸箕里的麥子迅速飛出右前方,又很秩序地穩穩落地,擺成一長溜。隨著左右不斷夾攻,那飛揚落地的麥子,彎成兩彎金黃的月亮。白花花的麥糠,已經規規矩矩飛到了另一邊。那時候的爺爺是莊稼漢里的巧把式。
屋后的小樹林里,有一畦菜地。一到夏天,草苗就比賽似的你追我趕地長,爺爺是喜歡這些草和苗的。他拿著馬扎,來到菜地,先是在地頭上坐一會兒,與這些草和苗說一會子話,就跟見了久違的老朋友一樣:“幾天不見,長這么高了。”言語中透著親切,也透著憂慮。爺爺費力地起身下到地里。他總是在蹲下身子時,順手將馬扎往身后一塞,馬扎的一對前腳著地,他半斜著身子靠著。這個曾像山一樣的漢子,如今卻也只能土堆樣堆在地上了。
爺爺的身子就像被抽離了筋骨,軟塌塌的,站立不穩,蹲下起不來。爺爺不能去地里干活,就在家幫母親納鞋底,做線穗子,看孩子。鋼鐵一樣的漢子,變得沉默寡言了。他在懷疑自己到底怎么了?強壯結實的身體,怎么就突然沒了力氣,沒了精神?曾有幾次,我放學回家,看到爺爺坐在院子里發呆,他是想起了什么?
那雙駱駝鞍的靴子仿佛墜著他的身體,搖搖晃晃走不動。
冬天爺爺最常穿的就是那雙駱駝鞍靴子。千層底,黑粗布面,上面兩道硬邦邦的箍,穿在腳上,有些沉重。下雪時候,爺爺總是穿著這雙駱駝鞍的靴子,背上糞筐,去雪地里撿還冒著熱氣的牛糞,咔嚓咔嚓的腳步聲凝重而親切。如今,爺爺的腳步越來越沒有氣力,走起路來有些飄,過去的強壯游離了他,只剩下虛弱的身子。爺爺時常望著墻角的糞筐出神,他再也不會與它一起去砍柴、收糧,去田間地頭與那些放牛人一起聊天了。
1979年正月初二的夜里,大雪紛飛,爺爺躺在炕頭上,奄奄一息。簌簌飄落的雪花,像被天空看不見的一雙大手拋灑著,仿佛要掩埋什么,又像要帶走什么。年幼的我們都有些害怕,偎在一起,說不出害怕什么,卻又真得從內心里害怕著什么。雪花無聲地飄落,把夜拉得很長很黑。就在我們又害怕又要睡下去的時候,爺爺睜開了雙眼,看看身邊年幼的我們,看了看父親,他用細弱的聲音說:“我——對——不起——你——娘——”說完,眼角滾下一大滴淚水。爺爺的氣息漸漸微弱,漸漸消失。在大雪之夜,走完了他八十三歲的人生之路。
一場雪的到來,仿佛是為了完成一種儀式,告別塵世,或者回歸泥土。
二
爺爺去世后,不常來我家的奶奶偶爾會過來幫母親照料小妹,卻很少在我家吃飯。奶奶個頭不高,微胖的臉龐上總泛著紅暈。我以為那是長久風吹日曬的緣故,后來才知道那是血壓高的一個明顯標志。她捻動那雙尖尖的小腳,搖晃著微胖的身子,慢條斯理的樣子。當然,那雙小腳換誰也快不了多少。稀疏的白發,在腦后挽成一個發髻,跟她微胖的臉龐有些不相稱。
奶奶總穿著那件藍色粗布大襟襖,黑粗布大腰褲子。常年用著一口大鍋,做著一個人的飯。飯總是糊在鍋底上那么一點點,跟漿糊似的,看上去連那口鍋都喂不飽的樣子。奶奶也總是會把鍋底上的那些糊了的用鏟子鏟下來,放在那只裂了好幾道紋的藍花粗瓷大碗里,一點不剩地吃下去。她喜歡吃野菜團子,比如:春天的曲曲菜、福子苗、臘子菜、薺菜……做的菜團子里面菜多面少,面只做菜的粘合劑而已。菜粘粥稀稀拉拉,看上去也僅有野菜。每頓飯都只有一樣兒咸菜,就是自己刮來鹽堿土,淋成咸水腌制的蘿卜或者菜葉子,吃起來又苦又咸。爺爺活著的時候,逢年過節,母親打發我們兄妹去叫奶奶過來一起吃飯,她是定不會過來的。母親就只好把盛好的飯或包好的餃子讓我送過去。奶奶極少包餃子,我吃過奶奶包的餃子,大長大長的,有點像是扁食,里面的餡兒是不會放肉的,油也少得可憐,奶奶卻吃得津津有味。
奶奶一個人睡一個很大的炕,她仿佛不知道什么是寂寞。一個大火炕,她睡在最北炕頭那邊,炕南邊放一輛瘸了腿的破舊紡車。一年四季,奶奶都會讓紡車唱出自己的歌。那輛紡車應該算是她的伙伴,也是她房子里最值錢的東西。火炕和鍋臺之間壘起一個小燈臺,上面放著一盞小煤油燈。如豆的煤油燈光,也只有在天徹底黑下來才點起。有月光的日子最好,白白的月光,灑在屋子中央,離奶奶的鍋臺不過尺把遠,奶奶就借著這一地的白月光吃飯、睡覺。月光透過窗欞,鋪在炕上,照亮奶奶寂寞的夜晚。直到一次骨折,奶奶才搬來與我們同住。
三
奶奶晚年享受著天倫之樂,享受著從來沒有過的幸福日子。天天白面饅頭,頓頓有炒熟的青菜,不再天天吃自己腌制的咸蘿卜了。過去盼望的一切都在自己不再奢望的時候到來。奶奶心中仿佛想到了什么。后來,在奶奶的斷斷續續的回憶里,我知道了有關爺爺奶奶的故事。
十七歲的花季少年,英俊瀟灑,黑亮的眼睛里透著睿智。這個老師學生都喜歡的年輕后生,寫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盤,不善言語卻聰明好學。人們預測著這個少年的未來肯定是個文化人,吃國家飯,是公家的人。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就在少年春風得意的時候,突然得了一場叫天花的病,發燒,無力,渾身長滿皰疹,痛苦的呻吟日夜煎熬著父母的心。有病亂投醫,做父親的不知從哪里聽來的土方子,用鹽巴搓皰疹,給孩子消毒。不成想,皰疹遇鹽反而害了孩子,少年中毒身亡。這少年就是我大爺爺的兒子,也就是我的伯伯。伯伯的死,猶如晴天霹靂,大爺爺滿心寄托的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
在魯北農村,大部分人存在著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有兒子的家庭,腰桿子特別硬;有兒子,就能延續香火;有兒子,就不怕別人欺負;有兒子,就能夠在祖宗面前好交代。他們信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失子之痛,讓大爺爺在村人們的唏噓哀嘆聲里,抬不起頭來。二爺爺也就是我的親爺爺心疼自己的哥哥,害怕大爺爺從此一蹶不振,毀了自己,就讓兒子過去陪伴大爺爺。
父親那時候也就五歲。奶奶只有這一個兒子,她心里一百個不愿意,礙于大爺爺剛剛喪子,奶奶也不好當面說什么。大爺爺天天把孩子帶在身邊,害怕一不小心會把孩子弄丟。陪孩子也成了大爺爺一天到晚的精神寄托,每天除了干活,就是逗孩子玩兒,一個鋼鐵一樣的漢子,在孩子面前溫柔似水。在孩子的陪伴下,大爺爺慢慢走出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時光。鄰居們也發現,大爺爺再也離不開孩子。再忙再累,只要見到孩子,大爺爺一向嚴肅的臉上充滿笑意,眼睛里閃爍著慈愛與溫和的光。
奶奶想把兒子要回到身邊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她看見兒子每天都很開心,并不十分想念她。隔了一條胡同,近在咫尺的娘兒倆并不經常見,即使有時間兒子跑回身邊,也只是拿了吃的就走。孩子的世界里只有溫暖的愛,沒有一絲芥蒂。奶奶不能說,也無法跟兒子說什么,本來窮苦的日子,更多了一份沒有兒子陪伴的苦。她跟爺爺天天鬧別扭,不理爺爺。爺爺是個讀書人,生性溫和,沒脾氣,又非常敬重自己的大哥,怎么好再張口把孩子要回來?爺爺忍受著奶奶時不時地數落,也只是默不作聲做自己該做的事。奶奶對大爺爺的態度越來越冷淡,甚至在兒子結婚一事上,奶奶用拿不出錢跟大爺爺置氣。僵到份上,誰也不讓步了,也就真把兒子留在了大爺爺身邊。
人大多都是認命的,更何況一個女人。再執拗,也拗不過命運的安排;再執拗,也逃不過大饑荒的那些苦日子。吃了上頓沒下頓,一個好幾百口人的村子,死的死,逃的逃,走不了的,大多是餓在炕上爬不起來,在院子里出不了門。死了的,尸首無人收,活著的連哭也不哭了,就把死的當睡著了吧。也就在那一年,食量大的二爺爺(我的親爺爺)餓死了。
作為一個女人,兒子送與他人,丈夫也不在人世,日子該怎么打發?最初的日子,奶奶是怎么熬過來的,她從不說與他人。熱鬧的家她不羨慕,凄冷的夜她獨自熬煎。
四
一腔愁怨無處訴,萬分感慨心頭雪。
1993年十月的那場雪來得太早,是人們所沒有預料到的。棉花還站在地里,上面還開著沒有開完的花,冬蘿卜還長著它滿頭的綠纓子,玉米還齊刷刷地列隊般站在地里,天空就集聚了仿佛好幾個世紀的云,厚得吹不開,掀不動,陰沉得很。后來淅淅瀝瀝飄起了雨,一下就是半月有余。連綿的秋雨,像扯不斷的思緒,分不清白天黑夜,分不清天地人間。十月初,忽然來了一股冷空氣,把先前的秋雨一下子凍了個趔趄。嘩啦嘩啦的雨,仿佛加了消音器,瞬時沒了聲音。雨夾著雪花,如生出翅膀的白蝴蝶在天地間狂飛亂舞。房頂上,樹枝上,溝沿上,雪花所到之處,都留下隱約的白。
踩著泥濘,我天天往返于家和學校。那時候我已經懷孕待產,每天早上捎好一天的飯菜,去二里外的小學去上班。雨雪泥濘掩蓋了原來的羊腸小路,我只好循著兩個村子之間的鹽堿地茬行走。那些鹽堿地邊上長著絆子草的地方還是能成步的,只是低洼處積水過多的地方,泡了數天,像經過發酵的面,看上去很光滑,一腳踩下去就拔不出來。那時候我的身子重得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大約二里來地,最少也得二十分鐘,甚至半個多小時。
雨雪天路上沒有行人,只有我在天地之間踽踽獨行。每天回家晚了,奶奶總會囑咐母親到大門外接我,怕我出意外。那個時候全村也沒有一部電話,即使真有意外,也不會像現在一個電話就能聯系到家人。
十月初六傍晚,母親搟了我最喜歡吃的面條。奶奶也喝得腦門上汗涔涔的。雨雪天,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喝上一碗熗鍋面,胃里舒坦心里也舒坦。那種溫暖,一輩子都忘不掉。早來的雪是有柔情的,無聲無息,落地為泥,直到天黑,南墻下的積雪才有了些白。
早上還沒起床,就聽見父親掃雪的聲音。我趕緊起床去看雪。打開門,一種特別刺眼的白,讓我忽然有些眩暈。厚厚的積雪鋪了一地,樹上房子上像一夜之間被畫上去的,一塵不染。這時候,父親小聲告訴我,奶奶病了。不知道是雪的白還是聽到奶奶生病的消息,我一下子沒回過神,再一激靈,我趕緊邁步到奶奶跟前,奶奶微閉雙眼,口中不時地溢出血來。那鮮紅的血,令我又是一陣眩暈。大雪無聲,奶奶亦不出聲。
我天真地以為,或許在雪停之后奶奶就會好起來。我心里記掛著學校那些孩子們,也沒有太多猶豫,就告別了奶奶,踏上了去學校的泥濘的路。上了一天的課,我的心始終忐忑不安,擔心奶奶能不能扛過這場風雪。北風不停地刮著片片雪花,我沿著雪花飛來的方向望去,茫茫的雪花那邊就是我的村莊我的家,還有我生病的奶奶。回家的路,我步履蹣跚,卻心急如焚。邁進家門,人們進進出出忙碌著給奶奶做火燒,做打狗棍,做放米的罐子。奶奶安靜地躺在靈床上,戴上了冬天最常戴的黑平絨遮耳帽,睡著了一般,面色肅靜。她不再惦記我,惦記我即將出生的孩子了。奶奶重回孤獨,她不害怕。起靈的時刻,大片雪花如扯不斷的棉絮,鋪天蓋地飄落下來。是靈幡,是呼喚,還是爺爺的絮語?再次相見,他們是否不再提及當年?
奶奶下葬的第二天,天大晴,我的兒子降生。生命的起承轉合,在一場雪中完成。
來世間化雪為泥是雪的宿命。也總有那么一場雪下在心頭,下在記憶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