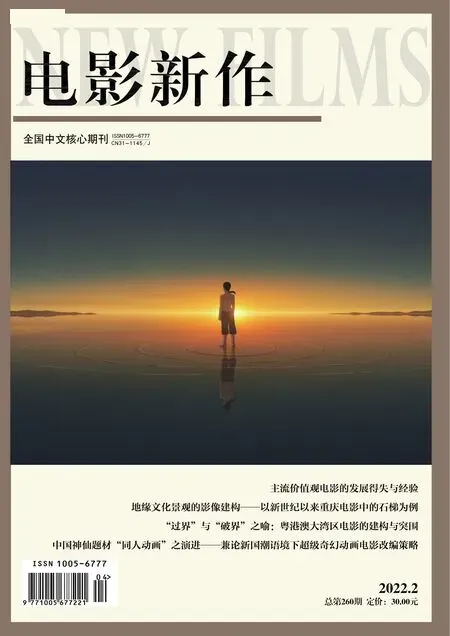“現(xiàn)代性”的雙向書寫
——新世紀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的文化互滲
李 淼 周澤民
新世紀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進程的持續(xù)推進,中國社會城鎮(zhèn)化進程逐漸加快。在社會城鎮(zhèn)化所帶來的強力沖擊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在接受現(xiàn)代性思維模式的同時,也遭遇了現(xiàn)代化所帶來的傳統(tǒng)民族文化生活的裂變。人們在融入現(xiàn)代城市經(jīng)濟圈的同時,也面臨著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的雙向選擇問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傳統(tǒng)村寨的“空心化”現(xiàn)象,讓此種選擇更具鮮明的矛盾性,一方面,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多數(shù)青年長期在“流動的現(xiàn)代性”城市生活中以“游牧者”的身份處于流動生活狀態(tài),此種生活狀態(tài)對原本相對穩(wěn)定的民族文化帶來直接影響。再者,城市便捷的生活條件、優(yōu)越的教育條件以及相對較好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吸引著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村寨中的“現(xiàn)代游牧者”在城市與鄉(xiāng)村之中作出“向城而生”的選擇。他們所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生活所帶來的集體焦慮;另一方面,“邊陲視角”下的傳統(tǒng)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成為現(xiàn)代人的旅游圣地,成為浪漫風(fēng)情的想象異域,也成為影視作品詩意化表達的對象,這些也讓傳統(tǒng)村寨與其他地區(qū)的文化屏障逐漸消解,為文化的多樣性發(fā)展提供了可能。
如果我們把民族文化身份看作是一種具有流動性的文化認同關(guān)系,在新世紀以來的影視創(chuàng)作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將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民族特性以及地域文化特征納入一個對等于漢族及其文化的影像的漸進過程。進入新世紀以來,“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電影認同是以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性危機為前提語境的。”例如,《婼瑪?shù)氖邭q》《花腰新娘》《季風(fēng)中的馬》《滾拉拉的槍》《碧羅雪山》《塔洛》《米花之味》《阿拉姜色》等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所展現(xiàn)的現(xiàn)代性對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滲透作用日益顯著,“一些影片開始冷靜反思現(xiàn)代性……用樸實、沉靜的鏡頭凝視著邊疆少數(shù)民族人民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困惑與選擇”。但仔細剖析,筆者發(fā)現(xiàn),一些影片中所展現(xiàn)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景觀同樣影響著民族地區(qū)外的文化,在一種流動性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文化互滲的現(xiàn)象尤為突出,這恰好打破了少數(shù)民族文化長期以來處于“被看”的狀態(tài)。“現(xiàn)代游牧”的生活方式、“向城而生”的時代選擇、“邊陲鄉(xiāng)土”的詩意回歸都讓少數(shù)民族文化在與其他文化的互滲中,逐步消解了單一性的集體焦慮,并確立了國家話語體系中的多元文化互存互依、共同發(fā)展的格局。
一、現(xiàn)代游牧:個體符號與異域溝通
在人口大流動時代,地處偏遠的少數(shù)民族群眾頻繁往返于城市與村寨之中,其生活和心理狀態(tài)處于動態(tài)的變化之中。他們逐漸與傳統(tǒng)的群居方式區(qū)分開來,村落中的個體自我意識逐漸強化且選擇外出漂泊,此種“游牧生活”具有現(xiàn)代性的明顯特征。可以說,它是個人的、易變的。
“處于這種流動之中,社會成員一改以往定居生活,搖身一變成為游牧者。”“游牧者”漂浮的生活方式突破了傳統(tǒng)的“群居游牧”,以一種“不確定性”讓少數(shù)民族群眾變?yōu)橛问幵诔鞘信c村寨維度之間的文化個體符號,成為民族地區(qū)與非民族地區(qū)文化交流的身體介質(zhì),但此種介質(zhì)具有身份認同的迷茫性。在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創(chuàng)作者逐漸站在現(xiàn)代性的對立面,以冷靜的態(tài)度反思傳統(tǒng)文化本真地位,但整體而言,這種本真地位正遭受來自“融不進去的城市空間”和“回不去的鄉(xiāng)村空間”的影響而變得更為多義。影片中個體的游牧方式則加劇了文化身份的復(fù)雜性,這種復(fù)雜性一方面受到外族群視角的影響,從而建立起一條影響本族群的文化感染路徑;一方面又由自身民族文化影響外民族地區(qū)的內(nèi)心世界,文化藉由孤獨的“游牧者”形成一種互滲現(xiàn)象。
《婼瑪?shù)氖邭q》中,生活在云南紅河深處的哈尼族小姑娘婼瑪與同村外出到城市打工的洛霞之間的對話將洛霞“游牧者”的身份確立起來:
洛霞:“電梯可不是飛機。它就像是一會兒升起來,一會兒又落下去的大箱子。靠的是電。”“阿慶對我可好了,我第一次上昆明,他就帶我去坐觀光電梯。城市可漂亮了,高樓大廈像山里的森林。”
通過洛霞對城市電梯的描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為在城市中以“游牧者”身份生活的洛霞顯然對游蕩在城市的生活有一種由內(nèi)心而散發(fā)出的自豪感,這也引起從未外出過的婼瑪對城市生活的無限向往,所以“電梯”成為少女婼瑪內(nèi)心對城市現(xiàn)代文化憧憬的符號。盡管婼瑪?shù)碾娞輭舨⑽磳崿F(xiàn),但藉由洛霞對于外面世界的描述,形成了婼瑪對未知城市現(xiàn)代化文明的美好想象;《花腰新娘》中,阿聰作為向外的“游牧者”在鳳美和阿龍的婚禮上,送給他們一臺彩色電視機作為結(jié)婚禮物。電視機這一象征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物,經(jīng)由民族地區(qū)的“游牧者”帶回該地區(qū),成為傳統(tǒng)村寨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交流的跨時空紐帶;《俄瑪之子》中,父親為阿水學(xué)習(xí)電影放映這一現(xiàn)代文明的活動則將父愛的主題渲染上現(xiàn)代性色彩,更有一種父愛如山亙古不變的永恒意味;《碧羅雪山》中的阿達則是通過“游牧”的方式離開怒江深山祖輩居住的地方,去往城市賺取能夠迎娶吉妮的彩禮。“游牧”生活所帶來的物質(zhì)享受讓阿達在村里風(fēng)光一時,但他在精神上卻與傳統(tǒng)傈僳人形成了矛盾。現(xiàn)代文明對于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挑戰(zhàn)與沖擊在男主角迪阿魯對著遠方的山群呼喊——“阿爸,阿哥,回來吧”——的無助中顯得更具有代表性。父親和哥哥在外面的世界“游牧”而杳無音信。現(xiàn)代文明所帶來“情與法”的壓力則讓迪阿魯幾近崩潰,這種沖突性讓傳統(tǒng)村寨中的群體生活籠罩上一種無所適從的壓抑氛圍;《塔洛》中的揚措則是另一種“心理游牧者”的代表。作為一名理發(fā)師,揚措是這個藏區(qū)小城鎮(zhèn)和現(xiàn)代社會最為接軌的潮流代表。她心中向往外面更豐富多彩的世界,卻桎梏于物質(zhì)的窘迫。“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雖然在地域的、特殊的環(huán)境里受到了全球化的意象的沖擊,但日常生活形態(tài)還是地域性的東西。”所以,揚措即使作為小鎮(zhèn)潮流的代表,帶著塔洛進入KTV、藏搖音樂會等場所,所唱的藏歌、身上所佩戴的民族飾品仍是一種在地性的表現(xiàn)。揚措暗示塔洛帶她離開閉塞的小地方時,表現(xiàn)出她作為“心理游牧者”的虛弱。這種人物內(nèi)心的流動際遇更具有感染力,以一種共情的方式引導(dǎo)塔洛對于“昆明”“北京”“紐約”等城市現(xiàn)代文明的想象。
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個體在現(xiàn)代文明中的游牧者身份對于傳統(tǒng)村寨生活的沖擊帶有強烈的內(nèi)視角,他們一方面是傳統(tǒng)文化的接受者與傳承者,一方面又對村寨外的現(xiàn)代文化欣然接受,兩種文化的交織帶來的民族身份認同“實際上就從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轉(zhuǎn)變?yōu)榭梢越?gòu)的多重身份和多重文化認同”。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的“游牧者”試圖以民族文化持有者身份在城市中建立起由馬費索利提出的“后現(xiàn)代部落”,以此突破被地域空間所限制的文化交流。
新世紀以來的蒙古族題材電影體現(xiàn)出創(chuàng)作者強烈的自省意識。草原環(huán)境惡化與城鎮(zhèn)化的影響讓牧民們被迫由鄉(xiāng)村轉(zhuǎn)入城市,并由此帶來了自身文化與身份認同的焦慮。《季風(fēng)中的馬》把鏡頭對準了沙漠化越來越嚴重的草原上的普通牧民烏日根。他視草原為生命。畢力格則像烏日根一樣具有蒙古精神。由草原轉(zhuǎn)入城市后,他的“草原游牧”情結(jié)并沒有被現(xiàn)代化的城市侵蝕。相反,他在自己的畫室擺滿了成吉思汗的畫像,內(nèi)心深處仍渴望民族文化的回歸。成吉思汗的畫像寄托了他對草原的思念,折射出他試圖在城市中建立起蒙古精神的信念;《長調(diào)》中的其其格在城市的家中用蒙古族掛毯裝飾室內(nèi),常用的鋼琴上也擺放了駱駝布偶,這些道具細節(jié)無不突顯出其其格作為從草原上走出來的音樂家對于草原文化的尋根。最終,她為了使“長調(diào)”能夠在更廣闊的現(xiàn)代城市社會傳播,在返回家鄉(xiāng)后又來到城市尋找更大的舞臺,以此傳承蒙古族的優(yōu)秀文化。這種在城鄉(xiāng)異域中往返的“游牧”生活,使其其格于現(xiàn)代化潮流中踐行著建立文化社區(qū)的夢想。
由此可見,無論“游牧者”對內(nèi)還是在外進行文化傳播實踐,他們都成為溝通“異域”的文化符號,并在宣揚城市現(xiàn)代文明和傳承民族文化傳統(tǒng)兩個方面起到了橋梁作用。這一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創(chuàng)作大多有意識地融入了對現(xiàn)代性的思考,在多元視角中既體現(xiàn)出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和復(fù)雜性,也展現(xiàn)出對現(xiàn)代化進程的反思性和啟示性。
二、城市想象:社會圖景與文化反思
“游牧者”在城鄉(xiāng)之間游走,以自身作為媒介符號,進行現(xiàn)代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現(xiàn)代化進程正改變著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心理,同時為身處邊疆的少數(shù)族群提供了一種“城市想象”。美國學(xué)者阿爾君·阿帕杜萊在《普遍的現(xiàn)代性》中認為,“‘想象’作為全球化時代流行的、社會的和群體的一種現(xiàn)實,對其作用的分析可使我們認識它的雙向性。一方面,在這種‘想象’中以及通過這種‘想象’,現(xiàn)代公民被國家、市場以及其他強有力的勢力所規(guī)范和控制。而另一方面,不同類型的群體模式以及對群體生活的新設(shè)計也因這種‘想象’的作用而紛紛出現(xiàn)。”地域的差異化因“游牧者”的流動而進行著差異混合,從而產(chǎn)生一種混合狀態(tài)的場域想象。這種想象在新世紀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集中地表現(xiàn)為一種對現(xiàn)代化城市的向往,從而導(dǎo)致群體性的社會文化認同心理的變化,由此也建立起對本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性反思機制。
《婼瑪?shù)氖邭q》以十七歲花季少女婼瑪?shù)囊暯墙⑵饘Τ鞘猩畹南胂蟆,F(xiàn)代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沖突和碰撞,從這個少女的心理變化中體現(xiàn)出來,當(dāng)婼瑪拿出好友洛霞皮包里在昆明拍的照片——洛霞與男友阿慶在觀光電梯里,令婼瑪流露出羨慕與憧憬。所以,當(dāng)城市來的阿明為婼瑪拍照以及許諾婼瑪帶她去昆明坐電梯時,婼瑪表現(xiàn)出了青春的第一次悸動。當(dāng)婼瑪聽著隨身聽而忽略奶奶的呼喚時,無疑突出了現(xiàn)代流行文化對傳統(tǒng)鄉(xiāng)村生活的影響。城市觀光電梯、隨身聽以及照相機等現(xiàn)代工業(yè)產(chǎn)品勾勒出婼瑪對城市生活的無限想象,這種物質(zhì)層面的偏差是誘導(dǎo)婼瑪向往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俄瑪之子》中,阿水因為對電影這一現(xiàn)代藝術(shù)形式的執(zhí)著而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期待,堅定的電影夢想成為他遠走他鄉(xiāng)的重要原因。父親最后那句:“阿水,走上路就別回頭”,是對阿水走出大山寄寓美好未來的期望。與婼瑪相比,阿水無疑是幸運的。婼瑪?shù)接捌Y(jié)束時也沒能離開哀牢山,坐電梯的夢想也沒能實現(xiàn),并“再也不去省城了”。阿水則被劇組選中,在追尋夢想的路上越走越遠。《塔洛》中,塔洛在城鎮(zhèn)與揚措相遇,當(dāng)他遭遇愛情騙局時,對更廣闊的外部世界充滿一種鏡花水月般的想象。對塔洛而言,揚措是外面世界魅力女性對男性的誘惑。及時享樂的揚措與塔洛的相識則帶有一種“游牧”之外精神空洞的焦慮。可悲的是,揚措的欺騙讓塔洛原本寧靜平和的精神世界變得空虛。塔洛的失落反映出現(xiàn)代性導(dǎo)致的人與人之間感情紐帶易碎易斷的特征。與塔洛不同的是,《米花之味》中的母親葉喃對城市的向往則是源于擔(dān)憂女兒喃杭的教育問題。城市較好的教育環(huán)境與資源條件讓長期以“游牧者”身份在城市漂泊的葉喃對子女的教育充滿城市向往與想象。
可見,在現(xiàn)代性視域下,新世紀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的身份認同是全方位的。少男阿水和少女婼瑪對外面世界的憧憬想象停留在都市文化的物質(zhì)層面,而青年的塔洛和葉喃對城市的向往則有了更為深層的指向,但影片中這些日常生活的想象性書寫,卻大多沒能成為現(xiàn)實,有的卻是對現(xiàn)代性的深刻反思。正如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所說:“他鄉(xiāng)是一面負向的鏡子,旅人認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屬于他的,卻發(fā)現(xiàn)那龐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擁有,也不永遠不會擁有的。”如果說以上這些影視形象是以一種積極的姿態(tài)去迎合他鄉(xiāng)的想象,而在另一些影片中則表現(xiàn)出“向城而生”的困惑與焦慮。可見,他鄉(xiāng)成為一種與之相悖的想象。

圖1.電影《米花之味》劇照
《碧羅雪山》中,傈僳族人民不愿意離開世代居住的山林,但現(xiàn)代生活不斷沖擊著這片原始森林。吉妮的哥哥偷盜紅豆杉樹皮被抓、迪阿魯?shù)母赣H和哥哥常年在外而不歸家、國家生態(tài)保護政策使村民遭受到熊的威脅,這些因素最終在吉妮以身飼熊后被雜糅成當(dāng)?shù)乩圩宕迕裣律綒w村的重要伏筆。迪阿魯為代表的傈僳族居民的精神壓抑“在匯入現(xiàn)代化進程的當(dāng)代中國民族地區(qū)有典型的文化意義”。傳統(tǒng)的少數(shù)民族山民因現(xiàn)代化進程而不得不搬離世代繁衍生息的原始山林,民族信仰在多重文化擠壓中成為精神上的困惑與焦慮。在現(xiàn)代生活的沖擊下,《季風(fēng)中的馬》中的烏日根一家因為草原沙化,導(dǎo)致羊群數(shù)量銳減,家庭經(jīng)濟陷入困局;兒子的教育費用成為壓在烏日根心上的石頭;即使他不愿離開草原去往城市,最終還是妥協(xié)了,主動與兒子退出草原到城市生活。烏日根的生存際遇正是當(dāng)代草原上的少數(shù)民族群眾生活的真實寫照。影片結(jié)尾,烏日根留下白馬,走向城市是則對當(dāng)下草原文化在現(xiàn)代性中的宿命隱喻。《德吉德》中,因丈夫生病,德吉德不得不變賣羊群,拖家?guī)Э谌コ鞘薪o丈夫治病。德吉德不愿離開草原的人生信條也被現(xiàn)實的困境所打破。對于生命的珍惜讓德吉德在人和羊都吃不飽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讓小羊和弟弟一起吃母乳的選擇。所以,當(dāng)丈夫生病后,她能夠做出一家人去往城市的抉擇。在這些影片中,城市生活不再是美好的憧憬,而是少數(shù)民族群眾被迫作出的艱難選擇。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現(xiàn)代性復(fù)雜的一面,也反襯出現(xiàn)代社會圖景的多面性。
無論是積極迎接城市現(xiàn)代生活,還是被迫選擇離鄉(xiāng)入城,城市景觀在少數(shù)民族影像中都成為一種集體景觀想象。現(xiàn)代文明帶來的既是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也是多元文化的混合認同,民族文化在“向城而生”的焦慮情緒中不斷碰撞并融合,形成兼具多重性和復(fù)雜性的文化表達。
三、鄉(xiāng)土回歸:邊陲美學(xué)與詩意表達
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過去常常在電影中被幻化為一種帶有神秘感且頗具吸引力的邊陲風(fēng)情,常常成為“外來人逃避現(xiàn)實矛盾、現(xiàn)代焦慮的療救之地”。伴隨流動的現(xiàn)代游牧生活而來,新世紀的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逐步“擺脫了單純展示地理景觀和自然風(fēng)光的敘事模式,而是深入到了自然環(huán)境與人物日常生活的關(guān)系內(nèi)部”。通過影像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化進程對少數(shù)民族鄉(xiāng)土生活的深刻影響,“游牧者”的身份在地域雙向選擇中實現(xiàn)了城市與鄉(xiāng)土之間的空間跨越,民族文化的融合性和獨特性則在對邊陲的寫實風(fēng)格中融入了詩意表達。
《婼瑪?shù)氖邭q》通過塑造阿明這個外來的“游牧者”,一方面連接起婼瑪與外部的世界,另一方面婼瑪所居住的哈尼族地區(qū)也成為阿明追求攝影夢想的詩意之地。他逃離厭倦了的城市生活,企圖在邊陲小鎮(zhèn)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正是通過不斷融入婼瑪?shù)纳钪校艑ψ陨碛辛烁畹睦斫狻S捌Y(jié)尾,他寄給婼瑪?shù)哪菑埧窃谔萏镞叺恼掌瑹o不流露出對鄉(xiāng)土回歸的渴望。《這兒是香格里拉》中,痛失愛子的中國臺灣母親季玲尋訪圣山后,重新認識了生命的意義。在藏族小孩的幫助下,她解開心結(jié),并重返家庭。《阿佤山》中的楊總在佤山找尋紅毛樹時,邂逅了初戀情人,重溫純真美好。《臨滄的誘惑》中,錢多多由一個網(wǎng)癮少年被佤族人民的淳樸感召,重新認識自我與找尋人生意義。《一點就到家》中,三個在都市生活失敗而歸的青年,在云南鄉(xiāng)土生活中重拾人生目標和信心,并通過奮斗取得成功……這些影片無不將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以一種帶有詩意表達的浪漫敘事,通過“他者”的邊陲想象塑造為外來者返璞歸真、回歸本心的鄉(xiāng)土圣地。
外來的“游牧者”大都以旁觀者的視角進行“鄉(xiāng)土想象”。邊陲鄉(xiāng)土則成為他們詩意表達的寄托之地。這種“田園詩意”的表達大多呈現(xiàn)為對鄉(xiāng)土生活的文化體驗,具有一種“他者”敘述的民族文化的多重認同。而作為內(nèi)部民族“游牧者”的自我敘述則表現(xiàn)為對社會大流動背景下的鄉(xiāng)土回歸的主題刻畫,呈現(xiàn)出極為明顯的文化差異化特征。
《長調(diào)》以藝術(shù)家其其格回歸草原為主題展開對現(xiàn)代性的思考。其其格作為一名長期生活在“他鄉(xiāng)”的長調(diào)藝術(shù)家,民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讓她在丈夫遭遇車禍后立馬回歸鄉(xiāng)土,以尋根的視角審視民族文化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危機與挑戰(zhàn)。在商業(yè)演出中,其其格的突然“失聲”,“與其說她是被迫失語,不如將其看作是一種身份焦慮對現(xiàn)代性的質(zhì)疑”。回到家鄉(xiāng)草原時的“復(fù)聲”,猶如新生一般,其其格感悟到回歸生命力。在其其格“失聲”與“復(fù)聲”的二次敘事中,在反思現(xiàn)代化語境下,影片展現(xiàn)了少數(shù)民族鄉(xiāng)土文化的艱難境遇,并由此讓主人公主動承擔(dān)起傳承長調(diào)的責(zé)任與使命。《米花之味》塑造的是一位入城“游牧”多年的傣族母親回到家鄉(xiāng),與女兒關(guān)系的不和諧到彼此理解,最后完成身份認同的自我救贖過程。葉喃作為大流動背景下入城務(wù)工的青年代表,常年將自己的孩子喃杭交給父親撫養(yǎng),從而使母女關(guān)系陷入陌生而僵持的局面。影片以母女二人為小伙伴喃湘露祈福為切入點,通過葉喃與喃杭從疏離到和解的心靈之旅,完成了葉楠回歸自我族群身份認同的信仰之旅。影片結(jié)尾,母女二人在山中以舞祭佛,為村寨祈福的場景,導(dǎo)演采用詩意化的鏡頭和開放式的結(jié)局,用文化儀式的展演體現(xiàn)了“游牧歸鄉(xiāng)”的文化認同。《滾拉拉的槍》中,賈古旺以剃掉象征自己本民族身份的戶棍,試圖迎合并融入現(xiàn)代城市中,象征現(xiàn)代文明的西裝并沒有讓他完成身份轉(zhuǎn)換,反而成為一種枷鎖,讓他迷失在城市中。最終,文化身份的缺失讓賈古旺折返鄉(xiāng)土,卻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賈古旺所代表的民族地區(qū)文化的不自信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表現(xiàn)出的精神認同的缺失成為當(dāng)下影視表達的重要現(xiàn)象,仍賦予邊陲之地一種悲愴地詩意表達。

圖2.電影《婼瑪?shù)氖邭q》劇照
結(jié)語
正如霍米·巴巴所言:“民族與文化現(xiàn)代性的跨界游離有密切的關(guān)系。”在不斷變動發(fā)展的中國城鄉(xiāng)社會背景下,少數(shù)族群通過自身的文化認同重新思考自我/他者,邊地/中心之間的關(guān)系,以此尋求與占主導(dǎo)地位的多數(shù)話語的對話。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創(chuàng)作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霍米·巴巴的這種“少數(shù)話語”策略。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一批以特定民族的族群記憶為中心,并呈現(xiàn)出相當(dāng)明確的文化自覺的電影作品”。這些影片通過不同的故事,塑造了迥異于前代的少數(shù)民族形象,并通過這些形象試圖建構(gòu)具有多重文化認同的族群身份。外部視角對邊陲鄉(xiāng)土的想象性敘述與內(nèi)部視角對故鄉(xiāng)記憶的迷戀與回歸,共同呈現(xiàn)出面對獨特的中國社會文化語境時民族身份認同的復(fù)雜性與多樣性。在這背后,是有關(guān)“流動的現(xiàn)代性”的思考與審視。
無論是“他者”的想象,還是“自我”的回歸,新世紀以來的少數(shù)民族影像成為一面反映現(xiàn)代性文化互滲的鏡子。在這種雙向流動中,個體的“游牧者”在確立自我意識時以協(xié)商的姿態(tài)融入文化空間中,讓現(xiàn)代性以更包容的姿態(tài)為文化持有者所接受,同時也由此帶來對處于文化斷裂與困境中的民族現(xiàn)代性的反思。我們期望通過這種影像意義轉(zhuǎn)換的分析,恰當(dāng)?shù)匕盐丈贁?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族群認同與現(xiàn)代性之間的關(guān)系。筆者認為,現(xiàn)代文明與傳統(tǒng)文化之間并非絕對的二元對立關(guān)系,在很多時候它們之間形成了一種文化互滲的“流動性”關(guān)系。因此,我們應(yīng)該以更加積極的姿態(tài)發(fā)展現(xiàn)代性,建設(shè)性地完成少數(shù)民族地域性特征所帶來的豐富性和多樣化的觀念及意義的轉(zhuǎn)換,尋找一條突出民族文化在時代洪流中的民族影像的道路,建構(gòu)具有民族共同體美學(xué)特質(zhì)的文化景觀美學(xué)。
【注釋】
1林鐵,張建永.現(xiàn)代性視域下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認同路徑[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漢文版),2012(3):128-132.
2李淼.云南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研究:邊疆想象、民族認同與文化建構(gòu)[M].昆明: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6:122.
3郭璐.游牧者:流動時代個體的生活敘事——基于鮑曼流動的現(xiàn)代性思想[J].理論界,2018(11):66-71.
4周永康.生命歷程與日常生活:大流動時代的鄉(xiāng)村家庭與個人[J].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5(1):29-38.
5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392.
6同2,127.
7Arjun Appadurai.全球化、研究與想象[J].張存山譯.國際社會科學(xué)雜志(中文版),2000(2).
8伊塔洛·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M].王志弘譯.臺北: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
9胡譜忠.2010年民族題材電影回顧[J].中國民族,2011(1).
10同1.
11同2,70.
12沙丹.《長調(diào)》:民族記憶、自我書寫與文化主體性[J].當(dāng)代電影,2008(5).
13霍米·巴巴.播撒民族:時間、敘事與現(xiàn)代民族的邊緣[J].廖朝陽譯.中外文學(xué),2000(5):74-96.
14李道新.新民族電影——內(nèi)向的族群記憶與開放的文化自覺[A].牛頌,饒曙光主編.全球化與民族電影——中國民族題材電影的歷史、現(xiàn)狀和未來[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