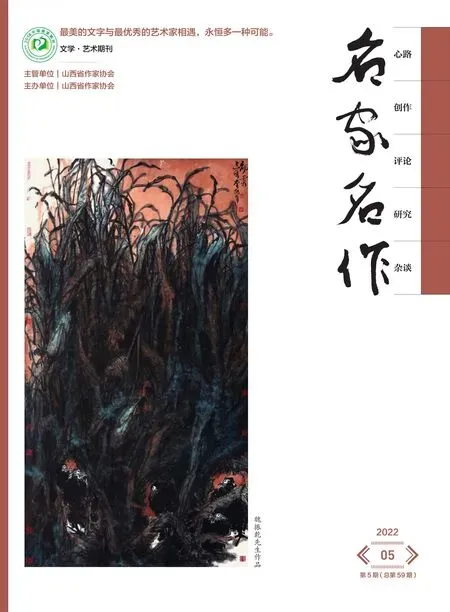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中“光”意象的探析
羅惠文
安東尼·多爾是當代美國文壇的優秀小說家,榮獲諸多獎項,著作頗豐。他的長篇小說《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以下簡稱《光》)榮獲普利策小說獎以來,多爾獲得了更多關注。作為小說的重要意象,“光”豐富意蘊的背后隱含多爾對科技倫理的思考。“光”蘊含“光明”與“陰影”二重性,這一特性使多爾借由“光”意象所寄寓的科技倫理觀既閃耀著“科技之光”,也伴隨著晦暗的“科技之影”。面對戰爭與科技日益密切的聯系,以“光”意象為路徑切入戰爭敘事下的科技倫理思考,對當下人們探索科技倫理、反思科技異化問題具有觀照意義。
一、“光”意象的實義
朱光潛認為,意象是以文字為代表的圖景,是作者情感與客觀形象的結合。在《光》中,多爾用諸多筆墨塑造了光的不同形態,并將情感浸入“光”意象中,賦予“光”多重意蘊。本文依據“光”意象在小說中的不同表現形態,將“光”意象的含義分為實義和象征義兩類。
(一)自然之光
多爾在小說中融入了豐富的自然描寫,并對其中寄寓的自然與人類道德的深刻思考予以肯定。
在西方文化中,“光”意象是重要的美學范疇之一。因此,人們早期將光視作生命的本源。多爾也將光投射到自然萬物,他筆下的自然常常光彩熠熠。例如,月光照耀下的群島,暴風雨中泛著藍色光芒的花崗巖,神圣的黎明之光,皎潔如瀑的月光,創世之光“海之焰”鉆石,馬廄上金黃的秋日陽光,光彩照人的鴨羽,光芒四射的巨柏針葉,等等。風光旖旎的自然不僅令人陶醉,也給予人物心靈的慰藉。瑪麗洛爾在父親被捕后陷入絕望,為幫助她走出精神困境,馬內科太太帶她到海邊散步,使她在機緣巧合下與海螺結緣;維爾納因誤殺小女孩一家而深感愧疚自責,但當他看到閃耀著陽光碎片的大海時,突然感到一陣愜意和輕松,大海的寬廣無垠似乎可以包容他所有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多爾筆下光芒四射的自然景象主要出現于戰爭前、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之初,戰火的蹂躪使自然幾乎消失了燦爛的光芒,隨之而來的是炮火的火光和滾滾濃煙,如原先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火光沖天,縹緲柔和的月光變得陰冷泛白,往日人與自然寧靜平和的狀態在轟鳴的炮聲中遠去。多爾通過對戰爭前后“光”意象的對比表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的狀態被戰爭中的高科技武器打破。
(二)科技之光
小說中“光”意象的另一層含義是指物理學中的一種看不見的光,即電磁波。多爾借小說人物艾蒂安之口,闡釋了電磁波的含義,“在電磁波譜上,光往這邊跑是零,往另一邊跑是無窮大,所以,事實上,孩子們,從數學的角度來講,所有的光都是看不見的”。
小說中“科技之光”的重要代表是無線電廣播。無線電廣播誕生于1920年,是20世紀上半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就之一。在其問世將近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在二戰中廣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它既是納粹德國散布謠言、制造恐怖的手段,也是盟軍進行抵抗的工具。基于此,多爾在小說中著力描寫了無線電廣播的正反兩方面作用。
小說中首先體現了其反面作用。納粹德國利用廣播進行強制性、統一性、連續性的宣傳,通過煽動性強的話語迷惑民眾,管控著民眾的思想和生活。在主人公維爾納生活的礦區里,人們不能私有和使用收音機,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是收聽帝國統一播放的廣播。
然而,小說更突顯的是廣播在促進文化傳播和教育、抗擊侵略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維爾納有極高的物理天賦,但作為一個礦工的兒子,他很可能要在礦區碌碌終生。一次偶然他拾到一部舊收音機,收音機里來自法國電臺的科學節目使他的命運軌跡發生了改變。節目講述的科學知識以及播放的古典音樂讓他得以接受科學教育和音樂的熏陶,使他深埋在心底的那個成為卓越科學家的夢想種子漸漸生根發芽,激勵他不斷追求科學理想。無線電廣播的反抗功能主要體現在以馬內科太太為首的法國抵抗組織用電臺為盟軍傳遞信息,為盟軍的反攻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支持,推動盟軍走向勝利。
小說中科技除了以電磁波為基本原理的無線電廣播外,飛機、高射炮、防空炮、轟炸機等在二戰中被廣泛利用的武器也值得注意。這些武器甫一出場幾乎都伴隨著閃爍的火光、黑色的光帶、血腥的紅光等,僅從多爾對光線的形容便可看出在戰爭中使用殺傷力極大的武器對人和自然帶來的巨大傷害。
二、“光”意象的象征義
小說中“光”意象還蘊含多重象征義。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中認為,意象可以作為一種“描寫”或隱喻而存在,可以轉化為隱喻,但如果作為一種表現和表征不斷重復,它就會成為一個象征。結合多爾對“光”意象的描寫,本文試圖將“光”意象的象征義歸納為人性之光與和平之光。
(一)人性之光
人性之光是小說中“光”意象象征義的核心。威爾賴特認為:“在象征系統的一般歷史中,光明和黑暗的對偶足以成為其他對偶的一個自然象征的代表。光的意象于是就格外適合充當心靈狀態的主要的意指性象征了:光是語義的媒介,心靈則是意蘊。”“光”在古英語中有“心靈”的意義,“光”隱喻“心靈”,在西方許多文學作品中被運用,在多爾的筆下也是如此,他在小說中塑造的主要人物都閃爍著人性中真善美的光輝。
瑪麗洛爾和馬內科太太是小說中體現“人性之光”的代表人物,多爾將這兩位女性塑造為光的化身,正如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或印象派的畫作,畫家通過將光引入畫中照亮女性來展現女性的美好。戰爭爆發后瑪麗洛爾與父親逃難到圣馬洛。戰爭期間,一系列危機接踵而至,這對于年幼且失明的瑪麗洛爾來說何其沉重。她曾感到憤怒、怨恨、絕望,但最后依然選擇勇敢地面對。不僅如此,她還在馬內科太太去世后接替她傳遞情報。面對德國軍事長馮·倫佩爾對“海之焰”的圖謀,她機智頑強地與其周旋,最終保全了自己,也避免了讓“海之焰”落入敵手。她還淡泊名利,獲救之后把獨一無二、價值連城的“海之焰”放歸大海。
女仆馬內科太太六十年來一直無微不至地照顧著在一戰中精神受到創傷的艾蒂安。同時,為了解開瑪麗洛爾的心結,馬內科太太在戰時物資緊缺的情況下依然想盡辦法給她制作美食,帶她到海邊散步,使瑪麗洛爾逐漸擺脫心靈的困境。德軍占領圣馬洛后,面對敵軍的壓迫,馬內科太太以“刀鋒”作為自己的代稱,積極成立抵抗組織捍衛自由法國,并說服艾蒂安用私藏的無線電設備為盟軍傳遞情報。
除了這兩位女性外,小說的許多人物也閃耀著人性之光,例如,維爾納雖然一直生活在納粹的高壓統治之中,但他的善良沒有蒙塵,三次解救瑪麗洛爾亦是對他自己的救贖;艾蒂安在正義感的驅動下鼓起勇氣戰勝自己的懦弱,加入抵抗運動中;弗雷德里克在納粹軍事化的教育中堅持個性,關懷生命,拒絕同流合污。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之光是那個黑暗年代里珍貴的光明與希望,表達了作者對人性中真善美的贊美。
(二)和平之光
“和平之光”亦是小說中“光”意象的象征義之一。小說的時間跨度很大,從1934年至2014年,經過了80年的時間。主人公瑪麗洛爾與維爾納的故事結束于1945年,但作者在此之后還特別寫了幸存的人物在1974年和2014年的生活。在2014年這一章中,瑪麗洛爾活著迎來了一個新世紀,生活安穩平靜。年近九旬的瑪麗洛爾在一個春日清晨與她12歲的外孫去散步,休息時他們坐在長椅上,沐浴著微風暖陽,畫面溫馨祥和。然而,作者在此圖景上增添了引人深思的一筆:他們休息時,外孫米歇爾正用游戲機玩著戰爭游戲。瑪麗洛爾想象著電磁波像艾蒂安形容的那樣在外孫的游戲機里進進出出,環繞著他們。最后一章中再次出現的電磁波與“科技之光”相呼應,而這一“看不見的光”也是“和平之光”。
生在和平年代的米歇爾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殘酷,對他來說戰爭像游戲里激動人心的冒險。游戲里的戰爭就算失去一切還可以從頭再來,而真正的戰爭會吞噬生命,將美好的家園變成荒涼的廢墟,帶來難以撫平的傷痛。正像被戰火毀滅的古城圣馬洛,盡管后人用12年的時間重建,但真正的古建筑永遠消失了。這實際上隱含了作者對戰爭的警惕,現代社會和平的表象之下似乎還涌動著戰爭的暗流,戰爭的威脅并沒有完全遠離我們。此處的“看不見的光”象征著警惕戰爭、珍愛和平。
此外,作者還描寫了在科技高速發展的現代,空氣中相遇的電磁波比二戰時多了百萬倍,極大地便利了信息的傳遞。瑪麗洛爾想象著她的父親、艾蒂安、馬內科太太和維爾納的靈魂像空中的電磁波那樣飛來飛去,或許只要足夠用心就可以聽到這架偉大的靈魂穿梭機的聲音。在這個信息爆炸時代,每個小時都有帶著戰爭的印記離開這個世界的人。作者借瑪麗洛爾的想象來緬懷經歷過戰爭的創傷,帶著戰爭記憶離開這個世界的人,表達了作者對反戰的深切呼喚。
三、“光”意象對科技倫理的思考
科技倫理指的是:“科技創新活動中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關系的思想與行為準則,它規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體應恪守的價值觀念、社會責任和行為規范。”小說中主要涉及科技活動中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關系兩個方面。
(一)人與自然的關系中的“光與影”
在物質世界中,“光”與“影”總是相伴而生,光影之間此消彼長、相互襯托。影的產生離不開光的投射,光的耀眼伴隨著影的襯托。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多爾指出了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光與影”,他首先描寫的是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光”。前文已分析了戰前無論是巴黎還是圣馬洛,多爾筆下的大自然總是光芒四射的,此時科技活動為人與自然的關系賦予光明。維爾納在進入納粹軍事學校前,通過收音機學習物理知識,并利用學到的科學規律修繕和發明機器,用科技為他人提供便利和幫助。失明的瑪麗洛爾認識自然的最初方式是閱讀盲文書籍和傾聽父親的講述。結識了叔父艾蒂安后,廣播成為她了解自然的又一途徑。在科技的幫助下,瑪麗洛爾得以更好地越過失明的阻礙去擁抱自然。
在“影”的層面上,多爾指出濫用科技會使人與自然的關系由和諧走向沖突。他將科技活動的“影”呈現在戰爭的白熱化階段和戰爭甫一結束。震耳欲聾的炮聲和搖曳的火光成為這兩個時期故事的底色,如瑪麗洛爾與爸爸從巴黎逃難到圣馬洛的途中感受到空氣中燒焦的味道和天空中轟炸機飛過的聲音,以及盟軍發動反攻時對圣馬洛進行猛烈的炮擊。黑色濃煙和熊熊炮火掩蓋了自然的光芒,失去生機的自然變得陰冷恐怖,而這前后的差異源于戰爭中高射炮、轟炸機、槍械等殺傷力極大的武器。馬克思認為:“科技負面作用的極端形式是以軍事科技為基礎的戰爭。”人類對科技的濫用造成科技的異化,使科技由“光”轉向“影”,打破了人與自然和諧的狀態,造成兩者之間的矛盾沖突。
“科技之影”的出現還與人文教育的缺失息息相關。在小說中,在納粹軍事學校的教育下,科技與人文之間出現裂痕,科技工作者只顧鉆研科學技術,成為缺乏人文教育的“科學匠人”。學生普遍缺乏對自然和生命的尊重,很多男孩熱衷于射鳥比賽,隨意對大樹開火,看到樹上的鳥受傷跌落或四散飛走,他們便哈哈大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殘忍的行為是對自然的傷害。
科技誕生的目的在于幫助人類發現自然萬事萬物的客觀規律,利用規律為人類造福的科技活動才是趨向光明的。若科技被誤用,將危害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導致人與自然的沖突,最終“科技之光”背后的“影”將投向人類自身。
(二)人與人的關系中的“光與影”
多爾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傾注了“光與影”的思考,小說中他主要描寫了科技活動中人與人之間和諧與對立的兩種狀態。
“科技之光”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進了人們的相識。維爾納和瑪麗洛爾正是通過廣播結緣。艾蒂安的廣播節目在維爾納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懷著期待和敬仰的心情找到艾蒂安的房子,想要與其見面,卻意外在門外見到瑪麗洛爾。戰爭后期,瑪麗洛爾在密室里用廣播傳遞求救信息。維爾納通過收音機聽到了瑪麗洛爾的求救,使瑪麗洛爾得以脫險。廣播在維爾納與瑪麗洛爾之間建立了紐帶,促成了他們之間珍貴的友誼,也使瑪麗洛爾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同時,科技也是人與人之間傳遞知識、進行教育的媒介。維爾納與艾蒂安來自不同的國家,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互相也并不認識,但艾蒂安講述的科學故事可以通過廣播傳遞給維爾納,生動的故事激勵著他努力學習,追求理想。“科技之光”照亮了維爾納的人生,啟蒙了他的心智。若沒有“科技之光”,維爾納本就灰暗的人生可能只剩下一片荒蕪。
“科技之光”還是使人們團結起來的力量。德軍占領圣馬洛時,馬內科太太聯合城中的法國婦女,成立了婦女抵抗組織,通過艾蒂安私藏的無線電設備向盟軍傳遞情報。無線電設備將婦女抵抗組織與盟軍團結起來,她們雖然沒有親赴戰場,卻能夠利用無線電與盟軍團結協作,推動戰爭取得勝利。
然而,“科技之影”使科技淪為束縛人的工具。小說中德國完全控制了德國的廣播事業,長期向民眾播放反動口號,煽動種族主義思想。于是,曾經不認同納粹思想的德國民眾在潛移默化中轉變了態度。
小說中“科技之影”在人與人的關系中產生的消極作用還包括使人與人之間變得冷酷無情、充滿敵意,缺乏同情、憐憫之心。戰爭期間高科技武器的大規模應用使生命受到摧殘,維爾納在車站看到一節節車廂里堆著一面面的尸墻,最后一節車廂里活人摞著死人,士兵們漠然地坐在死去的同伴身上。原本平靜祥和的小城圣馬洛也與之前大不相同,城里留守了大量的病患,流言四起,人們開始習慣鎖門。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是人們的目光交流、街邊閑談、歌聲、情侶的漫步都沒有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科技之影”的籠罩下變得對立。
小說的最后,多爾描寫了瑪麗洛爾的外孫在玩戰爭游戲,這一情景一方面表現了多爾對戰爭中逝去的人們的緬懷,另一方面還傳達了他對科技的隱憂。戰爭游戲的發明也是科技進步的體現,游戲中角色死亡還可以重新開始,但在現實的戰爭中,人逝去卻無法重生。這隱含了多爾的擔憂,現實與虛擬并不對等,過度沉浸于游戲易使人的性格變得暴躁,甚至在與他人的相處中產生暴力行為,加劇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
四、結語
“光”的二重性使光影相生相伴,《光》中光影的力量并非對等,作者的意圖在于突顯光。以光為中心,以科技為橋梁,聯結自然和人類,展現科技促進萬物共生共存。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影的存在,光本身融匯著影,科技之影雖然造成了種種沖突、分裂與隔閡,但影并不僅是光的對立面,影對光有建構作用,更突顯了光的重要性。科技本身不具備理性和中立,其是否會成為打開的“潘多拉魔盒”完全取決于使用科技的人。科技的本質是人的本質的體現,科技之光與影在一定程度上顯露了人性。因此,若運用科技時能秉持“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那么縱然有深沉的“影”,也遮蔽不了閃耀的“科技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