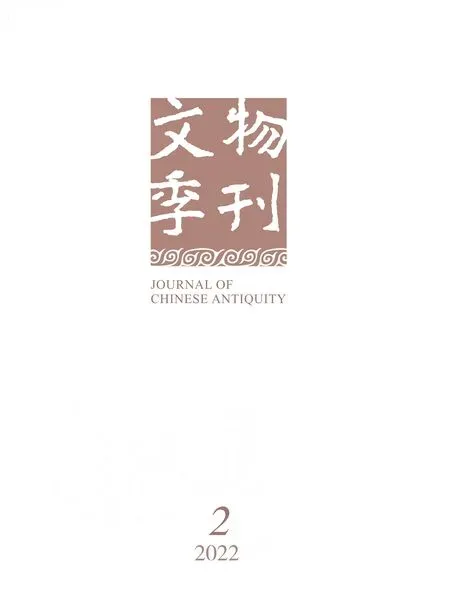云岡石窟的對外影響問題
韋 正 馬銘悅 崔嘉寶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云岡是中國東部地區最早的石窟,對此后中國石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宿白先生對此有提綱挈領的表述:“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西迄陜、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云岡模式的蹤跡,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窟歷史早于云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岡石窟影響范圍之廣和影響延續時間之長,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情況,恰好給我們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對我國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紀后半葉到7世紀前半葉)進行排年分期的標準尺度。因此,云岡石窟就在東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對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東方早期石窟的關鍵;對它研究的深入與否,直接影響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1]宿白先生的表述時間為1987年,在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來看,宿白先生的表述依然高屋建瓴。在這三十五年間,中國石窟材料得到更多地公布,石窟寺考古及中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也有所革新。宿白先生關于云岡石窟巨大影響的總體判斷依然有效,但一些具體問題則呈現出較為復雜的情形,揭示這些復雜的情形,可以讓我們更好地把握云岡對外影響的實際狀況,對中國石窟之間的關系有更辯證的認識。
云岡的對外影響可分為直接和間接影響兩種情況。直接影響即其他石窟與云岡石窟有明確的繼承關系,龍門石窟交腳彌勒大龕和古陽洞的多數大龕、慶陽南北石窟寺的七佛窟、義縣萬佛堂西區第1、4、5、6窟和東區第7窟屬于這種情況。涇川王母宮石窟更是直接模仿了云岡第6窟。一些小型石窟如甘肅合水保全寺和張家溝門石窟、河北宣化下花園石窟也是云岡直接影響下的產物。間接影響即某些石窟先受到云岡影響然后又影響到其他石窟,如龍門先接受云岡影響,然后又影響到其他石窟,這從原則上來說仍然可看作云岡的影響,但由于龍門在接受云岡影響的同時也接受了其他地區的影響,甚至還發展出了自身特色,受到龍門影響的其他石窟的面貌與云岡已經難覓共同點。在這種情況下,再籠統地談云岡石窟的影響有失之于淺之嫌。有鑒于此,本文擬討論三個相關問題,以期對北中國早期石窟寺總體狀況有更客觀全面穩妥之認識。
一、河西北魏石窟遺存與云岡之關系
河西石窟是一個比較復雜的話題,尤其是河西早期石窟,不論具體的時代,還是與其他石窟的關系,幾乎都存在不同的看法。這里不準備討論那些有爭議的石窟,只涉及意見比較一致的北魏時期遺存,這些遺存包括武威天梯山諸窟中北涼壁畫之外的北魏壁畫,張掖馬蹄寺第1、2、3、4、8窟中的北魏壁畫,酒泉文殊山前山萬佛洞、千佛洞和后山千佛洞、古佛洞壁畫,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窟即所謂“北涼三窟”之外的北魏諸窟。由于新疆以東地區河西最早出現佛教石窟,且出現年代為十六國晚期。上述河西諸地北魏遺存與十六國遺存面貌差異大,甚至形成斷層。這些北魏時期遺存部分學者認為與云岡關系密切[2],其實多不及與龍門石窟之關系密切,下面略作檢討。
上述河西北魏諸窟均無明確紀年,但均可通過比附將相關石窟年代推定在北魏,但能肯定的多是北魏洛陽時代,是否能到魏平城時代需要再斟酌,下面作簡要說明。武威天梯山石窟中,第1窟中心柱正面下層龕外右側第2層說法圖可以判定為北魏洛陽時代,依據是菩薩形態秀骨清像之外,還穿交叉式披帛(圖一)。以此為依據,可以將天梯山其他壁畫多推定在北魏洛陽時代。張掖馬蹄寺的情況與天梯山很相似,第8窟中心柱南向面下層龕內壁畫以千佛為背景,在中間位置為二佛并坐說法,二佛上有交腳彌勒菩薩,兩側有脅侍菩薩,從題材和布局看,與云岡很相似,但脅侍菩薩都是秀骨清像,也穿交叉式披帛(圖二),也屬于北魏洛陽時代。那么,這種形式是否可能從云岡傳去,從而視為云岡對外影響的一部分。本文認為,云岡的這種形態和服飾特點也是從龍門傳入的,詳下。因此,作為云岡的影響來看是不及作為龍門影響來看合適的,而且龍門不乏交腳彌勒和二佛并坐。酒泉文殊山前山萬佛洞中心柱南向面佛龕兩側菩薩為秀骨清像式,時代也以北魏洛陽時代甚至更晚點為宜。敦煌的情況略特殊,因為第285窟有西魏大統(535—550年)年號,其他被推定為北魏時期的諸窟與第285窟人物的形態服飾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所以推定為北魏時期是可靠的,但首先要考慮的是靠西魏近的北魏洛陽時代,然后再是更早的北魏平城時代。敦煌莫高窟存在北魏平城時代窟,但莫高窟只在西魏或略早可以看出受到東部地區文化而不一定是石窟的影響,更早的石窟看不出與東部地區的關系,更不用說受到云岡的影響[3]。根據上面的分析,河西石窟中不排除有北魏平城時代的遺存,但看不出與云岡的關系;河西石窟中很多內容可以推定在北魏洛陽時代,自然與云岡石窟也沒有關系。這個現象就不只是石窟問題,而必然也與歷史背景之間有一定關系了。
從歷史背景來說,除敦煌外,河西其他地方遭受北魏攻占的重創,“ (涼州)沙門佛事皆俱東”[4]是很好的注腳,佛教如此,當地人口、經濟上遭受的劫掠要更深重。佛教石窟營造頗需人力物力,河西地區在北魏很長時期內難以恢復和發展佛事實屬自然,這個現象可用墓葬來輔助說明。河西地區魏晉墓葬很多,五涼墓葬也不少,北魏墓葬則屈指可數,便是河西進入北魏后嚴重凋零的表征。河西之不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北魏平城時代對西方交流可以通過草原之路更便捷地實現,而不必一定依賴河西。北魏都城平城本身就是歐亞草原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大約與北魏同時興起的柔然政權控制了歐亞草原東部廣大地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西方交通。在大同發現的好幾批鎏金銅杯、銀長杯、銀盤、玻璃器,在距大同不遠的內蒙古正藍旗伊和淖爾北魏墓發現的銀碗,多數是東羅馬制品,在薩珊波斯阻止東羅馬經沙漠之路與東方交通的情況下,大同及附近地區的這些東羅馬物品只能通過草原之路而來。但定都洛陽后,北魏對外交通的形勢已很不同于定都平城,這個時期北魏只能主要通過沙漠之路與西方交通,河西的地位必然因此而上升。
河西地位在北魏遷洛以后的上升,與敦煌從孝文帝時期格外受到重視有密切關系。宿白先生對敦煌地位的變化有深入論述,其大意是:北魏攻占河西后,敦煌成為北魏經略西域東部的基地,在5世紀50年代之前是北魏積極進取的時代;從50年代至70年代,是柔然威逼敦煌,北魏試圖放棄敦煌移鎮涼州的時代;80年代開始高車強力牽制了柔然,敦煌進入安定時期,既解除了西部柔然的威脅,又加強了與東部的聯系,長樂王穆亮在485年作為見于文獻的最早的敦煌鎮都大將被孝文帝派遣到敦煌,此后駐節敦煌的官員身份都很高,東陽王元榮是其代表[5]。宿白先生整理敦煌這段歷史的目的是要說明所謂“北涼三窟”的年代可能產生于太和年間,其他北魏洞窟產生的年代要更晚點。關于“北涼三窟”的年代,我們覺得可能比宿白先生估計的還要早點,至于敦煌其他北魏洞窟,數量大、成系列,沒有連續穩定的外部環境的確難以出現。敦煌地區的這個情況,可以作為河西其他地區的參考。事實上,從已經公布的材料看,武威、張掖、酒泉三地幾乎沒有可以肯定的北魏平城時代開鑿的洞窟,北魏壁畫與北涼壁畫形成明顯斷層,這既可說明三地石窟活動恢復之晚,也力有不逮。要言之,河西石窟不能輕易建立與云岡的關系。
關于敦煌莫高窟,還有必要再作點闡釋。敦煌獲得安寧從5世紀80年代開始,敦煌莫高窟完全有可能從此進入興盛期,其時在孝文帝遷洛之前,似乎與云岡關系就不一般了,如宿白先生就認為莫高窟第275窟與云岡第7、8和9、10兩組窟接近[6]。對此我們的意見也有所不同。第275窟基本可以納入到敦煌北魏洞窟序列中,敦煌北魏洞窟的基本特點是前室為人字披,后室有中心柱,窟內和中心柱流行闕形龕,這些情況絕不見于云岡,也不見于其他地區,而是敦煌當地的發明。敦煌及附近地區有足夠的資源用以興造石窟,而不必外求于云岡或其他地區。宿白先生曾列舉若干具體例證來說明敦煌與云岡之間的聯系,這些例證包括:莫高窟第125~126窟間裂縫沙土中發現的太和十一年的刺繡、敦煌出土的五級和多級方形石塔、莫高窟第257窟南壁沙彌守戒自焚壁畫中的單層塔、第254窟南壁薩埵太子本生壁畫中的三級塔等都是中原塔式。根據這些例證,宿白先生在論述云岡的對外影響時,才有“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窟歷史早于云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的判斷。我們認為這些細節性的例證基本上無助于說明莫高窟受到云岡的影響:繡佛的存在只能說明這件刺繡來自平城,中原式佛塔也非云岡獨有。當然,我們不否認敦煌與平城之間的聯系。其實,從細節上來說,莫高窟與龍門的不少因素很接近,最顯著的就是秀骨清像的樣式,但我們同樣不認為莫高窟受到了龍門石窟的影響,而可能只是時代風氣導致了莫高窟菩薩、供養人等形體、服飾特征的變化。
上面牽涉到的其實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認定石窟之間彼此有關系。一個石窟是由形制和造像兩大部分構成的。形制屬于結構性特征,具有深層次的隱喻含義,雖然今人已不易明了,但形制的相似往往表示彼此之間具有關系。造像可分為題材及題材所構成的組合和布局、造像裝飾兩大部分。題材及題材組合不僅與石窟思想有關,也與石窟形制之間具有關聯性。造像裝飾屬于相對外在的內容,可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快速地變化,單獨用裝飾來討論不同石窟之間的關系,是需要慎重的。石窟形制、題材與題材所構成的組合和布局、造像裝飾構成相關的三個方面,在反映石窟相似性的能力上依次降低。此外,某個石窟的特殊內容,如果在另一石窟中出現,則也可推測彼此之間具有聯系。以此進行檢驗,敦煌莫高窟連云岡石窟的間接影響都談不上,雖然最早的“北涼三窟”的年代很可能在云岡“曇曜五窟”開鑿前后。
因此,可以確認與云岡石窟有直接關系的也就是上文所說的龍門古陽洞佛龕等。古陽洞與云岡的關系是由遷都引起的[7],慶陽南北石窟寺和涇川王母宮與云岡的關系是由供職北魏朝廷達官顯宦主要為政治而非宗教目的引起的,這些具有特殊性。義縣萬佛堂等符合文化傳播的一般情況。萬佛堂出現于義縣是任職于那里的北魏高官模仿云岡而開的,合水保全寺和張家溝門石窟、宣化下花園石窟等幾處小石窟是從平城到隴東或到遼西的路途上灑落下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石窟的年代多在遷洛以后,這就迫使我們考慮云岡對外產生影響的情形。我們不否認遷洛之前云岡可能對外產生一定影響,也不認為云岡之外地區在遷洛之前不能出現石窟,但云岡屬于皇家石窟這一性質可能并不有利于其對外產生影響。云岡第三期洞窟數量猛增,云岡附近出現的小型窟基本屬于第三期,都是云岡從此前的皇家性質窟中“解放”出來的標志,其他地區出現的與云岡類似的石窟大概也是這個情況下產生的。鑒于這個情況,我們更難以認為包括莫高窟在內的河西地區北魏石窟與云岡有關。
二、平洛道石窟與云岡之關系
孝文帝遷都洛陽,龍門隨之出現大量石窟,這些石窟自然與云岡石窟有密切關系,通常都將之視為云岡石窟的影響。不過,如果沒有遷洛之事,龍門未必會出現很多北魏石窟。這種隨著遷都而出現的石窟,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偶然性,與石窟文化的自然傳播不太一樣,這是不可不考慮到的,這牽涉到對平洛道上石窟的理解問題。
遷洛以后,平城與洛陽之間人員往來頻繁,由此導致平洛道上遺留下可觀的中小型石窟。這類小石窟的數量隨著近年國家對石窟寺考古的重視,隨著山西省大力開展石窟寺調查工作而在持續的增長之中。但關于這類小石窟的分布狀況、年代和價值問題,李裕群在較早階段進行的研究已作了相當透徹的闡釋,值得轉引。對于這些小型石窟的總體情況,李裕群說:“據文物普查資料的初步統計,全省石窟及摩崖造像約有三百余處,除著名的云岡石窟和天龍山石窟外,山西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小型石窟。這些石窟大都開鑿于北朝時期,分布區域主要集中在晉中和晉東南地區。這一地區是連接兩個石窟寺開鑿中心——平城和洛陽的交通要道,也是連接東魏北齊鄴城和太原兩都的交通要道。”[8]對于這些小型石窟的具體分布情況,李裕群說:“考察這些石窟的地理位置,我們不難發現,石窟地點或在古代交通線上,或在中心城市附近。如晉東南的高平羊頭山、高廟山石窟、武鄉良侯店石窟、晉中子洪鎮石窟都在太原到洛陽的交通干道上,榆社圓子山石窟和響堂寺石窟,左權石佛寺石窟和‘高歡云洞’石窟,既在太原到洛陽的交通線上,也在太原到鄴城的交通線上。平定開河寺石窟則在太原東出井陘,連接河北諸州的交通要道上。這一交通線上還有許多北朝石窟。”[9]
對于這些小型石窟的具體交通狀況,李裕群說:“由于并州、建州(引者注:今高平)是聯系兩京(平城和洛陽)重要的交通要道,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由平城率軍南征,就是經由太原和建州而抵洛陽的。遷都洛陽后,北魏官員亦常冬居洛陽,夏居平城,而頻繁往來于兩京地區。溝通兩京的交通要道主要在太行山東西兩條路線,太行山東線雖較平坦,但西麓一線卻(較)為便捷,路程亦短,故這一交通線似更為繁忙。”[10]
李裕群是連帶東魏北齊小型石窟一起敘述的,轉引時難以將北魏情況單獨抽離出來,不過東魏北齊連帶引述,倒也有助于凸顯平洛道上北魏石窟與太鄴道上東魏北齊石窟的不同。
從理論上來說,平洛道上石窟不是云岡影響下的產物,就是龍門影響下的產物,由于龍門石窟主要是在云岡影響下興起的,所以平洛道上石窟總體上都可以看作云岡影響下的產物,這與河西石窟很不一樣。這個宏觀背景是易于理解的,但面對具體材料時,這個宏觀背景往往又是容易被忽視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平洛道上的有些石窟年代李裕群認為要早于遷洛,從而被視為云岡對外產生影響的重要證據,“晉東南地區發現有北魏都平城時期的石窟造像,年代上早于洛陽龍門石窟,這引起了我們極大的關注。”[11]
當時引起李裕群極大關注的是武鄉良侯店石窟、高平羊頭山E—2龕和祁縣子洪鎮第2窟,特別是良侯店石窟。李裕群將這幾處石窟劃分為第一期石窟,認為它們在形制上與云岡和龍門石窟無法對應,因而主要從造像和裝飾特征上進行討論,因為體現了分析的方法,所以下面作較多轉引:“本期佛、菩薩和飛天造型古樸,具有早期造像的特點。如良侯店石窟佛像面相渾圓,廣額豐頤,雙耳垂肩,身體豐壯,身著袒右式袈裟,顯得較為古樸。袒右袈裟左肩處均有較寬的袈裟衣邊,衣紋帶有鉤形分叉的厚重衣紋,明顯具有北魏遷洛前云岡第一、二期佛像的特征。……因此良侯店石窟的開鑿年代可以推定為北魏遷洛前,約孝文帝太和中期前后(486年左右)。”[12](圖三)關于羊頭山石窟,李裕群說:“羊頭山E—2龕佛像寬肩細腰,身體碩壯,身著袒右式袈裟,有偏衫衣角,衣邊有折帶紋。這種樣式屬于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前的舊樣式,是云岡石窟第一、二期常見的佛像樣式。在龍門石窟古陽洞造像中似延續到宣武帝景明年間,以后完全為褒衣博帶式新樣式所取代。因此羊頭山早期龕像的開鑿亦約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中期至宣武帝景明年間以前(486—504年)。年代上略晚于良侯店石窟。”[13](圖四)關于子洪鎮石窟,李裕群說:“子洪鎮第2窟佛像面相渾圓,身著袒右式袈裟,也具有早期特征,佛像發髻旋渦水波紋與北魏太和八年(484年)比丘僧安金銅造像發髻一致,因此從佛像樣式而言,子洪鎮第2窟的開鑿年代也約在北魏孝文帝時期。”[14]李裕群將這三處石窟作結:“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將一期的年代大致推定為北魏孝文帝太和中期至宣武帝景明年間,即公元486年前后至504年。三處石窟的先后開鑿次序是良侯店、羊頭山和子洪鎮石窟。……看來第一期洞窟主要來自于云岡石窟的影響。……與洛陽地區石窟寺相比,第一期洞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年代上洛陽地區石窟寺亦略晚于第一期洞窟,因此不存在受到洛陽地區石窟寺的影響問題。……第一期洞窟主要受到北魏都平城時期的云岡石窟的影響,可以視作‘云岡模式’向南發展的一個重要地區。”[15]

圖三 武鄉良侯店石窟東壁左側坐佛與菩薩

圖四 高平羊頭山石窟F區雙佛并坐
李裕群發表《山西北朝時期小型石窟的考古與研究》一文時,高平大佛山尚未被發現。在后來公布大佛山材料時,李裕群直接將大佛山作為云岡對外影響的重要佐證,并在標題中直接點明,其名曰《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云岡模式”南傳的重要例證》。在正文中李裕群有更多的闡釋:“大佛山摩崖造像與云岡第二期偏早階段的洞窟造像有著驚人的相似,無論是題材布局,還是造像樣式都如出一轍。這是高平地區首次發現與云岡如此類同的摩崖造像。從表面上看,云岡模式南下影響到了高平地區是毫無疑問的,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工匠的身份或來源問題。”[16](圖五)具體說來,李裕群用大佛山摩崖與高平羊頭山石窟的大型釋迦多寶龕、高平建寧鄉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邑子等為皇帝陛下造石像”四面造像碑進行了比較,認為羊頭山遺存屬于當地民間工匠所為,“我們認為雕造大佛山摩崖龕像的工匠極有可能來自于平城,并且曾經參與過云岡石窟的開鑿。”[17]

圖五 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
李裕群關于良侯店、羊頭山、子洪鎮、大佛山摩崖或石窟受到云岡影響的判斷有理有據,關于大佛山工匠來自云岡的推測也有說服力。但是,關于這些遺存年代在遷洛之前的判斷似乎仍有討論的空間,事實上還存在著晚于遷洛的可能,至少對高平地區的羊頭山石窟和大佛山摩崖而言。將這些遺存作為“云岡模式”南傳的重要例證也需要斟酌。
李裕群進行年代斷定的主要方法是造像特征的相互比較,我們認為歷史地理狀況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高平地區屬于晉東南地區的東南部,這里的地形呈簸箕狀向南傾斜,丹河縱貫其間,丹河河谷是溝通黃河北岸與太行山南麓的重要通道,遷洛以后,這里成為平洛道上的重要節段。但在遷洛之前,高平地區距離平城遙遠,而且路途崎嶇。不僅如此,在孝文帝倉促決定移都洛陽之前,洛陽地位低落、經濟蕭條,沒能從魏晉瘡痍之中恢復過來。合此兩點,可見高平地區在遷洛之前沒有與平城和洛陽溝通的必要和可能,這里為偏僻閉塞之區,佛教石窟這樣的高級文化現象不太可能出現在這個地區,何況羊頭山和大佛山的規模也較可觀,絕非很鄉間的小龕小像可比。羊頭山E—2、大佛山具有的云岡一、二期因素不能作為其時代一定早于遷洛的證據,這一點其實李裕群在涉及古陽洞具有云岡一、二期特點的造像時,也提供了相應的證據,那就是李裕群根據題記等材料也指出古陽洞一些帶有云岡一、二期特征的佛龕年代可延續到宣武帝景明年間。但在具體討論到羊頭山E—2、大佛山的開鑿時間時,李裕群更多地依靠造像特征,選擇了更早的時間點,這就與歷史地理狀況產生了沖突,但李裕群沒有涉及這一點。李裕群的這個時間點選擇是與“云岡模式”南傳問題密切相關的,這是對宿白先生云岡對外產生巨大影響話題的呼應。我們在這里還想再次指出,孝文帝遷洛是比較倉促的偶然之舉,云岡影響到平洛道及洛陽都與正常的文化自然流動不太一樣,不宜作為“云岡模式”外傳的典型例證。
其實,良侯店和子洪鎮石窟也有可能是在遷洛之后開鑿的。兩處地點在平洛道以及后來的太鄴道上都是重要節點,這是沒有疑問的。但除了李裕群認為可能早于遷洛的這兩處地點外,沒有其他可以肯定的遷洛之前遺存。與這兩個地點鄰近的是沁縣南涅水石刻,數以百計的造像遺存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永平三年(510年),這在推測良侯店和子洪鎮石窟年代時是不能不顧及的。這里其實涉及的是遷洛之前平城與華北平原溝通的路線問題。相關文獻記載和歷史研究早已梳理得很清楚[18],從平城去華北平原,主要走靈丘道,今山西靈丘的“文成帝南巡碑”就是最好的證據。從靈丘道可以很快到達北魏重鎮定州以及鄴城。如果從祁縣、武鄉再沿漳河河谷即“滏口陘”而東出太行,那不僅路途遙遠而且沒有什么必要。
因此,比較合理而非流于造像表面特征的推測是,良侯店、子洪鎮、羊頭山、大佛山都是伴隨著遷洛而出現的石窟,而且是較早出現的石窟,所以保留了較多的云岡一、二期造像特點。為什么沒有將與遷都時間更接近的云岡二期晚段,即褒衣博帶式的造像更多地雕造出來,這個話題似乎更為誘人,更需要回答。同時還需要指出的是,云岡石窟借助遷洛傳播到晉東南地區,似乎更好地說明了遷洛之前云岡對外影響有限。
三、云岡三期洞窟與龍門石窟之關系
孝文帝遷洛以后,云岡才對外產生顯著影響。這個時期的云岡石窟進入了第三期,呈現出于第二期既有繼承,又很不一樣的地方。繼承者主要體現在造像的組合和布局方式,很不同者主要體現在流行方形窟形、有佛壇、秀骨清像的造像形態以及建筑新樣式等方面,這些新特點龍門同樣存在,這就牽涉到云岡與龍門的關系,即何者影響何者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宿白先生有明確的回答,那就是云岡影響了龍門。綜合各種因素,我們認為還是龍門影響了云岡的可能性比較大。由于如何認識這個問題同樣涉及到準確評估云岡的對外影響狀況,所以我們對可能是龍門影響了云岡而不是相反要適當進行闡釋。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有必要先介紹宿白先生研究的大致內容。宿白先生首先對云岡三期洞窟進行了仔細的考古類型學分析,并根據有關銘文得出“可以推測宣武一代云岡雕鑿尚未衰落”[19]的認識。由此宿白先生結合文獻提出三個值得認真考慮的問題:1.遷洛以后的平城并未荒廢。2.遷洛以后,對云岡開窟的實力,應作如實的估計。這一點的主要內容是云岡石窟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培養了大批技藝力量,而洛陽至少在永平(508—512年)之前,龍門沒有大規模開展,不需要太多雕刻技藝,因此云岡可以繼續興建。3.孝明(516—528年)以來洛陽佛寺工程急劇擴大與平城、云岡的衰落。這一點的主要內容是,龍門開鑿的盛期始自孝明,云岡的衰落在正光年間,正光四年(523年)柔然抄略平城,《魏書》與《金碑》的記載呼應[20]。宿白先生還列舉了幾項比較顯著的重要特征,如:“三壁設壇窟,在云岡既可以看到它的出現與A型窟關系密切,如第23窟(22);又可以了解窟形向方形發展的趨勢。在洛陽龍門這種窟形來源、發展俱不清楚,遠離龍門的新安西沃第1窟似乎才提供了它的發展趨向。”[21]在確認了云岡在遷洛之后雕鑿活動不衰,龍門的興盛期在孝明之后,宿白先生對云岡與龍門的關系進行了正面闡釋:“洛陽地區孝明時期開鑿的中小窟室,主要有接近方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的三壁設壇和三壁三龕兩種形制;亦即云岡第三期的B型窟和C型c式窟。云岡這兩種形制窟室的出現都比洛陽為早;而且在窟室形制,布局、佛像組合,形象造型以及細部裝飾等方面的發展變化,云岡不僅早于洛陽,更重要的是,其演變程序完整、清楚,與洛陽頗多突然出現或消失的情況不同,這就更有力地說明了變化的來源,主要出自云岡,而不是云岡較多地接受了洛陽影響。……以上情況可以表明,從窟室形制到細部裝飾,凡云岡、洛陽所共同具有的,主要應源于云岡。當然也不必排除在云岡第二期窟室進一步漢化時,吸取了某些中原因素,但從窟室整體觀察,應該考慮洛陽地區北魏窟室樣式,無論孝明以前,抑孝明以后,其主要來源應是云岡,而洛陽孝明以后的北魏窟室的主要特征,應屬于云岡石窟的第三期樣式。”[22]
宿白先生結合宏觀歷史背景,提示龍門與云岡相似的因素,就需要考慮來自云岡,這是很有啟發性的,但可能還要附加一個前提,那就是明確的云岡因素,才能考慮從云岡到龍門。還有,三壁設壇窟是否能從云岡A型演化而來,云岡三壁三龕窟是否能早到宣武帝時期,都還有討論的余地。這里僅就佛壇略作討論。賓陽南洞雖然沒有完工,但系宣武帝為孝文昭太后所開,開鑿年代可能同時或略晚于賓陽中洞,而且這樣的窟最初必然有統一的設計。現賓陽南洞窟門附近壁面下部有神王,表明現在的地面就是北魏時期開窟的地面。正壁佛像經唐初修改而成,但布局和大致形態維持北魏時期狀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佛座前面有一唐代特點的蹲獅,這表明唐之前蹲獅所在山石還保留著,現在看到的佛座以及旁邊的菩薩弟子蓮花座都很高,都是唐初為了將這里與洞窟前部地面找平時而形成的,這個地面也是北魏當時設計的地面而沒有完成(圖六)。兩尊菩薩的蓮座已經完成,是北魏特點的大扁蓮花,按照賓陽中洞、蓮花洞等北魏洞窟特點,略低于大扁蓮花座就應是一個連續的界面或地面,那么,賓陽南洞正壁當初的設計就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為通壁的高佛壇,一是佛座與菩薩弟子座隔斷,但佛座和菩薩弟子座都很高。前一種情況在龍門后來的北魏洞窟中有不少例,如皇甫公窟、路洞、魏字洞正壁。后一種情況在龍門未見,但見于大約同時期的南京棲霞山石窟,兩處石窟之間關系密切,詳下。總之,根據賓陽南洞,可推知高佛壇有可能在公元505年后不久就在龍門出現了,大概不待云岡之傳入。再者,即使我們接受龍門石窟在孝明以后方始大盛的認識,從孝明登基到正光四年平城衰落之間有約十年的時間,這個十年是龍門和云岡石窟都蓬勃發展的時期,更是龍門佛教活動大發展的時期,從地位日益提高的龍門向云岡輸送石窟因素既合理,時間也足夠。在平洛道上的北魏晚期洞窟如高平七佛山、高平石堂會、高平高廟山、高平羊頭山、長治交頂山、榆社圓子山、榆社響堂寺、左權石佛寺等如果都理解成云岡向龍門傳送影響之下的產物,是與洛陽地位日高而平城地位日低相違背的,何況有些特征還明確指向龍門而不是云岡,如左權石佛寺第1窟維摩詰和文殊的形態是龍門式的(圖七),與賓陽中洞維摩文殊對談相似。賓陽中洞是一處整體設計和完工的洞窟,開鑿年代為公元505年,其中的維摩文殊對談形象一掃云岡舊貌,而不可能由云岡的維摩文殊舊貌變化而來,這決定了與賓陽洞接近的左權和云岡維摩文殊新樣都只能來自龍門。

圖六 龍門石窟賓陽南洞正壁

圖七 左權石佛寺第1窟正壁
宿白先生討論云岡三期與龍門關系時,很多材料還沒有發現和公布。僅就兩處石窟而言,而且局限于石窟材料內部進行討論的話,得出云岡三期影響了龍門石窟的認識是當時最佳選擇。但正如我們上文提及的平洛道上小石窟材料,已顯示出的云岡與龍門之間關系的復雜程度超出通常的想象。南京棲霞山石窟材料的再發現和相關研究,使重新考察云岡和龍門的關系成為可能。上世紀80年代末,宿白先生就發表了著名論文《南朝龕像遺跡初探》[23]。上世紀90年代中期,南京棲霞寺僧大做功德,將20年代敷覆于南朝石窟造像上的水泥鑿去,南朝龕像面貌得以大致展露,林蔚發表了《棲霞山千佛崖第13窟的新發現》[24]一文,對此窟南朝造像特點進行了詳細介紹。上世紀90年代末,有關高校和南京市有關部門啟動“南京棲霞山石窟考古課題組”,并撰寫了考古報告《棲霞山·千佛巖》,惜至今仍未正式出版,但棲霞山石窟材料已廣為人知。魏正瑾、白寧將《棲霞山·千佛巖》的主要內容和結論節錄為《南京棲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概要》一文發表,對棲霞山、云岡、龍門三處石窟的關系有所討論,“棲霞山南朝一期(引者注:南齊時期)石窟佛造像的衣紋,與云岡、龍門的北魏石窟在雕刻技藝、紋飾樣式上是一致的,而在質感風格和紋飾的細部表現方面則有所區別。……云岡者顯凝重厚實,棲霞者顯輕薄飄逸,龍門者似有承繼棲霞之風的跡象。”[25]
近年則有費泳的研究最為深入,費泳將發掘出土的陳《江總碑》有關記載與棲霞山石窟現存龕像進行了對應,認為:棲霞山下20窟(此為費泳編號,下同)即無量殿對應的記載為“……造,齊文惠太子隨喜,齊豫章獻王隨喜,齊竟陵文宣……未明寶寺十五人”;下21窟、下22窟對應的記載為“齊雍州刺史田奐為巴陵王造……沂令明仲璋造”;下024窟(即三佛窟)對應的記載為“宋太宰為霍夫人造未成”;下019 (即雙佛窟)對應的記載為“梁東陽(揚)州刺史番禺”[26]。費泳認為下024窟所涉太宰為宋江夏王劉義恭,其死于宋永光元年(465年),“說明宋太宰所造龕像工程應已顯大略,但未能竣工”[27]。這將棲霞山石窟始鑿年代從以往認為的南齊提前到了劉宋,且與云岡始開年代接近。下024窟平面呈方形,三壁三佛,每壁主佛佛座與二脅侍菩薩的蓮座各自獨立而緊靠在一起(圖八),龍門賓陽南洞正壁造像的整體布局與此相似,只是佛座與菩薩座之間有較大空隙,不知是否因為賓陽南洞規模很大,所以能表現出間隙來。下024窟的這種布局可能表現的是劉義恭始創時的形態,“……漢地以5世紀中期前后為界,坐佛軀干高和寬之間的比例普遍發生變化,表現為由上身方短向上身修長轉變。這在古印度秣菟羅佛像由貴霜向笈多的風格轉變中發生過。漢地,約5世紀中期以后,佛像身軀較之前漸趨拉長。下024窟(三佛窟)正壁及東西側壁分別雕一坐佛,三坐佛的軀干高、寬比例,明顯較下022、021、020、019四窟坐佛要短許多,所以發生時間應更早。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死于永光元年(465年),下024窟的三尊坐佛應在義恭死前已開鑿軀干的大形”[28]。關于下026窟的年代,“下026和下024兩窟毗鄰,坐佛軀干高寬比例類同,二者呈現出的共性特征又有別于其他龕像,應視為同期造像”[29]。關于下021、022的年代,“下021、022兩窟主尊高度相似,……若依據閻文儒先生的考證,‘田奐’應為‘王奐’,《南齊書》卷三《武帝》載,王奐于齊永明九年(491年)被任命為雍州刺史,齊永明十一年(493年)伏誅。……下021或下022兩窟中的一窟應建于491至493年之間。下021窟主尊造像損壞嚴重,造像細節無法辨識。下022窟的佛衣樣式為‘褒衣博帶演化式’,軀干較下024窟明顯拉長,發生時間定在6世紀上半葉似更合理。這樣看來下021窟便更有可能是5世紀末王奐所造”[30]。費泳扼要總結到:“下022、021、020、019四窟為一組,其開鑿以無量殿為中心向左右兩側延伸,無量殿主尊約建于5世紀末,在6世紀初被改造。下021較無量殿開鑿時間相近或略晚,約為491至493年,接下來開鑿的為下022和下019兩窟,約建于6世紀上半葉和6世紀中期。”[31]費泳將下024、026窟的年代向前調整,將下019、022窟的年代略向后調整,維持無量殿大佛為南齊時期的既往判斷,就這一核心點來說,費泳與前人沒有根本分歧,但增加了棲霞山石窟在時間軸線上的豐富性。與本節主題相關,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下020窟即無量殿大佛坐于通壁的高壇上(圖九),這在時代略晚的下019雙佛龕中得到延續。下021窟正壁主尊兩旁現存佛壇為石塊砌成,不能判定是否本來就是如此,但這不妨礙通壁佛壇存在于棲霞山石窟且早于龍門石窟的事實。

圖九 南京棲霞山千佛崖下020窟無量殿大佛

圖八 南京棲霞山石窟千佛崖下024窟內景
盡管棲霞山石窟遠不及龍門北魏窟豐富,但上面的分析已經可以看出,棲霞山石窟當給予了龍門石窟直接的影響,這不只是佛、菩薩的形態和服飾特點相似的問題,也不只是兩地都有通壁佛壇而棲霞山更早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寺院造像布置方式和建康文化對洛陽影響程度的問題。石窟的形制和布局本質上是佛殿內部狀況的反映,通壁佛壇一則可能表明南方佛座較高,這從脅侍菩薩的蓮座多為兩層蓮花可推知,一則可能表示當時佛殿中一鋪造像的陳列方式。這種陳列方式見于龍門北魏窟和云岡第三期,不見于云岡第一、二期,但在棲霞山出現得較早,以棲霞山石窟為龍門的源頭,并從龍門再傳播到云岡,自然要比認為從已經走下坡路、且本來沒有這種陳列形式的云岡產生并逆勢傳到龍門要更說得通。至于說從大的歷史背景上,建康給洛陽以巨大的影響,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棲霞山石窟影響到龍門石窟只是這個大背景下一個方面而已。如果不限于石窟,就會看到不少細節更能反映龍門石窟與南方文化的關系,以賓陽中洞為例,雖說“準代京靈巖寺石窟”[32],但這大概只是籠統而言繼承在平城為新故帝王造窟的傳統,并在佛像特征上盡可能保留點鮮卑人特征以象征皇帝,在其他方面,如菩薩的裝飾、帝后禮佛圖、維摩文殊對談都與云岡差異顯著,不能不將之歸結為遷都洛陽后向南方學習模仿的結果。賓陽中洞窟頂的飛天或許更能說明南北文化的交融,一種飛天作蹬腿飛行的姿態,還保留著云岡特點,但飛天的頸后的飄帶呈曲折的三角狀,將其與南方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了(圖一〇)。

圖一〇 賓陽中洞頂部飛天
綜上,我們不否認北魏遷洛以后,云岡還可能對龍門有一定的影響,但比較強烈的影響如古陽洞所見,肯定是短暫的。在云岡全面進入第三期以后,云岡對龍門的影響也還會有,但必定是輕微和極其局部的,龍門和云岡表現出的共同點,主要應該是龍門傳遞給云岡而不是相反。這不僅是因為作為新都的洛陽不斷發展而舊都平城在不斷退步,更主要的是孝文帝遷洛以后得以放手漢化,全面向南方學習。在都城建設上派遣蔣少游去建康名為觀禮實質偷學的故事廣為人知,大體上也屬于都城建設一部分的石窟也模仿南方實在情理之中。以賓陽中洞為代表的帝王窟充當了漢化的先鋒,其他洞窟自然唯帝王窟是從。從三壁三龕的窟形和布局方式,到通壁的高壇,再到佛和菩薩的形態和服飾,保存狀況欠佳的南京棲霞山石窟仍然很能說明問題。因此,我們認為,以棲霞山為代表的南方石窟和南方文化直接影響到了龍門石窟,龍門石窟又傳遞給了云岡石窟,云岡石窟第三期表現出很多新特征,近源在龍門,遠源則在棲霞山石窟。
小 結
綜上所言,云岡石窟對河西地區沒有產生過多少影響,但對東部地區的影響如宿白先生所言是巨大的,從宏觀上來說東部地區石窟幾乎都受到過云岡石窟的滋潤。盡管如此,云岡石窟對東部地區的影響需要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進行具體評估,平洛道上小型石窟接受云岡影響的時間可能在遷洛之后,云岡先影響龍門然后龍門又影響云岡,所反映的情況不只是石窟本身,更與歷史狀況和自然地理之間存在關系。只有全方位考慮,我們才可能對北魏首都從平城遷移到洛陽所引起的石窟乃至文化上的變遷情況有更為客觀公允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