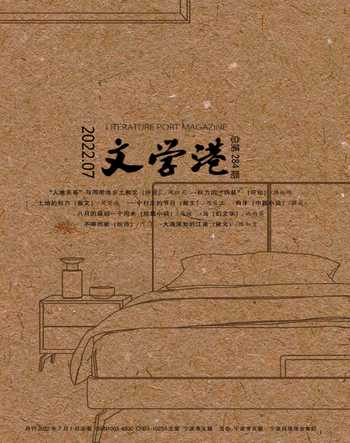在藍色的輕卡上
吳佳燕
1
時間到了。天還是黑的,泛著一絲幽藍。昏黃的燈光像是熬夜人的眼。靈車倒停在殯儀館的門口,是一輛藍色的輕卡汽車改裝的。她想起上一次坐這樣的汽車還是上小學的時候,她和五六個大人孩子正在路上走著,要走很遠的路去給親戚家一位剛出生的孩子慶生,意外地被堂哥家開汽車的舅舅順路捎上。她和小伙伴扶著欄板站在駕駛室后面敞開的車廂里,有種迎風而立、颯颯有聲的歡暢與威武。我們那兒的說法,辦滿月酒叫整“祝米酒”,是在孩子滿月這天,孩子外公外婆這邊的親屬相邀著一起到小孩家送“祝米”。“祝米”多為嬰兒的衣服用品及糕點、酒水之類的禮物,有祝喜祝福的意思。
30多年后,她又上了這樣的藍色汽車。不過這次是被招呼上了前面駕駛室的副駕。上次是為新生命的降臨,這次,她是要送父親到另一個世界。父親的靈柩已安放在后面的車廂里,黑漆發亮的棺木上搭著紅色的蓋布。她披麻戴孝,抱著父親的白色靈牌,端坐在副座上,靜靜地等待父親的出殯。
外面慢慢喧鬧起來,主事幫忙的人,守靈三宿的親人,早早起床從附近再次趕來的鄉鄰,在為送父親最后一程做著準備。車子已然發動,隆隆響著,司機還沒上來。她一個人木木地坐著,感覺有些寂靜。不,她不是一個人,她跟父親在一起,如此親近,又如此遙遠。爸爸,就讓我最后再陪陪你吧,她在心里哀哀地念著。
要啟程了,靈車排在隊伍的最前面,還有一輛皮卡做的電子鞭炮車在前端開路。后面是花圈車、工程車、裝滿送行者的一輛輛小車。她不知道妹妹在哪里。出殯時,姐妹倆分別抱著父親的靈牌和遺像,上車時就分開了。應該就在后面的花圈車上,靈牌和遺像是要前后護送著父親的。司機跳上車來,是個穿著深藍色工裝的中年男人,面目模糊,她用眼睛余光瞥見他把手機接上擴音設備,哀樂頓起,雙閃打開,靈車啟動。她身子往后一傾,本能地去找安全帶,沒有。“副駕上沒有安全帶嗎?”她問。“這樣的汽車主駕有,副駕上沒有呢。”男人答道,他是系著安全帶的。她只好用腳死死抵著副駕前面的一個坡墩,左手扶住座位一邊,右手把靈牌穩在懷里。父親的長眠之地她昨天就去看過,知道路途偏遠且坡多彎急。
殯儀館位于縣城西門的一個山坡上,一條馬路將其劈為兩半。這里的山村還可以土葬,殯儀館沒有火化的業務,其他的喪事一條龍服務都可以提供。是一座帶院子的U形兩層樓,樓下是幾間用來布設靈堂的大廳,樓上是餐廳和棋牌室。院子外面就是馬路,馬路的一邊是停車場,另一邊的梯田里豎著用來售賣的各種墓碑和墳頭。
這地兒她從來沒來過,毫無印象,而“西門”這名字她是熟悉的。現在她知道了,西門這荒郊空曠之地曾經魚龍混雜,充滿市井氣息。她恍惚記起小時候跟母親到蠶繭站賣繭,就是在西門。也是坡上馬路邊的一個開放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濃蔭蔽日的黃桷樹,她跟妹妹常常在樹下歇著等母親。等得久了,就拿上母親給的零錢,去路邊買地瓜吃,脆甜多汁,既解渴又飽腹。還有她中考時的考場,正是在西門坡上的城廂中學。中午從考場出來,父親早在校門口等著,把她接到附近的租處吃飯——其時父親正跟著做殺豬生意的肖玉強干活,常常需要起早貪黑,屠宰場和臨時的住處就在西門坡下。她從沒見過父親殺豬的樣子,只記得他帶回來的油渣很香,用來炒青菜或下面條都是人間美味。而中考時那頓午飯讓她驚嘆的是父親做的蛋花湯,她到現在都還記得。父親把蛋液一點點倒入沸水中,開出一大朵一大朵金黃色蛋花的情形。她到現在都不明白,父親是何以只用一個雞蛋就可以做出一鍋子金燦燦的、飄著點點蔥綠的蛋花湯的。
出殯的隊伍要從坡上往下走,過縣城、郊區,再走彎彎長長的山路,把父親送到一個叫石安的村子,那里青山環繞,天空澄凈。天色開始發白,下坡的路上竟然有些堵車,有為了生計早起出攤的人,還有一些步行或坐在摩托車后面的穿著校服的學生——看來她記得沒錯,沿著馬路往上走,翻到西門坡的另一邊,正是城廂中學。
2
車隊徐徐前行,車燈閃爍,走走停停,像熹微中蜿蜒的一條河流。終于穿過破舊逼仄的老城區,走到新城后面的北井大道。這是一條沿山腳開挖的新路,遠離鬧市區,因此變得開闊舒展、暢通無阻,她也從一種緊張中松了口氣。“北井大道”這個名字也是新命名的,她初聽時以為是“北京大道”,像很多縣城的街道、樓盤起一堆大名兒或洋名兒一樣,有些啞然失笑。后來大伯來看望父親時閑扯——他是一位對歷史饒有興趣的考證家加演說家——她才知道是自己無知了。“北井”正是她的家鄉小城巫溪建縣以來最早的命名,是東漢時期從巫縣分設而成,比她由家鄉的小三峽、大寧河引申記住的古稱“大寧縣”要早得多。也是因為這次父親去世,她才發現,大伯不僅很會“講古”,還會唱喪歌。守靈的一個深夜,她坐在靈堂的火盆邊半睡半醒,忽然感到喪歌的聲音變得有些熟悉、輕柔,抒情而綿長,像母親的手在一下一下拍著搖籃里的嬰兒。不是請的喪鼓班子的師傅唱的,他們雖然專業也敬業,但不會這么細膩有感情。她睜眼一看,果然是大伯在唱。他端坐在一只紅色的塑料凳子上,身體微傾,唱幾句就停頓一會兒,喪鼓聲起,師傅們在很有默契地配合他。她驚訝之余,心里一陣刺痛。沒想到大伯連著兩宿不睡覺陪著喪鼓班子,第三天晚上竟然親自上陣了。他的唱腔舒緩低沉,如泣如訴,每一句唱詞都是以“你”開頭。大伯在回顧父親的一生,他在跟父親講話,是一位兄長在表達悲痛與安撫。這歌聲如天籟之音,讓她緊繃多日的疲憊、凄惶、痛惜有所舒解,內心一下子安靜下來。她枕著大伯唱給父親的安魂曲陷入更深的睡意,迷迷糊糊中想起小時候一個夏天的夜晚,小學楊校長到村里來家訪,坐在院子里對著一圈人表揚她的學習成績。父親聽了并不喜形于色,只是不停地搖動竹扇給一旁的她扇風祛暑,一下一下的,就像這夜半的歌聲一樣。
哀樂聲中,她沉浸于思緒,自我撕扯。司機一路無話,看來是個沉默寡言之人。然而沉默中有某種積蓄的躁動。剎車和啟動都變得有些急迫,她看到他在開車的間隙,堵車、錯車或等紅燈的時候,一次次拿起手機。急性子?手機依賴癥?或者像詹姆斯·丹克特在《我們為何無聊》里所說的置身永無止境尋找新奇事物的“倉鼠輪”,需要每一個時間都被填滿?這習慣不好,不安全,何況她沒有系安全帶,更何況,這會驚動父親。她頻頻側目,眼睛伸出爪子,希望可以把他的手牢牢摁在方向盤上,或者把他的手機釘死在臺面上。但是在寬闊的北井大道上,車隊還是被壓著走得很慢(后來她知道是為了將就看好的落葬時間,以及等后面掉隊的車子),男人又忍不住拿起了電話。從通話中她才明白他是在給前面開路的鞭炮車上的人打電話,極不耐煩地催他們走快點。一次下坡的時候,因為遇上紅燈剎車太急,她聽到父親的靈柩有些往前移動發出沉悶的觸碰聲,她終于忍無可忍對他大聲喊道:“你能不能開穩點,別看手機了?!”
司機無言以對,終于消停下來,慢慢勻速前進。這個只想著早早完成出車任務的男人哪里知道,靈車的且行且慢正是為了讓父親最后看一眼這個他無比熱愛的人世間,在奔赴黑暗之前把他曾經生活的腳印一個個撿起。車子到了縣人民醫院。這是她的傷心之地,父親生命的最后一站。一周的住院經歷有如煉獄,她實在沒有勇氣去想。她只記得那秋日里溫暖的陽光,一遍遍從窗外照進來,灑在父親的病床上,又燦爛又絕望。她很想把父親推出去曬曬太陽,或者痛痛快快地吃頓大餐。可是被病痛折磨的父親,連小小的一粒降壓藥和止痛片都不能好好吞下去。終于有一次讓父親切切實實地見著了陽光。那是她和在隔壁病房照顧老母親的鄰居大叔一起,把父親從住院部推到前面的門診部去照背部CT——父親老是喊背部又疼又癢,要人不停地給他抓撓按摩,以至于在父親生命的最后兩周,只要他一叫喚她就條件反射地坐在床邊的小馬扎上給他側身按背,以至于父親走后她睡覺時還下意識地在愛人后背上做著摩挲的動作然后猛地一驚。連接住院部和門診的是二樓的空中走廊,檢查回來的路上,陽光直直地拂下來,她把病床停住,指著太陽指著廊下走來走去的人們對父親說:“爸爸你看多好的太陽啊,你一定要早點好起來,我們下去走走曬曬。”在那一瞬間,她想起了武漢疫情期間那張醫護人員陪患者看落日的著名照片,她不要那場景多么唯美動人,她只要父親像那個老人一樣可以活下來。而且不光是看一張別人的照片,父親和她一起經歷了2020年的武漢疫情。她是幸福的,在那些艱難恐懼的日子里,有父母從老家趕來和她團聚過年,母親還扛著一袋子臘肉,沒想到是自投羅網般來到疫情的重災區,和她一起擔驚受怕地關在家里70多天。還有父親的病,更讓她感到壓力倍增到一觸即潰。現在想想,那是一段多么難得的親子時光,她長大以后從來沒有這么長時間地陪過父母,想方設法地給他們做飯,陪他們打撲克,像是要把一生的欠缺都補回來。萬幸的是這期間父親病情穩定可以不用去醫院,而且心情舒朗,還長胖了一些。因為有父母在,小小的樓房成為疫情之下的避風港,讓她踏實心安。誰承想父親挺過了2020年的武漢,卻未能挺過自己的病。
3
天色亮了起來,東邊露出了一抹紅云。藍色的輕卡正向著那抹紅云緩緩移動。又是一個晴天。悲傷的時候難道不應該是風雨如磐逆流成河嗎?而父親留給她的總是陽光。住院的時候是這樣,走的時候也是這樣,大片大片的陽光照著父親從醫院到殯儀館的路,她在大片大片的陽光里天崩地裂大放悲聲。出殯的前一天,難得的秋雨嘩嘩地下了起來。因為父親的病亡,把散落各處的親人凝聚一起,曾經疏遠淡薄的家族變得親厚團結。幺爺爺家的大姑媽從山里趕來送父親。她犯有頭暈癥,不能坐汽車,是坐在陳姑父的摩托車后面來的。兩個人穿著雨衣雨鞋,一身雨水地走進來,天黑之前再冒著暮色一身雨水地趕回去。沒想到今天又晴了。這陽光如此善解人意,像父親永遠溫和的笑臉,他不要看到親人們的悲愁。她想起去年十一放假前,在去接孩子放學的路上接到父親電話,問她這個假期回不回老家,聲音里有隱隱的期盼和怯色。而在得到她的肯定答復后,父親的聲音一下子充滿了歡快高亢的情緒,像撲面而來的陽光下的花朵,讓她愣怔而感動。在整理父親的遺物時,她沒想到在一個筆記本上翻到令人淚崩的一頁,上面工工整整地記著一大家人的姓名和生日,上到父親80歲的姑姑,下到他3歲的小外孫女——她妹妹的第二個孩子。這都是他時時掛念于心、至親至愛之人。
陽光一遍遍照耀著回家的路。對她而言,有父母在的地方才叫家。長大之后在外求學工作、成家立業,回家就是回老家,回家就為看父母。以前回老家是為了陪父母一起過年,最近幾年更多是因為父親的病。想起去年春節,因為疫情的余波綿延,她原打算不回老家,可是聽說父親鼻子又流血了,立馬跟愛人孩子去醫院做了核酸,正月初二早上天沒亮就開車出發。走著走著太陽就出來了,她在陽光里揣著隱秘的擔心和興奮,她想給父親一個驚喜,直到快下高速才給妹妹打了電話,告知要回家吃中飯。父親的電話隨即就到了,那聲音里的喜不自禁呵,勝過這一路陽光。沒想到那是陪父親過的最后一個春節,她陪了父親兩天,又馬不停蹄地趕回武漢。在那兩天時間里,她陪父親去醫院看病,一家人照了全家福,還陪父母結結實實地打了一天撲克——這是互聯網時代之外的他們,唯一的娛樂方式。父親打得很盡興,原計劃去外面吃晚飯也取消了,“還是自己煮的好吃”,這是一貫節儉的他們找的說辭。11點多散場時她聽到父親還在由衷地感嘆:“今天真開心啊!”她沒想到的是,這次的全家福成了父親生前的最后影像,父親的遺像就是用的那個時候的照片,開心中透著愁苦與病容。她甚至覺得除了病容,都沒見過父親老了的樣子。怎么父親就沒有了呢?
縣醫院過去就是頤博園小區,這里面有父母的家。因為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征收與房屋拆遷,父母從她生長于斯的鄉村搬離,住上了附近新城里的樓房。這是父親生命里最后三年居住的地方,離住院部不過三站路,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她想起把父親從重慶轉院回家的路上,多日的陰霾轉為晴天,妹夫開著車,父親安靜地在副駕上半躺著,有時候還要起身坐一會兒。她和母親坐在后排,一面心里打鼓,一面盡量平靜地觀察和安撫父親,給他遞水、按摩和沖蛋白粉喝——因為腦部水腫帶來的風險,醫生原本是建議用救護車轉院的。那時候的父親因為病情,腦子已經偶爾犯糊涂了,時不時嘴里會冒出幾句出牌之語,讓她覺得這唯一的娛樂方式也可能給父親帶來最后的安慰。因為回家和陽光,父親變得清醒和高興,還認出了高速路牌上的字。她和母親心里也稍許松快,但是她又深陷于某種放棄的痛苦中。在服務區,父親甚至提出也要去衛生間,他忘記了自己插著尿管。在醫院的病床上,他多次想下地自己去廁所,并一遍遍質問母親:“怎么能在床上解手呢!”他是一個多么講究愛干凈的人。病后的父親對母親無比依賴,住院期間在醫院散步時會拉著母親的手,讓母親很不好意思。即便在轉院回家的路上,他還幾次提出,要跟她換座坐在后排挨著母親。她哪里料到,葬禮之后,她把母親帶回武漢的家,母親也是這樣有事沒事地湊在她跟前挨著,依賴于她。住進老家醫院之后,父親有次清醒又茫然地問道:“我們這是在巫溪?我們已經回家了嗎?”確認之后父親熱淚涌出,她把頭扭向一邊。
她有時覺得關注逝者年齡是件很殘忍的事情,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被生卒年兩個數字鎖定。長度正常自然死亡的,或可稍微心安,可那也是一個被世間諸多關系情感牽絆的、活潑潑的生命的消失;而生命長度偏短或突然被掐斷的,尤其叫人難以接受。都說死亡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公平的事,可是讓一個人還未真正老去就被病魔奪去生命,讓一個性格溫和、一生與人為善的人就這樣畫上生命的休止符,這公平嗎?死神面前,如何鳴冤?
因為父親,她對醫院醫生沒有選擇地信任,她愿意相信一切有關的鄉村迷信說法。她還記得從重慶出院之前,因為診斷方案的突然改變,讓她在病危通知書之外看到了救治父親的一絲曙光。她拿著醫生開出的petCT檢查單一邊準備下樓去繳費預約,一邊興奮地對妹夫說:“看來地理先生說得對,爸爸這次應該可以挺過去呢。”地理先生是她們老家的叫法,其實就是風水師。在得知醫院下達病危通知書的那一刻,她第一次開始正視有可能失去父親這個現實。而這個話題之前在她那兒一直是某種禁忌。只要母親或妹妹旁敲側擊地提起這件事,都會被她疾言厲色地堵回去。而這次,在電話里猝不及防的母親的哭聲中,在奔赴醫院的火車上,她不能不去想這個殘酷的可能。她給妹妹打電話,要他們得有所準備。原來妹夫早就在思謀此事,原來父親在去過一次石安(妹夫的父親長眠此地)后早就看上了那里的青山綠水。妹夫請地理先生去看那里的風水,覺得很不錯而且說據此看出父親的大限未到。這跟醫院在建議轉院后又讓做petCT檢查的轉變不謀而合。所以她才如在深水中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如此興奮。然而,冷靜之后,她跟在下鄉扶貧的主治醫生通了電話,隱隱明白無論是放射性損傷還是癌細胞占位引起的腦水腫,當務之急都是消水腫而不是去做昂貴的petCT,而且父親目前的不穩定狀態也無法在近半個小時內固定不動接受檢查。醫生對她臨門一腳取消預約表現出的慍怒證實了這一點,也加重了她內心的罪感。她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善于做選擇的人,尤其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之前父親鼻部腫瘤復發,兩次化療和PD1效果都不明顯,也是在醫生建議下到西南醫院做了粒子植入術放療。應該說,自父親生病以來,她一直在積極地為父親操心聯絡,學習了解病情、托人找好醫院好醫生,一次次到醫院溝通照顧;父親也一直在積極地配合,忍受著身心的痛苦和煎熬,那么努力地想活著。然而,粒子手術之后不久,父親的腫瘤縮小了,鼻子通暢不流血了,腦部卻有了進展轉移,病情陡轉急下,從復發到去世才半年多。她不知道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致命的問題,不知道在醫生的治療過程中她的選擇和判斷又起了怎么樣的作用,為此在以后的余生里她都將帶著深深的愧疚和罪感。
父親的生命被永遠定格在11月28日這天上午,離他的64歲生日還差4天。按民間的說法,如果一個人病危時挺過了自己的生日,那么這個劫就會安全度過。父親沒能扛到他生日那天,這該死的迷信說法,說好不靈說壞靈。她沒能見到父親老去的樣子,自己卻成了普希金所說的“遽然變老的人”,讓她在40歲這一年,感受到深入骨髓的喪親之痛和中年疲態,覺得自己還來不及體味“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豪情和美好,就倏然進入四面埋伏、捉襟見肘的中年壓力。馬克爾斯說:“父母是隔在你和死亡之間的一道簾子。”如今,這道簾子被父親掀開,以后她將無所遮擋地直面死神了。
微熹初露,她對著頤博園高大的暗影,默默地說:爸爸,我們回家了!
4
晨曦中,藍色的輕卡從北井大道駛過嶄新的縣城,駛過她生活過的田野和村莊,再蜿蜒上行,往深山里開去,光線在兩旁后移的樹影中時明時晦。她從情感記憶的深處潛回,聽到旁邊的司機在跟她說話。
“你,你還好撒?”他問,“莫太傷心了。”
“我有一個朋友,跟你一樣,個頭小小的,戴著個黑框眼鏡。”他奇怪的開頭讓她感覺這是一種蹩腳的搭訕。她不吭聲,仍舊呆呆地坐著。
然而男人緩慢的講述中有一種堅持,并終于把她拉回神來,代入他的故事。
“其實以前我并不是開靈車的,我在成都上班,有份體面的工作。”男人換了一種開頭。
“哦!”她終于應了一聲,因為“成都”這兩個字。這是一個令她感到無比親切的城市,那里生活著她姑媽一家,而且有父親的奮斗足跡——在她上小學的時候,就是因為父親在成都打的幾年工,讓她們家的土房子變成了兩層的小樓房。母親說,平時溫溫和和的父親關鍵時刻總顯得很有決斷,比如分家的時候他借貸了350塊錢買下村里的保管室讓剛出生的她有個安樂窩,比如她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那天他立馬騎著自行車去信用社貸了一萬元給她作學費。她還想起父親說的,當年在成都空閑的時候就和小表哥騎著自行車圍著城市一環、二環、三環一整圈一整圈地轉,那是多么難得的愜意而飛揚的時光呵。
“可是后來因為這個朋友,因為我媽,我從成都跑了回來,把工作也搞丟了。”他接著又說,但是讓她聽著有些迷糊。可這就是男人的講述方式,跳躍式地,顛三倒四地,沒頭沒腦地,獨立成段地,如珠子般一顆一顆往外蹦。她聽著聽著實在忍不住了,就在這些短句中時不時插上幾句問話,就像要用一條線把這些蹦落的珠子串起來。后來她明白了,這不僅是男人稍顯木訥的性格所致,還是一種讓她從悲傷中短暫抽身、參與講述的策略。
原來那個女孩是他的初中同學,很活潑爽朗的一個人,特別愛笑,如陽光撲面。他喜歡她很久了,然而真正得到回應,卻是在成都上中專的時候。一次在校外過馬路等紅綠燈,他猛然抬頭,看到女孩就笑盈盈地站在斑馬線的另一端。
這次的邂逅讓他的初戀如愿所償,“我們好得跟一個人似的。”他說。
“后來呢,那女孩是做什么的?”她問。
“她當時在成都打工。她初中時成績就不好,畢業后就沒讀書了。而我中專畢業后在成都一家公司做文職,她又回了老家。”
這為這段感情的終結埋下了伏筆。原來男人有一個強勢的母親,在老家一個城鎮當領導。她反對他倆結婚,因為門不當戶不對,因為女孩沒有正式的工作。女孩是個心氣兒很高的人,面對他母親的偏見,一氣之下離開他跑回了老家。男人又急又氣,撇下成都的工作追了回來,一邊跟母親理論一邊找女孩挽回。那真是一地雞毛焦頭爛額的一段日子。
“她還為我懷了孩子,”他又說,“可是我媽就是不接受,拿各種事情來要挾我。”他終是個懦弱之人,沒能頂住母親的軟硬兼施。或者說,他們80初的,還不是那種為了自己可以不管不顧做出多么激烈事情的一代人。為了愛情,把好好的工作丟掉已經算是驚天之舉了,而且他的骨子里本來就有一種四川男人的“耙耳朵”性格,結婚后是“妻管嚴”,結婚前是“母管嚴”。最終女孩打掉了孩子,再次遠走他鄉。
“封建家長制”,她心里不由得冒出了這個詞兒。她又想起了愛講古的大伯,身上也有不少封建余毒,重男輕女,家教嚴苛。在生下兩個堂姐后大伯又要了兩個兒子,四個孩子的負累加上超生的罰款讓這個農村家庭苦不堪言,一年到頭連個年豬都殺不起。她還記得小時候大堂姐在萬州讀中專,寒暑假總會從圖書館借些書回來,為此她經常去堂姐家蹭書看。有次大堂姐的一個初中男同學來看她,并邀姐妹倆去當地的一個著名景點雙溪溶洞玩兒了一趟。大伯晚上回來得知后大為震怒,讓堂姐兩姊妹和伯母三人齊齊跪在地上,狠狠地教訓了一頓。相比之下,她的父親又是多么開明的人啊,從來不會因為她是女孩另眼相看,從小到大,無論學習還是感情上,從來不過問、操心。她就像在陽光雨露中自由生長的一棵樹苗,父親從來不去修剪枝條,只是在背后培土施肥、默默支撐。
“她走后,我媽借助她手上的關系權力,給我找了新的工作,而我干了幾個月就跑了,然后她又給我找,我沒做多長時間又辭掉。我們就這樣相互對抗、折磨。直到后來我到殯儀館開靈車,才沒有再換,這是我自己找的一份工作。”男人又說開了。她對這個男人開始有了一份理解和同情,她不知他每次開著靈車把一個又一個亡者送上山的時候,自己是懷著怎樣一種悼亡的心情,為逝去的青春和愛戀,也為自己的懦弱和最后的掙扎。
“但是因為她老家還在這里嘛,她后來的消息我也會斷斷續續地打聽到。而且我們好的時候就去過她家里,她父母對我很好,就是把我當作他們的女婿。我現在還偶爾去她父母家,給他們買一些東西。我知道她在北京嫁了人,對方是個做生意的人,年紀比她大很多。”
“哦,那你應該放下來了。”
“是啊,我后來也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我老婆就是我媽要找的那種人,有自己的工作,很顧家,而且對我父母也很孝順。”他頓了頓,突然情緒流露地說道:“但是我就是不舒服啊,只要想起她就覺得心里難受,覺得對不起她。”
她突然覺得對這個男人有了開導的責任,這個在靈車上訴說青春遺憾、袒露內心傷疤的人,反而給她深深的安慰。誰的青春沒有明媚的憂傷,誰的人生沒有刻骨的遺憾,但是生活還要繼續,我們仍要負重前行,在可貴的活著中繼續經歷感受。
“那你們的事你老婆知道嗎?”
“她都知道,但是沒管沒問,當然,她若想管也是管不了的。她對我不錯,尤其是對孩子和我的父母。可是我對她沒有感情啊,我的感情還停留在年輕的時候,想拔也拔不出來。我甚至想過離婚,但是看著兩個孩子,一個剛上初中,一個還在上小學,又不由得把這個念頭打消了。你說人生為什么要有這么多牽絆和不自由啊,又是父母又是孩子。我只好把自己跟她的關系劃了個界限:只要她回老家有需要,我一定去接她陪她,而且是像朋友一樣光明正大的;而若她離開了老家在別的地方,我是不能去找她的。”
她聽了心里一戚,人生有所牽絆應該是種福氣啊,看來,他還體會不到那種“子欲養而親不在”的心情。
“那你這樣不挺好的嗎?”
“可是她過得不好啊,前兩年她得了重病,是肺上的毛病。我想肯定跟她心情抑郁有關。她老公對她肯定也不好,有句古詩怎么說的,商人重利輕別離。”
“啊?”她不由得驚愕出聲,沒想到青春愛情故事的后續如此陡轉悲涼,現實到底還有多少意外和突襲埋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那你怎么辦?她現在的病咋樣?”
他的聲音有些沉重:“我能怎么辦?我又不能飛到她身邊去照顧她。我除了給她發微信關心她,還有就是給她轉錢,讓她安心養病。她后來做了手術,然后是化療、放療,病好多了。但是,我還是很擔心她。我甚至想:要是我當初不顧一切地跟她結了婚,她是不是就不會得這個病了?”
她也難過,為父親也為那個不幸的女孩,兩人都籠罩在深深的遺憾與自責之中。她還要試著把這個長情的男人從傷感中拽出來:“那你已經做了不少啦,還能怎樣呢?”
“她生病之前回過一次老家,我陪她吃飯、摘菜、爬山、下河,在老家的田野山坡上瘋跑,像我們小時候那樣,真是好開心啊。沒想到好景不長,她就生病了。你說,現在我還要不要守著這個界限?萬一她病情惡化,我要不要飛過去看她?”
她看著這個痛苦而糾結的男人,不知道怎么給出建議。如果真到了那個時刻,男人的決定應該是可以被理解的吧,那是對一份情感一個生命最大的交代和慰藉。然而,誰都會祈禱,那個時刻永遠都不要到來。在病魔與死亡面前,青春的遺憾情感的虧欠算得了什么,平靜的生活正常的人生多么重要!這個開著靈車、心情復雜的中年男人,是在以這樣的方式積德祈福、緩解緊張還是預演悲傷?
除了祈禱,唯有對保留生命全力以赴地努力,趁還來得及,一切都值得。
5
講出這一切,男人似乎安心了很多,卡車拐入石安的村道,路面有些崎嶇不平,男人專注地開著車,車廂復歸于平靜。她沒想到在送父親的最后一程途中,有另外的故事插入,有另一個跟她一樣飽受中年生活碾壓的人會跟她握手交心、同病相憐。這也是她和父親一起承接的冥冥之中的分享與安慰?這樣的插曲,一如這一路上漸行漸明的天色,虛幻又真實。
真實的還有父親生命里的遺憾。運城,是他想再去而沒有去成的地方。這黃河邊的北方小城留下了父親的青春與汗水——他在此的五年軍旅生涯,成為他人生的一抹亮色。他愛吃面條的習慣,他愛看軍旅題材的電影電視,他珍藏的一本黑白相冊和三等功獎章,都與他在運城的當兵經歷有關。那是上世紀70年代末,從山村走出的父親到的最遠的地方,看的最大的世界,擁有的最昂揚熱血的芳華。盡管他并沒有因此改變人生命運復員回了老家,卻為人生的精神底色加持,還收獲了一班老戰友——他們在今后的底層生活中相互幫襯支撐,包括對于父親的病。她聽父親提起一次戰友聚會,相約著再去運城。父親沒有去成,他那時候已經生病了。后來有回她到北方出差,徘徊在運城的古墻下、河灘邊給父親打電話,聽他講當年的部隊故事,跟他說要陪他一起再來運城看看。她舉著電話走走停停、思緒無限,一邊給父親描述運城現在的樣子,一邊想象著40多年前風華正茂的父親在這片土地上的生活。
還有北京。父親在家養病的時候,曾有想去北京轉轉的念頭。故宮、長城、天安門,這是他們這代人的情結。她把這事記在心上,還準備帶父母坐飛機去北京,甚至已經提上日程:父親在重慶復查完怎么到武漢,她哪天請假帶父母去北京,她聯系的好友怎么開車來接,住什么酒店,在京行程怎么安排。可是人生呵,總以為還有大段的時光,還有很多來得及,結果為什么又有那么多猝不及防。沒完沒了的疫情,母親對農事的心心念念,她的時間精力的騰挪,還有父親病情的反復,導致去北京的事情一再延宕。最后那次臨門一腳的取消,讓她又氣又痛,仿佛是某種不好的預感。沒想到一個月后,父親的病情就陡轉急下,最后的日子都在醫院。而她在陪父親的最后一周內,接到了要去北京開會的通知,是很多人很看重的文藝界盛會。她根本沒有心思去管這件事情,她要陪父親把這千鈞一發的難關挺過去。但讓她痛徹心扉的是,父親還是遽然離世,冥冥之中似有某種體貼和托付。她沒有預料到的是,一個月后,當大巴車行駛在長安街上,當古典莊嚴的天安門城樓映入車窗,她在一眾注目拍照中內心翻江倒海、涕淚滂沱。
她回想父親生命的最后十四天,并沒有什么交代。好像沒有什么讓他不放心的,或者他根本就沒想到,他的病已經到了需要交代的地步。當她拿到核酸結果,第一時間趕到父親病床前,就想問問父親有什么想吃的、要做的,但是父親一如既往溫和的笑臉制止了她,讓她放下百般擔心如常地陪在身邊。母親說在她面前父親吃飯、打針、吃藥都要乖很多。而到了晚上她回到醫院旁邊的小旅館,母親一人在醫院陪護時,父親就有些鬧騰。一天晚上竟然搖搖晃晃地下床來,到病房的窗戶前、醫院的走廊上,這里那里地走走看看。她聽母親講后,驀地想起魯迅在《這也是生活》寫的:“我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欲望。”父親肯定不知道這篇文章,可是他的表現不就是這樣子的嗎?
她的心里悲愴無比,想起父親走后在她夢里變成了一個武林高手,可以在人世間自由穿行、叱咤風云。那不就是對病魔的掙脫和對正常生活的渴望嗎?如果真要找父親對她所謂的交代的話,應該是她40歲生日的那天,父親還沒有入院,他大清早打來電話說:“你今天過生,一定要高興點呵!”嗯,爸爸,為了你,往后的余生我也會盡量過得高興一些。她在心里默默地回答。
終于到了石安的半山腰,大片大片明亮的陽光傾瀉下來,讓她的眼睛有些不適。她抱著靈牌下了車,感到早晨的山風有些寒意。司機和迎接的幾個師傅把父親的靈柩抬下來安放好,看了她一眼,陽光下他棱角分明的面目讓她有一種奇異的陌生感。這個穿工裝的中年男人跳上藍色的輕卡,轟隆隆地把車開走了。而她一身素服地走在隊伍前面,要在一種莊嚴的儀式中把父親送到山上去,與青山綠水、藍天白云,還有無盡的山花與松柏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