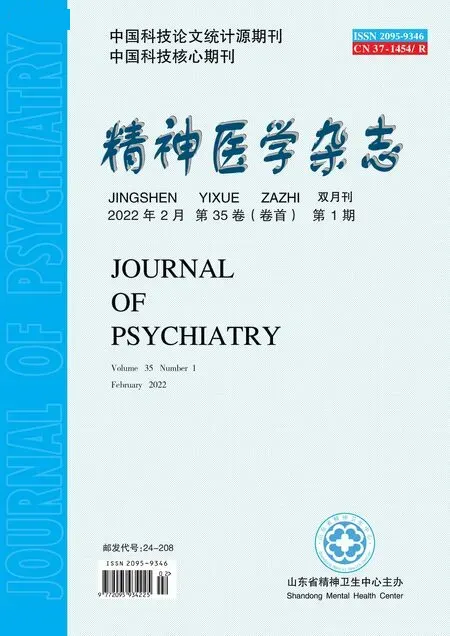新冠疫情防控常態化下上海市徐匯區居民的抑郁、焦慮、失眠癥狀及其相關因素研究*
趙文清 陳雙藝 胡 俊 周 卿 仇劍崟
自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以來,新冠疫情對人類的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成為了目前對全球健康最大的威脅[2]。既往的研究表明,重大的經濟危機或自然災害通常伴隨著抑郁癥、焦慮癥、創傷后應激障礙、藥物濫用和自殺傾向增加[3,4]。新冠疫情期間對普通民眾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中發現,在疫情暴發初期超一半受訪者的心理健康受到了中至重度的影響,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存在中至重度的焦慮癥狀[5],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的抑郁水平顯著下降[6]。2020年4月29日以來全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7],雖然疫情的嚴重程度減輕,但仍限制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及出行[8],對人們的心理健康造成持續的影響,給我國衛生保健系統帶來巨大壓力。這要求我們對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態保持持續的關注。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新冠疫情防控常態化下上海市徐匯區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為新冠疫情期間心理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于2020年6月~2020年8月期間,對14~79歲的上海市徐匯區的普通民眾進行調查。本研究采用滾雪球的調查方式,使用問卷星電子版收集被試資料,對無法完成電子問卷的被試采用紙質版的問卷填寫,再由評估員收集后統一進行數據的錄入。本研究共回收問卷2 502份,剔除無效問卷262份,共納入分析問卷2 240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9.5%。所有的被試均簽署知情同意書。該研究通過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倫理委員會倫理審批。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資料調查表 (1)收集一般人口學信息,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婚姻狀況、家庭關系、家庭年收入、居住狀況、運動情況、飲酒情況、吸煙情況、重大軀體疾病、精神疾病等。(2)自制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相關量表,包括本人及親屬疫情感染情況、疫情的參與程度、對疫情知識的了解程度、對疫情的關注程度、對疫情的恐慌程度等。
1.2.1.2 癥狀量表評定 (1)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9]:該量表用于評估個體抑郁狀態輕重程度。量表包含20個項目,采用四級計分。按照中國常模結果,53分以下為無抑郁癥狀,53~62分為輕度抑郁,63~72分為中度抑郁,73分及以上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該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α=0.794。(2)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10]:該量表用于評估個體焦慮狀態輕重程度。量表包含20個項目,采用四級計分。按照中國常模結果,50分以下為無焦慮癥狀,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69分以上為重度焦慮。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0.770。(3)失眠嚴重程度量表(Insomnia Severity Index,ISI)[11]:該量表是用于評估個體最近一周對失眠的主觀感受的自評量表。量表共7個項目,采用五點評分。分數越高,表明失眠越嚴重,對個體造成的困擾越大。分數范圍為0~28分,其中0~7分為沒有失眠困擾,8~14分為失眠困擾介于臨界范圍之內,15~21分為有中等程度的失眠困擾,22~28分為有重度失眠困擾。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0.808。
1.2.1.3 其他量表 (1)心理韌性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2]:該量表是用于評定個體的心理韌性水平的自評量表。采用五級計分,無反向計分條目。中文版由Yu X等[13]修訂。分數越高,代表心理韌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0.965。(2)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14]:該量表是用于評估個體感受到的社會支持總程度的自評量表。采用七級計分,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個維度。分別計算各維度總分和各條目總分,分數越高,代表感受到的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0.967。(3)簡易應對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15]:該量表是用于評估當個體在生活中經受到挫折打擊或遇到困難時可能采取的態度和做法的自評量表。采用多級評分,有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兩個維度組成,包括20個項目,其中積極應對維度由條目1~12組成,消極應對維度由條目13~20組成。本研究中,該量表的積極和消極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分別為0.927和0.833。
1.2.2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對各量表得分進行描述性統計,計數資料用例數(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與抑郁癥狀、焦慮癥狀、失眠的相關因素,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抑郁癥狀、焦慮癥狀、失眠癥狀的檢出率 2 240名被試中,共檢出抑郁癥狀457例(20.4%),其中輕度抑郁401例(17.9%),中度抑郁53例(2.4%),重度抑郁3例(0.1%);共檢出焦慮癥狀191例(8.5%),其中輕度焦慮163例(7.3%),中度焦慮25例(1.1%),重度焦慮3例(0.1%);共檢出失眠癥狀的52例(2.3%),其中亞臨床失眠44例(2.0%),中度失眠8例(0.4%),重度失眠0例(0%)。比較不同人群癥狀檢出率,抑郁癥狀檢出率隨著年齡的增大而降低,14~29歲年齡組抑郁癥狀檢出率最高(P<0.05);未婚的抑郁癥狀檢出率高于已婚和離異/喪偶(P<0.05);家庭關系絕大部分時間和睦抑郁癥狀和焦慮癥狀的檢出率最低(P<0.05),小部分時間家庭和睦組失眠的檢出率最高(P<0.05)。見表1。

表1 2 240名被試抑郁、焦慮和失眠的檢出率單因素分析[(n)%]
2.2 陽性癥狀組與非陽性癥狀組各量表評分比較 除失眠的陽性癥狀組與非陽性癥狀組SCSQ消極應對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陽性癥狀組SDS、SAS、ISI、CD-RICS、PSSS、SCSQ的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評分均高于非陽性癥狀組(P<0.01)。見表2。

表2 陽性癥狀組與非陽性癥狀組各量表評分比較
2.3 抑郁癥狀、焦慮癥狀及失眠癥狀相關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 將SDS、SAS、ISI任一結果為陽性者視為為陽性癥狀組,結果均陰性者視為非陽性癥狀組。以是否有陽性癥狀作為因變量,以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職業、家庭年收入、是否獨生子女、婚姻狀況、居住狀況、運動情況、飲酒情況、吸煙情況、重大軀體疾病、精神疾病、本人及親屬疫情感染情況、疫情的參與程度、對疫情知識的了解程度、對疫情的關注程度、對疫情的恐慌程度、PSSS、CD-RISC、SCSQ評分為自變量,進行Logstic回歸分析。模型的NagelkerkeR2為0.403,提示模型整體有效性較好。結果顯示中等家庭年收入(8~80萬)、家庭關系絕大部分時間和睦、較好的心理韌性、更多的感知到的社會支持、積極的應對方式是抑郁癥狀、焦慮癥狀和失眠的保護因素(P<0.05);獨居、重大軀體疾病和SCSQ消極應對是抑郁、焦慮癥狀和失眠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3。

表3 2 240名被試抑郁焦慮癥狀和失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疫情進入防控常態化下,普通民眾的焦慮、抑郁和失眠癥狀的檢出率分別是8.7%、20.5%和2.4%,這與疫情爆發期間一項針對來自31個省市共192 020名中國普通居民開展的研究[16]結果,廣泛性焦慮癥、抑郁癥狀和失眠的總患病率分別為27.5%、31.2%、33.7%相比,抑郁、焦慮和失眠癥狀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可能原因是對于處于疫情非核心爆發區的上海市的這個階段來說,疫情處于境內散發,境外輸入基本控制的狀態,生產、生活也得以恢復。
既往研究表明,疫情下民眾心理健康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除了年齡、性別[4]、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外,還包括生活地點、與COVID-19患者的密切接觸、共患身心健康問題、接觸COVID-19相關新聞和社交媒體、衛生溝通、對衛生服務的信心、個人防護措施、感染COVID-19的風險和感知的生存,當地醫療資源的可用性、地區公共衛生系統的效率以及對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4,6]等。這些因素很多是與個體自身與環境受疫情影響的程度的交互作用有關。而本研究發現在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除了維持中等的家庭經濟收入水平外,個體內在的心理狀態和外部的支持程度成為影響民眾心理健康水平的更加突出的因素,如個體的心理韌性,應對挫折/困難的方式以及感知到的家庭朋友和社會的支持和理解等。在疫情下,盡管每個人遭受的社會心理壓力可能類似,但是每個人對壓力事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韌性和應對機制,這可能導致不同的個體之間的心理健康結果。對于有效的應對策略和更高程度的心理韌性的個體在面對緊急情況時可以更少遭受抑郁、焦慮和失眠癥狀的影響。其他的研究也發現,心理韌性與個體的抑郁焦慮程度、創傷后癥狀水平呈負相關[17~19]。心理韌性會在創傷和個體心理健康狀況之間起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過增加個體的心理韌性來改善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20]。社會支持同樣是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COVID-19期間,缺少心理社會支持的個體對COVID-19心理社會應激源影響較高[21],更容易產生焦慮和抑郁[22]。對于心理韌性越好的個體,能夠采用更積極的應對方式,積極進行自我調適,更多的向周圍的親朋好友及同事尋求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持,并積極利用這些支持來應對工作生活中產生的負性情緒,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感知到的社會支持程度越高;反之社會支持水平越高,更能夠利用自身和外部的支持系統,采取相關措施減少身心不良狀況,從而更加積極樂觀地去應對工作生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心理韌性水平[23]。
獨居的個體,往往缺乏有效的家庭互動和人際支持;重大軀體疾病更容易增加對身體的擔憂和感染的風險,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和就醫保障,鼓勵以積極的方式應對疫情下的疾病治療,促進疾病恢復。以及對于有不良應對方式的個體來說,更容易造成情緒的累積,增加抑郁、焦慮和失眠的易感性。對于這種特征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專業的干預。從個人層面,面對負面情緒時,提高情緒應對能力,采取多種積極方式調節負面情緒;另一方面,鼓勵積極溝通,增加心理社交技能,建立更多的社會支持和人際連接,必要時尋求專業的幫助。從政府層面,增加心理健康的宣教,倡導和諧的家庭關系的建立,發揮社區和家庭的聯動作用,為特殊時期下需要就醫的群體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的局限是本研究使用了橫斷面設計,這不能提供強有力的證據的因果關系。另外,本研究采用的是自我報告問卷,存在主觀性和信度問題。進一步的研究將采用縱向設計,深入探索該地區新冠疫情對心理健康的動態影響。
新冠疫情除了造成生命健康的危險,給人類帶來的心理健康方面的影響仍在繼續。基于本研究的結果,反映了新冠疫情防疫常態化階段下,上海市社區民眾的抑郁、焦慮水平及失眠的水平以及其保護因素和危險因素,以期為進一步開展新階段下民眾心理健康管理和重點人群的心理干預提供科學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