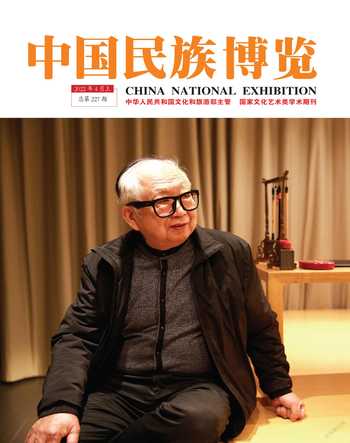“風雅頌”歌詩傳統視閾下的瑤族音樂研究
摘要:瑤族是我國一個古老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與漢民族有著根基性情感聯系的民族。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瑤族人民創造了流傳廣泛、內容豐富、曲調優美具有鮮明特征的民族歌謠。這些歌謠內容包羅萬象,從人類起源、瑤族歷史、祖先崇拜,到人物風俗、山川地理、生產生活、男女愛情等都是歌唱的對象。在對南嶺地區瑤族歌謠進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經過對以《盤王大歌》為代表的瑤族歌謠和民族禮儀進行分析發現,瑤族音樂傳承了我國古代歌詩樂“風雅頌”的古老傳統,不但反映了瑤族人民的時空意識、民俗禮儀和圖騰崇拜等或顯或隱的民族精神密碼,更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
引 言
瑤族系蚩尤之后,原始居住地在今山東、河南、安徽交界處,后遷徙到丹水流域,加入南蠻集團,歷經戰亂與天災,一路向南,再徙漢水流域,過洞庭至黔中郡,成為長沙、武陵蠻。瑤族的名稱,最早出現在初唐史家所修史籍中,稱為“莫徭”。唐代姚思《梁書· 張纘》記載:“零陵、衡陽等郡有莫瑤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自此瑤族以一個獨立的民族實體走上中華民族大歷史舞臺。自宋以降,瑤族再向南、西南遷徙,遍布湘西南、湘南、贛南、贛西南、粵北、桂北、黔東以及滇、瓊,乃至東南亞國家。瑤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其文獻古籍均以漢文記錄。而以《盤王大歌》為代表的瑤族音樂是彰顯其民族特質的主要載體和表現形式。
長期以來,在與漢族相互交融的過程中,以《盤王大歌》為代表的瑤族音樂深受我國古代“風雅頌”傳統影響,與我國古代詩歌總集《詩經》有異曲同工之妙,是瑤族最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以我國古代歌詩“風雅頌”傳統來觀照分析研究瑤族音樂,不僅對民族文化藝術遺產研究非常必要,而且對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再認識,進一步鑄牢各族人民群眾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古代歌詩“風雅頌”傳統在瑤族音樂中的呈現
我國早在上古時期即有歌詩。《尚書大傳》記錄有舜帝與百官相唱和的《卿云歌》,《孔子家語》記錄了舜帝所吟唱的《南風歌》,但這些上古時期的歌謠只是零星地被記錄流傳下來。
我國古代歌詩最輝煌燦爛的篇章是《詩經》。《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時期的詩歌,共305篇,善用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句式以四言為主,多用重章疊句,為后世文學創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和藝術底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由于《詩經》在周代是入樂的詩篇,所以先秦文獻中,又稱這些入樂詩歌為“歌詩”。六經皆史。作為“六經”之一的《詩經》,不僅是記錄商周時期社會畫卷的歷史典籍,更重要的是,開創了我國古代禮樂文化的先河,形成了中華民族具有典型特征的“風雅頌”歌詩傳統。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從《詩經》開始,我國古代歌詩形成了獨特的“風雅頌”傳統。以民間創作為主體的“風”,其表現形式,從漢樂府到魏晉古風詩歌,再到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戲劇音樂,還有各地不同時代的民歌洋洋大觀。辨其音聲,可知朝政得失、民間憂樂、世道人心。所以,每至朝代更迭或起義變亂之際,多以民間歌謠之“風”為先導。相對而言,“雅”“頌”于各個朝代均較穩定,因時微有斟酌損益。迄至于今,我國祭祀黃帝、炎帝、蚩尤、孔子之大典,均可視為承繼古代禮樂文化“頌”傳統之余緒。
在我國一些少數民族中,流傳著歌唱長篇敘事詩、歷史詩的民歌,這些歌曲記述了有關宇宙與人類起源的古代神話和傳說,先民對一些自然現象的認識,以及歷史、生產、生活和禮儀知識,和其民族的英雄歷史傳說。永不疲倦地歌唱棲身于其中的詩意的大地與天空,并在歌唱中安放自己對宇宙和人生和諧而生動的理解,無疑是先民生命活動的重心所在。瑤人無事不成歌,瑤山無處不有歌。動聽的瑤族音樂,是瑤族人民在漫長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作的藝術瑰寶,是瑤族璀璨文化寶庫中光彩奪目的明珠,是瑤族人民傳承民族精神基因和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
《盤王大歌》,又叫《盤王歌》或《大路歌》,是瑤族在每年陰歷十月十六日盤王節“還盤王愿”活動中所唱的各種歌謠的總集。全歌總共一萬多行,要唱七天七夜,是過山瑤、平地瑤、八排瑤、坳瑤、藍靛瑤的百科全書。《盤王大歌》可能形成于晉代以前,瑤族先民因漂洋過海產生的“還盤王愿”活動,經過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到唐代基本成型,到宋代完全成熟。各地瑤族有多種不同的抄本,篇幅不一,有38段歌書、24段歌書和12段歌書,唱詞多在3000行以上。《盤王大歌》內容包羅萬象,從從人類起源、瑤族歷史、人物風俗,到生產生活、男女愛情等都是歌唱的對象。受瑤族文化的影響,《盤王大歌》在傳承過程中,多以瑤族語言為主,沒有漢字形態的版本,有的也是漢字記音形式或者漢字口頭傳播的形式。
《盤王大歌》的音樂形式凝聚了瑤族先民的藝術創造力,其音樂全面充分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和智慧。其有七種曲,謂之“ 七任曲”,即《梅花曲》《南花子曲》《飛江南》《相逢延曲》《亞六曲》《萬段曲》《荷葉杯》。曲的藝術水平比較高,講究用韻,句式多為五言、七言句,各有特色。從句式特征可以推斷,《盤王大歌》最早當出現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不會早于《詩經》。
《梅花曲》基本為七言體,四句一段,每節二、四句押韻。如:“愿得圣王來舍世,兒孫世代使銀錠,日頭出早照層層,照得圣王上馬行。”有時第一句也押韻。如:“風過樹頭木飛花,水面船行底淘沙,一年三百六十日, 能有幾日賞梅花。”《南花子曲》為五五七七句式。如:“先唱南花子,再唱木蘭花,木蘭花開白雪雪,歌師唱歌酒席中。”再如:“前勸眾老大,再勸郎本身,抬頭接盞不曾停,酒盞落臺相認親。”《飛江南》基本句式為七三七七句式。如:“江岸砍木橫江倒,橫江倒,水推杉木滿江河,塞斷江河水一條。”《相逢延曲》以七言為主,每節均在句子中間或末尾嵌有襯詞“哪啰哩”,民歌色彩鮮明。比如:“且唱相逢迎客來,黃巢養女當鳳奇, 手拿錢串鎖銀線,鎖銀鎖線細彎彎。” 在“鎖銀鎖線”后面,有襯詞“哪啰哩”。《亞六曲》句式比較自由,但是多為五言、七言。《萬段曲》《荷葉杯》基本句式均為七言,每節句數可多可少,也有不分節的。

除《盤王大歌》外,瑤族還有數量很多、流傳廣泛的民間歌謠。比如《密洛陀》《發習冬奶》《十二姓瑤人游天下》《桃源峒歌》《千家峒歌》《過山根》《過山經》《交趾曲》《瑤族長鼓歌》《家事歌》《春耕歌》《敬四杯歌》《六合歌》《祝禱豐收》等等。隨著時代的變遷,瑤族同胞利用舊有的曲調,不斷填寫新的歌詞。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瑤族同胞徹底告別了受奴役受壓迫的歷史,創作了《永遠不忘黨恩情》《瑤漢人民心連心》等一批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人民、歌頌新社會的民歌。
值得注意的是,瑤族除使用日常瑤語唱歌之外,還使用當地漢語或鄰近其他民族的語言歌唱。有的既不完全使用瑤語,也不是單純使用當地漢語唱,而是兩者之混合,甚至運用古漢語。湖南郴州民族工作者趙硯球,曾當場演示“下雨”一詞,在瑤族歌謠中發音“落雨”,系古漢語發音,與日常瑤語完全不同。由于這種歌唱語言是專門用于唱歌的,可以稱之為歌謠語言。從這種歌謠語言,或許我們可以管窺瑤族音樂長期以來所受到的古漢語的深遠影響。這也是其自覺承繼“風雅頌”傳統的一個佐證。
二、瑤族音樂之“風”
瑤族音樂中,數量最多的是承繼“風”傳統而表現瑤人生產生活和風俗習慣的歌曲。這些歌曲大多以襯詞“深牌沙優塞沙優”開頭和結尾,中間常有襯詞“哪發”“哪深牌”,旋律多為二聲部。這類歌曲的內容非常豐富,尤以男女情歌為盛。比如湖南郴州莽山瑤族鄉的民歌大量運用“比興”手法,歌唱男女愛情。古人認為,“牝牡相誘謂之風”。從這個意義上看,瑤族音樂“風”之盛,也是上古時期先民風俗文化的生動反映。
瑤族民歌之“風”,極具歷史文化研究價值的是關于瑤族遷徙的內容。比如:“寅卯二年天大旱,江河湖海都枯竭。青山竹木自燃火,江河無水魚死完。男女老幼無奈何,漂游過海到廣東。一年三百六十日,饑寒憂愁在船中。坐在船中求神佑,五旗兵馬保人丁。四十九天船靠岸,燒香化紙謝神恩。瑤人出世高州上,踏上船頭水面撐。船頭上到三江口,瑤人分火入青山。”瑤族音樂之“風”,更具價值的是,音樂藝術哲學方面,集中體現了瑤族先民的時間意識、空間意識。
時間意識。孔子曾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人類的時間觀念主要來自于觀察到的自然運動和人文運動的有序性,來源于此等有序運動的節律性或律動性。可以觀察到的事象世界的有序性運動及其周而復始、循環漸進的節律或律動,是人類形成時間意識的真正源泉。《盤王大歌》是農業文明時期的產物,有一系列體現瑤族先民時間意識的組歌《日出早》《日正中》《日斜斜》《日落江》《黃昏歌》《夜深深》《大星上》《月亮亮》。“日頭出早挨松柏,轉上轉挨松柏枝,轉上轉挨松柏樹,折條松柏引路思。”“日正中,南蛇過海變成龍。”“日斜斜,邀君共傘過平車,邀君共飲平車水,裙角不齊撐傘遮。”日出日落,寒暑交替,決定了瑤族先民的生活節奏。如張蕾說“時間或時間詞本身并無情感,只有它與特定意象聯系在一起才會觸動人心,產生詩美。”
這些歌曲傳達了瑤族先民對于時間月令的感受與思考,表達了特有的時序感受、心理感受和生命感受。比如:
《黃昏歌》中體現的心理感受。“夜黃昏,作笑不知姐鎖門,待到門前偷拭淚,不得鑰匙開妹門。”在瑤山,天地蒼茫一片,暗暗日落,歸心似箭,與自己的愛人不可得見的心理感受,在瑤人的吟唱中無疑具有了原型的意義。再比如,《瑤族長鼓歌》表現時序感受: “正月行游春也到,二月行游春又深。三月行游下谷種,四月行游出小葉。五月行游春回水,六月行游滿水田。七月行游禾上節,八月行游一對花。九月行游半熟了,十月行游收進倉。十一月行游打白粉,十二月行游打粉白漣漣。”
音樂節奏是人類關于時間意識的一種微觀表達。瑤族先民在生產生活中,如捕捉獵物、刀耕火種、開山造田、伐木丁丁、泉水叮咚、木排飛駛、采茶收割、織布繡花、翻山越嶺等,都成為歌謠音樂節奏的源泉。因此,很多瑤族歌曲的節奏是多變的。比如《日正中》《日斜斜》《夜深深》《月亮亮》等歌曲,雖然整首歌不長,卻采用了四一、四二兩種節拍。《北邊暗》《雷落地》《葫蘆曉》《洪水盡》《為婚了》等歌曲,則采用了四二、四三兩種節拍。
《相逢延曲》竟使用八五、八六、八九三種節拍反復變換。可見,瑤族音樂具有封閉、陰柔的農業文明屬性。與現代音樂相比,其音樂形態具有節奏自由、速度緩慢、音域較窄、音量不大等特征。
空間意識。空間是物質存在的一種客觀形式,是物質存在的表現。德國哲學家博格耐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有基本象征物,表象該文化的基本精神。這樣的基本象征物主要指的是空間境界,而空間境界又是在藝術中表現出來的。瑤族音樂的空間意識,一是外在的,一是內在的。

從外在的空間意識看,主要體現為瑤族先民艱難遷徙歷程和對生活環境的空間感受。正如湖南宜章塘坊盤堂保師公《還愿歌吟》詞唱的“瑤人出世高州上,踏上船頭水面撐。船頭上到三江口,瑤人分火入青山。瑤人起屋三江口,瑤人作笑傍山頭。拋兵踏上連州廟,踏上連州廟上行。游到廣東樂昌府,又到莽山把身安。”再如《桃源峒歌》:“盤州歌詞都唱了,且唱桃源之歌謠。心心愛入桃源峒,不知桃源在哪邊。郎今且問桃源峒,不知桃源在哪邊。”“心心愛入桃源峒,莫在桃源洞口尋,桃源洞口七條路,三條修葺四條荒。三條修葺桃源路,四條荒路何處尋。”還有《千家峒歌》:“日上東山白石嶺,水過龍門石谷中,日落山陰映江水,彎彎河水似金龍。日頭落嶺南山背,收工回家過蓮塘。滿塘蓮花白又美,手搖蓮花四面香。”桃源峒、千家峒是瑤族人民在不斷遷徙歷史中的停留地,是瑤族人心中永遠的桃花源和祖居地。2001年,全國瑤族學術研討會確定早期的“千家峒”在湖南臨湘的龍窖山、晚期的“千家峒”在湖南江永大遠瑤族鄉。
內在的空間意識,是瑤族音樂傳達的一種心靈在虛與實、有限與無限之間的流轉。這種詩意的空間,是一種個人體驗化的空間,是一個內在觀照出的心靈空間。比如,《十二月想妹》:“正月想妹是新年,紅燈彩帶掛堂前,記得當初交情時,是在元宵看花燈。二月想妹李花開,哥是山伯妹英臺,蜜蜂挑糖不怕遠,哥哥想妹進山來。山高路陡好難走,穿爛好多布草鞋,……十二月想妹又一年,西山哥妹結姻緣,東山又辦娶親酒,哥妹哪時才團圓?”這首歌借景抒情,通過對時空的反復推移變化, 表達了對戀人熾熱的思念,感情非常濃烈。這樣的瑤族情歌很多,大體分為歌堂情歌和一般情歌。歌堂情歌是湖南瑤族“坐歌堂”時所唱歌謠的總稱。“坐歌堂”是瑤族人民喜聞樂見的一種傳統文藝形式。每當喜慶節日或勞動之暇,青年男女常歡聚一堂而歌,以此來交流和增進感情。這類瑤族歌謠通過獨特的藝術手法,描畫出一個藝術形象的女神或理想中的愛人,可以讓聽者從這種音樂藝術表達中,體味瑤族集體意識中的心靈空間境界,從而產生共鳴,得到精神的愉悅。
三、瑤族音樂之“雅”
雅者,正也,義為“合乎規范的”,“高尚的”。“雅”樂,在西周時期,即為朝會之樂。瑤族音樂之“雅”,我們可以認為是瑤族人民生活中各種莊重正式典禮之樂。
瑤族舉行婚禮和壽宴時,必有音樂,這種音樂頗具古風,即嗩吶鑼鼓之樂。“莽山的嗩吶曲優雅嘹亮,喜慶吉祥,是瑤人生活中的《歡樂頌》。經向道洞村的嗩吶手趙井生、盤塘生請教,得知其大致曲名:迎親曲。此曲一吹,客人們即從屋里屋外、村前村后赴宴席,無需侍客和主人請;開席曲。菜肴上席,美酒斟上,只等開席曲一吹即可動筷;董昌亨曲。上團子肉時吹奏;生欸仔曲。表示母親生孩子,肚子疼痛,曲子哀傷,喚起女兒惜娘恩;衡州曲。出雞肉時吹奏;敬酒曲。新郎新娘雙方家長互敬禮酒,和互敬對方親友時吹奏;豬花筒曲。上豬腸子時吹奏;滿堂紅曲。曲子很歡樂,最后出粉絲時吹奏。
為嗩吶伴奏的是四樣打擊樂器:鼓、頂鑼、獅子鑼、鈸。”瑤族的婚禮賀曲有《姻緣歌》,全歌很長,54節,每節4句,共有歌行216句; 每句以七言為主,偶有起句為三言;四句一韻,中間隨意換韻,有如排律。此歌關于“郎”的贊美,使人想到漢樂府《陌上桑》羅敷女贊美自家夫婿。婚禮賀歌《賀婚歌》:“二人雙雙像對鳳,龍鳳花開像對金。前世修成姻緣份,修成姻緣結成雙。二人雙雙像對鳳,龍鳳花開王殿臺。前世修成姻緣份,六合結成龍鳳妻。”《盤王大歌》的《富貴龍》也有關于婚嫁的內容:“女士樓上大婆女,正是五婆養出娘,十五年間逢養大,海岸劉王來對親”。從歌詞內容可以看出,舊時瑤族姑娘在十五歲時即可婚嫁。
《盤王大歌》中的《彭祖歌》,是一首極長的歌,從“千兩黃金未為貴,共床夫妻未為親。黃紗古木正為貴,送上青山相伴眠”等內容看,應屬瑤族“雅”樂中的祭祀歌。令人感覺奇特的是,《彭祖歌》不僅是一首祭祀歌,從“彭祖身中多有孕,身中有孕在深門,造書歸報郎爺姐,好酒安排三兩分”等內容看,還是一首生育歌。《大排良愿》哀婉綿長,也是瑤族祭祀音樂。
《脫孝歌》則是一首喪歌,不但表達了對已故親人的懷念,而且通過歌曲形式傳承了瑤族孝道孝制風俗。其詞為:“朝朝送飯到靈前,送到靈臺不見人。不見爺娘到靈邊,胸前衫領濕漣漣。孝兄孝姐孝三日,孝爺孝娘孝三年。孝道三年孝落地,脫下孝頭用為焚。”由此可見,瑤族有親人守孝的傳統習俗,為兄姐守孝為三日,為父母守孝則為期三年,孝盡之日,頭戴之白頭孝巾即在墓廬前焚燒,守孝期才算結束。
生育、婚姻、悼亡、祭祀,是人生之大事,千百年來瑤族人民通過嚴肅莊重的“雅”樂,表達展示民族的心靈空間和精神密碼。正如郴州市瑤族文化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趙硯球所說,這些瑤歌瑤調是在風雨滄桑的歷史變故中遺留下來的“不變式”。這種不變式表現在歷史的各個階段,與遷徙地的民族接觸過程中,既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養分,又堅定地保持著自我的民族音樂個性,以充實自我文化的內涵。莽山瑤歌充分顯示了這一特點。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力量,一種代代相傳的情感需求,沒有了這種禮儀就沒有了這種音樂。
四、瑤族音樂之“頌”
“頌”者,“容”也。“頌”樂,是一種歌舞一體的音樂,是頌揚祖先、崇拜自然、娛神娛鬼的音樂,是此岸世界通向彼岸世界的藝術橋梁。瑤族的“頌”樂,主要包括“始祖頌樂”和“泛神頌樂”兩個方面。
始祖頌樂。始祖文化是家族、民族的信仰,后世子孫通過慎終追遠獲得始祖的庇佑,保佑家族繁衍生息。《盤王大歌》是自稱為“勉”的瑤族,舉行祭祀盤王“還盤王愿”時師公吟唱的一部“頌”樂。
據史料記載,盤瓠是高辛氏時代的一個以犬為圖騰標志的氏族首領,在歷史傳說中被神化了。盤瓠事跡,在瑤族珍藏的典籍《過山榜》和漢文史籍《搜神記》《后漢書》《山海經》等都有記述。由此可知,“瑤族始祖與高辛氏有關系,其遠古先民亦當屬東夷集團的一支。盤王去世后,瑤族祭祀甚篤。
相傳,瑤族在遷徙過程中漂洋過海遇到大風浪不得靠岸,于是向始祖盤王許下大愿,祈求保佑子孫平安到達彼岸。族眾平安到達為感謝始祖盤王舉行還愿儀式,即“還盤王愿”。清代學者顧炎武對“還盤王愿”儀式樂舞作過描述:“衡人賽盤瓠……娛祈許盤瓠。賽之日,巫者以木為鼓,圓徑手一握,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杖鼓, 四尺者,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是日,以帛畫懸之長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鼓繞身而舞;二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學者趙書峰認為,還盤王愿”儀式,是說勉語的過山瑤和優勉支系民間共同的一種祭祀祖先盤王神的傳統儀式,是以頌唱《盤王大歌》為主的盤王祭祀儀式。“還盤王愿”是道教音樂與瑤族傳統文化的合流,是以祈福還愿為主體的民間神圣性信仰儀式音樂。在《盤王大歌》中有《盤王出世》《盤王起計》《祭盤王》等樂歌贊頌祭祀盤王。茲錄部分歌詞。
《盤王出世》:
出世盤王先出世,盤王出世在福江。
盤王出世福江廟,帽帶齊齊朝上江。
……
月亮光光照下海,照見劉王書案臺。
閻王執起攔胸照,照見唐王出世中。
……
從《盤王出世》的內容看,不僅唱了盤王,還唱了唐王、劉王等祖先。
《盤王起計》則從神話的角度,贊頌了盤王對瑤族生產生活的重大影響。如:“盤王起計立春煙”,“盤王起計斗犁耙”,“盤王起計種芋麻”,“盤王起計斗高機”,舉凡瑤族山區春耕秋收、紡織繡花等農業社會的生產技術和生活技能,均由盤王起計教民。
《祭盤王》既是祭祀歌,也是祈福歌。詞曰:“三巡酒氣歌聲出,歌詞相伴贈王侯。來時三迎三召請,起腳騾生馬若蹄。鳥去留名在樹上,圣去留名在廟堂。……奉送皇上回鸞殿,留恩布福與東君。答應過后全無事,各坊人畜盡太平。”


瑤族的始祖“頌”樂,還有《密洛陀》。密洛陀是瑤族母系氏族共同崇拜的祖先,是布努瑤的始祖母。《密洛陀》的內容豐富多彩,包羅萬象,所以有人曾把它比喻為布努瑤的“百科全書”,其中有反應密洛陀的誕生和天地日月形成的;也有反映人類萬物的起源和與妖魔作斗爭的,也有反映民族歷史遷徙原委的內容等。《密洛陀》主要是在每年農歷五月二十九日“祝著節”(密洛陀生日)或平時辦紅白喜事時演唱。
泛神頌樂。馬克思曾說:“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 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在所有文明民族經歷的一定階段上,他們用人格化的方法來同化自然力。正是這種人格化的欲望,到處創造了許多神。”瑤族崇奉盤瓠,同時亦信奉多種自然神祇。此屬原始自然崇拜和巫教范疇。瑤族認為在現實的此岸世界外,有一個看不見的彼岸世界,主導并影響著現實的此岸世界。在看不見的這個世界里,由超越現實世界萬千事物的神靈組成,天有天神,地有地神,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電風雨、霜雪云霧、山川河流、草木竹石皆有神靈存在。因此,瑤族常以歌舞娛神頌神。
瑤族反映創世神話的《盤古歌》唱道:“當初未能有天地,未有日月及乾坤,先有玉皇共盤古,我共玉皇共出身,我倆不是爺娘養,無色浮云生我身。”“浮云結氣自生煙,未有乾坤及原始,又無日月又無天。”“云氣”在這里成了生養玉皇和盤古的神靈,而盤古開天辟地,創造了世間萬物。這與我國中原文化盤古開天辟地創世學說如出一。
再有,社稷“頌”樂。《禮記》載:“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所以神地之道也。”瑤族村寨普遍建有土地廟祭祀土地神祇,是為“社神”,也就是瑤民日常所稱的“土地公婆”。瑤族認為,谷物也像人一樣有靈魂,其魂名曰“禾魂”。谷物之所以能養育人們,是有神的主宰,其神就是“谷神”。還有梅木“頌”樂。梅木,即銀杏樹。瑤族認為梅木在人類起源和民族繁衍過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湖南瑤族有《洪水淹天的傳說》,相傳洪水淹天之后,世上只有伏羲兄妹二人,兄妹在梅木的撮合下婚配,族群自此不斷繁衍。瑤族《源流歌》唱道:“伏羲兄妹無上賜,梅木樹下結成親,金花傳粉身有孕,十月懷胎不成人,生下冬瓜無人樣,冬瓜有籽瓜內眼。太昊年間無百姓,只有瑤人十二賢。”
瑤民多在房前屋后種植梅木,常以梅木命名所居之地,以求得梅木的護佑。宋代瑤族聚居地湖南新化、安化,即稱梅山,故瑤族當時稱為“梅山蠻”。泛神“頌”樂,反映的是一種民間信仰。在中國少數民族民間,亦指民眾自發地對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體的信奉與尊重的行為。正如和云峰先生所說,民間信仰一般認為是遠古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原始文化現象,是人類對世界萬事萬物初始認識水平的客觀反映,是人類族群漫長歷史記憶中不斷變異的文化意識。
結 語
考察我國兩千多年的詩歌音樂歷史,我們發現,漢族的詩歌音樂越來越文人化,越來越注重格律,越來越華美綺麗,某種程度上,反而失去了《詩經》那種天真質樸的青春氣象和蓬勃生機,距離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越來越遠。傅斯年《詩經講義稿》指出:“后人做詩,雖刻畫得極細。意匠曲折得多,然刻畫即失自然,而情意曲折便非詭化的人不能領悟,非人情之直率者。”禮失求諸野。在中國南方廣袤險峻的武陵山脈、雪峰山脈、羅霄山脈和南嶺地區,在瑤族群眾聚居的山野之間,在以《盤王大歌》為代表的瑤歌瑤樂瑤舞中,我們欣喜地發現,中華民族詩歌音樂的“風雅頌”古老優良傳統在這里得以賡續與傳承。(本文是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南嶺走廊瑤族傳統儀式音樂的空間結構與傳承機制研究”項目編號: 21YJC760041之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李爽霞(1981-),女,湖南長沙人,湘南學院教授,南嶺走廊鄉村振興研究基地成員。研究方向:音樂學、民族學、人類學。
作者簡介:陳夢琳(1991-),女,湖南湘鄉人,湘南學院助教,南嶺走廊鄉村振興研究基地成員。研究方向:音樂學、民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