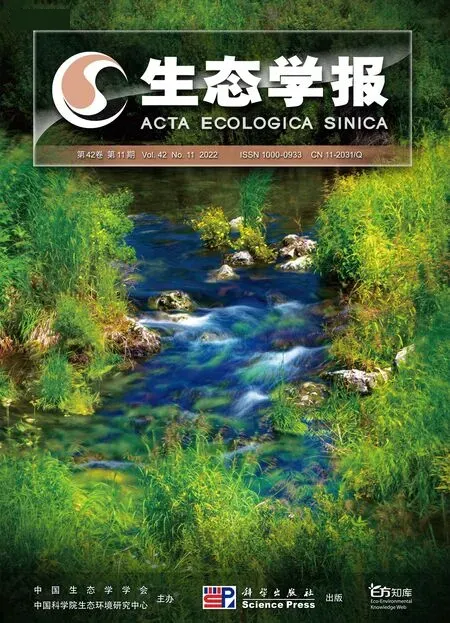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群落及其衛星樣地物種多樣性特征
魏識廣,葉萬輝,練琚愉,李 林,周景鋼
1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桂林 541004
2 廣西師范大學珍稀瀕危動植物生態與環境保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桂林 541006
3 廣西漓江流域景觀資源保育與可持續利用重點實驗室, 桂林 541006
4 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退化生態系統植被恢復與管理重點實驗室, 廣州 510650
5 中國科學院核心植物園植物生態中心,廣州 510650
21世紀以來,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人類對生境的干擾導致多樣性的損失日益加劇,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圍內也備受關注[1]。森林動態大樣地是生物多樣性科學綜合研究平臺[2]。近年來,隨著對森林大型固定樣地數據的不斷深入獲取,生物多樣性的研究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相關研究成果極大地推動了對群落物種共存機制的認知[3]。
20世紀60年代,生態學家Robert H. Whittaker提出了α、β和γ多樣性用來表征不同尺度群落的物種多樣性[4]。α多樣性檢測特定群落或區域的物種豐富程度;β多樣性檢測不同群落間由于環境作用導致的物種組成差異或群落分化的程度;而γ多樣性表征包括許多群落的大區域總的物種豐富度[5]。此后多樣性測度的方法日趨完善,并得到廣泛應用,特別是針對特定群落多樣性水平評價時,α多樣性備受推崇[6]。α多樣性與群落其他特征的相關性研究也備受關注:有研究發現人工林物種多樣性的增加有利于林分生物量的提高[7];對植物群落α多樣性與地形特征的關系研究中發現中海拔區域的多樣性高于高海拔和低海拔區域[8]。隨著生物多樣性監測范圍的不斷擴大,采用β多樣性指數比較樣地間的多樣性也引起關注[5,9]。有研究用β多樣性指數檢測顯示:西雙版納望天樹樣地內的群落組成和結構變化很大,任意兩固定樣地間均有50%以上的植物物種不相同[10]。利用β多樣性指數對湖南省八達貢山的環境異質性分析發現:不同地點的環境異質性值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11]。
近年來,圍繞生物多樣性的形成機制和影響因素也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如,研究發現群落類型和海拔是中亞熱帶古田山森林群落α和β多樣性的主要影響因子,生境過濾等機制對該區域的森林物種多樣性格局起著主要作用[12];隔離度顯著影響島嶼植物的β多樣性[13];坡向影響到秦嶺松櫟林群落生物多樣性分布格局[14];以Jaccard物種相異性指數為指標發現群落物種在空間上的更替是環境限制和擴散限制綜合作用的結果[15]。而目前在高生物多樣性的南亞熱帶森林群落的此類研究還有待加強。
鼎湖山的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群落DHS大樣地屬于中國森林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成員,迄今為止已經15年連續監測數據,對其群落結構、多樣性組成以及多樣性維持機制方面開展了研究[16—18]。由于鼎湖山自然保護區植被的獨特性(全球同緯度帶上遍布沙漠),以及其超過400年的保護歷史,造就了此區域內群落類型多樣,深入研究發現即使是20 hm2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群落中也存在不同發育階段的斑塊[19]。為了拓展和補充該區域多樣性的監測范圍,在20 hm2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群落周圍建立了5個1hm2衛星樣地。本研究首次以鼎湖山20 hm2南亞熱帶地帶性常綠闊葉林群落大樣地結合其不同海拔和林型的衛星樣地群落作為研究對象,分別從種面積關系、α多樣性和β多樣性幾個角度進行分析比對,旨在探索南亞熱帶典型大樣地群落與其衛星樣地的多樣性狀況的異同性,全面深入探索南亞熱帶森林區域多樣性特征與分布格局,為該區域森林群落的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地概況
鼎湖山(以下簡稱,DHS)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12°30′39″—112°33′41″E,23°09′21″—23°11′30″N)屬于科技部重點野外臺站,對于鼎湖山的詳細介紹見文獻[20]。本研究選取20 hm2的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群落,及其周圍約2000 hm2范圍內5個1 hm2的不同林型衛星樣地群落為研究對象,各樣地位置及類型見表1。各衛星樣地與大樣地的相對位置見圖1。樣地調查按照 CTFS(Center of Tropical Forest Sciences) 在熱帶森林生物多樣性長期監測研究的方法來實施[21]。采用DHS大樣地及其衛星樣地2015年度的調查數據進行統計計算和分析。

表1 DHS大樣地及其5個衛星樣地的位置及類型Table 1 Location and types of Ding Hu Shan large-scale plot and 5 satellite plots

圖1 DHS大樣地與及其衛星樣地的相對位置 pFig.1 Relative positions between DHS large-scale plot and satellite plots 0為DHS(鼎湖山Ding Hu Shan)大樣地,1—5分別為衛星樣地的編號
2 研究方法
2.1 衛星樣地位置轉換
通過R里的geoxy函數把6個樣地的四個角點的經緯度轉換為直角坐標系的x值與y值,然后輸出并繪制為矩形框圖(圖1)。geoxy函數默認以最小經緯度樣地的西南角點作為平面直角坐標的原點。6個樣地中,3號衛星樣地的經緯度最小,故它的西南角點為圖1直角坐標的零點。各衛星樣地均為邊長為100 m的正方形,DHS大樣地X方向(東西方向)長度為400 m,Y方向 (南北方向)為500 m。
2.2 種面積曲線繪制
上述六個樣地中,20 hm2DHS樣地的數據經過核對檢驗后載入R工作空間,從20 m到400 m每隔20 m取一個尺度總共20個尺度作為取樣方框的邊長,每個尺度上隨機位置方形取樣各8次,統計每次所取的物種數其均值。5個衛星樣地數據,則從5 m到100 m每次增加5 m共20個尺度,直至取樣完1 hm2樣地全部植株,每個尺度上隨機方形取樣8次,相應面積所對應的物種數取自于隨機取樣的平均值。6個樣地統計的系列數據對應到X-Y坐標圖繪制為種—面積曲線。
2.3 多樣性計算
依次選取3種α多樣性指數:Shannon-Weiner 指數[22]、Simpson指數[23]與Heip均勻度指數[24];選取3個β多樣性指數:Jaccard指數[25]、Sorenson指數[25]、Bray-Curtis指數[26];用于表征群落物種多樣性狀況的6個多樣性指數詳見表2。

表2 α和β多樣性指數Table 2 α and β diversity indices
上述所有數據處理均在R3.5上編程實現[28]。
3 結果與分析
3.1 物種概況及種面積關系
各樣地的物種概況見表3,其中的個體數量不含分枝數。20 hm2大樣地共有80937個體,分屬于177物種。1 hm2衛星樣地3號的物種數最多,為96個物種;其次為1號和2號;4號和5號低于1—3號樣地,其中4號樣地物種數最少,為41種。5個衛星樣地總個體數差異較大,排序為:1號>3號>5號>4號>2號樣地。1號南亞熱帶山地常綠闊葉林總個體數4050株,明顯多于其它衛星樣地。2號南亞熱帶溝谷雨林個體數最少,僅有1997株,比1號樣地少2053株,甚至比4號馬尾松林少371株。由于2號樣地中分布著許多大樹和巨樹,42株樹木胸徑DBH(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大于40 cm;有16株胸徑大于60 cm,其中錐栗(Castanopsischinensis)9株;5株胸徑超過100 cm的個體都是建群種錐栗(DBH分別為:119.4 cm、119.7 cm、165.6 cm、178 cm、184 cm),因此2號樣地的胸高斷面積遠大于其它樣地。

表3 各樣地的物種概況Table 3 Species profiles in each plots
20 hm2大樣地的種面積曲線顯示(圖7):隨著面積增大,物種數不斷增多,特別是0—5 hm2范圍增加的最快,5 hm2時出現拐點,物種數達到128,是整個樣地物種數的72.3%;20 hm2時仍然呈現輕微上升趨勢,說明20 hm2的典型樣地物種并未達到完全飽和,周圍的衛星樣地可以有效補充代表該區域物種。衛星樣地的種面積曲線顯示:4號南亞熱帶常綠針葉林(馬尾松林)物種在1 hm2面積時物種達到飽和(圖5),而其余四塊樣地物種均保持明顯上升趨勢,充分體現了鼎湖山南亞熱帶森林群落高多樣性特征。
3.2 α多樣性比較
物種豐富度S、Shannon-Weiner指數、Simpson指數和物種均勻度Heip指數表征各樣地的物種多樣性見表4。比較發現:DHS大樣地的多樣性較高。綜合Shannon-Weiner指數和Simpson指數結果發現:DHS樣地多樣性水平僅次于衛星樣地2號南亞熱帶溝谷雨林和3號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而表征物種個體數之間差異的物種均勻度Heip指數的計算結果表明DHS大樣地物種均勻度較小,僅高于5號南亞熱帶針闊混交林。

表4 各樣地的α多樣性統計結果Table 4 Statistical results of α diversity in each plots
衛星樣地之間的比較結果表明(表4): 4號和5號衛星樣地的豐富度明顯低于其它類型樣地,其中4號物種豐富度最低。以荷木為優勢種的3號樣地的物種豐富度最高,其次是1號和2號樣地。體現物種數和相對多度綜合作用的Shannon-Weiner指數結果顯示:2號樣地的物種多樣性最高,其次是3號樣地,繼而是1號和4號樣地,最后是5號樣地。而主要統計優勢種影響力的Simpson指數,也表現出與Shannon-Weiner指數相同的規律。體現群落均勻度Heip指數計算結果顯示:2號樣地的物種個體分布均勻度最大,其次是4號樣地,繼而是3號和 1號樣地,最后是5號樣地的針闊混交林的物種個體分布最不均勻,這與針闊混交林植株聚集度較高有關。
考慮到DHS大樣地面積遠大于其衛星樣地,故綜合比較面積相同的衛星樣地的α多樣性指數,多樣性指數計算結果顯示(表4): 2號,3號和1號衛星樣地明顯高于4號和5號衛星樣地,其中2號溝谷雨林樣地Shannon-Weiner指數、Simpson指數及Heip指數的數值皆在5個樣地中最大,說明南亞熱帶溝谷雨林在各個樣地群落中物種是最多樣化的。4號和5號衛星樣地均屬于低海拔樣地,4號衛星樣地南亞熱帶常綠針葉林(馬尾松林)的物種豐富度最低,但其海拔跨度(38—93m)大于5號衛星樣地(50—85 m),因此物種多樣性高于5號衛星樣地。
3.3 β多樣性比較
采用Jaccard、Sorenson和Bray-Curtis指數表征β多樣性又稱生境間的多樣性,表征群落之間由于生境差異造就的物種組成的相異性。3個指數統計顯示(表5):DHS大樣地與其幾個衛星樣地的物種之間存在差異,與3號衛星樣地物種相似度最高(Jaccard指數和Sorenson指數最大),Bray-Curtis指數也較高,高相似度的主要原因是兩者植被類型較為接近;其次是2號衛星樣地,DHS大樣地與1號和5號衛星樣地的物種差異逐漸增大;DHS大樣地與其4號衛星樣地的Jaccard指數和Sorenson指數最小,Bray-Curtis指數較低,說明它們之間的物種組成差異相較于其他樣地之間是最大的。

表5 樣地間β多樣性指數統計Table 5 Statistical results of β diversity between each plots
衛星樣地之間的差異為見表5,3個指數的計算結果均顯示:1號、2號、3號樣地之間差異較小,2號和3號樣地之間的物種相似度更高:Jaccard指數最大(0.383)和Sorenson指數同樣在衛星樣地間最高(0.554),Bray-Curtis指數也僅次于1號和3號之間(0.643),屈居第二 (0.629),說明2號和3號衛星樣地的群落結構很接近。
4號與1、2、3號衛星樣地物種差異較大,其中4號與2號衛星樣地群落差異最大,相似度Bray-Curtis值只有0.044。各個衛星樣地之間的物種差異主要是海拔差異和群落小生境的不同而導致的。4號與5號樣地的物種差異最小,在4號樣地與其他衛星樣地中的相似度最高(Jaccard指數、Sorenson指數和Bray-Curtis指數都最大),其中Bray-Curtis指數達到0.841,即4號與5號衛星樣地物種相似度高達84%。
4 討論
4.1 種個體和種面積變化規律
20 hm2大樣地三次調查結果統計表明2005年到2010年期間喬木總多度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增加了6812株。可能與樣地內的倒木死亡形成多個林窗有關,林窗對森林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短期的調節作用比較明顯[29]。林窗對群落組成、功能結構、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生物多樣性維持起著重要作用,是群落演替的主要驅動力[30]。經過更新演替,2015年DHS大樣地的總個體數出現了爆發式增長,比5年前增加2792株,比10年前甚至增加了9604株。進一步探索群落更新演替的趨勢還需要后期持續調查監測結果來分析。
衛星樣地間物種數和個體數的差異主要是由其生境類型和海拔不同造成的。南亞熱帶山地常綠闊葉林 (1號樣地) 海拔遠高于其他幾塊衛星樣地,其總個體數也遙遙領先,其次是3號樣地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荷木林)。而南亞熱帶溝谷雨林由于位于低海拔區域,受人為干擾較大,其植株個體數在衛星樣地中是最少的。也是因為樣地中大樹和巨樹分布較多,在群落中占到絕對優勢,導致相同面積上生長的個體數最少。
除了4號樣地種面積曲線在1 hm2時物種趨于直線外,其他衛星樣地物種在1 hm2時均保持明顯上升趨勢,甚至大樣地在20 hm2時種面積曲線仍然呈現輕微上升趨勢(圖2—7)。這也說明了對物種豐富的鼎湖山南亞森林群落生物多樣性進行研究時還需要結合考慮周邊衛星樣地情況,與大樣地物種存在較大差異的衛星樣地會是大樣地物種更新的重要來源。

圖2 樣地1種面積曲線圖Fig.2 Species-area curve of plot 1

圖3 樣地2種面積曲線圖Fig.3 Species-area curve of plot 2

圖4 樣地3種面積曲線圖Fig.4 Species-area curve of plot 3

圖5 樣地4種面積曲線圖Fig.5 Species-area curve of plot 4

圖6 樣地5種面積曲線圖Fig.6 Species-area curve of plot 5

圖7 大樣地種面積曲線圖Fig.7 Species-area curve of large-scale plot
4.2 多樣性變化規律
根據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的計算結果,結合表1各樣地的海拔范圍,發現除了2號樣地(雖然2號樣地總物種個體數最低,然而由于大量大樹和巨樹的存在導致物種均勻度提升,從而使得多樣性指數計算結果最大),其它衛星樣地呈現出多樣性與海拔高度正相關的規律,這與其他區域的相關研究結論不盡相同。海南島不同海拔高度青皮林群落的多樣性與海拔高度呈相反變化趨勢[31]。白龍江干旱河谷不同坡向主要灌叢群落隨著海拔的升高,不同坡向物種數表現為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即中海拔多樣性最高[32]。對林窗植物多樣性及其海拔動態研究顯示:低海拔林窗中植物多樣性最高,其次為中海拔,高海拔林窗中多樣性中低海拔之間存在顯著差異[33]。鼎湖山地處南亞熱帶區域,水熱條件充沛,屬低海拔丘陵區,最高峰雞籠山海拔1000m,而南亞熱帶山地常綠闊葉林樣地所處的最高海拔為660m。低海拔區域受一定的人為干擾,相對區域內較高海拔樣地其光熱條件處于劣勢,因此低海拔樣地多樣性也較低。前期鼎湖山樣帶的研究也發現:隨著海拔升高,水、熱、光等條件隨海拔升高而趨于優化,多樣性也逐漸增大[34]。
同一區域內不同群落α多樣性的大小也與其群落演替階段密切相關。黑石頂森林群落演替系列α多樣性的尺度效應研究表明:闊葉林樣帶比混交林樣帶在群落組成結構上具有更高的空間變異[35]。鼎湖山樣帶的研究發現:喬木層物種多樣性指數是中生性闊葉林>針闊混交林>陽生性闊葉林[36]。針闊葉混交林是我國南亞熱帶針葉林向地帶性常綠闊葉林演替的中間林分類型,故豐富度處于中間,本研究也發現了各個不同演替階段群落物種豐富度的規律為:溝谷雨林、常綠闊葉林(1,2,3號樣地)>針闊混交林(5號樣地)>針葉林(4號樣地)。
β多樣性度量群落間物種組成的變化,由物種更替和豐富度差異兩種過程決定[3]。同一區域內處于相同或相近演替階段的群落其物種相似度高,相反處于演替階段兩極的群落物種相似度最低。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DHS大樣地)與其3號衛星樣地(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荷木林)處于相近演替階段,因此物種相似度最高:Sorenson指數檢測出有60%的物種相同(表5);與其4號衛星樣地南亞熱帶常綠針葉林演替階段相差最遠,物種差異性也最大:Bray-Curtis指數檢測出僅有5%的物種相同;DHS大樣地與其1、2、5號衛星樣地的物種相似性都介于上述與3號和4號衛星樣地之間。衛星樣地之間的物種相似性也存在差異。因此,這些與典型大樣地物種各有差異的不同海拔和林型的衛星樣地有力地促進了南亞熱帶典型森林大樣地群落的物種更新和提高多樣性。
5 結論
鼎湖山物種資源豐富,公認為北回歸線上的“綠色明珠”,對典型植物群落及其衛星樣地物種多樣性狀況進行探索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研究工作。文中通過種面積關系、α多樣性和β多樣性的計算和分析比較,得出以下幾個主要結論:
(1)20 hm2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DHS大樣地)經過10年的更新演替,總個體數出現了爆發式增長。1 hm2衛星樣地的物種數表現出: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荷木林)最多,南亞熱帶常綠針葉林(馬尾松林)物種數最少。衛星樣地之間總個體數差異較大。
(2)種面積曲線表明:20 hm2DHS大樣地的物種并未達到完全飽和,周圍的衛星樣地可以有效補充代表該區域物種,衛星樣地也是自然保護區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3)α多樣性研究發現: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 (DHS大樣地) 的α多樣性較高,多樣性水平僅次于衛星樣地2號南亞熱帶溝谷雨林和3號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荷木林)。同一區域內不同群落豐富度的大小與其群落演替階段密切相關。
(4)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 (DHS大樣地) 與其3號衛星樣地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荷木林)處于相近演替階段,因此物種相似度最高;與其4號衛星樣地南亞熱帶常綠針葉林(馬尾松林)演替階段相差最遠,物種差異性也最大。衛星樣地之間比較:4號南亞熱帶常綠針葉林(馬尾松林)與5號南亞熱帶針闊混交林的演替階段相近,物種相似度最高,Bray-Curtis指數表明兩者具有84%的相似度。
綜上所述,若要獲取鼎湖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整個區域群落的多樣性特征,研究不能僅聚焦到該區域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典型大樣地(DHS大樣地),還需統籌考慮其周邊輻射范圍不同海拔和林型地衛星樣地群落。通過聯合研究多個衛星樣地與20 hm2的DHS大樣地構成的復合群落系統,即可給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區域森林群落的多樣性特征與分布格局以一個精準畫像,為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提供更加科學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