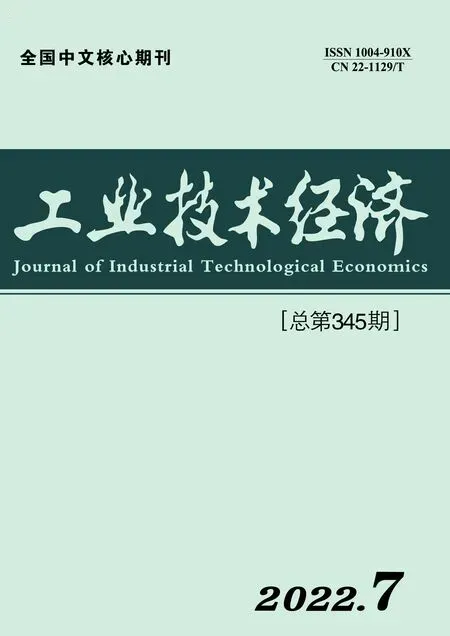數字經濟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岳 立 韓 亮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蘭州 730000)
引 言
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在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中占據重要地位。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重大國家戰略,提出了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的重要方針。數據表明,近20年來,流域地表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呈持續上升趨勢,2001~2019年其開發利用率達到80%,遠大于一般河流40%的生態戒線。黃河流域的水資源人均占有量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7%,且不能滿足河道外用水需求,缺水問題嚴重,這說明水資源問題是黃河流域最突出的問題。因此,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研究很有必要。
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快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工業4.0時代。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要素與傳統生產要素資本、土地、勞動等相融合,推動傳統產業向智能產業邁進。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要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1]。此外,數字經濟通過滲透其他產業會激發創新、增加產業的競爭力。
在此背景下,本文探究數字經濟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影響及影響機制,有助于通過數字經濟提高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促進流域生態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1 文獻綜述
1.1 關于水資源利用效率的研究
這類文獻主要集中在效率的測算、影響因素、區域差異等方面。在效率測算方面,大多數文獻主要基于投入產出來進行測算,如李騰等 (2022)[2]采用SE-DEA-IAHP(超效率DEA模型、區間層次分析法)方法計算出貴州省巖溶地區的水資源利用效率; 張凱等 (2021)[3]構建 RAM-SFA-RAM組合效率測度模型來測算中國省級的水資源利用效率。在影響因素方面,朱曉梅等 (2022)[4]、李德山和茍晨陽 (2021)[5]從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人口密度以及環境規制等方面研究了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鄧淇中和張玲 (2022)[6]從資源稟賦、科技水平、外貿等方面研究了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在區域差異方面,何偉和王語苓 (2021)[7]從黃河流域流經區的自然環境和水文情況研究了其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區域差異;岳立等 (2021)[8]從黃河流域流經城市所在水文、生態區的實際狀況及降水情況分區研究了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區域差異。
1.2 關于數字經濟的研究
這類文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數字經濟對其他方面的影響,主要是經濟發展、產業、環境等方面。在經濟發展方面,羅茜等 (2022)[9]研究表明,數字經濟通過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的發展直接作用于實體經濟;另外,數字經濟通過影響實體產業供需結構,促使產業結構合理化來間接推進實體經濟發展。在產業方面,于世海等 (2022)[10]發現數字經濟水平通過降低成本和提升技術創新降低了中國制造業資源誤置程度,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在環境方面,繆陸軍等 (2022)[11]發現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特征,二者間呈現倒U型關系;鄧榮榮和張翱祥 (2022)[12]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不同污染物的降低程度不同。
1.3 數字經濟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方面
該類文獻主要集中于數字經濟通過管理服務方面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產生影響。如蘇心玥(2015)[13]認為將互聯網深度融合于黃河流域水質量調度管理系統中,增加公眾服務平臺模塊,組建水權交易平臺,能夠實現水資源的高效配置;劉鑫和韓宇平 (2021)[14]認為用大數據對傳統水資源配置系統進行改進,有利于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高管理水平、促進數字產業發展、與其他產業融合來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鑒于此,本文將數字經濟、資源稟賦及制造業納入統一框架中,研究在資源稟賦和制造業發展的調節下,數字經濟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
2 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2.1 數字經濟與水資源利用效率
數字經濟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對于水務管理系統來說,以互聯網、大數據等為主的數字化信息技術能夠突破時空限制,為水資源管理者與社會公眾、不同行業用水戶以及流域發展需求方建立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務平臺,這將實現水量精確派送、減少灌溉棄水,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2)數字經濟通過賦能效應,應用新技術為傳統產業提高賦能,從而對產業結構數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級產生促進作用,緩解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周曉輝等,2021)[15],降低對有形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3)數字產業化背景下,數字化信息技術逐漸滲透于傳統產業中,從消費端向生產端、從線下向線上對傳統產業進行多角度、全方位改造,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16],從而使要素配置合理化,提高地區經濟增長效率,加大了環境污染治理力度,從而降低了工業廢水等污染物的排放。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促進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2.2 數字經濟、制造業發展與水資源利用效率
數字經濟通過 “產業數字化”,對制造業進行數字化整改,帶動制造業生產效率上升、產量增加;也能通過 “數字產業化”,把數字化帶來的知識、技術和信息轉化為生產要素,形成最終產品,發展新興產業,使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發揮更大作用,促使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相互促進,共同推動數字經濟與制造業在更深更廣層面融合。此外,制造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制造業與數字經濟協調發展會對數字經濟中的產業數字化部分起到強化作用,進而壯大了數字經濟的實力[17]。在此過程中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會逐漸擺脫傳統要素依賴路徑,推動各區域實現集約型和高效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提高要素資源利用效率[18]。據此,提出假設2。
假設2: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數字經濟與水資源利用效率兩者的關系存在正向調節作用。
2.3 數字經濟、資源稟賦與水資源利用效率
在資源豐裕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會產生明顯的資源依賴傾向,存在 “資源詛咒”現象。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的觀點,一個地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自然資源越豐富,其勞動生產率越高,生產成本越低,對經濟發展更有利。經濟的快速發展,增加數字經濟發展的需求,從而倒逼當前社會加大數字經濟發展的力度[19],產生資源依賴現象;另外,資源豐裕的企業不重視與資源有關的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技術開發。據此,提出假設3。
假設3:資源稟賦對數字經濟與水資源利用效率兩者的關系存在負向調節作用。
3 研究方法與指標選取
3.1 研究方法
(1) 非徑向、非導向性距離函數(Super-DDF)
測算水資源利用效率時,需要將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同時考慮在投入-產出指標體系中。Super-DDF模型可以同時將其考慮在內,而且能夠考慮要素的 “松弛”效應,從而有效地計算約束條件下的水資源利用效率值。因此,本文采用Super-DDF模型,以黃河流域56個城市作為決策單元構成技術前沿面。x表示每個DMU的N種投入,x=(x1,x2,…,xN)∈R?N;y表示M種期望產出,y=(y1,y2,…,yM)∈R?M;b代表K種非期望產出,表示第i個地區在t時期投入產出, (gx,gy,gb)為方向向量,為投入和產出的松弛向量。具體模型如下所示:

(2) Tobit模型
采用Super-DDF模型測算的水資源利用效率值以0為下限,若使用OLS回歸可能會使估計結果出現偏差。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來解決該問題。Ykt為第k個市在t期的水資源利用;Xit為解釋變量;βT表示回歸參數向量;εkt為殘差項。Tobit面板回歸模型如下:

3.2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3.2.1 投入產出指標
本文將地區生產總值作為期望產出指標,工業廢水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指標,資本存量、用水總量和勞動力作為投入指標,來測算2011~2020年黃河流域56個城市的水資源利用效率,各種投入產出指標體系見表1。其中產出指標用地區生產總值,以2011年為基期,進行平減。計算公式如下:

表1 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投入產出指標體系及描述性統計

其中,Ki,t和Ki,t-1為各城市在t和t-1 年的資本存量;Ii,t表示第i個城市在第t年的固定資產投資;δi,t代表t年的資本折舊率,本文參照復旦大學張軍老師的做法[20],將其取值為10.96%。
3.2.2 影響因素指標
(1)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
目前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還未有統一的標準,已有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對其進行了測度:①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視角進行測度[21];②依據數字經濟發展基礎和應用視角進行測度[22]。從已用文獻來看,前者包含了后者。因此,借鑒王軍等 (2021)[23]做法對兩者進行了融合,各類指標設定如表2所示。為了消除三級指標量綱與性質的影響,本文借鑒胡燕等 (2022)[24]的做法對正向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并采用熵值法進行TOPSIS權重測算。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量指標
(2) 機制變量
制造業發展水平(MI):采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資源稟賦(RE):采用各地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對資源稟賦衡量。
(3) 控制變量
為了防止由于變量缺失產生的誤差,本文還在回歸中控制了一組特征變量,主要有經濟發展水平(EDL),采用人均GDP衡量;環境規制(ER),采用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衡量;科技水平(TEC),采用黃河流域沿線城市的科技支出額衡量;財政集中度(FC),采用GDP中地區財政支出所占比重衡量;土地城市化(LU),采用城市建設用地占市區面積比重衡量。
3.3 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來自于 《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各省(區、市)的統計年鑒、各市水資源公報及各省(區、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統計公報。為了消除異方差影響,本文對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人均GDP及科技支出額為絕對額指標進行了取對數化處理,少數缺失值根據已有數據進行了線性插補。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對本文2020年的樣本數據影響不明顯,所以實證結果依然可靠。
4 實證結果及討論
4.1 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測算結果分析
(1)水資源利用效率時序演變特征
本文利用Maxdea軟件計算2011~2020年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值,并繪制了流域整體、黃河上、中、下游的效率均值變化趨勢圖。如圖1所示,2011~2020年間,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變動趨勢在前期呈波動變化趨勢(2011~2016年),在2016年達到頂峰,中后期平穩下降(2016~2020年),研究末期變化基本保持不變。從三大區域來看,其發展趨勢同整體大致相同。在整個變化過程中,上游水資源利用上升幅度最大,研究后期有所下降,下、中游地區變化趨勢與流域整體變化趨勢最為接近,而中游水資源利用效率大部分年份低于其他地區。

圖1 2011~2020年黃河流域整體及三大區域水資源利用效率圖
(2)水資源利用效率的空間分布特征
本文使用ArcGIS軟件繪制了黃河流域2011年、2015年及2019年的水資源利用效率空間分布圖(圖略)。研究發現,2011年流域內大部分地區水資源利用效率處于中等水平,56個城市中只有7個達到完全有效,中、上游的平涼、定西等地區的效率水平較低;2015年,流域56個城市中鄂爾多斯、慶陽等地水資源利用效率達到完全有效,其余城市均處于中等水平,且2015年較2011年整體顏色變淺,效率有所下降。2019年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較2011年和2015年有所下降,大部分地區處于中等水平,上、中游地區水資源利用效率水平相較于下游地區普遍較低。
4.2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基于Tobit模型對黃河流域56個城市2011~2020年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數字經濟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由于不同時期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因而對水資源利用效率會產生不同影響,所以本文將研究樣本進行了調整,表3同時報告了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的Tobit回歸結果。從全時段的回歸結果來看,數字經濟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從分時段來看,第一時段內數字經濟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同全時段回歸結果一致,但第二時段的回歸結果卻相反,這可能是因為2015年我國提出的“國家大數據戰略”,使得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在不斷落實和推進,從而促進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其在發展過程中對能源需求量也在逐漸增加,一些地區也會忽視環境的保護,從而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產生抑制作用。據此,假設1成立。

表3 基準回歸
從全時段控制變量估計結果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了水資源利用效率的上升,這與預期結果一致;財政支出增加并未伴隨著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這可能是因為政府支出規模越大,會對市場的干預度程度越高,導致其利用效率越低;土地城市化帶來水資源利用效率的下降,這符合預期。
4.3 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回歸結果是否穩定,本文使用以下兩個方法對回歸結果進行了檢驗,并使用相同實證方法重新進行回歸:(1)更改效率測算方法。在上文回歸中使用Super-DDF模型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進行了測度,在穩健性檢驗時,使用Super-SBM模型來計算水資源利用效率,其他變量保持不變,重新進行Tobit回歸; (2)替換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測算方法。本文借鑒趙濤等(2020)[21]的做法,采用主成分分析來測算數字經濟水平。上述檢驗結果同前文回歸結果一致,所以回歸結果具有良好的穩健性。
4.4 調節機制分析
基于前文回歸結果,本文進一步進行調節效應分析,以驗證能否在調節效應的驅動下,使得數字經濟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的作用產生有調節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4。在模型 (1)和(2)中依次加入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發展水平、資源稟賦的交互項。結果顯示,前者交互項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后者交互項具有顯著抑制作用,這說明數字經濟在制造業發展水平提高的調節下有益于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資源稟賦的調節下不利于水資源效率的提高,即存在調節效應,假設2和3成立。

表4 機制分析估計結果
4.5 區域異質性檢驗
在進行區域異質性分析時,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回歸。(1)根據黃河流域流經區的自然環境和水文情況,分為黃河上、中、下游3個區域; (2) 借鑒岳立等 (2021)[8]的做法, 根據黃河流域流經城市所在水文、生態區的實際狀況及降水情況,分為東北部濕潤半濕潤生態區(簡稱生態區Ⅰ)、北部干旱半干旱生態區(簡稱生態區Ⅱ)、南部濕潤生態區和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簡稱生態區Ⅲ),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區域異質性分析
分區域來看,在黃河上游和下游、生態區域Ⅱ和Ⅲ,數字經濟對水資源利用效率存在顯著促進作用;黃河中游,數字經濟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作用效果不顯著,原因可能在于相較于黃河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數字經濟處于進一步上升期,面臨突破瓶頸,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較小;在生態區域Ⅰ,數字經濟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但效果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該區域大多地區經濟相對落后,數據中心尚處于早期發展階段,技術水平不高,資源使用效率比較低下。
黃河上游、下游及生態區域Ⅰ的數字經濟與資源稟賦、制造業發展水平交互項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同整體一致;黃河中游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發展水平交互項對水資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顯著抑制作用,這可能是因為隨著高新技術在制造業領域的滲透,使現代制造業成為發展速度快、技術創新能力強的部門,但在此過程中卻忽視了資源和環境方面的問題;生態區域Ⅲ,數字經濟與資源稟賦交互項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數字經濟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這是因為黃河流域發展存在不協調、不平衡現狀,從而造成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所差異以及水資源利用效率不同。
5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采用Super-DDF模型對黃河流域56個城市水資源利用效率進行了測算,并使用Tobit模型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識別。研究發現: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水資源利用效率處于中等水平,未達到完全有效。全流域來看,數字經濟有利于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分區域來看,數字經濟在黃河上、中游對水資源利用效率存在顯著促進作用,在黃河下游存在抑制作用,但結果不顯著。數字經濟在制造業發展水平的調節下,有利于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在資源稟賦的調節下,不利于其利用效率的提升。據此,提出以下建議:
(1)基于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存在區域異質性,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各地區應根據自身發展狀況,制定適合的發展戰略;(2)黃河下游應該加強數字經濟的發展力度,使其突破瓶頸,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堅持綠色發展模式,減輕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負效應;(3)東北部濕潤半濕潤生態區(生態區Ⅰ)應加強相關科研人員的培養,加大人才培養力度,重視技術基礎的創新和突破,建立全新的數字經濟發展格局;(4)黃河上中游和生態區Ⅱ、Ⅲ區域應繼續加大創新研發投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提高基礎性和公共適用性技術的轉化,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5)實現制造業和信息產業融合發展,構建網絡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水務交流平臺、服務平臺以及交易平臺;(6)筑牢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補足區域資源稟賦存在的差異。在此過程中,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還要積極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
注釋:
①在本文中,黃河流域共有56個城市,黃河上游地區包括20個城市:分別為西寧、銀川、石嘴山、吳忠、中衛、固原、蘭州、白銀、天水、武威、平涼、慶陽、定西、隴南、呼和浩特、包頭、烏海、鄂爾多斯、巴彥淖爾、烏蘭察布;黃河中游地區包括21個城市:分別為西安、銅川、寶雞、咸陽、渭南、延安、榆林、太原、陽泉、長治、晉城、朔州、晉中、運城、臨沂、臨汾、呂梁、鄭州、洛陽、焦作、三門峽;黃河下游包括15個城市:分別為開封、安陽、鶴壁、新鄉、濮陽、濟南、淄博、東營、濟寧、泰安、萊蕪、德州、聊城、濱州、菏澤。
②生態區Ⅰ包括18個城市,分別為:濟南、淄博、東營、濟寧、泰安、臨沂、德州、聊城、濱州、菏澤、鄭州、開封、安陽、鶴壁、新鄉、濮陽、焦作、陽泉;生態區Ⅱ包括30個城市,分別為蘭州、白銀、定西、平涼、慶陽、天水、武威、太原、長治、晉城、朔州、晉中、運城、忻州、臨汾、呂梁、銅川、延安、榆林、呼和浩特、包頭、烏海、鄂爾多斯、烏蘭察布、巴彥淖爾、銀川、石嘴山、吳忠、中衛、固原;生態區Ⅲ包括8個城市,分別為隴南、洛陽、三門峽、西安、寶雞、咸陽、渭南、西寧。
③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留存備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