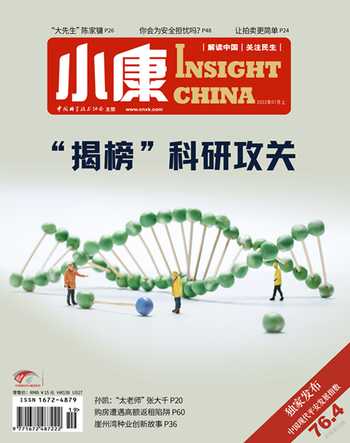孫凱:讓“張大千”回到巴蜀
于靖園 李鵬

陪伴 張大千生活照。孫凱表示,能夠跟在“太老師”身邊生活三十多年,對自己來說非常幸運。
“我知道大家都在期待著開館,所以我一定要設計、打造出一座真正意義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一流藝術博物館,我十分迫切地希望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于明年國慶節前能正式開館接待游客。”目前博物館主體建筑建設已經收尾了,成都市張大千藝術博物館總設計師孫凱對《小康》雜志、中國小康網記者說道。
張大千,別號大千居士,四川內江人,生前在亞、歐、美多次舉辦國際畫展,蜚聲國際,被譽為“當今最負盛名之國畫大師”。來自中國臺灣省的孫凱先生,是張大千先生入室弟子孫云生之子,他自幼陪伴在張大千身邊,隨之輾轉巴西、日本、美國及中國臺灣等地。
張大千是孫凱的太老師,在孫凱眼里,太老師是一位非常傳統的中國文人畫家,“他不僅僅擅長繪畫,書法、詩文、篆印樣樣精通,這是中國文人對自身的要求,說太老師是中國最后一位文人畫家也不過分,之后再也沒有人能趕得上他。”孫凱說,太老師常戴東坡帽,也喜歡穿著長衫馬褂;行遍歐美,始終說著一口四川話。“他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向來對故鄉有著非常深厚的懷念之情。”
除此之外,張大千還具有十分難能可貴的文人品質。“在我看來,太老師特別尊師重道,講究禮數。”孫凱表示,張大千有兩位恩師:曾熙和李瑞清。一次席上,有人拿出張大千恩師的書法作品請他觀賞,張大千立馬站起身來說:“這是我老師的作品,我必須要起身。”在孫凱看來,這是張大千對于他的老師的一份尊敬。而正是從這些細節,能看出張大千身上的偉大和文人品質。
都說“五百年來一大千”,孫凱表示,能跟在太老師張大千身邊生活三十多年,是幸運的。可以說,張大千深刻地影響著孫凱,不僅是他的作畫,還有他的為人處世。“太老師畫畫時,我都有在一旁幫其磨墨、陪伴、觀看他作畫。印象深刻的還有太老師的做人處事,他待人真誠大方,凡事不計較,有人向他求畫,他從不吝嗇,也有人轉手就將太老師的畫送到拍賣市場,太老師知道了也不生氣,反而笑說是自己的畫有市場。別人再求畫時,太老師仍然會好心贈畫,從來不計較自己作畫付出的辛勞,他就是這樣一個慣于站在別人立場、更多為別人著想的人。”孫凱說道。而從藝術的審美上來說,孫凱也受到太老師張大千、包括父親孫云生的影響:“張大千的繪畫是美的,在我自己這兩年親身用馬克筆作畫時,才真正體會到作畫的過程,過程本身就是美好的,它會傾注我的想法、心情,也有創造和快樂在其中。”
張大千和孫凱的父親孫云生的感情非常深。孫云生被張大千視為大風堂衣缽的傳人,孫云生陪伴張大千47年之久,他們在日本、巴西、中國臺灣等許多地方都一起生活、工作過。“我的父親1936年正式向張大千行過拜師禮,三跪九拜之禮,遞交三代家譜,在北平時宴請眾多賓客見證,這樣才進入張大千的大風堂門下的。”孫凱說,在張大千遷居巴西時,來信給他父親,并請他隨自己一同前往,信中張大千諸事都安排妥當,包括定好行程機票,安排孫云生一家如何生活等,事無巨細。“我父親當然也沒有猶豫,帶著我還有我母親一同去往巴西,我也在那里度過了童年。”?在孫凱的記憶里,張大千對自己的父親孫云生非常信任,可以說是依賴。“太老師每天醒來第一句話都是‘云生呢,云生在哪里’。”而就在巴西,張大千的潑墨潑彩誕生,這可以說是張大千在繪畫上最偉大的創舉,孫凱的父親陪伴左右,是見證的第一人。

傳承 建設中的張大千藝術博物館。未來這里將成為成都市的又一處文化地標。
“一生心血付托無人,故有望于吾弟也。”張大千在給孫云生的信中這樣寫道。他將傳承大風堂、傳承中國古典繪畫的火炬遞到了孫凱的父親孫云生的手上。后來,孫凱從自己父親手上接過這批珍貴的太老師粉本畫作。父親臨終前的托付,一千多張粉本畫作的重量……這些促成了孫凱在家鄉四川省建立一座張大千藝術博物館的決心。在孫凱看來,博物館是文化聚集之地,是一座城市精神文化厚度的體現,所以他決心以博物館的形式來承載這份傳承。“我要將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從里到外、從精神內涵到園林建筑都做到最好,也就是成都市政府在捐贈儀式上確認的要建成‘國際一流,國內領先’的張大千博物館。”孫凱表示。
出于愛國情懷和民族大義,孫凱先生遵從張大千落葉歸根的夙愿與父親文化傳承的囑托,決定讓張大千先生的作品回歸故土。他毅然把自己珍藏的張大千畫作及物品捐贈給成都市人民政府,雙方共同籌建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孫凱表示,這是對太老師張大千的鄉愁有所交代。“萬里故山頻入夢,掛帆何日是歸年”“行遍歐西南北美,看山須看故山青”,在孫凱的記憶里,太老師抒發鄉愁的詩文不在少數。“讓這批珍貴的粉本藏品回歸祖國,完全合乎情理,是我父親的心愿,也是對太老師一生的鄉愁的交代。”他說,在完成這件事的過程中,“傳承”成為核心。“一是將太老師與我父親長達半個世紀的師徒情義傳承下去,更重要的是以‘張大千’繪畫藝術為根基,將中國傳統古典繪畫乃至中國傳統文人文化傳承下去,這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業。”

左起:孫凱,孫云生,張大千,徐雯波。

在巴西時的兒時玩伴。左起:張大千兒子張心印,孫凱,張大千女兒張心聲。
帶著毅然的決心,還有不曾放棄的努力,2008年孫凱通過北京師范大學出版了張大千的粉本畫冊,并在上海、常州各地舉辦畫展。他的目的就是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張大千,了解中國畫家的偉大藝術精髓,而不是只知道同時期西方的畢加索。“我一直覺得堅持很重要,做事情和做人一樣。到現在,我花費了自己所有的時間和心力,我每天都會巡視在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的建設工地上,與展館建設者、設計團隊一起工作,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即使過程艱辛了一些。以太老師張大千藝術為根、傳承弘揚大千文化的事業,在這個過程中也更加清晰與堅定——這是我要堅持走的道路。”孫凱說道。
孫凱心中理想的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將擁有園林景觀、有現代元素的展廳、有內涵的展覽。園林景觀是以張大千在巴西親自建造的八德園為意象藍本的,復原的除了漂亮的松、石、湖景等等之外,還有中國文人的詩意造園意境在。“這是一座中式的文人山水園林,也是太老師的一幅立體水墨畫卷。”孫凱表示,該展廳通過現代技術和手段來呈現作品,既能滿足現代人的各項觀展功能,還是很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比如涉及藏品的保護,解決潮濕、存放等安全問題,都會運用目前最好的設施。比如細致到殘障人士的參觀通道設計等,最重要的是展廳不是一個建筑殼子,它要靠有中華民族傳統內涵的展覽內容來支撐。
“太老師張大千是詩、書、畫、印面面精通的全能手,我們在展廳的設計上完全依據太老師的繪畫特性展開,展館劃分為14個主題展廳,再結合太老師的藝術生涯,系統性地去展示他的繪畫藝術成就。”孫凱說,展覽要在傳承、教學、美學上下苦工夫,從中國文化的“根”上去思考如何努力做到。他表示,一切學問到最后都歸于美學,這里會是一座充滿著美學意境的博物館。
從2016年起,孫凱和四川的年輕設計師們,以“樸素稱心,乘物游心,明鏡之心”的設計用意,逐步細化設計方案,推敲園林景觀規劃布局,商討每一處建筑細節,希望新時代的年輕人能了解、接受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蘊藏的中國珍貴傳統文化。
孫凱和四川的年輕設計師們,以“樸素稱心,乘物游心,明鏡之心”的設計用意,希望新時代的年輕人能了解、接受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蘊藏的中國珍貴傳統文化。
孫凱本身是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室內設計專業的建筑設計師,他表示,五十歲之前他努力工作,五十歲過后則將人生的重心轉到建立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這項事業上來。“我的專業告訴我,中國人自己也能設計、建造出最好的博物館來,不見得會輸給國外的建筑大師,于是我帶領成都市本土的年輕設計團隊一起設計,我每天守在他們工位旁,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設計出了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設計就花了我整整六年時間——從使用功能到設計理念,從內部結構到外部裝飾、庭院園林景觀布局。我想這些對專業的執著,也是受到太老師張大千的影響吧。”
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的總體設計以張大千在巴西的故居八德園為藍本,把“館園一體”作為核心設計理念,將張大千的立體繪畫《八德園》,以借景的方式把原本不屬于園區的山水呈現于現實,把因角度和建物不同所產生的視覺效果進行展現,將畫作里的世界活生生地表現在大千館的庭園中。博物館主體建筑由各展廳有高差變化的連廊串聯,極富空間層次感,實現“館、園、景”的有機融合,形成一湖兩山多組團的總體空間格局,博物館內通過植入本土植物,再現了大千山水畫境。整個建筑群則采用小體量院落式布局,形成環線的參觀游線、建筑和庭院交匯共生,重現八德園景觀。
讓人間勝境在成都市重現,讓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成為這里的文化新地標,是孫凱想做成的事情。
“成都正在建設世界文化名城,文化歷史是這座城市的靈魂,成都有金沙遺址,有三星堆文化,有武侯祠,有杜甫草堂,各個時期,成都都有舉世矚目的文化成果,在近現代還有張大千,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是這條文化根脈上的重要一環。”孫凱說,“全世界都知道張大千,毫無疑問,這座備受成都市人民乃至全國人民期待的博物館,會成為成都市的又一張城市名片,一張像鉆石一樣閃亮發光且珍貴的名片。”
這張珍貴的名片不僅有著“傳播”的力量,還有著“傳承”的份量。“張大千先生是一位從四川走向世界的偉大藝術家,他對中國傳統繪畫的革新與推動做出了巨大貢獻,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的建成和開放運行可以讓大眾系統地了解張大千先生的藝術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們將從張大千先生的偉大藝術生涯中認知到創新才是最偉大的傳承。”?國家藝術基金評審專家、成都千高原藝術空間創始人、藝術總監劉杰對《小康》雜志、中國小康網記者說道。
“傳承”這個詞也是孫凱經常提起的。“這批藝術藏品是捐贈給全體中國人民的文化寶藏,通過這些珍寶,教育、感化我們的下一代,讓我們的年輕人將傳統文化根基打穩。就像粉本是繪畫的基本功一樣,沒有捷徑可走,而我們的根基只能是扎根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傳承最終要靠年輕的下一代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