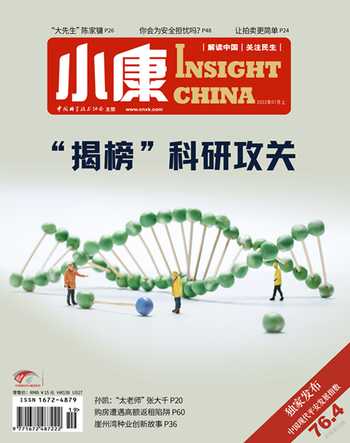高效整治醫藥腐敗需治標又治本
梁嘉琳
近日,國家衛健委、公安部等九部委聯合印發《2022年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這份一年一度的醫療/醫藥反腐重磅文件提出,加大對生產環節的財務監管力度,防范將“回扣”資金的套取從流通環節轉移至生產環節,嚴厲打擊套取資金用于藥品耗材設備回扣、商業賄賂行為。縱觀歷年工作要點文件,這是國務院糾風辦首次將反腐對象從傳統的醫藥購銷領域延伸到醫藥全產業鏈。此舉勢必對我國的大健康產業帶來深刻影響。
醫藥產業、醫療服務行業的風氣好壞,決定了醫師能否合理診療、合理處方,決定了醫藥產品能否優勝劣汰,進而影響人民群眾的健康權益、就醫負擔。一些國家的經驗教訓顯示,如果大部分醫藥企業通過“帶金銷售”等違法違規行為獲得醫院準入、醫師處方優勢,進而將所謂“營銷”成本轉嫁到終端藥價或其他患者附加費用,患者會成為腐敗的最終受害者。
雖然大部分醫療/醫藥腐敗是微腐敗,但事關根治“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這一醫改目標,因此,國家歷來重視行風建設工作。如今,我國的糾風工作已經發展為衛生部門會同紀檢部門、公安部門聯合辦案,會同商務部門、市場監管部門開展流通執法,會同醫保部門、藥監部門實現“三醫聯動”。值得一提的是,國家醫保局自2018年成立以來,開辟了醫藥反腐“第二戰線”,特別是建立藥品招采信用評價制度,將被司法機關判定相關違法行為的醫藥企業,納為嚴重/特別嚴重失信行為方,使之喪失某省甚至全國招標市場,從而對腐敗分子形成強烈震懾。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隨著反腐力度逐步加強,與醫生從患者收取紅包等個體化、顯性化行為不同,醫療/醫藥腐敗向著系統化、隱蔽化的方向發展。以醫藥企業向醫院/醫生支付的“回扣”為例,在行賄方,一些醫藥企業不直接行賄,而是將銷售費用打包給銷售外包機構(CSO),部分機構往往由資深醫藥代表注冊工作室,打起“游擊戰”,作為行受賄雙方的“白手套”和洗錢機構;在受賄方,一些醫療管理者將“回扣”變相分給科室內醫務人員,或轉為本單位的“小金庫”,甚至“寄存”在醫藥企業,試圖通過“吃人手短”“法不責眾”來規避黨紀國法的追究。
近兩年,隨著銷售外包機構得到整頓,跳出藥品流通環節,一種藥品研發生產環節的新型腐敗產生了。因此,上述九部委文件強調,防范將“回扣”資金的套取從流通環節轉移至生產環節。比如:一些所謂“醫生科研平臺”的真實盈利模式是助力醫藥企業向科研型醫生輸送非法利益,即通過將患者管理調研問卷與藥品處方量掛鉤,再將醫生課題勞務費與調研問卷發放量掛鉤,間接地支付畸高的回扣費用。再比如:一些所謂“專利服務機構”的真實盈利模式是助力醫藥企業向醫院研究團隊及其管理者輸送非法利益,即通過促成醫藥企業向大型醫院購買新藥專利,間接地支付畸高的服務費、專利費。
為持續高效整治醫療/醫藥腐敗,筆者建議,在治標層面,可實施信息流、資金流、數據流“三流合一”模式,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制定法律強制醫務人員的所有收入來源面向醫療共同體公開,對囊括研發-生產-銷售-使用等全產業鏈的現金流進行穿透式監管,并通過大數據手段篩查出高危機構、高危崗位、高危人員進行重點督辦、飛行檢查。在治本層面,要讓守法者獲益、違法者受懲,通過提升服務收入、降低藥品收入的“騰籠換鳥”改革,既要破解大部分醫療服務項目價格長期畸低問題并對醫務人員予以足夠激勵,又要對寬限期內不交“回扣”或整改不力的機構和個人予以從嚴懲處。
(作者系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健康國策2050”學術平臺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