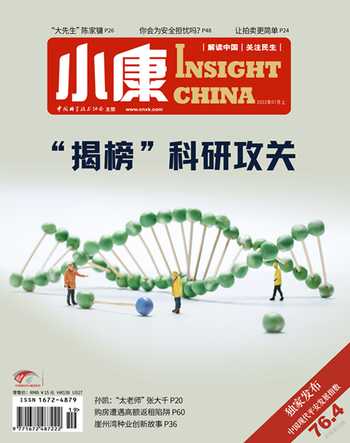科學振興瓷業
東升
上回說到,抗日戰爭爆發后,景德鎮遭到日本侵略者飛機的狂轟濫炸,坯坊、窯房大面積遭受破壞,僅剩30多座窯生產,瓷器產量銳減。至景德鎮解放前夕,全鎮只剩下百余個處于停業狀態的作坊和1000名左右失業的工人,景德鎮的陶瓷工業陷于奄奄一息的狀態。
而景德鎮制瓷史上有兩件不容忽略的大事:一是明代御器廠的建立,二是清末江西瓷業股份公司的建立。其間,有兩個不可忽略的人:一是唐英,一是杜重遠——同樣的殫精竭慮,同樣的良苦用心,同樣的滿腔熱血。
清人藍清所著的《景德鎮陶錄》對唐英這位乾隆年間的督陶官做了很高的評價,“公深諳土脈火性,慎選諸料,所造俱精瑩純全……廠窯至此,集大成矣”。在清代景瓷的發展過程中,唐英功不可沒。他在景德鎮督陶15年中,虛心向陶民學習,與工匠打成一片,完全以陶人自居,終于變外行為內行。他掌握了制瓷方面的各種知識,并身體力行,與瓷工們一起從事工藝鉆研,同時對瓷業生產技藝進行科學總結,從理論上加以提高,先后編寫出《陶務敘略》《陶冶圖說》《陶成紀事》《瓷務事宜諭稿》等著作。那個時期的瓷器產品被稱為“唐窯”,其制造水平和質量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過了鼎盛之年的景瓷制造業,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屠刀再次變得舉步維艱。民國期間,出身貧苦農民之家、以實業救國為畢生志愿的杜重遠走了一條與唐英截然不同的道路。作為瓷業改革者,他為景德鎮陶瓷工業的改革傾注了心血,力主重新振興景瓷,成立陶業管理局,自任局長。從外地招攬人才,培訓瓷業工人,制訂改革陶瓷工業的各項措施,促使景德鎮瓷業生產煥發出勃勃生機。求學期間,他目睹袁世凱與日本侵略者簽訂21條賣國條約,非常激憤,遂參加游行抗議,“寢食俱廢”。為興辦實業救國,杜重遠東渡日本學習窯業,對于運用現代科技于瓷業生產了然于心,因此決心大膽引進西方科技,徹底改造景德鎮瓷器面貌,以科學振興古老的景德鎮瓷業。

那個時期的瓷器產品被稱為“唐窯”,其制造水平和質量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為景德鎮陶管局局長,杜重遠首先鏟除了窯禁、“買位置”等瓷業陋習,大膽引進西方科學的陶瓷生產方法,改進生產技術與工藝,實行分工負責制,同時普及工人文化,提高工人素質,舉辦工人訓練所教工人識字,灌輸國外生產常識。此外,他還改進瓷業的供銷方法,主動尋找市場,創建了江西陶業人員養成所,全國范圍內招生,培養陶瓷工業技術、陶瓷工藝品外貿方面的人才,從而實現整個行業的現代化,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經歷和見識,決定了杜重遠關于瓷業的改革一開始就根植于近代化機器大生產和現代化管理,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制度里,在封建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形勢下,在傳統小作坊式相傳見習的背景中,在外強入侵、民族危亡、政局動蕩的歲月里,無論是新生產方式的強行推行方式還是長時期的接觸、了解,都是無法實現的。改造景瓷的道路在當時變得異常艱難,實業救國的道路也變得茫茫無期了。1937年,杜重遠遭人排擠,被迫離職,他改造景瓷的理想徹底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