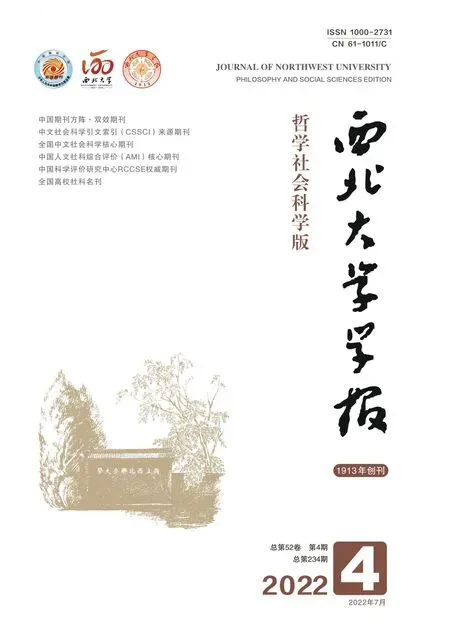諾音烏拉31號墓人物繡像考論
梁 云,許稼樞,李偉為
(西北大學 文化遺產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7)
諾音烏拉(Ноин-ула)匈奴墓地位于蒙古國中部,南距該國首都烏蘭巴托市(Улаанбаатар)約100千米,北距恰克圖(Кяхта) 250 千米。1924—1925年,由蘇聯考古學家科茲洛夫(П.К. Козлов)率領的蒙古—西藏考察隊前往該地調查發掘,在其中名為“蘇珠克圖(Судзуктэ)”“珠魯木圖(Цзурумтэ)”和“古德日勒圖”(Гуджиртэ)三處山谷的針葉林帶中發現了212座屬于匈奴時期的墓葬遺存,對其進行了編號,并發掘了其中12座墓。1954—1957年道爾吉蘇榮(Ц.Доржс?рэн)又發掘了5座。2006—2011年,娜塔莉亞·波羅西瑪克(N.V.Polos′mak)率領俄蒙聯合考古隊在蘇珠克圖發掘了包括M31、M20、M11在內的3座墓葬(見圖1)[1]6。
31號墓位于蘇珠克圖墓地西區的中部,是一座單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見圖2,1),墓道位于墓室南側,南北長20米,東西寬18米,深約8.8—13米。地表之上有長方形帶坡道的低平土石封堆,中部有塌陷。封堆周邊及其內部砌筑石墻。墓室為四壁帶多級臺階的豎穴土坑,深約13米。
墓室內有內外兩層木槨,均用松木搭建,其中外槨長5.5米、寬3.5米,內槨長3.5米、寬2.1米。木棺位于內槨室中部。在內槨與木棺之間的東部發現有羊毛織物殘塊,其中一部分壓在棺木下的松木底板上, 縫有鑲邊,另一部分位于棺東側回廊底板上。織物上部均覆蓋很厚的一層青色淤泥(見圖2,2)。
經過提取和室內清理修復, 發現有三塊織物殘件, 其上都有人物、 動物以及植物的刺繡形象。 本文重點探討第一塊織物繡像的內容, 繡像人物的族屬和信仰, 以及它所反映出的匈奴與古代中亞國家的關系。
一、人物繡像內容及相關研究
羊毛織物應為掛毯或壁毯,第一塊壁毯殘件為橫長方形,長1.92米,寬1米(見圖3);其頂部由兩條黃色鑲邊分隔開,第一條鑲邊上部繡成排的長葉植物,每株植物有5—7片葉子,一般帶著兩個圓形的漿果,可能為月桂樹枝或蘭科植物。兩條鑲邊間的圖案殘缺嚴重,其左端繡一口部張開、顧首展翅的鳥,形似鴻雁;中間繡有花朵,與底部中排的裝飾圖案類似。
中部刺繡的畫面主題,可以命名為“走向圣壇的隊伍”。圣壇位于畫面右部,為塔形的帶二級底座和雙層托盤的火壇,上部托盤中火焰正在燃燒,中間繡有一S形符號,兩旁有舌形符號。火壇左邊有行進狀態中的6人,帶隊的首領位于圣壇左側,手舉蘑菇狀物,奉獻給圣壇右側的祭司。
圣壇左邊第一個男人(首領),有淺褐色卷發,高鼻深目,唇上有髭(小胡子),頭上扎有發帶。他穿著下擺敞開的華麗深紅色長袍,領口和下擺開口處有黑色滾邊,胸部和臂部裝飾有金色條帶、圓點和半圓點。長袍下部露出黃色的褲子,腳穿缺少后跟的軟底鞋。腰部系帶,從帶后可見一個帶有花式首和十字格的終端,可能屬佩戴的武器。男人左手持有一個蘑菇狀物,右手微曲向前,神情注目于左手所持之物(見圖4,1)。
圣壇右側的男人(祭司),大臉,有黑色卷發,唇上留有茂密的髭須。上身著騎士式帶長尾的黃色上衣,領口和袖口留有黑色滾邊;下穿緊腿長靴,其上有斜線裝飾,靴頭上翹。左腿外懸掛大型箭袋,右腿前伸靠近圣壇。他左臂上舉,手部緊握,似持有某物,看向圣壇左側的首領,二者似乎在進行儀式上的交流。
左邊第二個男人留有較短的黑色卷發,有黑色大眼睛和“一”字型髭須,面頰較寬。他身穿黃紅色短上衣,裝飾黑色毛皮,著黃色褲子。左臂前伸,手握成拳,在腰帶左面可見劍柄,劍格為梯形。背后背著背袋或編簍,里面放置一曲棍狀物。右手緊握韁繩,牽一匹牡馬(見圖4,2)。
牡馬圓眼,腦門有額鬃(劉海),鞍上有四個角形支座,鞍下懸掛兩個幼虎或獅子的爪形腳掌皮革。長尾根部上彎,中部結扎箍帶。馬胸前系穿圓形牌飾。
左邊第三個男人立于馬側,像是騎士,頭部似系額帶,留著齊整的層疊式卷發,高鼻深目,無髭須。他上身著甲,覆蓋著矩形甲片,以淺黃色細線縫合,立領可能沒有保存下來;下身著紅色褲子,背披斗篷。騎士左臂抬起,回手呈眺望狀,右手似乎握著馬鞭。
左邊第四個男人,留著層疊式紅褐色卷發,上身穿著黃色短袍,領口和下擺處繡有黑色滾邊,下身著紅色褲子,腳踩無跟軟鞋。左肩扛著一根曲棍狀物體,右手持矛,矛頭缺失。腰間系佩長劍,其前端位于腰帶左側,劍格呈圓角梯形,劍莖細長,劍首缺失;后端位于股間。他的右大腿上綁系著匕首,從腰帶左邊飄揚著兩條帶子,末端為三角形。在他的眼前、腰部及大腿內外,飛舞著蝴蝶。
左邊第五個男人,頭部繡像圖案殘損,僅見高鼻深目和卷發。他穿著紅黃雙色短上衣,胸部和胳膊上裝飾著黑色條帶和黃色圓圈,下身穿黃色褲子。右大腿上用皮帶綁系著匕首。右臂屈持著帶柳葉形鋒刃和彎鉤的矛柄;左臂前遞,手掌向前張開。腰帶左邊可見帶橢圓形劍格的劍柄,劍首缺失;劍鞘用黃色絲線繡出,與矛柄下部在兩腿之間交叉。腰帶右邊兩條帶子飄揚,末端均為燕尾形。
左邊第六個男人,頭向后轉,似乎在觀望后面跟隨的人,他留著層疊式紅褐色卷發,圓臉,黑目,高鼻,唇上有黑色的條形短胡,身著下擺敞口的黃色長袍,紅黃兩色的褲子,以及不大適足的軟鞋。他右手持矛,矛柄直到足部;左手扶握長劍柄的中部,長劍帶有半圓形劍首和長方形劍格。
底部繡有三條金黃色鑲邊,在第一條及第二條鑲邊之間繡有一排圓圈,圈內有十字形交叉。在第二條、第三條鑲邊之間的中部繡一朵黃色的彼岸花(曼珠沙華),花瓣舒展反卷,邊緣呈皺波狀;兩側有平行彎曲的細線,可能表現的是倒披針形的花蕊。花的兩側各有一雙翼小人(或精靈),左側小人著圓領寬袖長袍,左臂前伸,指向花朵,右臂彎曲,手抓在腰部;右側精靈長嘴猴腮尖耳,左手執月桂樹枝,展翅飛行,前后有卷云紋。第三條下為成排的長葉植物,與頂部上排的裝飾圖案一致。
第二塊壁毯殘件保存較差(見圖4,3),中部繡有兩個向右行走的人,均高鼻黑目,有黃褐色卷發,唇上留髭須。前面一人上身著紅黃雙色短袍,胸部和臂部飾有黑線和黃邊;下身著黃色褲子,足穿黃色軟鞋。左側腰間掛有長劍,帶圓首長莖和“一”字形劍格,劍尾位于兩腿之間。左手前伸,握一曲柄之物,右手持長矛,腰后可見兩條絲帶。后面一人上身穿黃褐色短袍,領口、袖口及胯部繡有黑色滾邊;下身著黃色長褲。右手上舉至眉心,左手持矛。殘件頂部有兩道、底部有三道金黃色鑲邊,其中底部上排可見內含十字的圓圈圖案,中排殘存一個雙翼小人,下排為成排的長葉植物,構圖與第一塊完全一樣。因此,第二塊應為第一塊左邊的延伸部分,二者屬同一整體,畫面中的二人也屬“行進中的隊伍”。
第三塊殘件保存更不樂觀(見圖4,4),上繡兩對戰斗的士兵。左邊一對中的勝利者高鼻深目,黑色短發,留絡腮胡須,上身著紅黃雙色圓領長袍,下身穿黃色馬褲,腰部左側掛劍。他左臂前伸,抓住失敗者,右臂揚起似在抽打。失敗者頭部耷拉下來,卷發雜亂,眼睛緊閉,嘴角流血。他身穿矩形甲片的鎧甲,腰左側懸掛劍鞘,身體彎曲成駝背,左臂向上伸開,似被吊在梁架上。右邊一對士兵,其中左側男人有齊耳黑發和“一”字型髭須,身著黃色左衽交領上衣,領口處有紫紅色滾邊并夾雜金線裝飾,下身著紅褲,褲上有黃色垂帶裝飾,足登軟鞋,腰后佩劍,右大腿上綁系帶鞘匕首。他左臂屈伸握拳,右臂高舉似乎握著武器,要落下擊打。右側男人留絡腮胡須,似為左對中的勝利者,著紅色羅馬式圓領長袍及黃色燈籠褲,右肩有鉤扣,左腕帶金鐲,腰左側佩劍。他右臂前伸執長方形盾牌,處于防御狀態,盾面飾雙線菱形格紋。
該墓出土了漢成帝“元延四年”(前9)刻文的漆耳杯(見圖4,5),為西漢少府屬下考工制作。耳杯內紅外黑,外繪水鳥圖案,刻文還提到主造者、副職、監造者的名字。墓葬的年代不能早于公元前9年,再考慮到漆木器的使用有一定壽命,墓葬很可能屬新莽至東漢早期,或者說公元1世紀的前期。
發掘者波羅西瑪克認為繡像中的人物是印度-塞克(saka)或者是印度-帕提亞(Indo Parthia)人,壁毯來源于印度西北部地區。因為壁毯與敘利亞帕爾米拉(Palmyre)遺址出土的織物在制作工藝上有相似之處,繡像中立于馬側的武士形象及其胸甲、捆扎的馬尾、人物腰部后的三角形末端飄帶,均與印度-塞克和印度-帕提亞諸王錢幣上的形象類似[2]。
俄羅斯學者亞琴科(Sergey A. Yatsenko)對繡像上人物的服飾組合進行了系統梳理,他認為從色彩搭配(紅色或玫瑰色搭配白色)、服裝組合(交領短上衣或袍服搭配直腿褲和軟鞋)、人物發飾(短而齊整的卷發)來看,繡像上人物服飾與巴克特里亞的月氏人有直接聯系,因此將繡像人物比定為巴克特里亞的大月氏人,并認為壁毯的加工地不在印度地區而在巴克特里亞,當時匈奴強而月氏弱,壁毯是月氏進獻給匈奴的貢品[3]。
法國學者弗蘭克福特(Henri-Paul Francfort)認為31號墓氈毯屬于公元1世紀的犍陀羅文化或巴克特里亞的月氏-貴霜文化,繡像上大多數人物明顯是月氏-貴霜或吐火羅人。其中第一幅壁毯上火壇左側貴族的面部特征與赫勞斯(1)“赫勞斯”又被稱為“赫萊烏斯”(Heraios),“薩那布”(Sanab) ,“毛斯”(Miaus)。銀幣上的人像類似, 火壇右側人物可能是來自貴霜王室的最高首領(“萬王之王”)。壁毯繡像與烏茲別克斯坦哈爾恰揚(Khalchayan)遺址雕塑都表現了月氏的宮廷儀式,繡像是作為月氏的禮物被送給匈奴的[4]。
楊富學認為壁毯表現了大月氏人的戰爭和祭祀場景,他注意到繡像上首領的腳踝系有靴扣,與貴霜翖侯及貴霜王相似,由此認為貴霜王朝的建立者源自大月氏,是月氏王室的支系[5]。
二、繡像人物的族屬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壁毯出自匈奴貴族墓,但繡像人物大多高鼻深目,且有卷發,屬印歐人種,體貌特征及人種與匈奴大不一樣,其族屬不可能是匈奴。諾音烏拉匈奴貴族墓的顱骨經鑒定為北亞蒙古人種,或者說蒙古人種的古西伯利亞類型,這也是匈奴主體民族的人種類型[6]292-301。匈奴的體貌特征可以概括為“低顱闊面”,即顱型偏短,面部較闊,鼻骨扁平,與繡像人物迥異。諾音烏拉墓葬殘存不少匈奴發辮,頭發黑而且直,與繡像人物的紅色卷發完全不同。魯金科(S.I.Rudenko)將之與其他地區人群毛發比較,發現最直的是諾音烏拉出土的毛發,最卷曲的是斯拉夫人的毛發[7]106,131。此外,匈奴人男性發式為“椎髻”,即將額頭、兩鬢的頭發都梳向腦后并在末端束結;匈奴婦女則習慣留二至三股頭發編成的發辮[8]314。這兩種發式均不見于繡像。
公元前2世紀末塞克人南下入侵印度西北部,逐步建立了分散的印度-塞克王朝,存在了約百年時間,其最早的統治者是毛厄斯(Maues)[9]144。該王朝發行銀幣和銅幣,正面以國王騎馬像為主,背面為希臘神像(見圖5,1—4),如斯帕拉雷西斯(spalarizes 前60—前57)、阿澤斯一世(Azes Ⅰ前57—前35)、阿澤里西斯(Azilizes前57—前35)、澤翁尼西斯(Zeionises前10—公元10)的錢幣。公元20年原居帕提亞東部蘇倫家族的貢多法勒斯脫離宗主國自立,建立印度-帕提亞王朝,逐步吞并原印-塞王朝,存在了約140年。該王朝發行帕提亞式錢幣,正面為國王頭像或騎馬像,背面有希臘神像或牧人執弓像(見圖5,5—8),如貢多法勒斯一世(Gondophares 20—50)、阿布達加西斯(Abdagases 50—100)、索庇多尼斯(Sorpedones 65)、帕柯雷斯(Pakores 100—135)的錢幣[10]135-137。
上述錢幣國王騎馬像的面目模糊不清,與繡像人物沒有可比性;國王肩后有斗篷或披風,不同于繡像人物身后的腰帶;而且扎束馬尾的習慣在很多國家地區廣泛存在,不屬于某個特定地區。帕提亞和印度-帕提亞錢幣上的王像頭戴氈帽,或束發帶,或著王冠[11],其中束發帶的習慣與繡像人物首領一致;但前二者王像一般留有大胡子或絡腮胡,腦后或有球髻,與后者均大不相同。況且印度-塞克、印度-帕提亞王國位居興都庫什山以南,與蒙古高原的匈奴距離遙遠,之間相隔新疆、中亞,很難想象它們之間有什么直接的交流和聯系。因此,發掘者的說法理由并不充分。
公元前2世紀晚期至公元1世紀中期巴克特里亞地區有大月氏國,其統治范圍東至帕米爾,北至西天山,西北至鐵門關,西至阿富汗西北部,南至興都庫什山。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這個區域陸續發掘到與月氏相關的墓葬,如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阿魯克陶(Aruktau)、圖爾喀(Tulkhar)、土布哈那(Tup-Khona)墓地,烏茲別克斯坦東南部的拉巴特(Rabat)、阿依塔姆(Airtam)墓地,土庫曼斯坦最東部的巴巴沙夫(Babashov)墓地。這些墓葬的文化特征相當一致,以偏洞室墓為主,還有一定比例的豎穴土坑墓,流行單人一次葬和頭北足南的仰身直肢葬式(見圖6,1—2)。從時間、空間、文化因素、外來屬性等方面看,它們應屬月氏文化[12]。需要注意的是,20世紀70年代在阿富汗北部席伯爾罕(Shibargan)的特里亞特佩(Tillya-tepe)發掘到6座公元1世紀前期的貴族墓,出土大量金器,被稱為“黃金之丘”。這6座墓以唯一的男性墓M4為中心分布,其他為女性墓;墓葬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坑內有木棺;皆為單人仰身直肢葬;其中M1、M3、M4死者頭向北(見圖6,3—4),M2頭向東北,M5、M6頭向西。其墓向、葬俗與上述阿姆河以北的月氏墓相一致,應是一位大月氏國王及其王后、夫人的陵墓。
繡像“走向圣壇的隊伍”以畫面右部的火壇最醒目,發掘者及研究者都一致認為它是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標志,這說明繡像人物是信仰拜火教的。該教由瑣羅亞斯德創建,時間不晚于公元前7世紀,后來成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國教。繡像上的階梯束腰狀火壇與米底亞王國君主基亞克薩雷斯(Cyaxares前625—前585)陵墓大門上方火壇圖、魯斯塔姆的大流士摩崖陵墓上部浮雕火壇、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及阿契美尼德時期印章上的火壇酷似[13],區別僅在于頂臺和底座的階梯,后者們除了二級外還有三級(見圖7,1—4)。這種形制的火壇源遠流長,在薩珊波斯王朝錢幣上作為拜火教的象征出現,如沙普爾一世(Shapur)、霍米茲德二世(Hormizd II)銀幣(見圖7,5—6),被研究者歸為“波斯類”[14],是拜火教火壇的標準樣式。
拜火教認為死者尸體會污染大地,嚴禁將之直接入土埋葬。阿維斯塔經《辟邪經》規定將人或狗的尸體直接埋于地下半年以上者,要被罰抽一至兩千鞭,兩年以上者罪無可赦;死尸應置于高處(達克瑪)曝曬,任鳥獸啄食,剩下的骸骨收斂在甕中[15]99,126,131。在阿契美尼德、帕提亞、薩珊王朝時期普遍流行曝尸天葬,再斂骨二次安葬的習俗,在伊朗和中亞都曾發現與達克瑪相關的高臺建筑,只是波斯王室貴族將尸體涂香防腐,置于石制陵墓里,與土地隔開[16]。但是上述月氏墓葬,無論平民小墓還是王陵,均流行一次性土葬,死者直接入土為安。月氏人顯然不信仰拜火教,由此可知,繡像上人群絕不是月氏。此外,目前僅在月氏女性墓中發現了頭帶飾,如圖爾喀ⅤM7、拉巴特M36、特里亞特佩M1,而不見于男性墓。可見月氏男性沒有扎頭帶的習慣,如特里亞特佩M4就未發現頭帶飾,墓主復原形象也是不扎頭帶的[17]246(見圖6,4)。這一點與繡像上的首領形象不同。
繡像上首領頭上的發帶從前額束至腦后,腦后有兩根飄帶,唇上有髭(小胡子),下顎無須(見圖8,1),與赫勞斯銀幣上的頭像及烏茲別克斯坦哈爾恰揚遺址宮殿墻面上裝飾的彩繪黏土貴族塑像酷似(見圖8,2—3),三者應屬同一家族,甚至不排除有些屬同一人。
赫勞斯(ΗΙΑΟY)錢幣主要發行于公元1世紀的巴克特里亞地區,包括減重后的阿提卡標準四“德拉克馬”(Drachma)銀幣,其正面為向右的國王側面頭像,波狀卷發扎頭帶,著交領長袍;反面為向右的國王騎馬像,身后勝利女神尼克持花環加冕,人像上、馬腿間、馬蹄下有三處變寫的希臘文。經英國甘寧漢(Alexander Cunningham)和迦德勒(Percy Gardner)等學者研究,三處銘文分別為“獨裁者赫勞斯”(ΤYΡΑΝΝΟYΝΤΟΣ ΗΙΑΟY)、“薩那布”(ΣΑΝΑΒ)、“貴霜”(ΚΟΡΡΑΝΟY)。還有減重后的阿提卡標準一“奧波爾”(Obols)銀幣,正面為國王頭像,反面為人立像及兩側銘文“赫勞斯、貴霜”[18]107-134。哈爾馬塔(Harmatta)認為“赫勞斯”乃君主的稱銜,是“yabgu”(翖侯)的最古老形式[19]247。克力勃(Joe Cribb)也認為“赫勞斯”是“翖侯”頭銜的希臘文音譯[20],他還認為“薩那布”是鑄幣廠的標記[18]107-134。大英博物館藏有兩枚發行于巴基斯坦北部的銅幣,其正面與銀幣一樣,為赫勞斯頭像,只是周緣有一圈佉盧文maharayasa/rayatirayasa/devaputra/kuyula katakapasa,即“大王、王中之王、天子、庫朱拉·卡德菲塞斯(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2)maharayasa源自梵語mahārāja,意為“大王”;rayatirayasa源自梵語rājatirāja,意為“王中之王”;devaputra源自梵語devaputra,意為“天子”;kuyula katakapasa即kujula kadphises,為丘就卻姓名。,文字與丘就卻發行的公牛駱駝錢幣完全一致;反面與四德拉克馬銀幣一樣。克力勃由此認定赫勞斯就是丘就卻,他在位于公元30—80年[18]107-134。目前學術界已基本達成共識,赫勞斯錢幣是某一位貴霜翖侯發行的。克力勃的論證很有說服力,發行者很可能就是丘就卻。
1959—1963年,普加琴科娃(G.A.Pugachenkova)帶隊發掘了烏茲別克斯坦東南部的哈爾恰揚遺址,遺址位于蘇爾漢河右岸的迪諾市(Денау)附近,在其中發現一座公元初期的宮殿建筑,長35米、寬26米,面向東,中部為帶廊柱的前廳、正殿和后室,北部為門房和回廊,南部為儲藏室和回廊(見圖9,1)。在接待前廳三面墻的上部有兩米多寬的人物浮雕裝飾(見圖9,2),主要有三組浮雕群像:第一組位于正壁(西壁)中心,是坐在寶座上的國王與王后及其左側的公主夫婦,右側是帕提亞王子夫婦和巴克特里亞當地小王夫婦(見圖9,3);第二組在第一組北邊不遠,為居中而坐的首領及其右側站立的長子、次子、戰車女神,和左側侍衛(見圖9,4);第三組在第一組南邊,為四位策馬奔騰、彎弓射箭的騎士(見圖9,5)。三組之上為較窄的裝飾帶,由拱形花環及點綴其間的半身人像構成。
發掘者認為三組浮雕主要的男性人物屬同一家族,面貌特征相似:頭顱扁平、顴骨較高、鼻子挺直,眼角較長接近太陽穴,唇上有修整精致的小胡子,頭發用環帶束緊。其形象與赫勞斯錢幣頭像很相似,因此該家族為赫勞斯家族,有貴霜君主血統,哈爾恰揚是早期貴霜的統治中心[21]190[22]127。
準確來說,與赫勞斯錢幣頭像相似的僅限于第二、三組浮雕,尤以第二組首領及其長子為最(見圖9,6、見圖8,3)。第一組的國王頭戴游牧風格的尖帽(見圖9,7),系用兩片氈布或毛皮由中縫合而成,中間從前到后高銳,兩側斜廣。這種尖帽不同于斯基泰或塞人用一塊毛皮圍合縫制的細長尖頂帽,類似者僅見于諾音烏拉匈奴墓和蒙古阿爾泰巴澤雷克文化晚期墓葬[8]308-311。國王眉眶彎弧,鼻翼較寬,下巴豐厚,唇上無髭,相貌服飾與第二組首領大不相同,顯然不屬于赫勞斯家族。如果第二組首領就是一位貴霜翖侯,那么第一組的國王就可能是一位大月氏王,因為后者占據前廳正壁中心位置,地位最高。宮殿建于大月氏統治時期,據《漢書·西域傳》“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貴霜翖侯作為臣屬將月氏王及王后像奉于正位,自己及家族成員的像附翼于旁,是合乎情理的。
法國學者葛樂耐(Franz Grenet)將第一組國王右手邊站立的有三角形卷曲絡腮胡貴族男子比定為帕提亞國王瓦爾達尼斯一世(Vardanes I)(見圖9,8),后者曾流亡巴克特里亞地區,后來又重掌權力[23]。如果此說成立,則哈爾恰揚宮殿建于瓦爾達尼斯一世時期(39—47),當時丘就卻年約50歲(3)余太山先生認為丘就卻出生于公元前5年。參見余太山:《貴霜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35頁。,與第二組首領身份、年齡吻合,其右側長子就可能是維馬·塔克圖(Vima Takto)。當然,如果宮殿年代略早,那么首領長子就是丘就卻,首領為其父親。
除了人像,繡像上馬的形象也與浮雕一致:頭部較小,額頭鬃毛較長,胸部有圓形牌飾(見圖10,1、4)。馬側武士身上矩形甲片的甲衣與第二組浮雕首領長子腿前的鎧甲相似(見圖10,2、5)。此外,繡像上長葉植物亦見于哈爾恰揚出土陶質建材上圖案(見圖10,3、6)。凡此種種,都說明了繡像與哈爾恰揚的密切聯系。
綜上所述,繡像人物不是匈奴,與印度—斯基泰或印度—帕提亞無關,也不屬月氏,而是屬于早期貴霜,繡像氈毯為早期貴霜之物。繡像上首領是一位貴霜翖侯,與赫勞斯錢幣的發行者、哈爾恰揚第二組浮雕首領或其長子或為同一個人。考慮到諾音烏拉31號墓的年代以及繡像上首領的年齡(30—40歲),不排除他是第一位貴霜王丘就卻的可能。繡像上首領所率的隊伍,或許就是丘就卻賴以開創王朝、建功立業的團隊。第三幅繡像的著甲武士和揮手戰士也屬貴霜人,至于他們的對手,則可能屬于早期貴霜周邊的敵對政權。
三、貴霜王族的來源
貴霜王族的來源,或者說貴霜的淵源,是貴霜史研究的重要問題,但也是薄弱環節,爭議較大。很多學者認為貴霜就是大月氏,二者是一回事或前者是后者的部落之一,如(德)夏德(F.Hirth),(美)孟赫奮(Maenchen-Helfen),(日)內田吟風、小谷仲男,(印)納拉因(A. K. Narain)(4)以上學者文獻見楊富學,米小強:《貴霜王朝建立者為大月氏而非大夏說》,載《寧夏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普里(Puri)[24]188,(英)克力勃[20],(中)楊富學等[25]。還有不少學者認為貴霜出自大夏,貴霜翖侯是大夏人,如(挪威)寇諾(Sten Konow),(日)桑原騭藏、羽田亨,(法)伯希和(P.Pelliot),(中)余太山、王欣[25]。由于“大夏”被視作吐火羅(Tochari)的漢字音譯,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志》記載塞克人(斯基泰)的吐火羅等四部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里亞,余太山進一步認為貴霜源自塞克人,即四部之一的帕色尼(Pasiani)[26]7-11。
從宗教信仰入手探討此問題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目前早期貴霜宗教方面的資料較少,但也反映出希臘、印度及伊朗宗教因素混合的特點。希臘因素如錢幣上的希臘文、尼克女神,哈爾恰揚彩塑中的尼刻、宙斯和雅典娜。印度因素如銅幣上的佉盧文,維瑪卡德菲塞斯(Vima Kadphises)錢幣上的濕婆、公牛像。伊朗因素如索特梅加斯(Soter Megas)錢幣正面的密特拉式國王頭像(見圖11,1),頭頂有數目不等的光芒,這種錢幣被認為是由維馬·塔克圖發行的[27]180-183;又如哈爾恰揚浮雕裝飾帶中頭戴弗里吉亞尖帽的男子(見圖11,2),可能是密特拉(Mithras)或其隨從;再如主浮雕第二組最左邊站立在奔騰戰車上,頭頂有光芒放射的女神(見圖9,4),發掘者認為可能是阿維斯塔經中的阿希(Ashi)女神,當然也可能與密特拉有關(5)巴米揚(Bamiyan)大佛石窟內有站在駟馬拉車上的太陽神米特拉形象,希臘化時期犍陀羅地區印章上也有馬車上的密特拉形象。參見張小貴,毛寶艷:《米羅:貴霜錢幣所見的密特拉》,載《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輯)》2018年版,第173—188頁。此外,阿伊哈努姆遺址出土的鎏金銀盤上有站立在雙獅拉戰車上的女神,構圖與哈爾恰揚類似。。三類中伊朗因素代表了貴霜族自身的傳統信仰。密特拉在瑣羅亞斯德教中地位很高,幾乎與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比肩,在該教經典《密特拉頌》中有全面記錄[28]。維瑪卡德菲塞斯銅幣上國王右手伸向束腰火壇(見圖11,3),暗示了其宗教信仰。同樣的火壇亦見于迦膩色伽一世(Kanishka Ⅰ)金幣(見圖11,4)。諾音烏拉繡像壁毯彌足珍貴,它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貴霜在王朝建立之前的翖侯階段就已信奉瑣羅亞斯德教,畫面中貴霜翖侯帶領眾人在舉行一場莊嚴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動。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烏茲別克斯坦達爾弗津特佩(Dalverzin-tepe)、塔吉克斯坦沙赫特佩(Shah-tepe)等遺址發現一些用泥磚在地面壘砌的、帶龕室的墓葬建筑(見圖12,1—2),被稱為“納烏斯”(Наус)。其年代屬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4世紀。龕室內人骨散亂,屬二次遷葬,與瑣羅亞斯德教將尸體預先處理、清除皮肉,待化白骨后再遷葬的習俗吻合。這些墓葬屬于貴霜的遺存,與月氏的土坑或土洞墓完全不同[12]。因此,貴霜與月氏是兩個不同的族群,不可混淆,前者不可能出自后者。
關于月氏與大夏的關系,《史記》和《漢書》的記載有所不同。這些不同,恰好反映了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巴克特里亞地區的歷史變化,其脈絡有跡可循:巴克特里亞整個地區本來都屬于大夏(6)《漢書·張騫傳》說大月氏西遷,“徙大夏地”,顯然班固認為阿姆河以北區域原屬大夏。,月氏西遷后占據阿姆河以北并建立王庭,大夏的勢力范圍收縮至阿姆河以南,當時大夏無大君主,各城邑相對獨立,它更像是多個以城邑為據點部族的松散聯盟,而非統一王權國家(7)敦煌懸泉置漢簡中有康居,大月氏,罽賓,安息,烏弋山離等國與漢通使,唯獨沒有大夏,印證了這一點。見張德芳,郝樹聲:《懸泉漢簡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頁。。藍市城是大夏境內最大的城市(8)《史記·大宛列傳》:“大夏……其都曰藍市城。” 藍市城是大夏的大型或最大城市,不見得是國都。因為中國古文獻中“都”指一定規模的城邑,一般內設宗廟,不特指國家的首都。如《左傳·隱公元年》:“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叁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到西漢后期,大月氏疆域或者說統治區域向南擴張到興都庫什山,與罽賓(今喀布爾河)相接,將之前大夏的范圍囊括在內,大月氏王移治監氏城,可能就是藍市城[29]61-62。與此同時,大月氏在大夏部族中扶植并冊封了五翖侯,通過他們控制原大夏民眾。五翖侯奉月氏為宗主,為其臣屬,但有相對獨立的外交權。五翖侯治地不限于阿姆河南,如貴霜翖侯治所就位于河北的哈爾恰揚,因為大夏人在阿姆河南北均有分布。學者們認為貴霜出自大夏,無疑是正確的。
巴克特里亞曾是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的東部行省(郡),亞歷山大東征后進入希臘化時期,后又經歷了塞琉古王朝、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統治。據斯特拉波記載,來自錫爾河以北的塞克人四部攻占了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的統治隨之結束,時間約在公元前140年[30]。可能因為四部之一的吐火羅勢力最強,或名氣最大,或曾為盟主,張騫將其名轉譯為“大夏”,用以指代這一地區及其月氏之外的原住民。選擇“大夏”為譯名有精心考慮,目的是為了喚起漢朝精英的歷史情感及關注[30]。后來的漢文獻將巴克特里亞地區統稱為“吐火羅”(或曰吐呼羅、土豁羅、睹貨邏),如《魏書·西域傳》《隋書·西域傳》《大唐西域記》等,《新唐書·西域傳》云“大夏即吐火羅焉”,可謂流傳有緒。
《史記·大宛列傳》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媯水南。……無大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漢書·西域傳》作“皆臣畜之”。其“皆”字說明臣畜的對象不止一個,大夏各置小長、分散不一的局面在月氏西遷前已經存在。塞克人侵奪巴克特里亞后沒有建立統一國家,還是保持各自為戰的狀態,其大部短期停留后,可能迫于月氏西遷的壓力,又南下闖入安息(帕提亞)境內,直抵德蘭吉亞納(Drangiana)和阿拉霍西亞(Arachosia),占據錫斯坦(塞克斯坦),與安息開戰(9)余太山認為這些塞克人是迫于月氏西遷的壓力才離開巴克特里亞而入侵安息。參見余太山:《安息與烏弋山離考》,載《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2期。。月氏西遷巴克特里亞約在公元前130年,塞克人入侵安息并與之交戰發生在公元前129年,二者前后銜接,此說從時間上來看很有道理。公元前128年到公元前124年,帕提亞先后兩任國王弗雷埃蒂茲(Phraates)和阿爾塔巴努斯(Artabanus)與東部的斯基泰人作戰戰死,與阿爾塔巴努斯作戰的斯基泰人的準確族名被查士丁(Justin)記載下來——吐火羅人[31]134。可見吐火羅主力已經南下,滯留大夏地者應屬小眾。彼時張騫剛剛結束對大月氏、大夏的訪問,吐火羅的大名他一定有所耳聞。總之,大夏人的構成相當復雜,除了塞克人,還有希臘移民,以及阿契美尼德時期就已居住于此的當地土著。那么,貴霜來源于他們中的哪一個?
哈爾馬塔曾言:“當塞克部落和月氏部落初抵巴克特里亞之時,他們肯定擁有自己的宗教觀念和宗教崇拜。……幾乎無可懷疑的是,塞克人與貴霜人的古宗教決不是瑣羅亞斯德教。”[19]245這里“貴霜人”指月氏人,他認為二者是一回事。他還指出,“無論是塞克人早先的居地,還是月氏人的故鄉,都不屬于瑣羅亞斯德教早期傳播的區域。”[19]246已有考古資料證明哈爾馬塔的論斷是正確的。
雖然西方古典文獻中斯基泰人常被稱為“saka”(塞克),但前者主要分布在黑海周邊的歐洲草原,后者主要分布在烏拉爾山以東的亞洲草原。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墓葬在地面一般有大小不一的封堆,封堆下多為土洞墓,死者流行頭向西或西北的仰身直肢葬[32]37-38[33]46。興起于南烏拉爾草原的薩爾馬泰(Sarmatian)文化流行南北向偏洞室墓,在其早中期階段(前4世紀—前2世紀)死者普遍為頭向南的仰身直肢葬式[32]120-138[34]58。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哈薩克斯坦中部塔斯莫拉(Tasmora)文化的墓葬在地表有土冢,其下有豎穴土坑或偏洞室,流行頭向西的單人仰身直肢葬[35]294-295。這些斯基泰或塞克的墓葬雖然在不同區域的墓形、墓向有別,但都流行一次性土葬和單人葬(見圖12,3-5),葬俗不符合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顯然不信仰該教。從墓葬封堆頂部的浮雕武士石像、墓內小型金屬人像及石祭壇來看,斯基泰和塞克有自己的信仰,可能是薩滿教。因此,貴霜并非源自塞克。
大流士、薛西斯二世的石刻和泥版銘文提到三種塞克人分支,其中“飲豪麻汁的塞克人” 居住在費爾甘納,“戴尖頂盔的塞克人”居住在錫爾河至謝米列契(七河),“海那邊的塞克人”(歐洲斯基泰)居住在黑海周邊[36]21。余太山認為貝希斯頓(Behistun) 銘文中大流士一世征伐的尖帽塞克,游牧于錫爾河北岸,其后代就是吐火羅四部[37]。波斯波利斯阿帕丹石階上有塞克人列隊進貢的浮雕(見圖13,1—3),其中尖帽塞克的帽子又尖又長,略向后彎,其他兩種塞克戴短而尖的兜帽[38]142-144。無論哪種塞克,都沒有貴霜翖侯那種束頭帶的形象。
束頭帶是希臘巴克特里亞國王的傳統習慣,在其發行的銀幣上正面幾乎都有面向右的束頭帶國王頭像,腦后一般還有兩根飄帶[10]。貴霜翖侯的頭像在這一點上與之相似,說明受希臘化影響很深。但其祖先不是希臘人,原因有二:一是亞歷山大東征夷毀波斯波利斯王宮,熄滅圣火,屠殺瑣羅亞斯德教祭司“麻葛”(mwrzt)[39],對該教打擊很大(10)中亞地區波斯時期圣火廟也被摧毀,如烏茲別克斯坦克澤爾臺培的神廟建筑毀于古波斯帝國末期,可能與亞歷山大東征有關。參見吳欣:《帝國印記: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亞的統治》,載《歷史研究》2021年第3期。,嗣后希臘人大舉移民,居住在中亞各地新建的希臘文化城市中,堅持自己傳統的多神信仰,實不可能轉而信奉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二是第一、二塊繡像上人物皆穿交領左衽的袍服,窄袖、束腰帶,下身著長褲和軟靴,亞琴科認為這種服裝有東伊朗風格[3],與希臘人披掛和纏繞式的傳統服裝大不一樣。
貴霜王族來源于阿契美尼德時期就已生活在當地的巴克特里亞人,或者說東伊朗土著居民。幾乎所有的大流士石刻、泥版、釉磚銘文都提到了“巴克特里亞人”[38]135,介于“花拉子模人”與“索格底亞那人”或“阿里亞人”之間。波斯波利斯阿帕丹東階為巴克特里亞人進貢的浮雕(見圖13, 4), 他們手捧圜底碗或牽雙峰駱駝, 上身穿窄袖袍服束腰帶, 下身著寬筒褲及軟鞋[38]127,服飾與諾音烏拉繡像較為相似。 巴克特里亞與波斯王朝的關系非常密切,屬于后者第十二稅區; 居魯士二世次子、 薛西斯一世之兄曾任巴克特里亞總督; 波斯軍隊中有巴克特里亞騎兵; 大流士三世戰敗后向東逃亡被巴克特里亞總督柏薩斯劫持, 后者一度稱王[40]。
一般認為瑣羅亞斯德教起源于東伊朗,可能在花拉子模或錫斯坦,傳布于索格底亞那、馬爾吉亞納、巴克特里亞[41]19。大流士一世將之立為波斯國教,奉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為至尊神。有充足的證據表明至遲阿契美尼德時期該教已流行于巴克特里亞,如阿姆河(Oxus)寶藏中手持巴薩姆的麻葛(祭司)金箔像;塔吉克斯坦國家博物館所藏手持巴薩姆枝條的祭司金(銀)像,年代在公元前6世紀[42]。當然,該教在流傳過程中會發生變異而出現不同的版本,除了阿契版、薩珊版、粟特版外,還應有貴霜版[43-44]。貴霜翖侯承襲了巴克特里亞的拜火教傳統,但繡像上首領和祭司均不戴口罩。首領手中所持蘑菇狀物,波羅西瑪克援引相關研究認為是蛤蟆菌,也就是豪麻(Haoma)[45]。豪麻是中亞薩滿教的一種致幻植物,而瑣羅亞斯德本人反對飲用豪麻汁的祭祀儀式[46]。這些都說明貴霜瑣羅亞斯德教吸收了中亞本地的一些習俗,有自身特點。
宗教信仰是一個民族最根深蒂固的傳統,也是其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很難放棄或改變。根據貴霜的瑣羅亞斯德教信仰可以將月氏、塞克、希臘人從其族源名單中排除,從而上溯至古波斯時期的“巴克特里亞人”。
四、貴霜繡像壁毯見于匈奴墓葬的原因
《太平御覽》卷708引杜篤《邊論》曰:“匈奴請降,毾登毛、罽褥、帳幔、氈裘積如丘山。”其中“毾登毛”是“氍叟毛”毛細者,系用羊毛雜以群獸之毛織成,上有動物、植物和人物形象;施于大牀前的小榻之上,用以登而上牀[47]3157。杜篤逝于漢章帝建初三年(78),他所說“匈奴請降”可能指公元49年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單于比“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也可能指公元52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48]2943-2946。
《太平御覽》同卷引班固《與弟超書》云:“月支毾登毛,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公元89年竇憲率師大破北匈奴,班固隨軍,作燕然山銘。《與弟超書》所述應屬漢軍繳獲的匈奴物資。當時貴霜王朝已經建立,漢朝因襲故國舊名,這里所說的“月氏”(11)《后漢書·西域傳》:“月氏自此之后,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921頁。其實指的是貴霜。文獻記載匈奴藏有貴霜所產的毛織品,可與考古發現相印證。諾音烏拉繡像壁毯懸于廳堂或廬帳內,與用以登床的“毾登毛”略有不同,但屬同一大類。貴霜繡像壁毯出土于匈奴墓中,反映了早期貴霜與匈奴一段不為人知的交往歷史。
學界一般認為貴霜王朝建立于公元 1 世紀中葉(50—55)[49]。公元1世紀前期,漢朝與西域基本處于隔絕不通的狀態;公元45年西域十六國遣子入侍,請求恢復都護,光武帝因中原初定,匈奴未服,竟然不許[48]73。本來西漢時期蔥嶺以西諸國如康居、大月氏、罽賓、烏弋山離等與漢朝遣使往來不絕,但自新莽以后基本中斷。懸泉置漢簡中,與大月氏有關年代最晚者為簡28、簡30,從同層簡的年號看屬漢成帝至王莽時[50]206-207,此后不見。《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 元壽元年(前2)是文獻中大月氏國與漢朝交往記錄的最晚年代。貴霜翖侯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崛起,攻滅其他四翖侯,取代月氏的統治,自立為王。
在漢朝勢力從西域撤出的同時,匈奴加強了對西域的控制。公元52年北匈奴乞求和親,愿率西域各國代表進貢并求見,班彪奏曰:“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44]可見當時西域諸國臣服于匈奴。匈奴亦常派遣使者至諸國,如永平十六年(73),班超在鄯善國所斬殺“北虜使”;或常駐某國,如于闐國,“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或扶立小國國王,如龜茲王建[48]1572-1574。西漢晚期匈奴就試圖役屬蔥嶺以西的中亞國家,郅支單于西奔康居,發民筑城,“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陳湯矯詔遠征,斬殺郅支,就是擔心匈奴降服大宛、康居,“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51]3010。公元1世紀前期國際形勢彼進我退,陳湯的擔心恐不幸變成現實,匈奴的影響大有可能向南滲透至巴克特里亞地區。
月氏與匈奴為世仇,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52]3157。雖然西遷中亞后月氏安于現狀,報仇之心逐漸淡薄,但張騫出使西域之后,月氏與漢朝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并保持著友好往來。懸泉置漢簡中有17條簡文記載大月氏“使者”“王副使者”“副使者”“諸國客”“客”“翖侯”“貴人”“降歸義”者來朝,從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至新莽時期,平均四五年來訪一次,不可謂不頻繁。雖然東漢初年中原內戰,未遑外事,但因前世血仇大恥,月氏實不可能向匈奴稱臣或與之結盟,《漢書》“南排月氏”亦透露出兩國間的仇隙。這也反過來說明諾音烏拉繡像上的人物不屬月氏。
《后漢書·西域傳》關于貴霜翖侯崛起的記載過于簡略,許多細節有待揭示。貴霜可能原本是大夏“小長”,被月氏封為翖侯后不過一方諸侯,最后能脫穎而出,與其得力的內政、外交手段不無關系。內政方面,余太山認為丘就卻打著大月氏的旗號,“挾大月氏王以令諸翖侯”[26]25-27,進而吞并其他四翖侯,是很有道理的。哈爾恰揚宮殿主浮雕第一組如果確屬月氏王,或許反映了當時的情勢,月氏王明面上被貴霜奉為宗主,但實際已被后者操控。阿富汗特里亞特佩一號墓曾出土一枚“赫勞斯”奧波爾銀幣[53]239-244,說明“黃金之丘”與丘就卻同時,年代約在公元1世紀的第二個25年內[54]78。特里亞特佩東距巴爾赫約100千米,如果藍市城在巴爾赫,那么王陵與都城相距較遠,顯得較為孤單;在那里僅發現7座月氏墓葬,發掘了6座,墓葬打破波斯時期的神廟建筑,未見陵園設施和同族墓地,埋葬也顯得較為草率;6座墓中5位女性和1位男性的年齡均為20—30歲,相當接近,6人幾乎同時死亡。綜合這些現象,“黃金之丘”應是大月氏末代之君或亡國之君的陵墓(12)學者王建新在學術會議上表述過類似看法。。
在外交方面,丘就卻積極結交周邊強鄰及大國勢力,向之示好,與其結盟。公元45年印度帕提亞國王貢多法勒斯的塔赫蒂巴希(Takhti-Bahi)銘文提到erjhuna kapa,意即“青年卡德菲塞斯”,也就是庫朱拉·卡德菲塞斯(13)塔赫蒂巴希(Takht-iBahi)刻石現收藏于拉霍爾(Lahore)博物館,由萊特納博士捐贈(Dr.Leitner)。目前關于它最初的發現地,還存在不確定性:甘寧漢(Cunningham)起先認為它被貝魯博士(Dr.Bellew)發現于沙赫巴茨迦西(Shahbazgarhi)遺址,但之后又稱其發現地為Takhti-Bahi遺址,今據后者名之。這兩處地點相距不遠,均位于伊祖夫載(Yusufzai)的馬爾丹(Mardan)區[今巴基斯坦西庫貝爾-帕赫吞赫瓦(Khyber Pakhtunkhwa)省]。該刻石長約17英尺,寬約14.5英尺,上有六行刻銘,由佉盧字母書就。由于它早先被用于加工香料,故刻銘多有磨損。甘寧漢(Cunningham)識別出刻銘中的國王名稱(Gondophares)。英國學者道森(Dowson)通過萊特納博士提供的拓本,成功釋讀出銘文的前兩行,將之轉寫為:“Maharayasa Gunu…Pharasavasha IIX Samvatsarasa atamae iii x ivekhasamasasadivase.”,并考訂出銘文中的紀年,即阿澤斯(Azes)紀元103年(公元45年)。挪威學者孔諾(Konow)結合塞納特(Senart)和博伊爾(Boyer)等人的釋讀結果,將銘文中的erjhuna比定為于闐塞語中的:alysanai及eysanai,即梵語:kumāra(青年);將kapa比定為kadphises的異稱。因此上述兩詞可理解為青年卡德菲塞斯。具體研究見:DOWSON J .Notes on a Bactrian Pali Inscription and the Samvat Era.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75(2),PP.376-383.S KONOW.corpvsinscriptionvmindicarvm vol ii part 1.Calcuta:Central Publication Branch,1929,PP.57-63.;表明丘就卻曾以王公的身份出現在印度帕提亞宮廷[25]。當時正值丘就卻自立為王的前夕,而印度帕提亞稱雄于阿富汗南部及巴基斯坦西北部,他自然會主動前往,尋求支持,引為南方強援。匈奴“百蠻大國”,“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48],丘就卻最終目的是要取代月氏的統治,恰好可以利用月氏與匈奴的仇隙,與后者結交,得其助力,以制約前者,并獲北方諸國認可。諾音烏拉壁毯繡像描繪貴霜翕侯的宗教祭祀場景,不是日常用品,也不是一般商品,它有特殊意義,或者是早期貴霜與匈奴結盟的信物,或者是前者向后者稱臣的貢品。早期貴霜的崛起,期間可能有匈奴的暗中支持。
事實上,貴霜建國后與漢的關系不算和睦。閻膏珍與康居新婚不久,又求娶漢公主,遭拒后遣副王謝率兵七萬,逾蔥嶺攻漢,被班超挫敗。其要求無禮,行動冒失,似乎完全不了解漢朝情況,這與西漢時期月氏與漢朝密切交往形成了鮮明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