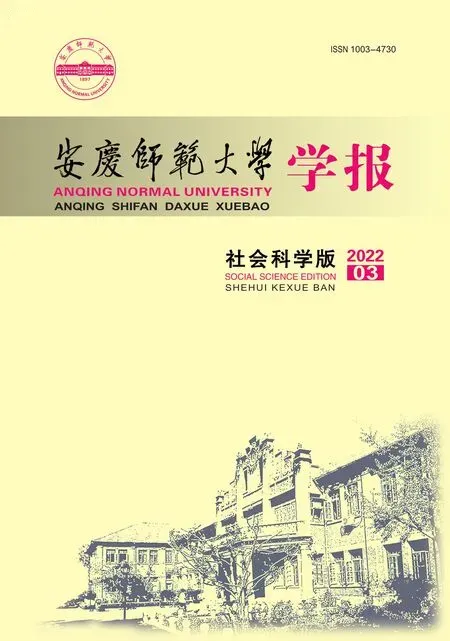方維儀對《古詩十九首》的接受及其美學意義
李鵬飛
(阜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清代沈德潛《明詩別裁集》中曾收錄著名皖籍女詩人方維儀的《死別離》《出塞》和《旅秋聞寇》,《死別離》是閨怨鄉思主題,風格纏綿婉約,《出塞》和《旅秋聞寇》著眼亂世兵燹、民不聊生的場景,寄托了作者悲天憫人的痛切感喟,風格沉郁、筆力雄健。沈德潛等對這三首詩的選錄固然是肯定了方維儀的文學史地位,但其觀念卻帶有濃厚的男性化視角,對后世詩家評價方維儀以及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成就頗有負面影響。這些批評家們常常有意無意鼓勵那些具有去女性化色彩的詩作,他們輕視詩人書寫家庭生活以及離愁別恨的作品,激賞那些具有現實政治、社會關懷的作品。他們引導女性詩人放棄自我的性別屬性而追求男性化的倫理表達,塑造符合儒家詩教傳統的溫柔敦厚的女性角色,都是對女性從屬性身份的規訓,她們無非都是男性政治理想的犧牲品、道德代價的承擔者與道德人格的附屬品。
對方維儀詩歌美學的研究,今人多秉持知人論世的視角,從探析其家學傳承、地域文化、時代氛圍入手評價其文學成就;或者是從性別視角著眼,意圖發現文本的反封建、反男性中心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價值。以此視之,前者視角囿于將詩作視為個人化的戲劇獨白,視為個體壓抑而苦悶的呻吟,并未實現真正的精神解脫,從而削弱對其詩學成就的評價;后者的癥候式閱讀方法,也常因其詩歌創作范圍的狹窄、風格的柔婉與德性意識的強烈而多有批評,踏入期待視野的落空。在研究對象上,方維儀的詩歌創作對以《古詩十九首》(以下簡稱《十九首》)為代表的漢魏古詩的接受,較少進入學者的視域。但實際上,方維儀古詩風格的作品在清代就已經獲得較高的評價,如《神釋堂脞語》就曾說:“近世閨秀多工近體小詩耳,能為古詩者什不二三;能為古文詞者百不二三也。夫人獨兼能之。”[1]81-82
本文力圖超越以上兩種研究思路的限制,重回文學現場,從其詩歌對古詩的接受入手,梳理其所受古詩的影響,在考察抒情事件的要素與功能的前提下,思考詩歌本來的美學意義。借此進一步探討其詩歌創作的風格與成就,以期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評價方維儀的詩歌美學面貌及其文學史地位。
一、對漢魏古詩的接受與復古主義詩風的塑成
(一)詩歌套語的傳承
整體來看,方維儀對古代經典的接受是多元的,其《申哀賦》是對楚辭的傳承,五、七言詩也體現出唐代詩風的影響,但漢魏古詩卻是奠定其詩歌美學底色的最重要來源。鐘嶸《詩品》評《十九首》說:“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2]劉勰《文心雕龍》則譽之為“五言之冠冕”[3]。《十九首》經《文選》選錄而定型后,其中國抒情詩經典地位得以奠定。《十九首》中個體生命價值意識的覺醒、真情實感的表達、辭淺意深的語言美、溫柔敦厚的美學風格等,對后世五言詩的美學風格、形式技巧都具有極為重要的范型意義。明代詩人對此多有稱許,王世懋說“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4],陸時雍說“《十九首》謂之風余,謂之詩母”[5]5。
漢魏古詩代有遺響,陸機、劉鑠、沈約、蕭衍、鮑令暉等詩人的擬作受其直接沾溉,陶淵明的擬古詩亦頗受其影響。在唐代有李白與韋應物兩大詩人的擬作組詩,此風在宋元時代略為沉寂。至明代,前后七子高舉文學復古大旗,《十九首》的文學經典地位再次昭如日月。何景明、李攀龍都曾寫過擬作類的組詩,李夢陽、康海、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世貞、宗臣、吳國倫、徐中行等也都有擬作,復古主義已然是明代中后期詩壇的流行風格。方維儀也頗受時代詩風沾溉,其《短歌贈從弟方夫人》曾自謂“百卉萋萋春日遲,觀書喜誦漢人詩”[6]194,詩中也有《擬古》《死別離》等多篇模擬古詩杰作。
她受到《十九首》等漢魏古詩的影響,首先體現在詩歌套語的傳承。《龍眠風雅》《名媛詩緯初編》《桐舊集》等典籍所收錄的方維儀詩歌與《十九首》、蘇李詩等明代詩人視域中的漢魏古詩相類似的套語,可以概括為情感意象、動作意象、自然意象、社會意象與生命意識等五大類。如表1所示:

續表1
詩學中的套語,是指在詩歌中那些被大量重復使用的短語、句子或結構,“同時它還是一種固定的,以不變形式重復使用的表達方法”[7]。套語可以是兩到三個字,也可以是一句話。套語曾是口傳文學時期詩人的重要創作手段,是詩歌情感生成的基礎:憑借大量類似重復的言語片段,塑造特定的意象以喚起關聯的情感。漢魏詩人也使用在詩中反復出現的包含敘述與描寫的話題單元與一定的主題形成固定聯系,通過語象與意象的提示制造人物狀態與情境的重現,借此從接受者那里獲得習慣性聯想、審美積淀、詩性直覺等審美心理反應。如方氏《死別離》“與君永別離”和古詩及樂府中的“與君生別離”“悲莫悲兮生別離”“憂來生別離”“使君生別離”等套語,與離別傷悲的主題生成總是有著固定的搭配。
(二)詩歌主題的繼承
《十九首》是書寫人類最普遍情感的經典,是人們對生命價值的體驗與思考,是對愛情、親情、友情等美好情感的珍視,方氏對《十九首》詩歌主題的接受,有取舍、變通。《古詩十九首》的主題無外乎游子、思婦兩個序列。游子的生活場景涵蓋京師游宦、野外游歷、城市穿行、飲宴行樂、聽曲生情等,借此抒發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識、懷鄉思歸之情、仕途坎坷之嘆與及時行樂的主題。思婦的生活情景多屬于家庭日常活動,在男女送別、家書往來、日常勞作、采集植物、月夜徘徊等場景中嘆息青春年華的飛逝、表露對游子的思念及表白忠貞篤守的誓言。在結構上多是由星象的遷移、物象的變遷、生活事件引發出人生無常、生命可貴的主題,延伸進入游子、思婦的日常生活場景,再呈現為男女的各類情感反應,具有模式化結構特征。
《十九首》對方維儀的影響多體現在閨怨的主題、悲情的基調以及自覺的生命意識。如表1 所示,悲苦、別離、拘束、結束等表征悲苦的情感,悲風、冷月、枯草、寒露、歸燕、蟋蟀等提示時間流逝感的自然意象,坎坷、苦辛、奄忽等寄托人生艱難與生命短促的用語。其中,又以閨思主題的借鑒最為典型。
宇文所安曾這樣總結古詩的基本技巧:“這一時期的詩歌是一個流動的詩歌材料庫的一部分,而這個共享的詩歌材料庫由可以被用不同方式實現的聯系松散的話題和程序句組成”[8]83。“這一時期詩歌所共有的是主題(theme)、話題(topic)、描寫的順序、描寫的公式和一系列語言習慣”,是三個層面“話題、主題和主題的組合”[8]107。如《明月何皎皎》有“明月”“床”“不能寐”“攬衣”“徘徊”“出戶”“彷徨”“愁思”“流淚”“裳衣”,曹丕《燕歌行》還有“秋風”“草木搖落”“白露”“秋霜”“燕歸”“鵠翔”“援琴”“清歌”“仰觀”“星漢”“斷腸”等套語(主題),這些語詞程序、意象組合、場景要素在整體面貌上包含著戲劇性與敘事性,呈現線性邏輯,是構成創作閨思主題抒情事件的基本元素。
此類要素在方氏詩作中較為常見,如:
《北窗》:綠蘿結石壁,垂耿清芬堂。孤心在遙夜,當窗明月光。悲風何處來,吹我薄衣裳[6]192。
《暮秋》:一夜深秋雨,山林天色青。攬衣出房戶,落葉暗階庭。寒露沾枯草,飛鴻亂遠汀。蒼茫河漢沒,唯見兩三星[6]195。
《寒夜》:獨坐南窗下,無燈天未明。愁懷言不盡,歸雁莫哀鳴[6]197。
《月夜》:幽亭溪水碧,惆悵撫孤琴。夜夜湘潭月,清輝滿竹林[6]197。
《獨坐》:獨坐空階清露涼,夜深有影落衣裳,砧聲何處頻催月,照見愁人欲斷腸[9]。
如上所見,閨思幽怨是方維儀詩歌中受《十九首》影響較為突出的主題,此外其詩中人生憂嗟的主題所受《十九首》時序感主題的浸染也很深。代表作有《死別離》:“昔問生別離,不言死別離。無論生與死,我獨身當之。北風吹枯桑,日夜為我悲。上視滄浪天,下無黃口兒。人生不如死,父母泣相持。黃鳥各東西,秋草亦參差。余生何所為,余死何所為。白日有如此,我心自當知。”[6]191-192其中化用《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童童孤生柳》《飲馬長城窟行》多句詩意,動情書寫丈夫生離死別之痛,清一代流傳甚廣。
其《傷懷》[6]192在抒發“十七喪其夫,十八孤女殤”的自我感傷時,用“奄忽發將變”說衰老之速,其意源自“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古詩中另有“奄忽隨物化”(《回車駕言邁》)“奄忽互相逾”(《良時不再至》),均是言說人生短暫,忽如剎那之間,這也與其“人世何不齊,天命何不常”二句命意相通。又如《贈新安吳節婦》[6]192中多處化用《十九首》套語,除了“聞之一何苦”源于“音響一何悲”(《西北有高樓》),“金石亦云堅”出自“人生非金石”(《回車駕言邁》)“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坎軻同苦辛”同于“轗軻長苦辛”(《今日良宴會》)。“白露下庭柯”中的“白露”與“白露沾野草”(《明月皎夜光》)“年命如朝露”(《年命如朝露》)呈互文性關系,不僅塑成孤寂清冷的詩境,更呼應了兩人命運的艱難與悲辛。
又如《晨晦》:“終朝無所見,茫茫煙霧侵。白日不相照,何況他人心。枯梅依古壁,寒鳥度高岑。靜坐孤窗中,幽響成哀吟。春水一已平,楊柳一已深。故物無遺跡,蕭條風入林。”[6]192“枯梅”二句仿用“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行行重行行》)結構,“春水”二句仿擬“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行行重行行》)句式,“故物”二句化用“所遇無故物”(《回車駕言邁》)“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去者日以疏》),詩風自然流轉,抒發了生命無常、人生易老的感傷。
再如《有感》:“枯樹蕭蕭北山曲,北山墳墓西山屬。登樓直視空躑躅,從來壽命榮與辱。千古圣賢更相續,塵沙已掩顏如玉。黃金萬鎰焉能贖,富貴繁華人所欲。毋寧庸愚侮世俗,一心區區常結束。四十余年甘局促,十日床下鳴蟋蟀。庭前冬青子常綠,憂來撫膺歌黃鵠。苦言雖多為誰告,常聞老學如秉燭。日夜詩書聊自勖,庶幾不慚徒食粟。”[6]193詩中有意仿寫古詩的特點非常鮮明,此詩沿用《驅車上東門》與《去者日以疏》結構,先以遠眺墳塋場景的動作興起生命脆弱的感嘆,其后轉為珍視生命意識的覺醒并作出現實的選擇。在人生選擇的方向上,《驅車上東門》是飲酒行樂,《去者日以疏》是還鄉思歸,而《有感》則是詩書自娛,更符合明清女性的生活實況與人生理想。
套語化寫作以及明白曉暢的語言風格,是漢魏時代《十九首》、秦嘉夫婦贈答詩、蘇李贈別詩以
及部分文人徒詩可以描述為“古詩”的特有風格。朱彝尊評價方維儀時說:“不纖不庸,格老氣逸”[10]721,“其詩一洗鉛華,歸于質直”[10]725。樸拙天然、格高調逸的風格,與這類作品對古詩套語及其主題的嫻熟化用密不可分。
二、儀式性的抒情表演
(一)抒情性的回歸
《十九首》本身的男性視角十分突出,在“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等文字中,讀者不難察覺男性目光的游移,女性的美貌是他們觀賞的對象與想象的產物,女性人格應有的主體性缺失。馬茂元先生也曾提出:《十九首》“篇篇都表現出文人詩的特點,其中思婦詞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還是出于游子的虛擬。在窮愁潦倒的客愁中,通過自身感受,設想到家室的離思,因而把同一性質的苦悶從兩種不同角度表現出來,這是很自然的事”[11]。《十九首》中的性別角色雖有游子思婦兩種,但其女性抒情聲音實際為男性代擬,其女性視角及悲苦情感主題源于男性的想象,如此當然會影響后世對詩歌意義闡釋的價值導向。
《十九首》中的思婦之嘆可以歸為思婦詩范疇,側重表達妻子對遠行的丈夫的思念之情。方維儀的很多詩作則屬于閨怨詩,以女性視角寫生活中物象變遷、人事交接、憶友懷舊、悼亡追思、身世感懷,大于思婦詩的范圍。即便寫思婦之怨,其也有《征婦詩》寫征夫遠戍的主題,比之《十九首》以游宦京師為中心,更有平民氣質。
從抒情視角與抒情聲音來看,方維儀詩作的特點是將《十九首》男性代擬的女性聲音革新為敏銳細致的女性聲音。《十九首》有佳人彈琴的主題,如:
《西北有高樓》: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愿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5]26-27。
《東城高且長》:……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5]38-39。兩者結構類似:男性聽佳人彈琴而興起知音之感,悲情感動士人,表露愿偕之展翅齊飛的愿望。對《西北有高樓》,歷代詩評家多從政治道德隱喻的角度來解釋其主題與功能。李善注說:“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5]27曾原說:“此詩傷賢者忠言之不用而將隱也。高樓重階,此朝廷之尊嚴;弦歌音響,喻忠言之悲切。”[5]53吳淇說:“此亦不得于君之詩。”[5]67張庚說:“此抱道而傷莫我知之詩。”[5]85姜任修說:“閔高才不遇也。”[5]101張玉谷說:“此忠言不用而思遠引之詩。”[5]125劉光蕡說:“此為困于富貴不能行其志者之詞。”[5]192
以上比興寄托來解詩的模式之所以代代相承,是因為在詩歌結構上有兩個特點,為懷才不遇與求賢若渴的主題解讀范式提供了可能:一是采用了虛寫想象的方式而非實景描繪,二是其男求女的結構。進一步說,《十九首》中思婦主題詩歌的愛情寓意的真實性同樣令人生疑,無論是創作者或是傳播者的原意如何,至少在讀詩者那里并不能消除這種政治隱喻——求賢——的存在合理性。
但是,方維儀的生平經歷人盡皆知,女性的身份、家庭的角色都在生成抒情主人公角色時讓其與真情實感相接,祛除了政治隱喻解詩范式的可能性。以鼓琴主題為例,方氏詩作中有多首出現彈琴鼓瑟的意象。在一些作品中,場景是對親戚朋友彈奏樂器的描寫或者回憶,都來自于真實的生活事件,并未沿襲古詩琴瑟生悲的固定主題。如“君家玉樹發薰風,一曲瑤琴云閣中”(《短歌贈從弟方夫人》),是對子侄藝術才能的贊賞;“詩調凄霜鬢,琴聲咽暮天”(《居慈親故樓有感》)與“對月金尊歌璧樹,彈琴玉柳拂羅幃”(《過先翁故居》),源于對青少年時期愜意的家庭生活的追憶。
此外,還有兩首典型復古風格的作品:
《擬古》:八月天高雁南翔,日暮蕭條草木黃。與君別后獨彷徨,萬事寥落悲斷腸。依稀河漢星無光,徘徊白露沾衣裳。人生壽考安得常,何為結束懷憂傷。中夜當軒理清商,援琴慷慨不能忘。一心耿耿向空房[6]193。
《月夜》:幽亭溪水碧,惆悵撫孤琴。夜夜湘潭月,清輝滿竹林[6]197。
抒情主人公起于哀怨惆悵,繼而鼓琴抒懷,歸于淡泊寧靜。這里沒有男女因聽曲而知音的描寫與暗示,反而近似于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與阮籍《詠懷詩》“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的意境,是超越性別角色的士人憂思怨憤情感的升華與人格境界的顯現。方維儀月夜詠懷類的詩歌中很少忠貞自守的告解,多是自我愁情的排遣。這些寫法都是對人間真實情感的回歸,對詩人性靈的張揚,對詩歌抒情性的堅守。
《十九首》美學路徑是由人生短促而激發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與對生命價值的珍視,進而由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而做出人生價值的選擇。其中,游子的選擇有思鄉懷人、早立功名、企慕愛情、及時行樂等,而思婦一端雖然同樣有青春易逝的焦慮,其主題發展只限于嘆息孤單、表露思念、表白誓言和珍愛身體的狹窄范圍。方維儀的詩作常常可以見到對《十九首》中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與生命價值珍視的接受,但其后的詩學主題除了鼓琴抒懷,還有讀書養志、詩文自娛、親友聚會、賞玩風景、參禪悟道,而不囿于感傷嘆息與自勸自憐。方維儀的詩作雖然受《十九首》思婦詩影響很大,但抒情內容卻回歸了明清貴族女性源于日常生活的真情實感。
(二)抒情主體的非個人化
劉光蕡曾說:“《古詩十九首》作非一人一時一地。”[5]197與同時代作品相比,《十九首》的抒情具有更為強烈的非個人化色彩。秦嘉夫婦贈答詩、蘇李贈答詩與《十九首》的風格類似,雖然其創作背景故事十分可疑,但是后世讀者卻不能不受到這些說法的影響,對詩歌解讀系于其人其事。但《十九首》作者不可考,讀者無法回到、也沒有必要回到詩人言說的文學現場,知曉其姓甚名誰、事發于何年何月、向何人言說,讀者完全沒有必要滑稽地以“索隱派”的方式去讀詩。如陳祚明所說:“《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低回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有,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唯十九首以為至極。”[5]204-205故而,《十九首》表現的可謂是個人在世界中獲得的普遍情感經驗。
對于前所引方維儀鼓琴題材的作品,我們并不能準確定位詩中“幽亭溪水碧,惆悵撫孤琴”的情境在詩人生平中的坐標系,“斑白蕭條,愁苦多病,第鼓琴詠詩,借清風明月以自解”[1]84,是方式姐妹生活的常態。雖然詩人的生活情感是詩歌的原型,但是詩人并不等同于抒情主體,詩人在對自身命運、現實、歷史的觀照與詩歌形式的錘煉中創造了特有的女性抒情聲音。如方維儀所言,“余伯姊夫人,苦其心志,生平催折,故發憤于詩歌者也”[1]83。方氏三姐妹中,方孟式因丈夫與清軍交戰犧牲而殉夫,方維則十六歲喪夫,她們多是青年守寡,含辛茹苦教養家族晚輩成才,方維儀作品中的抒情聲音首先帶有家族女性們悲劇命運的影子。此外,她還曾編撰《宮闈詩史》,對女性命運的觀照具有寬廣的歷史視野,《讀〈蘇武傳〉》中“但有漢忠臣,誰憐蘇氏婦”[6]198的呼聲,即體現了為湮沒于歷史長河中的這些特殊身份女性發聲的自覺意識。
方維儀的古風詩作具有這樣一種取向,在抒情事件中她的個體身份變得模糊,詩歌發生的情景及其受眾變得曖昧不明,一種距離感于是得以生成:詩人并不是沉溺于個人感傷,而是從人生遭際升華為對普遍人生境遇的觀照,成為傳統社會在世亂流離時代被迫與之沉浮的無數女性的代言人,完成對道德人格的追問、人生意義的探尋與對生命價值的反思。
這恰巧符合了艾略特所謂的“非個人化”的抒情策略:詩并不能簡單等于詩人的個性,詩人要放棄自我,不能把詩當做私人情感的直接宣泄。對詩人價值的評價往往取決于他與以往詩人的關系。艾略特看重文學傳統和文學經典的重要性,“現存的文學經典本身就是一個理想的秩序(order),這個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紹進來而發生變化”[12]。方維儀對《十九首》風格的繼承,是個人與古詩傳統對話意識的體現,詩人將自己納入文學的長河,實現互文性文化空間的建構,將自身化為歷史與傳統的傳承者,在對傳統的不斷轉化中建構了詩歌的當下意義。
(三)抒情表演的儀式性
抒情詩的儀式性是美國著名批評家卡勒(Jonathan Culler)提出的觀點,他在2015 年出版的《抒情詩理論》中的相關觀點引領了近年西方“新抒情詩”理論的興起。他提出,抒情詩是一種具有對讀者游說、感染和熏陶目的的儀式性(ritualistic)話語,其目標的完成是借由抒情詩重復性的表演來實現。抒情詩的創作與閱讀被看做是一種抒情性的話語事件,它的核心是以格律節奏、聲音模式、抒情演說及排印形式為基礎,通過讀者的反復誦讀生成詩歌的儀式性。“抒情表演獲得成功,是因為它通過反復閱讀使自己變得難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終的成功是變成陳詞濫調,進入語言和社會想象,起到塑造社會的作用。”[13]
卡勒的理論比較看重讀者閱讀對詩歌價值完成的功績,讀者因天然的時空距離而能建立審美態度,在誦讀中可以不自覺地將自己暫時代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得以進入詩所產生的場域與詩人展開相遇與對話。詩不再是人生事件的敘述和自我情感的再現,所謂的抒情事件只存在于讀者閱讀的當下。它擺脫了特定的時空條件因素的限制,從而演變成具備詩性表演性質的抒情事件。這種呈現為閱讀的表演行為化高妙幽微為平凡日常,能為讀者帶來情感宣泄與精神愉悅,乃至于建構一個可以詩性棲居的世界。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明清復古主義詩風中的擬古風潮,是閱讀接受與創作兼具的抒情表演,同樣具有突出的表演性功能與儀式性品質。方維儀等詩人對詩歌傳統和文學慣例有較高水平的掌握,作品中的語言、意象與《十九首》等詩歌的大量重復,在創作中完成對詩歌經典的形式再現。
方維儀的復古主義詩歌中,女性抒情角色是言說者,受話者則較為多元:一類是有明確的致語對象,如《寄娣吳夫人》《贈新安吳節婦》《贈方侄女鳳儀》,除了《求合墓詩》是直接以亡夫為呼告對象,其余詩作的期待讀者則是較為泛化的姐妹、晚輩及相知朋友,或社會之人;另一類則似乎是在自言自語,沒有明確受話者,這在擬古和古風的詩作中很明顯,有些以情感命名如《有感》《傷懷》,另一些則以物象命名,如《晨晦》《北窗》《秋雨吟》《暮秋》。
從《十九首》所謂思婦之詞來說,思婦為言說者,游子是聽話者,而讀者扮演的卻是旁聽者的角色。方維儀詩歌中的抒情結構相比《十九首》,游子的受話者角色已經淡化,讀者作為聆聽者的作用更為突出,抒情言說從直截了當變得更為間接,這也為讀者在閱讀實踐中完成一次次抒情表演事件提供了便利,更為強烈地凸顯了詩歌的儀式性特征。
在所謂桐城“名媛詩社”這樣的文學群體中,方維儀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文學領袖的角色,也是外地評論家眼中本地詩人的翹楚。同處于復古的文學語境,詩歌有意識地用典、對詩歌套語的襲用不難被他們讀解,“空室獨彷徨”“寒露沾枯草”這樣的套句顯然較為缺乏陳述現實的功能,卻更擅長將讀者導向審美的人生之境與夐絕的宇宙意識。
方維儀曾對侄子方以智囑咐說:“余《清芬閣集》,汝勿漫贈人。余甚不欲人之知也”[14],她還有不少“離優怨痛之詞,草成多焚棄之”[1]82。寫成之后即被毀棄,這一現象在她周圍女性詩人群體中也并不鮮見。過去多解釋為她們是迫于儒家“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規訓,無奈為之。今天看來,也許是她們某些儀式性情境中以知音式讀者的身份品味古詩,并隨時擬作,這樣的作品多不能脫去蹈襲前人之貌,又已完成儀式化功能,因此詩人事后舍去也不難理解。
三、結 語
癥候式閱讀批評路徑,脫離不了傳統男權中心觀念的意向性,可能導致性別詩學視角下對女性作者的苛求與誤讀。孫康宜就反對這種思路,她說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女性品節操守的成就能給她們帶來一種“自我崇高”的超越和道德權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這些女子(不論她們表現德行的方式為何),都能用傳神而優美的文字把她們的心聲表現出來,否則她們也不可能在歷史上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換言之,是文字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使她們最終獲得了道德的權威。”[15]這可謂是對包括方維儀在內明清女性作家人格理想與文學成就的生動寫照。
方維儀的詩學路徑回歸了人類普遍情感表達的本色,又跳脫出儒家詩學比興寄托的傳統,擺脫了性別角色的限制。她并沒有束縛于被動的思婦聲音,也沒有以才學、賢德自傲來期望博取功名利祿,其所建構的女性抒情聲音并未受到前代文學慣例的約束,且以不一樣的方式來發聲,凸顯了女性自身的倫理角色與日常生活中的美好情感,種種喜悅、悲傷、曠達的真實人生體驗。在女性抒情聲音的擬真中,探尋了生命的價值,樹立了獨立的人格理想。其作品不僅完成了個人心靈史的書寫,也實現了女性命運的寓言式重構。
她的另一個重要成就是促成了桐城女性詩人群體道德人格與情感共同體的塑造。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吳令儀與吳令則等“名媛詩社”的代表成員,相互之間通過詩歌寄贈、唱和、寫序,建構了親族、同輩群體之間的情感共同體,成為家族倫理與共同生活的心理因素。她們與姚氏家族、張氏家族、左氏家族的文學交往與家族婚姻相融合,彰顯了家學聲名與桐城地域文化風采。詩人的文學活動與家族文化傳承關系更加密切,后代詩人潘翟、方御、陳舜英、張瑩多受其影響,詩人輩出,成為深化桐城地域文化認同的一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