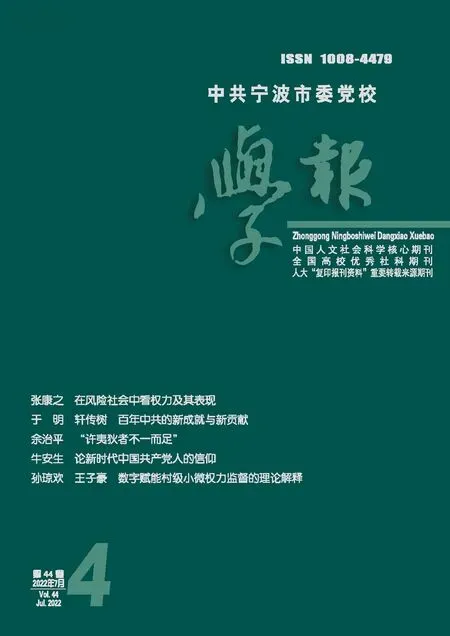中國省級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
陳小華 祝自強
中國省級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
陳小華 祝自強
(浙江工商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近年來,中國地方政府陸續開展了數字政府建設實踐,但各地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卻呈現顯著差異。以中國大陸31個省級政府為研究對象,基于TOE理論框架,從技術、組織與環境三個維度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省級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受多元復雜因素影響。除財政資源供給的影響不顯著外,技術管理水平、信息基礎設施、領導注意力、府際競爭、公眾需求均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顯著正相關。此外,經濟發展、區域位置等因素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并不明顯。在實踐上有助于深化對地方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影響因素的認識,也為地方數字政府建設提供政策啟示。
數字政府;公共服務;TOE框架;政府創新
一、問題的提出
新世紀以降,信息技術成為中國政府改革與治理創新的核心推動力之一[1],信息技術持續助推電子政務創新實踐勃興。電子政務不僅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而且增強了政府回應性和政府透明度[2]。近年來,隨著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突破式進展,其在深刻影響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對政府治理構成了機遇與挑戰。為此,中共中央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強調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是創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舉措,對于服務型政府建設意義重大。因此,中國各級政府都積極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建設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例如上海的“一網通辦”、浙江杭州的“城市大腦”、貴州的“一云一網一平臺”,這些實踐表明政府創新從電子政務階段逐漸轉向數字政府階段[3]。
數字政府建設作為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和公共決策智慧化的重要手段,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相關研究如雨后春筍般持續涌現。在豐富的研究文獻中,有一個現象尚未展開實證分析:中國數字政府發展雖然已經取得了可喜進步,但各地區之間的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根據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顯示,在省級評估中排名第一的上海(76.7)和排名末尾的青海(39.6)相差37.1分,而在副省級與省會城市評估中排名第一的深圳(82.2)和排名末尾的烏魯木齊(37.8)更是相差44.4分[4]。為什么地區之間的數字政府發展水平會形成較大差異?換言之,影響中國地方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差異的因素有哪些呢?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采用中國大陸31個省份的數據,基于技術、組織與環境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簡稱TOE),實證分析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差異化的原因,識別影響省級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本文以下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首先,將對數字政府的研究文獻進行評述,并基于TOE框架提出本研究的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假設;其次,介紹研究樣本和數據來源,并闡述核心變量的測量和分析方法;再次,從技術、組織與環境三個維度進行實證分析并得出結果;最后,討論和結論。
二、文獻述評
數字政府建設日益成為學術界格外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綜觀數字政府建設研究的豐富文獻,可以發現數字政府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若干關鍵議題上。一是數字政府的內涵與概念,有學者認為數字政府發展歷久彌新,因此需從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視角去加以理解[5];也有學者提出數字政府是運用數字化思維實現數據資源共享,再造行政流程,優化服務供給,增強公眾服務滿意度的一種新型政府形式[6]。二是數字政府的發展階段,有學者提出數字政府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公告板、部分服務提供、門戶網站和互動式民主[7](pp11-15);另有學者認為數字政府發展歷程可劃分為政府信息化、電子政務與數字政府三個發展階段[8]。三是數字政府建設水平評估,由于數字政府部門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建設,學者們由此認為需要從內外兼顧的角度對其進行綜合評估[9]。四是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影響因素,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建設數字政府的動機和能力往往與當地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正向關系[10];還有學者發現公民的持續使用意愿及其滿意度是各地數字政府建設背后的核心驅動要素[11]。五是政商關系與數字政府共建,作為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者們對政商關系理論、政商關系行動策略以及政商關系對數字政府的影響均進行深入研究[12]。六是數字政府建設中的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有學者提出政務服務數據共享仍停留在初始階段的關鍵點是缺乏標準、運維、軟件及落實,未來應重點研究數據共享與業務協同的模式選擇[13]。七是數字政府的用戶使用和優化路徑,學者們認為公民作為數字政府建設的核心服務對象,其高需求和高期盼始終未得到滿足,因此提升公民體驗獲得感與滿意度是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出發點[14]。
在眾多議題中,數字政府發展影響因素是影響未來更好建設數字政府的關鍵所在,值得深入研究。目前,數字政府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歸結為三種理論,即技術決定理論、技術執行理論和技術—組織—環境模型(TOE)。技術決定論假定組織和個人會無差別的利用信息技術,致使官僚制政府組織發生全方位的變革,最終達到預期結果[15]。技術執行理論認為,與被執行的信息技術相比較,客觀的信息技術會受到制度安排的制約,政府組織對于信息技術的利用會受到組織形態和官僚制度的左右[16](pp76-97)。技術—組織—環境模型(TOE)認為,信息技術的引入和執行對組織產生的影響,取決于組織所處的環境[17]。因此,學界普遍認為除了信息技術之外,數字政府發展還受既定制度結構、組織文化等諸多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
雖然數字政府發展影響因素的理論研究相對成熟,但鮮有實證研究文獻探討數字政府發展的影響因素,與之密切相關的文獻則討論了電子政務、“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政府網站的影響因素等主題。例如,Wu和Bauer運用省級政府數據分析了中國各省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及影響因素,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公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城市化率都同地方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呈正向關系[18]。馬亮的研究顯示,府際競爭與學習、上級領導壓力、政治資源與能力、公眾需求以及地理位置等都對電子政務發展構成顯著影響[19]。丁依霞等基于TOE框架的研究發現,上級壓力、經濟發展以及互聯網資源等因素與地級市政府電子服務能力呈顯著正相關關系[20]。王法碩采用定性比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國大陸30個省級政府“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省級政府“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受電子政務基礎和領導重視等多重綜合因素影響[21]。譚海波等使用fs/QCA對中國大陸31個省級政府門戶網站開展的組態分析發現存在技術型、平衡型等四種推動政府網站建設的優化路徑[22]。
上述理論和實證研究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既有研究仍然存在可以深入的空間:數字政府發展受到諸多方面要素的影響,至今卻仍處于探索階段,鮮有文獻實證研究中國地方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尚未形成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的有力解釋。
三、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一)理論框架
前文已述,數字政府發展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主要包括技術決定理論、技術執行理論和技術—組織—環境模型(TOE)。在諸多分析框架中,Tornatzky和Fleischer提出的TOE分析框架具有較好的可擴展性且適用面最廣[23]。TOE模型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技術應用情境基礎上的多層次分析框架,它強調多層次的技術應用場景對最終應用效果產生的影響,并將影響技術應用的條件劃分為技術條件、組織條件與環境條件三類[24]。技術條件指的是技術本身的特征及其與組織之間的關系,具體包括技術是否與組織的應用能力相匹配、與組織的結構特征相協調以及能否給組織帶來好處等[25];組織條件指的是組織自身的規模、制度安排、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等方面,其對技術應用的影響備受關注[26];環境條件則比較關注組織的外部競爭與市場結構,是一個相對新穎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基于TOE框架開展了多層次、多維度、多方面的實證研究,該模型的內涵與應用價值由此不斷豐富與完善[27]。顯然,TOE框架適用于探究數字政府發展的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從技術、組織與環境三方面建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設(如圖1所示)。

圖1 分析框架
(二)研究假設
1.技術管理水平
數字政府發展是技術驅動的政府創新實踐,地方政府網站建設與專業技術人員的管理能力極大程度上會影響數字政府發展水平[28]。在中國數字政府建設實踐中,由于各地政府均面臨專業技術人員匱乏以及管理人員能力不足的問題,導致政府網站建設水平不均衡,從根本上制約數字政府發展潛在效能的實現[29]。可見,當政府專業人員的技術管理能力越強,政府網站建設水平越高時,越有助于數字政府的發展;如果在政府網站建設不完善的情況下,往往缺少專業技術人員的支持,進而會妨礙數字政府發展。由此,提出研究假設:
H1:技術管理水平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之間呈正相關關系。
2.信息基礎設施
數字政府發展建立在信息資源與基礎設施上,信息基礎設施完備度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密切相關[30]。隨著信息基礎設施的更新迭代,數字政府發展更加依賴于標準化信息基礎設施的支撐。當缺乏數字政府建設所需的關鍵基礎設施與先進信息資源時,數字政府發展進程勢必大打折扣。因此,一個地區越是具備充足完備的信息基礎設施,當地的數字政府發展也會越順利。因此,提出假設研究:
H2:信息基礎設施完備度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之間呈正相關關系。
3.財政資源供給
數字政府建設作為一項政府創新實踐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詳言之,數字政府發展建立在互聯網技術基礎之上,而數字平臺的建立與維護、高端信息技術人才引進等方面都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因此財政資源是否豐富可能直接影響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動力和意愿[31]。由此可見,一個地區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高低與強有力的財政資源供給密切相關。換言之,財政資源供給是數字政府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據此,提出理論假設:
H3:財政資源供給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
4.領導注意力
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決定了政治制度帶有濃厚的自上而下推動的色彩,政府領導支持是很多政策和項目得以大力推行的根本保障[32]。作為科層制運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領導注意力分配能直接左右政府部門的部署和決策,進而保證政策目標的有效執行[33]。近年來,許多政府領導對數字政府建設產生興趣并予以重視,有力推動了各地政府積極向數字化轉型,加劇了數字政府建設錦標賽競爭。因此,上級領導傾注在數字政府發展上的注意力越多,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就越高。綜上,提出理論假設:
H4:領導注意力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
5.府際競爭
地方政府競爭是地方治理中的一個重要機制,地方政府為更好發展區域經濟,往往與其他地區展開競爭,尤其傾向于同鄰近地區競爭,數字政府發展領域也不例外[34]。數字政府作為創新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的新形態,政府往往會投入大量的資源和技術來推進數字化改革,以此作為競爭的重要杠桿[35]。由于不同省份面臨的數字政府發展壓力不同,使各地區數字政府發展差異化,導致不同政府之間相互競爭效仿,無形中形成了彼此間的府際競爭壓力[36]。府際競爭通常以地域位置鄰近或經濟社會屬性類似的其他省政府開展創新的數量或比例為主要考量標準。因此,當鄰近省份的數字政府建設發展較快時,會直接影響該省份的發展動力。由此,提出理論假設:
H5:相鄰省份的數字政府發展水平與該省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
6.公眾需求
公眾需求一直以來都是推動政府創新的重要外部力量。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公民意識的不斷增強,社會公眾對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的要求同各級政府數字政府發展水平息息相關[37]。在公眾需求的驅使下,政府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從而更好地服務公眾,提高公眾滿意度。因此,如果轄區內社會公眾對于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要求越高,政府建設數字政府的意愿就越強烈[38];相反,如果社會公眾對于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要求較低,政府就缺乏足夠的動力去提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由此,提出理論假設:
H6:公眾需求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
二、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以中國大陸31個省級政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如下:第一,數字政府作為政府創新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省級政府率先開展實施數字政府建設,且相較于其他層級政府,取得的成效相對更為顯著;第二,相比地級市、縣級政府,省級政府的數據庫更加充足,數據資料更易于獲取和收集。
本文的因變量——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數據來源于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4]。信息基礎設施、府際競爭、公眾需求的數據均來自賽迪智庫信息化與軟件產業研究所編寫的《賽迪白皮書:中國大數據區域發展水平評估白皮書(2020)》[39],其他自變量的信息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20》[40]《中國政務數據治理發展報告(2020)》[41]及《2019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報告》[42]。所有主要變量的定義和數據來源見表1。
(二)變量測量
1.因變量
數字政府發展指數是一個多維度概念,必須以恰當方式深化、度量相應數字政府的水平。鑒于此,為規避單向維度研究得出無從解釋的研究結果,本文選取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結果,用省級數字政府發展指數評估結果來衡量數字政府發展水平[4]。該指數通過組織機構、制度體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較為系統全面的體現數字政府發展水平。
2.自變量
(1)技術管理水平。數字政府發展極其依賴有力的信息技術支持,因此政府網站建設與數字化技術水平高低對各省份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至關重要。本文采用政府網站績效評估得分來衡量技術管理水平,該指標來自中國軟件評測中心發布的《2019年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報告》。
(2)信息基礎設施。本文選取賽迪智庫信息化與軟件產業研究所編寫的《中國大數據區域發展水平評估白皮書(2020)》中的信息基礎設施就緒度進行衡量。該指數從基站建設數量、大數據中心數量以及互聯網數據專用通道數量等方面出發,較為科學系統的評估了各省強基賦能設施水平。

表1 主要變量與數據來源
注:*表示對該變量取自然對數。假設中,+、-、?、/分別表示自變量與因變量正相關、負相關、未知或不適用。
(3)財政資源供給。地方政府資源狀況通常缺乏直接衡量指標,財政資源是較為合理的替代指標之一。本文借鑒已有研究,采用各省財政支出占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衡量省級政府財政供給狀況的指標,即全省一般預算財政支出除以地區生產總量的值。比重越大,說明財政資源供給越充足,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可能越高。該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2020》。
(4)領導注意力。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對數字政府發展的關注和重視程度,能從根本上影響數字政府的發展水平。為了考察領導注意力對省級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中國政務數據治理發展報告(2020)》中一把手關注度作為衡量領導注意力的指標。該指標反映了黨政一把手領導在政務數字治理方面進行工作部署、開展相關會議、履行相應責任以及總結工作經驗的綜合情況。
(5)府際競爭。對各省級政府而言,與其地域位置鄰近或者經濟社會屬性相似的轄區通常存在一定的相互學習與競爭“攀比”心理[43]。本文選取《中國大數據區域發展水平評估白皮書(2020)》中各省份的大數據發展指數,并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原則,將與本省份相鄰其他省份的大數據發展指數均值作為衡量指標。相鄰省份大數據發展指數均值越高,該省數字政府發展壓力越大。
(6)公眾需求。指各省政府轄區內社會公眾對于大數據運用的意愿與要求的激烈程度。本文使用《中國大數據區域發展水平評估白皮書(2020)》中的民生應用指數作為公眾需求的測量指標。該指標對教育、醫療、就業、社保、就業等方面進行全面評估,系統全面的評估了社會公眾在各領域對大數據的應用程度。其數值越大,表明省級政府轄區內公眾對數字政府建設需求越高。
3.控制變量
設置控制變量可以更好地排除其他因素對實證結果的影響,因此本文設置的控制變量如下。
第一,人口規模作為影響地區發展的重要因素,與數字政府創新實踐密切相關。為此,本文將人口規模作為控制變量,選取各省年末人口總數作為衡量指標,并進行對數化處理,使數據更加平穩且易于解釋實證結果。
第二,地區經濟發展可能是影響數字政府發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在模型中選取各省人均生產總值(GDP)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這一控制變量,且對其數值進行對數化處理。
第三,本文控制了各省所在的地理位置,通過設置中部省份為參照組,區分反映地理位置差異的東部省份和西部省份兩個虛擬變量。
(三)模型設定
對于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研究,本研究的分析單元為省級政府,數據庫為截面數據,因變量為連續變量。因此,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歸模型對上述研究假設進行驗證檢驗。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與相關性分析
表2描述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通過觀察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表現最佳省份的數字政府發展水平與表現最差省份的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差距非常大,分別為76.7分和39.6分。雖然中國大陸31個省份的平均值得分接近58分,但標準差高達10.63分,說明各省份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描述了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統計分析。由表可知,大部分自變量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關系與預期結果相同,均呈現正相關關系。僅存在少數幾個自變量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顯著負相關,即財政資源供給與西部省份虛擬變量。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各主要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7,平均值為4.320,故通過多重共線性檢驗。

表3 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注:***p<0.01,**p<0.05,*p<0.1。
(二)回歸分析
表4描述了各個回歸模型的主要分析結果。結果顯示,除了模型2的R2(0.360)小于0.50外,其他模型的R2均遠大于0.50,且F值都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p=0.0000),說明本文的模型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釋。
模型1中僅納入了技術條件的兩個變量,結果顯示技術管理水平與信息基礎設施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顯著正相關,兩者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587和0.49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假設H1、H2成立,說明技術管理水平、信息基礎設施水平越高,數字政府發展水平越高。

表4 自變量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回歸分析結果
注:此處為主要變量的回歸分析結果,括號外為回歸系數,括號內為穩健性標準誤。***p<0.01,**p<0.05,*p<0.1。
模型2驗證了組織條件的兩個變量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其中,財政資源供給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通過顯著性檢驗,但符號為負號,這說明隨著財政資源供給的增加,數字政府發展水平逐漸下降,故假設H3未通過檢驗。領導注意力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正向關系,這說明黨政領導傾注在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上的注意力越多,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也越高。假設H4獲得支持。
模型3進一步考察了環境條件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結果顯示府際競爭(β=0.480,p<0.01)、公眾需求(β=0.781,p<0.01)對數字政府發展指數的正向影響依然顯著。假設H5、H6成立。
模型4顯示了控制其他變量后,綜合考慮技術、組織與環境三個維度的因素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發現財政資源供給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不存在顯著的關系,其余變量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財政資源供給同數字政府發展水平未呈現統計顯著性,原因可能是黨政領導對于數字政府發展的重視,削弱了財政資源供給對數字政府發展的影響程度。
模型5在控制了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東、西部省份等變量后,回歸分析結果與前述保持一致,除財政資源供給未能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現統計顯著性外,技術管理水平、信息基礎設施、領導注意力、府際競爭與公眾需求均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呈顯著正相關,回歸分析系數分別為0.354、0.557、1.818、0.238和0.360。實證檢驗支持H1、H2、H4、H5、H6假設。
此外,引入控制變量后,模型5中R2值達到0.858,解釋力度進一步提高。但結果顯示,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等虛擬變量均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未呈現統計顯著性,說明區域環境特征極有可能不是影響數字政府的發展水平的因素。最后,地理位置虛擬變量與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關系在各個回歸模型中不一致,說明它們同其他變量之間的復雜相關關系可能影響其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解釋。
五、討論與結論
(一)研究發現與實踐啟示
在數字化變革的浪潮下,中國地方政府紛紛開啟了數字化轉型,推進數字化治理。在治理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不同地區的數字政府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為了解釋地方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現象,本文以中國31個省份為分析對象,基于TOE框架建構了數字政府發展影響因素的分析模型,然后運用OLS方法實證分析了技術、組織與環境三個維度因素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水平。研究發現與實踐啟示如下。
第一,技術條件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最為顯著,尤其是信息基礎設施,其次是技術管理水平。數字政府發展是基于技術創新的政府實踐活動,其發展水平與政府信息基礎設施和政府網站建設水平息息相關。許多省份早些年份更加重視信息技術的應用,使其在數字政府發展中具備先發優勢,這也是導致各省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不均衡的重要因素。因此,為保障數字政府建設的區域間協調發展,未來需要國家層面的進一步統籌規劃,鼓勵地方政府高度重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不同地區政府信息基礎建設的均衡發展。同時,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地區則應重視數字化轉型與發展,加大保障信息基礎建設的投入力度,夯實數字政府發展的技術基礎。
第二,在組織維度中,領導注意力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產生顯著影響,這是因為中國的治理體制決定了領導注意力在公共事務治理中具有關鍵性作用。換言之,如果黨政領導對某件事給予關注,將有助于該領域的建設發展,數字政府建設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財政資源供給與假設相悖,并未通過假設驗證,可見省級政府財政預算水平在提高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中作用并不顯著。究其原因,可能是黨政領導對于數字政府發展的重視,將其視為一項政治任務,形成超越財政考量的政策激勵,無形中抵消了財政資源供給在數字政府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效力。因此,加快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首要條件是領導重視,只有領導真正重視數字政府發展的重要性,才會集中各種力量和資源,推動地方政府部門數字化改革,并將改革勢能轉化為治理效能。
第三,環境維度的兩個變量都對數字政府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但相較于府際競爭,公眾需求在提高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上發揮了更重要的推動作用。與已有研究發現一致,各級政府在面對外界龐大公眾需求時,更能切身感受到數字政府發展的壓力感和緊迫感。各級政府在府際競爭中對自身發展數字政府的要求固然重要,但公眾需求才是影響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外部核心驅動因素。因此,地方政府要重視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在準確識別公眾真實需求的同時,鼓勵公眾參與數字政府服務平臺的使用和評價,以此來強化地方政府對數字化改革的用戶理念,最終實現數字政府建設惠及人民。
(二)研究不足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數字政府的發展是政府長期創新實踐的成果,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數據,未來可以使用面板數據或別的研究設計進一步驗證本文的研究結果,以獲得更具普適性的研究結論。另一方面,受限于樣本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僅從技術、組織與環境三個維度研究了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未來可從其他維度對其進行研究,例如數字政府的國際學習、普通政府官員的行為和動機、新聞媒體壓力等對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的探索中國數字政府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
[1] Dunleavy P. , Margetts H. , Bastow S. . 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Long Live Digital-era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6(3): 467-494.
[2] West D. M. . Digital Government:Technology and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M].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陳小華, 潘宇航. 數字政府: 演進階段、整體形態與治理意蘊[J]. 觀察與思考, 2021(1):97-98.
[4] 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 2020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R]. 北京: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 2020.
[5] 戴長征, 鮑靜. 數字政府治理——基于社會形態演變進程的考察[J]. 中國行政管理, 2017(9):21-25.
[6] 王偉玲. 加快實施數字政府戰略:現實困境與破解路徑[J]. 電子政務, 2019(12):86-94.
[7] [美]達雷爾·韋斯特. 數字政府: 技術與公共領域績效[M]. 鄭鐘揚, 譯.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1.
[8] 黃璜. 數字政府:政策、特征與概念[J]. 治理研究, 2020, 36(3):6-8.
[9] 劉銀喜, 趙淼, 趙子昕. 政府數據治理能力影響因素分析[J]. 電子政務, 2019(10):81-88.
[10] 馬亮. 公共部門大數據應用的動機、能力與績效: 理論述評與研究展望[J]. 電子政務, 2016(4):62-71.
[11] 王法碩, 丁海恩. 移動政務公眾持續使用意愿研究——以政務服務APP為例[J]. 電子政務, 2019(12):65-74.
[12] 馬亮. 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理論框架、研究議題與未來展望[J]. 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 2021, 23(2):71-85.
[13] 鄭磊. 開放的數林:政府數據開放的中國故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4] 鐘偉軍. 公民即用戶: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邏輯、路徑與反思[J]. 中國行政管理, 2019(10): 51-55.
[15] 張燕, 邱澤奇. 技術與組織關系的三個視角[J].社會學研究, 2009(2):200-204.
[16] [美]簡·E. 芳汀. 構建虛擬政府: 信息技術與制度創新[M]. 邵國松,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
[17] 邱澤奇. 技術與組織:多學科研究格局與社會學關注[J]. 社會學研究, 2017(4):181-185.
[18] Wu Y. , Bauer J. M. . E-government in China: Deployment and Driving Force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Portals[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 3(3):290-310.
[19] 馬亮. 電子政務發展的影響因素:中國地級市的實證研究[J]. 電子政務, 2013(9):50-63.
[20] 丁依霞, 徐倪妮, 郭俊華. 基于TOE框架的政府電子服務能力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 電子政務, 2020(1):107-113.
[21] 王法碩. 省級政府“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的影響因素——基于30個省級政府樣本的定性比較分析[J].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2):173-179.
[22] 譚海波, 范梓騰, 杜運周. 技術管理能力、注意力分配與地方政府網站建設——一項基于TOE框架的組態分析[J]. 管理世界, 2019(9):81-94.
[23] Tornatzky L. G. , Fleischer M. . the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Lexington Books, 1990.
[24] Rogers E. M. .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New York:Free Press, 1995.
[25] Chau P. Y. K. , Tam K. Y. .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Open Systems:an Exploratory Study[J]. MIS Quaeterly. 1997(1):1-24.
[26] Walker R. M. .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tecedents of Process Innovation:A Review and Extension[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4(1):21-44.
[27] Awa H. O. , Jiabo O. U. . A Model of Adoption Determinants of ERP within TOE Framework[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 2016(4): 901-930.
[28] Moon M. J. . the Evolution of E-government Among Municipalities:Rhetoric or Realit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2(4):424-433.
[29] 黃萃, 夏義堃. 政府網站信息服務外包的利弊分析[J]. 電子政務, 2014(9):58-62.
[30] Tolbert C. J. , Mossberger K. , Mcneal R. . Institutions, Policy Innovation and E-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Stat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8(3):549-563.
[31] Kim S. E. , Lee J. W. . The Impact of Management Capacity on 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Korea: an Empirical Study[J].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3):345-369.
[32] 龐明禮. 領導高度重視:一種科層運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J]. 中國行政管理, 2019(4):93-95.
[33] 文宏, 趙曉偉. 政府公共服務注意力配置與公共財政資源的投入方向選擇——基于中部六省政府工作報告(2007-2012)的文本分析[J]. 軟科學, 2015, 29(6):5-9.
[34] Berry F. S. , Berry W. D. . State Sottery Adoptions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0(2): 395-415.
[35] Weare C. , Musso J. A. , Hale M. L. .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Diffusion of Municipal Web Pages in California[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9(1):3-27.
[36] Berry W. D. , Baybeck B. .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 Study Interstate Competi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4):505-519.
[37] 何艷玲, 鄭文強. “回應市民需求”:城市政府能力評估的核心[J]. 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6):56-65.
[38] Ma L. . Diffusion and Assimilat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4(2):274-295.
[39]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 賽迪智庫, 信息化與軟件產業研究所, 中國大數據產業生態聯盟. 中國大數據區域發展水平評估白皮書(2020)[R]. 北京, 2020.
[40] 國家統計局. 中國統計年鑒2020[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20.
[41] 中國電子信息聯合會. 中國政務數據治理發展報告(2020)[R]. 北京: 中國電子信息聯合會, 2020.
[42] 中國軟件評測中心. 2019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結果[R]. 北京:中國軟件評測中心, 2020.
[43] Frederick J. , Boehmke. Disentangling Diffusion: the Effects of Social Learning and Economic Competition on State Policy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4(1):39-51.
2021-10-10
浙江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數字政府建設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機理與對策研究”(2021C35070)
陳小華(1980-),男,浙江杭州人,管理學博士,浙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數字治理、公共政策;
祝自強(1998-),男,浙江金華人,浙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數字治理、公共政策。
D035-39
A
1008-4479(2022)04-0096-11
責任編輯 范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