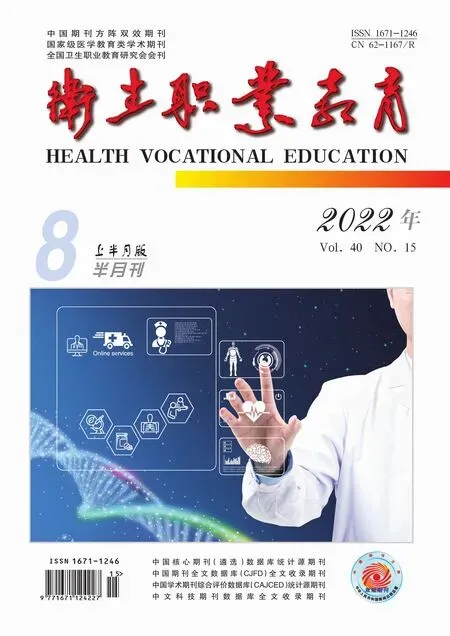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及影響因素研究
易文琳,余雨楓,陳紹傳,王 影,張夏夢,童禹浩,呂顯貴
(1.成都大學附屬醫院,四川 成都 610081;2.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 成都 610075;3.成都市婦女兒童中心醫院,四川 成都 610000)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生活環境的日趨復雜,我國居民精神壓力越來越大,加之藥品、毒品、酒精等成癮物質的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數量不斷增加。國家衛計委工作報告指出[1],截至2016 年底,我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冊管理系統約有540萬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其中有75%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是指經過住院系統治療后,癥狀得以控制,認知基本恢復,行為基本正常,病情穩定的階段[2]。正因為該階段患者病情趨于穩定,因此往往最容易因被忽略、輕視而出現負性情緒和自殺行為[3]。隨著精神衛生服務事業發展,患者康復模式發生變化,在社區進行康復治療的患者占90%[4]。自我感受負擔是慢性疾病患者能感知到的最重要的社會應激源[5]。當患者無法有效應對該應激源時,會產生一系列負性情緒,從而影響疾病治療效果及生活質量。目前,鮮見基于社區開展的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對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及其影響因素進行調查,為后續康復及心理干預策略的制訂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20 年7—12 月,采用隨機結合便利抽樣的方法對成都市6 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冊管理并符合納入標準的240 例患者進行調查。納入標準:(1)符合第10 版《國際疾病分類標準》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2)病情好轉,陽性癥狀基本消失,專科醫生診斷處于康復期;(3)病情穩定,自知力基本恢復,能正確表達意愿;(4)年齡≥16 歲[6-9];(5)納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嚴重精神障礙在冊管理系統;(6)有一定閱讀能力,能獨立或通過調查員的協助完成調查;(7)本人及其監護人知情同意,自愿參加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癡呆、精神發育遲滯或其他原因導致的智力障礙;(2)合并其他嚴重軀體疾病;(3)視力障礙或聽力障礙;(4)有酒精或藥物依賴史;(5)近3 個月內發生重大生活事件;(6)人戶分離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自行設計一般資料調查表,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病程、費用支付方式、住院次數等。
1.2.2 自我感受負擔量表(SPBS) SPBS 由Cousineau 等[10]于2003 年編制,是目前唯一用于測量慢性疾病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量表。該量表包括身體負擔、情感負擔以及經濟負擔3 個維度,共10 個條目,采用Likert 5 級評分法,總分為10~50 分。本研究采用武燕燕等[11]漢化和驗證后的量表,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30。
1.3 資料收集方法
征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患者及其監護人同意后,對患者本人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開始前,調查小組成員需向患者及其監護人詳細說明研究目的,告知其有權在調查的任何階段退出。取得患者及其監護人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后,采用統一、規范、無誘導性的語言介紹問卷填寫方法及注意事項等,請患者獨立填寫。若無法填寫者,由調查小組成員為其閱讀問卷信息,待患者獨立做出判斷后,依照患者觀點如實填寫。調查結束后,當場檢驗問卷填寫是否完整。問卷回收后,及時進行雙人數據錄入及核對。共發放問卷240 份,回收210 份,有效問卷203份,有效回收率為84.58%。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一般資料中滿足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s)描述,不滿足正態分布的采用M(P25,P75)描述;計數資料采用頻數、百分比描述。自我感受負擔量表各維度得分及總分均采用(±s)描述,采用Mann-Whitney U 檢驗和Kruskal-Wallis 檢驗不同情況下一般資料對自我感受負擔量表得分的影響,對其中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203 例患者,男94 例,女109 例,平均年齡(42.43±14.36)歲。62.07%的患者年齡為>30~60 歲,61.58%的患者病程>10年,42.36%的患者婚姻狀況為未婚,48.77%的患者文化程度為初中或高中,80.79%的患者目前處于無業狀態,57.64%的患者個人平均月收入≤1 000 元,65.02%的患者有醫療保險,43.84%的患者住院次數≥4 次。患者的主要照顧者為父母(占34.98%),其次為配偶(占27.09%),主要照顧者的平均年齡(46.37±14.79)歲。
2.2 患者自我感受負擔量表得分情況
203 例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量表得分為(32.19±9.48)分,條目均分為(3.22±0.95)分。各維度條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為:經濟負擔、情感負擔、身體負擔(見表1)。

表1 患者自我感受負擔量表各維度得分情況(n=203)
2.3 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單因素分析
采用Mann-Whitney U 檢驗和Kruskal-Wallis 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病程(χ2=29.064,P=0.000),疾病平均月支出(χ2=13.573,P=0.004),費用支付方式(Z=-2.791,P=0.005),住院次數(χ2=12.953,P=0.005)患者的自我感受負擔量表得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單因素分析
2.4 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本次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自我感受負擔量表總分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中具有統計學意義的4 個變量(病程、疾病平均月支出、費用支付方式、住院次數)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自我感受負擔量表總分與病程、疾病平均月支出、住院次數呈正相關關系,與費用支付方式呈負相關關系,5 個變量可以解釋總變異的21.2%(見表3、4)。

表3 患者自我感受負擔影響因素的自變量賦值
3 討論
3.1 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處于中等水平

表4 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量表總分為(32.19±9.48)分,處于中等水平,略高于其他慢性疾病患者,這可能與研究的疾病種類不同有關。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因疾病的特殊性,相較于其他慢性疾病患者需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更容易導致肢體僵硬、自知力障礙以及自理能力下降等不良后果,在生活中更加依賴照顧者,從而產生更重的負擔感、內疚感。3 個維度中,患者經濟負擔維度條目均分最高,與陳龑等[12]的研究結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精神分裂癥是一種需長期治療的慢性精神疾病且尚無根治方法,導致人力、物力、財力持續性消耗。提示精神衛生工作者在日常照護過程中,不僅要關注患者的身體健康,同時也要關注患者更深層次的需求,有針對性地實施干預措施,幫助患者調整心態,積極面對自身疾病,從而提高生活質量。
3.2 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影響因素
3.2.1 病程 研究結果顯示,病程是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影響因素,病程越長自我感受負擔越重,與張瑋[13]的研究結果一致。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患者病情反復發作,身體機能逐漸降低,隨患病時間的增加大多數患者會逐漸喪失自理能力[14],越來越需要照顧者幫助,導致在生理上產生強烈的身體負擔、心理上產生內疚感。另一方面,從前期的綜合治療到后期的康復治療,長期的治療過程會加重患者及其家庭的經濟負擔[15],患者家屬需要努力工作獲取更高的收入,而這也無疑使患者產生愧疚感和負擔感。
3.2.2 疾病平均月支出 研究結果顯示,疾病平均月支出是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影響因素,疾病平均月支出越高自我感受負擔水平越高,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13,16]。疾病平均月支出可間接反映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疾病平均月支出越高,患者病情可能越嚴重,越需要被照護。此時,家屬不僅要努力工作增加收入,同時也要花費更多精力與時間照顧患者,導致患者的內疚感進一步加重。因此,建議相關部門加大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政策幫扶力度,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提供更多幫助。為病情基本穩定、自知力基本恢復的患者,提供適宜的就業崗位與機會,減輕患者經濟負擔,幫助患者融入社會。
3.2.3 費用支付方式 研究結果顯示,費用支付方式是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影響因素,自費患者自我感受負擔水平顯著高于醫保患者,這與張瑋等[13,17-18]的研究結果一致。有研究指出[19],費用支付方式是影響患者經濟負擔的重要因素。有醫保的患者,疾病支出大部分可以報銷,患者及其家庭的經濟壓力相應較輕,患者的心理負擔和經濟負擔遠低于自費患者。自費患者的疾病開銷均需自己承擔,因此心理負擔和經濟負擔相對較重,長此以往,患者的負擔感逐漸加重,不利于康復。現階段,我國正逐步完善醫療保障體系,建議相關部門在推進精神衛生服務建設方面,通過簡化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醫保辦理手續,打消因害怕疾病信息泄露而拒絕辦理醫保患者的顧慮;通知降低抗精神病藥物價格、提高抗精神病藥物報銷比例等方式,減輕患者及其家庭的經濟壓力,促進患者康復。
3.2.4 住院次數 研究結果顯示,住院次數是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影響因素,隨著住院次數不斷增加,患者的自我感受負擔水平也會逐漸升高,這也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13,17,20]。住院次數增加,意味著患者病情惡化,這對患者及其照顧者來說也是沉重的負擔。隨著住院次數增加,患者的心理發生了極大轉變(從初期的積極治療到中期的倦怠、消極,直到后期的失望、沮喪),對照顧者的照護需求也會增多,家庭經濟壓力也越來越大,導致患者自我感受負擔水平升高。
4 結語
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處于中等水平,影響因素包括病程、疾病平均月支出、費用支付方式、住院次數。提示精神衛生工作者從多方面幫助患者,采取針對性措施,減輕患者自我感受負擔,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促進患者融入社會。本研究僅探討了某一時間節點的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自我感受負擔現狀,然而,自我感受負擔是動態變化的,未來可針對某些時間點進行重復測量,探討社區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動態變化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