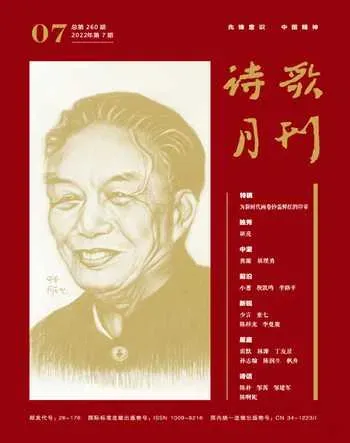少言的詩
少言
火樹銀花
多么壯觀的街景,當夜晚降臨,
人群成為燈火,和街道匯于
蒼莽天際。這路燈垂下
晨昏的柔情,點亮葉子,
穿越寒冬的葉子,隨風輕響。
沙沙,這是祖國的街道,
萬千英雄,留下脆生的腳印,
向東,向西,向南,向北,
順著街道,走進祖國的土地。
同樣的街景,深植于祖國的
每一平方公里,喧鬧的街市,
人們偎著燈火,繁衍生息,
餐食店飄出香氣,勾起舌尖,
蠢動的八大菜系,神州風靡。
而當靜謐降臨,它又會成為
三兩行人的樂土,聽輕舞的葉子
唱首歡快樂曲,目賞那
更貼近宇宙的影,——銀花似嫦娥逐月
又好似天河遨游;在歲月的長街里
凝聚著古人,千年問天的好奇。
“唯愿祖國,街道般鋪展,
像扎根古樹的,火紅星旗”。
海洋序曲
多么壯觀啊,他們相逢
在一望無際的海上,
怒濤滾滾,如冰涼銅鐘,
時間在撞擊,從高空俯視,
每個人,踉蹌織網的命運。
有時候,我真覺得天也是海,
雷聲劃過,你最愛的江南,
便開花結果。不可及的事情,——
比如,每個人都只是,一滴水,
向一個透明的寓所涌去,
而后又消隱,了無蹤跡——
時代,既無愛,也不會有恨,
但那些海洋晝夜拍打,總會驚擾
一位途經的生靈,捧起水滴,
把那灼熱歌聲嘹亮。
心靈之旅
我要到橋上去,帶回幾條游魚
潛進浴缸,嬉戲。也許,
這里的水比不上城市,投入一潮浪的
忙碌;霓虹浮動,拽下天一片
陰影壓向人群,從人行道到機動車道
步履匆遽,車燈擴散焦急
延伸向黑壓壓的邊際,像一些吻合的面具。
也許某次偏差,迷宮般的岔路駛進“我”
看見一位油漆工,粉刷著環境
(也許比不上原來美麗,也許只是修補)
我將不斷向空白的土地走去,
帶回一陣風,帶回一陣雨
帶回幾條幼魚。——你也來吧,
趁時間還未逼你回去,沿我走來的腳印
追趕我。不要訝異
當你看到我還是那個人從未改變
唯愿令你心怡,當你溯洄心靈。
早春
我有個愿望,愿那些如毛的雨,
它們沾濕鞋尖,落下同一串腳印,
當他與我在一起,淋濕的日子
雖然料峭,卻也美麗。
早春的燕子斜飛,剪刀似的尾巴
劃開嫩藍天空,他愛幾個小黑點,
嘰嘰喳喳的電線桿,像黑白琴鍵;
他漫步在小路,潔白的牙齒因花朵飽脹
而欣喜,而令我驚異不已。
他柳絮般的嘮叨,只因我愿聽,
聽湖面蕩漾的小圓暈,游過的
小魚,傾訴昨夜做的好夢。他高興
那件旋轉的長裙,因風碧綠,
那些碧綠的圓盤生長,托舉天地,
他以為我不懂,不懂這份美麗:
當銀月高懸,河流和泥土融化。
只因我從未把這話對他講,
只因他的心怡早春更添拔萃
跨年夜
當玻璃杯彼此靠近,碰撞如鐘
嘀嗒:我們共度了時間
一秒鐘,一分鐘,一小時,一天,甚至于年
理所應當的,人們偏愛,相聚勝于獨處
勝于十字街頭,寒冷,吐息安撫指頭
此刻,分隔陌生的桌椅,我們察覺不到
冷,那只存于高樓與高樓之間,孤獨的風。
原因不該只歸功于酒,還有密封的屋子
聚光燈與駐唱歌手,客氣有禮與人間善良
我卻偏愛
只歸功于這個,如月溫柔的酒精之水——
辛辣酸甜,殊途同歸的模糊。人們抹去邊線
相會于一個屋檐;尖叫聲,玻璃杯撞倒時間揮舞的熒光棒
照亮身后:
每個人歷經的山水異景,一切,一切,一切
一切融成一首歌,一段倒數,一聲美好祝愿
理所應當的,人們早已忽略告別與相遇
始于一個奇點,始于一個大寫的零,而
而那個零仿若,仿若,我們已并肩幾十年
而這一切
只歸功于,我們飲下一杯如月之水。
荒誕
炎熱的冬天,降臨
你星星般的眨眼,留下一塊陰影
大把大把的雪片帳篷般,蓋下
試圖,遮掩你內心的汐漲變化
這里,仍有一些事情,葆有勇氣
蠢蠢欲動地,準備盛開幾株梅花
浪漫的約定,雖然未被冬天殺死
但我們依舊無法保證,春天他會歸來
所以,你一次次揮霍時間
倚靠在眺望的墻邊,像不穿毛衣的冬天
輕薄是一種希望,持久的,發動的
藍色野百合——你,
你要和我一起跳舞嗎?在花的高腳杯。
蝴蝶
當風溜進草叢,夏天斂起它的小脾氣
蝴蝶聽見青草吹響口琴
她拄著花的手杖,在樹蔭的搖籃小憩
觸須如腳,揚起的水花灑向誰的夢沿?
墻壁
你知道我愛你,并試圖依靠酒精
贏得你回來,可是,你一直在失去
像我讀過的一些長篇小說,具象著變遷。
不需要太長時間,你永遠的去了
倒在空白的地上,碎成一片片土塊
南邊,麥子般彎腰的人消失不見
北邊,花朵般盛開的池塘,在凋謝
柏油路張開四肢,抓住和山野瘋跑的小孩
高樓鎖緊院子,乘著涼席搖著蒲扇,看星子逐月的閑憩
那時,人們爭著說,那時,人們爭著聽。
什么時候開始,他們不再吐露心跡
轉而念叨樓盤空洞,商品琳瑯,薪資如水?
像我打開的手機,看見世界,目不暇接的
不屬于你,也不會屬于我。我只是看著
無關緊要的你,脫落、消失,像逐漸暗淡的
金色田野,割斷的麥子一茬接一茬,倒下
而我將再一次拒絕這種結果,確信
在一切失去的時刻,你留給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