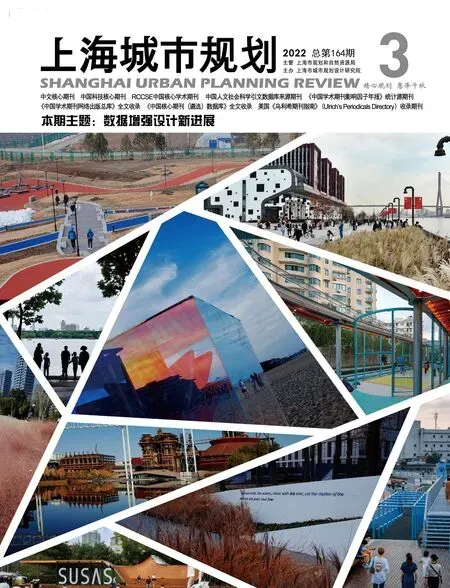城市詳細規劃中地理學方法的應用途徑*
——以站域空間研究為例
張晨陽 錢巧云 江宇凡 戴一正 ZHANG Chenyang, QIAN Qiaoyun, JIANG Yufan, DAI Yizheng
0 引言
城鄉規劃學與地理學長期以來相輔相成、協同發展,地理學對城鄉規劃學科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夯實了城鄉規劃的理論基礎,使其從單純的工程技術學科向綜合性學科轉變[1]50。城市規劃中的城市總體規劃與地理學聯系最為緊密,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尺度方面有諸多重疊,地理學中的大量理論和方法可以在城市總體規劃中直接應用。
2019年5月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正式印發,城市(鎮)總體規劃與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海洋功能區劃等一同并入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城市總體規劃從此正式融入地理學的相關學科中,“多規合一”成為當前城市規劃學科最大的研究熱點。
可以預見,未來城市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的知識體系將會分流,總體規劃與地理學充分融合,發揮“宏觀導控”作用;詳細規劃則朝向回應多元需求和指導工程建設的方向發展,發揮“底層管控”作用,學科的綜合性將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2]。
因此,直接審視詳細規劃和地理學之間的關系,分析地理學中的哪些研究方法可以被應用到詳細規劃中,強化詳細規劃的基礎理論,將成為城市規劃學科中的十分重要卻易被忽略的議題。
1 地理學與城市詳細規劃的關系研究
地理學有著龐大的學科體系,主要由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和地理信息科學3大分支學科組成,其中人文地理學與城市詳細規劃的關系更緊密些;城市詳細規劃也有著豐富的內容,以控制性詳細規劃為例,涉及土地利用、生態環境、建筑建造、行為活動等諸多因素[3]。具體而言,人文地理學中的城市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交通地理學等學科分支在城市詳細規劃中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另外,地理信息科學作為一種新興的交叉學科,其多種技術手段已經在城市詳細規劃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1.1 相關研究現狀及分析
國外城鄉規劃的學科邊界比較模糊,近年來在城鄉規劃與地理學的交叉領域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宏觀研究也有微觀的城市空間研究,而微觀研究又多關注人的行為活動,屬于社會地理學的范疇,偏向于純粹的學術研究,對實踐項目的指導意義不強[4]。
例如Rushton[5]在地理學的視角下研究城市中行動者的偏好、行為、感知對城市空間的影響;地理學家Harvey[6]38-39批判了傳統規劃思維以“效率”作為第一評價標準,他認為以“社會公正”為原則進行規劃,才能長久地促進城市發展;Schetke等[7]483-503認為城市收縮現象不僅與城市地理學中的人口、就業、社會等因素有關,還受到城市規劃中的住房結構、基礎設施質量、建成環境品質等因素的影響;Cooke[8]研究了貧困現象在城市中心和邊緣的發生、遷移、消失的現象,這種現象直接影響了城市職住空間的布局規劃;Buxton等[9]通過研究墨爾本森林火災與城市邊界社區的關系,從應對自然災害的角度對原有城市的土地規劃進行了修正;Mukhija等[10]把社會地理學中廣泛研究的“非正規性現象”融入城市規劃和設計領域進行研究,發現在美國的城市十分普遍地存在著“非正規性現象”。
國內的相關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城鄉規劃和地理學關系的研究,二是城鄉規劃對地理學方法借用的研究。
國內對城鄉規劃和地理學關系的研究側重于發展過程的梳理和宏觀導向,缺少具體方法和實踐案例,且尺度較大,對應的是城市總體規劃,甚至是對總體規劃的背景研究。趙中樞[1]48通過梳理古代城市的發展歷程,指出地理學對城市規劃的重要影響;沈遲[11]指出國內在城市地理學中的“首位度”對于指導城市規模分布規劃時存在誤區;王紀武[12]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分析了我國城市空間發展的機制和動因,認為新時期的城市規劃造成了城市文化觀念的異化;顧朝林[13]在多規合一的語境下系統梳理了城市總體規劃和其他多種規劃之間的共同演化過程,肯定了各種規劃間合作的貢獻和潛力,但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交叉沖突和協調失效;孫鵬[14]梳理了實證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對于人文地理學和城市規劃間交互演變的影響,指出人文地理學和城市規劃的交叉點在于空間規劃,但各自的側重點又有不同。
城鄉規劃對地理學方法的借用則集中于具體的技術手段,缺少對地理學基礎理論的挖掘,未能產生新的知識體系。關振斌[15]介紹了WebGIS的概念,通過計算機程序的設計,在城市規劃領域應用計算機網絡、數據庫管理、GIS和影像壓縮技術;翟金慧等[16]闡述了城市規劃地理信息系統的實現及功能,研究如何通過GIS提高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喬家君[17]以鄉村社區建設為例,探索了人文地理學中的微觀視角在介入社區空間機制中的作用;張晨陽等[18]36利用交通地理學中的等時交通圈方法對高鐵圈層的范圍進行了修正;張靈珠等[19]結合GIS和SDNA(Spatial Design Network Analysis)兩種技術手段,從三維的視角分析了香港中環地區的步行體系。
1.2 地理學方法應用途徑
城市詳細規劃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尤其是研究對象間尺度的差異過大,因此多數地理學方法不能直接應用在詳細規劃中,需要經過一系列的轉換過程(見圖1)。
首先是地理學方法的層析,對方法的理論基礎、技術過程、模式結論或數據結論分別分析,探究其中的哪個部分有在詳細規劃中借鑒的潛力。其中理論基礎、技術過程和模式結論需要經過驗證和重構才能應用,而數據結論如城市的就業預期、人口比例、氣候數據等則可以直接在詳細規劃中引用。
其次是地理學方法的驗證。如果需要借鑒技術過程或模式結論,要在詳細規劃的實踐案例中驗算、比對,發現矛盾之處后,研究是基礎理論哪些方面的不適用導致了矛盾的產生,再分析當研究對象的尺度大幅縮小后,會對該方法產生怎樣的影響。如果只是借鑒基礎理論,例如研究城市空間分布方法的基礎理論——空間的相互作用機制[20],則可以省去實踐案例比對的過程。
最終通過基礎理論研究、技術路線修正、研究結果求解,產生適用于城市詳細規劃的新方法。根據借鑒對象的不同和轉換途徑的差異,可以將地理學方法的應用途徑歸納為4種類型:理論基礎借鑒、技術過程借鑒、模式模型借鑒和直接引用數據。
2 站域空間及其相關規劃理論
2.1 站域空間的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的站域空間指的是火車站及其周邊的城市區域,站域空間的范圍大致是以鐵路站點為中心、半徑2 km的城市區域。站域空間的尺度符合城市詳細規劃的尺度,而且在實際項目招標過程中,站域空間也通常作為一個詳細規劃的獨立標段,因此站域空間是一種典型的且易于獲取資料的城市詳細規劃的研究對象[18]37。
站域空間一方面是其所在城市的一個空間組成部分,具有城市詳細規劃對象的典型性,受到地塊功能、空間體驗、建筑形態等微觀因素的影響[21];另一方面,站域空間也是鐵路交通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參與了宏觀的旅客、貨物、資金、信息等的流動,具有與城市地理學、交通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緊密結合的特殊性[22]。
因此,站域空間是探索詳細規劃與地理學之間關系的理想研究對象。本文選取站域空間詳細規劃的兩個核心理論,即高鐵圈層理論和節點場所理論,作為應用地理學方法的“接口”。
2.2 高鐵圈層理論
高鐵圈層理論的產生有著深厚的地理學淵源,是典型的從宏觀地理學尺度向微觀城市空間尺度轉換的例證。在最初由德國農業經濟學家馮·杜能(1826)根據租金梯度推演出的農業土地圈層結構中,最外層圈層的半徑為80 km;而發展到舒茨(1998)、波爾(2002)等學者提出的“三個發展區”的高鐵站區結構模型,圈層的半徑則局限在2—3 km范圍之內[23]。
城市地域結構中圈層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城市中心對周邊區域的影響能力隨著距離的增加而減弱,因此區域的功能配比發生變化[24]274。高鐵圈層理論沿襲了這種觀點,以鐵路站房為中心,根據鐵路站房與周邊區域的緊密程度不同,將5—10 min步行可達的區域劃分為樞紐核心區,集中布置站區功能;將15 min內可達的區域劃分為樞紐外延區,作為站區功能的補充、疏解和拓展;而將多于15 min可達的區域劃分為樞紐影響區,其土地利用狀態與一般的城市區域相似[25-26](見圖2)。

圖2 高鐵圈層結構模型Fig.2 "3-ring" spatial structure model
溯源高鐵圈層結構的產生,可以看出其明顯受到1923年伯吉斯提出的同心環模式的影響。但伴隨城市地理學的發展,城市的地域結構模式經歷了不斷的發展和修正(見圖3),例如1939年霍伊特提出的扇形模式,1945年哈里斯和厄爾曼提出的多核心模式,曼提出的英國中等城市的典型模式,麥基提出的二元經濟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等[24]277-278。

圖3 城市地域結構模型Fig.3 Urban regional structure model
中國高速鐵路雖然起步較晚,但從2008年開始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至今已建成占全球高鐵運營里程2/3以上的高速鐵路網絡,新建站區層出不窮,有著大量具有研究價值的高鐵站區。高鐵圈層理論作為一種較早提出的、指導站區土地利用的理論,應該在我國的新建案例中進行驗證,并根據地理學中城市地域結構模式的發展而修正。
2.3 節點與場所理論
節點與場所理論認為,站區具有作為交通節點的節點價值和作為城市組成部分的場所價值,是宏觀的交通地理學研究與微觀的場所規劃研究結合的典范。
1998年,貝托里尼將軌道站點地區中價值的相互作用機制總結為節點—場所(nodeplace)模型。模型提出兩種基本假設:其一是通過提高站點所在地區的交通容量來提升節點價值,通過改善區域的可達性來增強站點地區的活動強度和多樣化程度,促進節點價值和場所價值的平衡發展;其二是由于城市公共交通所帶來的客流量與站點周邊地區場所價值成正比[27]9-20,[28]。
根據節點與場所理論,站區的功能協同狀態可以分為5種類型:“平衡”,節點功能與場所功能的協同性較高且強度適中,站區發展較為成熟;“壓力”,交通與城市活動的強度均達到最大狀態,站區承受空間擁堵壓力;“從屬”,兩種功能的強度均較低,屬于城市普通站點;“失衡節點”,交通發展優于城市開發,城市功能不足以為節點提供配套支持;“失衡場所”,城市活動豐富但區域可達性差,交通發展的滯后制約了城市的開發[29]37(見圖4)。

圖4 節點—場所模型Fig.4 Node-place model
節點—場所模型的核心問題在于節點價值和場所價值的確定。節點價值受到宏觀的鐵路網絡客運能力和微觀的節點在站域的可達性的影響,場所價值主要受到微觀的站域開發和城市活動的影響。節點價值和場所價值均是較為主觀的指標,只能通過一個或一組客觀的指標進行描述[29]39,[30],這在單獨討論時尚可自圓其說,但在探討節點和場所兩個價值之間關系時,其準確性就難以保證。
3 高鐵圈層相關地理學方法的應用
3.1 原方法驗證
高鐵圈層理論是城市地域結構模式在站域空間應用轉化的結果,上文提到,城市地域結構在不同的研究階段、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發展出了多種模式。因此,要對高鐵圈層理論開展進一步的研究,首先應當在實踐案例中對這些模式進行驗證和比對。本文選取北京西站、蕪湖站、杭州東站、青島西站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北京西站和蕪湖站的站域是比較成熟的,可以對其建成現狀進行研究;杭州東站和青島西站的站域尚在開發過程中,應該對其詳細規劃方案進行研究;另外,北京西站和杭州東站是鐵路客運特等站,而蕪湖站和青島西站相對較小(一等站),選擇這樣的4個站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對照高鐵圈層理論中各圈層功能的分類,可以劃分出4個站域的功能布局情況(見圖5-圖8)。從劃分的結果來看,站區的土地利用模式更接近霍伊特提出的扇形模式,并與多核心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另外,站域還有其空間結構的特殊之處,即插入了大片的楔形綠化用地。

圖5 北京西站用地功能劃分圖Fig.5 The land function map of Beijing West Railway Station

圖6 蕪湖站用地功能劃分圖Fig.6 The land function map of Wuhu Railway Station

圖7 杭州東站用地功能劃分圖Fig.7 The land function map of Hangzhou East Railway Station

圖8 青島西站用地功能劃分圖Fig.8 The land function map of Qingdao West RailwayStation
從理論適用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影響城市地域結構模式的因素可以歸納為付租能力(同心環模式)、交通聯系的緊密程度(扇形模式)、產業布局的配套需求(多核心模式)、氣候因素(英國模式)和產業模式(二元經濟土地利用模式)。這5種影響因素在站域同樣適用,因此使得站域的空間模式與城市地域結構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從尺度適應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城市地理學中的租金和氣候的變化規律在站域的尺度下是不適應的,而交通和產業的變化規律卻是仍然適應的。另外,在站域中,城市綠地的尺度變得不容忽視,不能籠統地看作是大的功能分區中的一部分,而應當單獨視其為一種功能類型。這是站域空間模式與城市地域結構模式產生差異的原因。
3.2 新方法構建
根據上文對城市地域結構模式的驗證研究,站域空間模式的理論基礎可以歸納為交通聯系、產業結構和生態景觀3個方面。
交通的影響在站域空間中是至關重要的。相似的功能會沿著交通線路延展和集聚,因此與火車站聯系緊密的功能會以火車站為中心,通過交通要道向四周放射;另外,城市軌道交通因其巨大的交通疏解能力,可以將火車站與周邊的城市軌道交通站點緊密地聯系起來,從而催生出站域的次級中心[18]39,例如,北京西站(見圖5)通過地鐵9號線與六里橋東地鐵站緊密聯系,從而實現與西南側的蓮花池長途汽車站的便利換乘。
產業結構的影響進一步消解了站域空間的圈層化發展趨勢。站域的產業結構不僅受到鐵路經濟的影響,而且也是兩種經濟模式共同作用的結果,即客運、物流、商務、旅館等鐵路經濟功能和商業、辦公、工業、居住等城市經濟功能,因此站域的邊緣會出現數個以城市功能為核心的次級中心區(見圖6)。另外,由于居住、辦公和工業的配套需求,也會在功能區塊內產生商業次級中心(見圖8)。
在“暢通融合、綠色溫馨、經濟藝術、智能便捷”的現代化鐵路客站樞紐建設理念下,除了交通和產業,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也成為站域規劃的重要要求之一[31]。因此,可以通過設置從站域邊緣插入站域核心的楔形綠地來引入站域外的自然景觀,例如蕪湖站通過東廣場的綠化軸線連接了站域和東側的神山公園(見圖6);或設置被其他功能組團包圍的斑塊狀綠地來提升站域局部的空間品質,例如在杭州東站的詳細規劃中,結合東側的莧弄口港水域布置濱水公園(見圖7)。
根據上述研究,不能完全依照與站點關系的緊密程度來進行站域的功能劃分,而是應當充分考慮站點和城市兩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將站域劃分為3個新的功能區:與鐵路站點關系最為緊密的“交通樞紐功能區”,以商業、政務、文娛等為主的“城市核心功能區”,以居住、辦公、工業等為主的“一般功能區”。通過與實際案例的對比,發現站域空間模式在形態上呈現出放射狀和斑塊狀,并以放射狀為主導;在功能上則呈現出多核心和圈層化,并以多核心為主導(見圖9)。

圖9 站域空間結構模式Fig.9 The spatial structure model in station field
4 引力模型在節點價值計算上的應用
4.1 原方法驗證
在節點場所模型中,關于節點價值的計算,當前大多通過對交通的行為和強度進行統計來確定,但這種計算方法得出的結果是站點的交通價值現狀,而非交通價值潛力。交通價值和場所價值處于相互影響、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場所價值的提升會帶來交通需求,站域的開發狀態也會成為交通價值的限制因素,因此單方面統計交通價值現狀的意義不大。
本文引入地理學中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來估測站域的節點價值潛力,是城市詳細規劃對地理學方法的“理論基礎借鑒”。引力模型最初是由卡利在1858年參照牛頓萬有引力定律提出的,認為兩城市間的互動強度與兩城市的人口之積成正比,與兩地之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引力模型自產生后經過了多位學者的發展和修正,本文主要借鑒的是康維斯提出的斷裂點公式:

式中:i、j為兩座城市,Fij為兩城市間的引力,K為引力常數,P為人口,dij為兩城市間的距離,r為距離摩擦系數(一般K=1,r=2)。
從理論適用性的角度進行分析,鐵路站點的交通價值分為由鐵路線路帶來的城際交通價值和由城市道路帶來的區域內交通價值,可以通過站點所在城市與其他城市間的聯系強度來計算城際交通價值潛力,通過站點與站域中其他部分的聯系強度來計算區域內交通價值潛力。上述兩種聯系強度均與被聯系者的“質量”有關,且遵循距離衰減規律。因此,可以通過引力模型來計算上述兩種聯系強度,進而估測站點的交通價值潛力[6]472-473。
從尺度適應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在站域的尺度下,聯系強度雖然遵循距離衰減規律,但距離摩擦系數r仍然有待確定;小尺度的地塊相對于大尺度的城市,其功能相對單一,地塊與地塊間的功能差異很大,難以用人口作為其計算時的“質量”,需要考慮地塊的使用強度,以及不同功能間的相互關系。
4.2 新方法構建
以蕪湖火車站為例,計算其節點價值需要依據其鐵路網絡結構(見圖10)和站域網絡結構(見圖11),分別計算其城際交通價值潛力和區域內交通價值潛力。

圖10 蕪湖站鐵路網絡結構圖Fig.10 The railway network structure around Wuhu Railway Station

圖11 蕪湖站站域網絡結構圖Fig.11 The network structure in Wuhu Railway Station field
經過蕪湖站的高鐵線路有寧安線和商杭線,普通鐵路線路有寧蕪線、寧銅線、皖贛線和淮南線,其中寧蕪線、寧銅線、淮南線與高鐵線路重合,可以不加考慮;鐵路將蕪湖與16個主要城市聯系起來(見圖10)。計算城市間的鐵路交通引力,為排除列車速度、線路繞行、中途停靠等因素,應采用城市間最短的鐵路出行時間來充當距離;為排除不同列車類型的影響,應加入列車類型修正系數;蕪湖站鐵路網絡的節點價值,即蕪湖市與這16個主要城市的鐵路交通引力之和:

式中:Vr是站域的鐵路網絡節點價值,G1為權重常量,K1為列車類型修正系數,i為與站域通過鐵路線路連接的目標站點編號,n為目標站點數量,P0為站域所在城市人口,Pi為目標站點的城市人口,t0i為該站點至目標站點的最短鐵路出行時間。
分析蕪湖站站域,將每個地塊作為一個功能節點,并根據節點的主要功能不同來劃分功能區,最后根據城市道路的實際建設情況對功能節點進行連線(見圖11)。計算功能節點間的引力,可以用節點面積和使用強度之積作為“質量”,其中節點使用強度可以通過單位面積出入人數的抽樣調研來統計[7]47-52;不同功能節點間的聯系強度是不同的,例如居住區和商業區的聯系強度就遠大于居住區之間的聯系強度,因此需要加入功能復合類型修正系數;站域是主要以步行距離為依據劃分的城市區域,因此可以用步行距離作為節點間的距離;蕪湖站站域網絡節點價值,即站點與其他功能節點間的引力之和:

5 結論與展望
城市詳細規劃的研究尺度較小,與地理學的研究范疇重合度不高,且從學科發展歷程來看,城市詳細規劃與建筑學的關系更為緊密,這決定了地理學的多數方法不能直接應用在城市詳細規劃中。
本文屬于城市詳細規劃與地理學的交叉研究,是通過地理學的“理論溢出”來發展詳細規劃的知識體系,為了避免學科間的生硬融合,沒有直接在詳細規劃的研究對象中套用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而是做了兩點努力:一是對地理學的方法進行一系列的驗證和轉換;二是在詳細規劃中找到相應理論作為承接地理學方法的接口。這不僅避免了詳細規劃知識體系在橫向的冗余,而且進一步強化了詳細規劃本身的核心理論。
基于站域空間的高鐵圈層理論和節點場所理論,本文目前只搭建了新方法的模型框架,需要在城市規劃實踐中進一步驗證,計算公式中的各項系數也需要通過收集更多的樣本數據進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