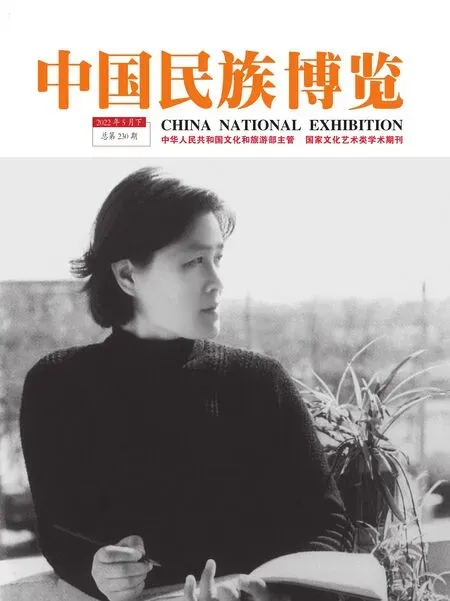真誠待藝術(shù) 孤獨(dú)對自己
——解讀周思聰
文/華天雪

1969年,周思聰與盧沉結(jié)婚,并下放到南口農(nóng)場勞動。圖為盧沉和周思聰合影。
1939年1月11日,周思聰出生于河北省寧河縣蘆臺鎮(zhèn)一個(gè)舊式大家庭里。祖父晚年做過鎮(zhèn)上女子小學(xué)校長,祖母亦能識文斷字;外祖父為當(dāng)?shù)孛t(yī),醫(yī)術(shù)精湛,閑時(shí)喜歡寫詩作畫,尤善畫太湖石和蘭花,且擅書法,登門求字畫者絡(luò)繹不絕。父親周之楷曾是北京西城區(qū)美術(shù)工廠的一位實(shí)用美術(shù)設(shè)計(jì)師,做些展覽會布置、包裝設(shè)計(jì)、商標(biāo)設(shè)計(jì)、廣告繪制等方面的事,工作極認(rèn)真,為人忠厚老實(shí),一生勤謹(jǐn),為全家人的生計(jì)奔波辛勞,雖然生活負(fù)擔(dān)沉重,但仍盡最大努力讓孩子接受盡可能好的教育,并在周思敬、周思聰兄妹剛到上學(xué)年紀(jì)的時(shí)候,便帶領(lǐng)全家四代九口人遷居北平,幾經(jīng)輾轉(zhuǎn),選擇租住西單東鐵匠胡同,目的就是為兄妹二人轉(zhuǎn)入當(dāng)時(shí)北平最好、最正規(guī)的國立小學(xué)—北平師范大學(xué)第二附屬小學(xué)就讀,其果敢與堅(jiān)韌決定了兄妹二人的命運(yùn),使他們受益終生。母親李佩琴,做過小學(xué)教員,文學(xué)功底深厚,并受家庭影響,略通醫(yī)方,婚后一心操持家務(wù),相夫教子,侍上護(hù)下,屈己待人,極具忍耐精神,為家庭奉獻(xiàn)出全部心血,從不顧惜自己,勇敢地承擔(dān)著生活的艱辛,且永遠(yuǎn)溫和而平靜,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式賢妻良母。周思聰在回顧母親一生的時(shí)候曾非常苦澀地說:“母親的操勞,使我暗想:人,生來就是受苦的吧!”就是這樣的父母,以這樣的性情和品行潛移默化地奠定了周思聰一生為人處世的方式。
小學(xué)和初中階段的周思聰不僅品學(xué)兼優(yōu),對繪畫的愛好也得到很好的保護(hù)和激發(fā)。初中時(shí)期創(chuàng)作的《小隊(duì)會上批評打架的人》被《光明日報(bào)》發(fā)表出來:表現(xiàn)十幾名少先隊(duì)員在批評兩名衣帽不整、一臉頑皮神情的剛打完架的男孩子。能在這樣的大報(bào)上發(fā)表作品,通常在別人看來是極為難得和榮耀之事,但周家卻無人知曉,即便是父親偶然翻報(bào)看到問起她,她的表現(xiàn)也極其平淡,毫無得意之色—性格和品質(zhì)中務(wù)實(shí)、遠(yuǎn)大、淡泊名利的潛質(zhì)盡顯無遺。對美術(shù)與日俱增的熱愛終致周思聰在初中畢業(yè)的時(shí)候,“戰(zhàn)勝”了權(quán)威的父親,固執(zhí)地走入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附中的校門,正式開始了她的美術(shù)之路。在這條路上,她忘我、拼命式的勤奮,少言多思的內(nèi)斂,對認(rèn)定之事的果敢與固執(zhí),得意淡然、失意泰然的行為方式等等,都成為她成功的助力。
1958年附中畢業(yè)的40幾名學(xué)生中只有少數(shù)幾名被中央美院錄取,周思聰是其中的幸運(yùn)兒。更幸運(yùn)的是,在中央美院中國畫系五年的學(xué)習(xí)中,李可染先生任山水課,蔣兆和、葉淺予、劉凌滄先生任人物課,李苦禪、郭味蕖先生任花鳥課。能得到這些技藝精湛、行為世范、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深厚的各領(lǐng)域的領(lǐng)軍人物的親身指導(dǎo),今天想來是相當(dāng)奢侈和令人艷羨的。周思聰浸淫其中,所耳濡目染的不僅是專門而系統(tǒng)的中國畫學(xué)習(xí),還有文人氣質(zhì)、畫品與人品并重的人文氣息的熏染,這在那個(gè)極左的年代又是極為難得的,令她終生受益匪淺。

1980年,周思聰與盧沉在遼源煤礦寫生。

1980年,周思聰在日本畫家丸木夫婦家中做客。
由于實(shí)行分配制,到本科三年級分專業(yè)時(shí)學(xué)生不能自主選擇,盡管周思聰很喜歡山水畫和李可染先生,但當(dāng)她因造型能力強(qiáng)而被分配到蔣兆和工作室專攻水墨人物畫時(shí),她也必須服從。更何況在那個(gè)一切為政治服務(wù)的年代,無論哪個(gè)畫種,人物畫都是最熱門和最具前途的,對藝術(shù)技巧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能被分配去畫人物畫,是件值得驕傲的事。這個(gè)強(qiáng)制性的分配對她日后的藝術(shù)道路是決定性的。
蔣兆和將寫實(shí)性素描與中國畫的勾線結(jié)合起來,發(fā)展出一套對徐悲鴻教學(xué)體系有繼承有發(fā)展、符合主流意識形態(tài)要求的寫實(shí)性水墨人物畫教學(xué)方法,流行于當(dāng)時(shí)的美術(shù)院校。作為蔣兆和最喜愛的學(xué)生,周思聰很好地掌握了這套方法,為其日后的人物畫創(chuàng)作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同時(shí),蔣兆和先生正直的品格和“為勞苦大眾傳神寫照”的藝術(shù)追求,以及對諸如深沉、悲劇性等美學(xué)觀念的認(rèn)同,與周思聰對德國女畫家珂勒惠支和日本畫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婦《原爆圖》的長久認(rèn)同連接起來,進(jìn)一步激發(fā)了她天性中悲憫和崇高的精神因素,決定了她日后對藝術(shù)風(fēng)格的選擇。
以漫畫、速寫和舞臺舞蹈人物畫享譽(yù)畫壇的葉淺予先生,是中央美院歷史上主持中國畫系最久的人,他創(chuàng)建了一套把觀察寫生與傳統(tǒng)線描結(jié)合起來的教學(xué)體系,在照顧主流意識形態(tài)要求的同時(shí),盡最大可能地注入了學(xué)習(xí)傳統(tǒng)的分量,奠定了以臨摹和寫生并重、以重視藝術(shù)技巧和觀察生活能力為主要特色的央美中國畫系的傳統(tǒng)。作為一位有高度責(zé)任心的、出色的美術(shù)教育家,20多年后葉先生還對1959年帶中國畫系師生到河北束鹿進(jìn)行實(shí)地寫生、創(chuàng)作一事記憶猶新:在所有學(xué)生所選非常雷同的題材和構(gòu)思中,唯有周思聰?shù)摹段也×恕贰安煌岔憽保∫驗(yàn)樯《荒苋ナ程贸燥埖闹芩悸敚l(fā)現(xiàn)房東老大娘和鄰居們把為自己的孩子省下的一點(diǎn)白面和雞蛋拿給她吃,把她當(dāng)親人待,令她很感動,產(chǎn)生了創(chuàng)作的沖動。對于她的真情實(shí)感、能從身邊平凡生活挖掘主題的意識和能力,葉先生給以充分的肯定和關(guān)注。而這種來自于自己無比敬仰的前輩的鼓勵,對當(dāng)時(shí)還是學(xué)生的周思聰而言,無疑是重要的。事實(shí)上,她日后的創(chuàng)作歷程表明:從自身感受出發(fā),注重真情實(shí)感,從平凡中發(fā)現(xiàn)不平凡,捕捉人情味,力圖不落俗套等等,的確成為其中國畫人物畫的最主要追求,而這些追求也最終成就了她。
1963年,周思聰從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中國畫系畢業(yè),被分配到北京畫院從事專職繪畫創(chuàng)作。直至“文革”前,她并沒有很快成名,而是在社會環(huán)境和時(shí)代氛圍的影響下,積極而真誠地多次到工廠、農(nóng)村、服務(wù)行業(yè)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創(chuàng)作了《售票員》、《童工血淚》、《周總理來到紡織廠》、《焦裕祿》、《朵朵紅花送模范》、《女清潔工》、《紡織女工》等作品,算作她的第一個(gè)創(chuàng)作期。僅從標(biāo)題即可大致推斷出,這是一些寫實(shí)的、配合政治形勢和社會需要的作品,用后來她自己的話說,是些“有生活氣息,但膚淺,思路、技法單一”的作品。作為一個(gè)涉世不深的年輕人,這樣的自我評價(jià)想必是客觀的。“文革”開始后,周思聰也與大多數(shù)同行一樣,連同現(xiàn)實(shí)生活一起被裹挾在一種無以逃避的非正常的時(shí)代狂潮中,業(yè)務(wù)中斷,少數(shù)幾件作品也多是反映派性和個(gè)人迷信思潮的,等同于空白,很少有畫家愿意再去面對自己在那樣一個(gè)極為特殊年代里的所謂“創(chuàng)作”!
直到1973年以前的一段時(shí)間,周思聰結(jié)婚生子,一如她的母親般獨(dú)自擔(dān)負(fù)起照顧丈夫、服侍老人、主持全部家務(wù)的重任,全是“生活”,幾乎沒有了“藝術(shù)”!好在她終是千難萬難地度過了:“我生活上的負(fù)擔(dān)是極繁重的。然而我所無比熱愛的繪畫是那樣使我無法拋棄。我深知一個(gè)婦女要想從事自己所熱愛的事業(yè)尤為艱難,那時(shí)我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來。我對自己感到滿意的是,我沒有因?yàn)槔щy而動搖。”

1982年10月,周思聰于涼山昭覺畫速寫。

1984年,周思聰在東京上野美術(shù)館展出《礦工圖》時(shí)與丸木先生合影。
從1973年開始,隨著整個(gè)美術(shù)界的業(yè)務(wù)活動的逐漸恢復(fù),周思聰也進(jìn)入了她的第二個(gè)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期。1973年至1978年,她先后創(chuàng)作了《毛主席和小八路》、《毛主席和兒童》、《魯迅和青年》、《魯迅和陳賡大將》、《朱德和白求恩》、《白求恩在中國》、《柯棣華大夫》、《長白青松》、《山區(qū)新路》、《重返前線》、《抗震小學(xué)第一課》等多件作品和大量英雄模范的肖像畫,其中以《長白青松》和《抗震小學(xué)第一課》最具影響。她的作品開始不斷在各種展覽和出版物上出現(xiàn),獲得廣泛好評,為她帶來了一定的聲譽(yù),個(gè)人風(fēng)格也開始逐漸有了清晰的面目。
周思聰這一代畫家大多沒什么政治抱負(fù),但卻充滿了歷史責(zé)任感,胸中郁積著近乎無窮無盡的真誠和革命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激情,對社會主義有著美好的憧憬和堅(jiān)定的信念,“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與其說是文藝方針,不如說已經(jīng)融化在他們的主動追求之中了。周思聰?shù)倪@類創(chuàng)作熱情尤其飽滿而真摯,她的那些不會“撒謊”的充滿健康、昂揚(yáng)氣質(zhì)的作品告訴了我們這一點(diǎn)—她在一心一意地歌頌著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普通勞動者和新人新事。

1994年12月12日,周思聰、盧沉與黃苗子、郁風(fēng)先生合影。

20世紀(jì)80年代,周思聰與李可染先生等合影。
周思聰?shù)目少F在于:在已經(jīng)被擠壓得幾乎沒有縫隙的風(fēng)格選擇空間中,發(fā)展出了自己的藝術(shù)面貌。她的面貌首先得益于她極其嚴(yán)肅、認(rèn)真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對每一個(gè)選題的仔細(xì)推敲以及每一件作品都要到生活中收集很多素材。其次,每件作品不僅主題鮮明、立意獨(dú)特,且均注重選取富有人情味的細(xì)節(jié)、刻畫出生動的形象,與學(xué)生時(shí)代的《我病了》一脈貫通,在首先感動自己的前提下感動觀者,突出于那個(gè)年代所有用繪畫圖解政治觀念、膚淺粉飾的作品。
在具體的藝術(shù)處理上,周思聰在構(gòu)圖、形象塑造和筆墨表現(xiàn)等方面均有獨(dú)特把握:
她用以處理構(gòu)圖的方法,雖然主要是焦點(diǎn)透視的,但在講究主要人物與陪襯人物的對比,人物與環(huán)境的比例、面積、形狀、輕重、高低錯(cuò)落等的對比,近景之實(shí)與遠(yuǎn)景之虛的對比等方面,有李可染和葉淺予的神髓,使得她的畫面的勢脈感和區(qū)域性非常明確,整體感強(qiáng),干凈利落,主題突出、鮮明,一目了然。
群像式的主題性繪畫源自西畫,這種更適合西畫的形式,在建國后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要求下,也成為中國畫人物畫家勉為其難的追求,能勝任者寥寥,除了黃胄在這方面做出了極為突出的成績外,就只有新浙派的方增先和周思聰較具說服力了(但方增先又僅有《說紅書》一件群像式人物畫)—無論是準(zhǔn)確生動并神態(tài)各異的人物形象、群像整體氛圍的營造,還是人物之間關(guān)系的合理性及復(fù)雜性、人物安排上的張弛有度等等各方面,周思聰均顯現(xiàn)出過人的能力和才華。
周思聰用以刻畫形象的筆線大多類似傳統(tǒng)的鐵線描法,但不追求傳統(tǒng)書寫性筆線的獨(dú)立審美性,而主要是以寫實(shí)性的形、色、質(zhì)感為主要出發(fā)點(diǎn)的一種運(yùn)用。主要人、物大多有完整、緊實(shí)的輪廓,次要人、物的輪廓線則注意不完整性和松弛感,使得畫面富有虛實(shí)、松緊的節(jié)奏;大多用長直線穩(wěn)定、分割或統(tǒng)一畫面,達(dá)到既豐富又整體的效果;襯景部分的筆線多有書法用筆的表現(xiàn),賦予畫面濃重的中國畫特征;既不強(qiáng)調(diào)線條感也不突出塊面,而是在線與塊面的相互制約中規(guī)避著西畫感和傳統(tǒng)中國畫之“舊”,平衡著“中”與“西”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墨色的運(yùn)用綜合了素描明暗法和傳統(tǒng)的平涂法,但很注意用水,以此弱化了素描感和勾勒填色的裝飾感,尤其在臉部處理上,雖然也是“紅光亮”式的時(shí)代臉譜,但因恰當(dāng)?shù)挠盟コ恕盎饸狻薄?傊漠嫾染邥r(shí)代所要求的健康樂觀的精神特質(zhì)和生動深入的寫實(shí)功力,又能以清新、自然、細(xì)膩、溫暖、透潤、松秀等特點(diǎn),散逸出一股掩抑不住的清芬,有別于那個(gè)時(shí)代大部分同類型作品的臉譜化、程式化和雷同感。
1976年發(fā)生的撼動中國的“四五運(yùn)動”,喚醒了許多麻木在個(gè)人崇拜中的國人,在迷信、禁錮、驚恐下生活了10年的人們開始反思和抗?fàn)帲还煽是笳胬淼募ち鲝牡磕钪芸偫淼奶彀查T廣場涌向全國。在文藝界,人們開始試探用隱喻或象征的手法有限地表達(dá)這一精神需求—通過悼念曲折地表達(dá)對“文革”的不滿、憤怒甚至控訴。周思聰參加了北京的悼念活動,也被這一精神覺醒思潮所激動,她于1976年至1979年間創(chuàng)作的《周總理會見印度醫(yī)療隊(duì)》、《周總理和紡織女工》、《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yuǎn)懷念你》、《清潔工人的懷念》和《人民和總理》等“周總理系列”作品,成為這一思潮中最具說服力的表達(dá)。在這些作品中,周思聰秉承自己一貫誠懇、純粹的藝術(shù)認(rèn)知,沒有一次把總理置于當(dāng)時(shí)表現(xiàn)領(lǐng)袖人物時(shí)慣用的高山大川式的背景前,更沒有領(lǐng)袖周圍虛幻的光環(huán),而總是把總理放在人民中間,放在真實(shí)生活的場景中,力求突出總理親切平凡外表下的不平凡魅力。《人民和總理》表現(xiàn)的是1966年邢臺地震中總理看望災(zāi)區(qū)人民的歷史場景。此作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美術(shù)作品展覽”上獲一等獎,并被中國美術(shù)館收藏,為她贏得了巨大聲譽(yù),不僅集中代表了周思聰個(gè)人在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上的成就,也是20世紀(jì)50年代至70年代整個(gè)中國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的最高代表之一。此作在情節(jié)的選擇和人物動態(tài)的處理上依然延續(xù)著之前主題性繪畫的習(xí)慣,但在人物刻畫上顯然更為成熟—無論是把人民疾苦裝在心里的總理形象,還是不同年齡的村民群像,均體現(xiàn)了她組織、安排形象的能力,較強(qiáng)的筆墨寫實(shí)能力和準(zhǔn)確、深入把握形象的能力,再加上與特定情緒相協(xié)調(diào)的環(huán)境描寫,使得畫面既具戲劇性沖突,又自然、合理、真實(shí)。用筆也更加松緊自如,更具書寫性和表現(xiàn)意味,更注重線與塊面的結(jié)合;墨色上則注重渴筆、焦墨與大面積濕墨的對比和陰天雪地的灰色調(diào)的渲染。整件作品“一氣呵成,沒有一處挖補(bǔ)”。以這樣的筆墨塑造的包括周總理在內(nèi)的所有形象,都意在突出一種苦難感,不再追求“紅光亮”式的光鮮與樂觀,甚至有別于她的其他以周總理為題材的作品。不難看出,她的人道主義情懷和悲劇意識,在這個(gè)時(shí)候開始被重新調(diào)動出來,使她獲得了擺脫人云亦云、獨(dú)立思索社會及人生的自由,進(jìn)而更接近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本質(zhì)。這種思索催發(fā)了她的成熟,使她得以從容面對新時(shí)代賦予的轉(zhuǎn)折機(jī)遇,走向自主自覺的藝術(shù)新階段。

1993年7月29日,在302醫(yī)院周思聰與美國友人高居翰(左一)、曹星原(左二)合影。
1979年前后,在文化界日漸活躍的反思和批判中,中國美術(shù)進(jìn)入了20世紀(jì)又一個(gè)觀念的大變革時(shí)期。人們在長期的禁閉之后開始對一切外來的和被反對過的東西懷有極大的好奇和熱情,特別是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諸流派,給當(dāng)時(shí)的畫壇帶來了最直接的觸動,畫家們不約而同地嘗試著突破單一的藝術(shù)模式,追求富于個(gè)性的表達(dá)方式。周思聰也不例外,她對新形式新語言特別留意,并進(jìn)行了各種力所能及的嘗試。以她內(nèi)斂、沉靜的個(gè)性,她屬于能夠積極主動地對過去一切進(jìn)行深刻反省但并非發(fā)動潮流的畫家,因此,在大多數(shù)同代人彷徨失衡的時(shí)候,她沒有盲從于任何一種過激的主張,而是依憑自身已有的基礎(chǔ),同時(shí)從新時(shí)代汲取變革的動力和膽量,默默而有效地完成了自身的轉(zhuǎn)變,這種發(fā)揚(yáng)了自身優(yōu)勢的成功轉(zhuǎn)變顯得非常自然。若僅以“建國后”和“文革后”這兩個(gè)主流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極度變化的關(guān)口為例,我們發(fā)現(xiàn),藝術(shù)技巧和藝術(shù)觀念存在一個(gè)錯(cuò)位問題,即觀念的變遷通常可以走在表達(dá)的前面,而用恰當(dāng)?shù)募记砂炎兓说挠^念充分地表達(dá)出來則要困難得多。這也是為什么對于通常不乏真情和激情的畫家們來說,并不都能在文化變遷中完成自我轉(zhuǎn)換的原因。

周思聰 同胞、漢奸和狗(草圖) 速寫 1980年
1979年,從未畫過人體的周思聰,自己找來模特兒,在北京畫院她的工作室里開始嘗試用水墨畫人體,這差不多開了中國水墨人體畫的先河,而她的藝術(shù)新階段也由此展開。對于周思聰而言,這些通常只是作為習(xí)作的人體練習(xí),可以作為重尋個(gè)性化的藝術(shù)感受力、嘗試夸張與變形的藝術(shù)手段的憑借。與此同時(shí),她還通過插圖畫和各式水墨小品進(jìn)行廣泛的嘗試。這些嘗試終使過去寫生式的寫形為主的直率、外露、直來直去的很帥的線條,逐漸變?yōu)橐环N松松的、含蓄的線條,渴筆、干筆多起來,微妙和細(xì)膩的東西多起來,追求一種拙味兒和筆線本身的表現(xiàn)力,一種與緊繃繃的英雄形象截然相反的作畫狀態(tài)和境界,是一種所謂由革命和紅色向抒情的轉(zhuǎn)換。身為女性畫家,性別特色與生俱來,所抒細(xì)膩與溫柔之情幾乎就出自這種本色,但尤為可貴的是,周思聰又多了一些寬厚與質(zhì)樸,達(dá)到秀而不媚,巧而不俗,雅致而不矯飾,疏朗通透,平淡沖和,落落大方之類境界,這些筆墨品質(zhì)使她超越了性別依附,超越了人們慣常對女性畫家的“寬容”或偏狹,從而得以在“畫家”這一共同的平臺上被認(rèn)可,這在古今中外的女性畫家中也是較為少見的。
周思聰這一代人學(xué)畫于“文革”之前,重寫生而輕臨摹、重造型而輕筆墨差不多是他們共同的中國畫認(rèn)知,即絕不像老一代那么擁有“傳統(tǒng)”;但相比于傳統(tǒng)觀念更為淡薄的下一代,他們又做不到完全放棄傳統(tǒng),因此常常處于新與舊、中與西的進(jìn)退兩難之境。而周思聰?shù)某晒D(zhuǎn)換,與她重新認(rèn)識到傳統(tǒng)筆墨語言的重要性有很大關(guān)系,她進(jìn)而對中國畫本質(zhì)特色的深刻理解與把握,直接促成了她后期藝術(shù)風(fēng)格的確立。這一經(jīng)驗(yàn)對我們思考中國畫的時(shí)代性發(fā)展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在周思聰?shù)乃囆g(shù)轉(zhuǎn)變歷程中,《礦工圖》組畫具有開端、標(biāo)志的意義,是她在水墨人體習(xí)作之后首次在正式的創(chuàng)作中進(jìn)行的變形嘗試。當(dāng)時(shí)的畫壇有一種普遍的認(rèn)識,即源自學(xué)院教育的寫實(shí)手法并非適用所有題材、適宜表達(dá)所有人類情感,有相當(dāng)?shù)木窒扌裕@種局限在觀念變化的新時(shí)期被特別放大,以至產(chǎn)生一種離寫實(shí)而去的掙脫潮流,于是由寫實(shí)而變形就順理成章,并由變形而引發(fā)審美趣味的變化。周思聰無疑是這樣一個(gè)潮流的敢為先者。從《礦工圖》的尺幅、構(gòu)圖、視覺效果到她所付諸的心血,均可感受到她渴求新語言、表述新情感的強(qiáng)烈愿望。對她這個(gè)水墨寫實(shí)人物畫代表畫家的新嘗試,人們一時(shí)很難接受,非議紛至沓來,但她無所畏懼:“我就想畫那種受壓抑的狀態(tài),壓得透不過氣來的那種狀態(tài)。這種思想感情要求之下,開始把人有些變形了。但變得并不是非常厲害,因?yàn)槭浅醪絿L試。當(dāng)時(shí)很多人反對,有人說我趕時(shí)髦。我心里明白,我不是趕時(shí)髦。因?yàn)楫?dāng)時(shí)還不時(shí)髦,當(dāng)時(shí)變形是受指責(zé)的。我覺得當(dāng)時(shí)是我自己要表達(dá)我自己想表達(dá)的東西,我自己想說的話,我想盡辦法想把我說的話說清楚。我必須這樣做。表達(dá)得不好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我當(dāng)時(shí)堅(jiān)決要這樣做,就這樣做了。后來《礦工圖》畫出來展出的時(shí)候有很多人就看著不舒服,說你畫的這個(gè)讓人感覺很壓抑,透不過氣來。我說:‘對了,我就是要這效果’。所以我覺得不能說成功吧,至少還達(dá)到一些目的。”這番話既表現(xiàn)了她的自信、執(zhí)著和堅(jiān)韌,也印證了她在觀念上的深刻變化。
這套擬以解放前礦工史為主線的組畫,是周思聰與丈夫盧沉(任教于中央美院國畫系),早在1966年便萌發(fā)的構(gòu)思,卻在1980年才得以重拾。這一年的4月中旬,他們同赴吉林省遼源煤礦收集創(chuàng)作素材,畫了大批礦工速寫。這是當(dāng)年日軍為掠奪我國資源,集中華工最多的煤礦之一,老礦工們都還深切銘記著當(dāng)年的亡國之痛。除了形象素材,周思聰夫婦還收集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并到吉林省博物館查閱了日偽時(shí)期的歷史資料。從煤礦歸來,周思聰有機(jī)會作短暫的日本之行,拜訪了敬慕已久的丸木位里夫婦,欣賞了始終心儀的兩件鴻幅巨制《原爆圖》和《南京大屠殺》,再一次激發(fā)了她的創(chuàng)作沖動。回國后,這種長期的情感積蓄和對一切新鮮的外來藝術(shù)形式的躍躍欲試的激情,終使他們開始了創(chuàng)作。但創(chuàng)作工作開始不久,盧沉便因嚴(yán)重的肝病而退出了合作,構(gòu)成組畫的《同胞、漢奸和狗》、《王道樂土》、《人間地獄》和《遺孤》四件作品,幾乎都是周思聰獨(dú)自完成的。她在藝術(shù)語言上采用了表現(xiàn)性的夸張變形手法,苦澀而扭曲;構(gòu)圖上也一反慣常的手法,引入拼貼和平面分割手法,試圖在同一畫面中表現(xiàn)不同的時(shí)空—人物形象交錯(cuò)重疊,畫面顯得錯(cuò)綜復(fù)雜、支離破碎,視覺效果驚心動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壓抑憤懣的環(huán)境氣氛的烘托是她最為用心的,90多個(gè)人物,有橫七豎八疊壓在一起的尸體,有驚恐無助的孩童,有蒼涼麻木的老人,有無望的母親,有殘肢的少年,有賣唱的少女,有坑道里爬行著的采礦工人,一切都統(tǒng)一在一種陰森可怖的氣氛里。1983年夏,周思聰因患類風(fēng)濕關(guān)節(jié)炎而不得不停止了這樣一個(gè)費(fèi)盡心力的創(chuàng)作,使得原計(jì)劃的最后一幅《歷史的見證》終未完成。

周思聰 兵團(tuán)女戰(zhàn)士 素描

周思聰 龍?zhí)洞缶頁P(yáng)機(jī)手曹永敏 速寫

周思聰 深夜(草圖) 速寫
周思聰曾說過:“我喜歡悲劇,喜歡揭示人生苦難的作品,也許這就是一種特質(zhì)。”從不諳世事時(shí)即為珂勒惠支動容到后來為《原爆圖》戰(zhàn)栗,變形的受難者、悲劇的人生、表現(xiàn)主義的激情語言等等,契合著她的內(nèi)在個(gè)性和氣質(zhì)傾向。對她來說,畫畫從來不僅僅是消遣,而是要表現(xiàn)真實(shí)的生活,喚醒人類的良知,促進(jìn)社會的進(jìn)步的,“繪畫的功能不僅僅使人賞心悅目。人生充滿了苦難,它往往最震撼我的心靈,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表現(xiàn)欲望。它不容我裝腔作勢,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實(shí)實(shí)訴說出來。”《礦工圖》組畫便是她這種精神的充分體現(xiàn)。從醞釀到完成,周思聰承載了遠(yuǎn)遠(yuǎn)多于畫面的苦難,而最終因身體原因的停止,對她來說又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她在創(chuàng)作中始終追求諸如深沉、力量或男子氣概,但“盧沉因病不能畫,我的壓力很大。這畫要表現(xiàn)一種力,需要有男子的氣概。我感到自己還缺少這力量。這似乎是沒有辦法的事”,她的滿腔激情與她無法擁有的某些特質(zhì)所構(gòu)成的矛盾一直困擾著她,或許性別以及相關(guān)感受和能力是必須面對的,更或許繪畫到底多大程度以及如何承擔(dān)社會責(zé)任也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這個(gè)停頓可以看做她依循自我本真和藝術(shù)真實(shí)的一種誠實(shí)態(tài)度。至此,重大主題在周思聰?shù)膭?chuàng)作中告一個(gè)段落,這套組畫既是她由寫實(shí)走向表現(xiàn)的一個(gè)標(biāo)志和出發(fā)點(diǎn),也是她對以往藝術(shù)觀念的一次歸結(jié)。
還在創(chuàng)作《礦工圖》期間的1982年5月,周思聰曾去四川大涼山彝族地區(qū)寫生:“農(nóng)民苦極了。這是天府之國?我在旅途中所經(jīng)的縣城,街面上多是些擺小攤攤的,幾杯帶顏色的甜水,或一小堆花生,幾只青桔子,就算是生意。還
有一兩個(gè)壯勞力呆坐在攤子前守著。這樣的攤子有無數(shù)。半死不活的日子,難道中國老百姓只能如此么?水田里仍是幾千年前的耕犁水牛。真是太緩慢了,太緩慢了,緩慢得令人窒息。”一種原始的、自然的、蒼茫的與悲涼的人類原生狀態(tài)觸動并撞擊著她的心靈,“當(dāng)我靜下來回味的時(shí)候,似乎才開始有些理解他們了。理解那死去的阿芝,理解那孩子痛苦的眼睛,理解那天地之間陰郁的色彩……他們愚昧、迷信,樣子使人害怕,但他們都是天生的詩人……他們?nèi)諒?fù)一日平淡無奈的生活,他們的目光,他們踏在山路上的足跡都是詩。……詩不會在那漂亮的衛(wèi)生間里,也不在那照相機(jī)前的忸怩作態(tài)里。那里是一片空虛啊!”就這樣,在這種與她自身現(xiàn)實(shí)生活迥然相異的氣息中,她找到了某種精神上的共鳴—他們雖然沒有文化,“人與人之間卻很干凈,比較原始,這就很入畫”,“好像在上一個(gè)世紀(jì)的夢中曾經(jīng)相見,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融洽”。這種共鳴使她超越了采風(fēng)式的獵奇狀態(tài),真正將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這樣一個(gè)題材上:“這些天,我的魂依然在涼山飄蕩,就在那低低的云層和黑色的山巒之間。白天想著他們,夢里也想著。我必須試著畫了。”周思聰?shù)牡谝粡堃妥孱}材作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創(chuàng)作于《礦工圖》期間,對藝術(shù)的理解和具體處理手法難免帶有《礦工圖》濃重沉郁的氣息,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用筆也帶有《礦工圖》對變形和力度的追求,但與《礦工圖》激烈而悲愴的氣氛相比,這件作品的氣息主要是悲涼與滄桑—負(fù)重途中的喘息是沉重的,表情是木然的,面對命運(yùn)既是無奈而茫然的,也是堅(jiān)忍并擔(dān)當(dāng)著的,畫家的精神指向顯然要比英雄主義時(shí)代更為豐富和復(fù)雜。

周思聰 蔣兆和先生肖像30×69cm 紙本 設(shè)色 1962年鈐印:周(白)

1990年,周思聰在作品《廣島風(fēng)景》前留影。
1983年,周思聰又根據(jù)彝族寫生素材創(chuàng)作了《邊城小市》、《秋天的素描》、《母子》、《三個(gè)女孩》、《牧歸》、《高原暮歸》、《負(fù)薪暮歸》、《戴月歸》等,筆墨逐漸松動,苦澀之味逐漸減淡,抒情、淡雅之意逐漸增加。雖然依舊是負(fù)重的女人形象,依舊是孤獨(dú)地前行,依舊是路途漫漫、生活艱辛、神情淡漠,但畫面的空間開闊了,精神的負(fù)累減弱了,撲面而來的壓抑感減輕了。較之過去一味強(qiáng)調(diào)的凝重感,更多了些形式上的審美意趣。把這些彝女或藏女形象與周思聰本人的生活感受聯(lián)系起來應(yīng)該不算牽強(qiáng),在她對普通勞動女性的關(guān)切中,實(shí)際上包涵著一種詢問:“我們這一代中年人過來很不容易,政治運(yùn)動的壓力,家庭生活的操勞,社會上人與人的關(guān)系,種種東西都讓人感到很累。”周思聰曾坦言:“實(shí)際上我并不是在表現(xiàn)彝民,而是表現(xiàn)我自己”。正因如此,這個(gè)題材在她后期創(chuàng)作中一直延續(xù)到生命的最后幾年,當(dāng)然面貌與氣質(zhì)還是不斷有所變化的。到了1987年的《落木蕭蕭》,對人物神情的刻畫已經(jīng)完全淡出,而對整體意境的營造則更為突出,人變得小且不那么重要了,景色變得明凈而優(yōu)美了,同時(shí),筆也更加毛毛澀澀的,墨色也更加清清淡淡的—落木蕭蕭中彝女在倚樹喘息,一派清濛。此后出現(xiàn)的談情、采集、游玩、踏歌、閑坐等情境,所繪雖源自現(xiàn)實(shí),所追求的卻是越來越理想的、非現(xiàn)實(shí)的精神境界,一個(gè)遠(yuǎn)離喧囂的、澄明而寧靜的境界,一個(gè)雖優(yōu)美卻憂郁的境界。正是這樣一個(gè)系列,使周思聰完成了由大主題向小主題的過渡,由剛性向女性的回歸,由崇高莊嚴(yán)向平樸淡雅的轉(zhuǎn)移,由凝重向細(xì)膩抒情風(fēng)格的轉(zhuǎn)向。
1985年前后,是周思聰探索面最寬的時(shí)期,除了筆墨語言上的精進(jìn)、題材樣式上的拓展,還包括多種材料和手段的嘗試,如油畫、拓印、拼貼、潑灑等,而對任何陌生的材料,周思聰都有著天生的敏感,對筆墨、紙張、肌理、顏色等都有很好的控制力,非常清楚不同的材料將要出現(xiàn)的不同效果,以至于丈夫盧沉不無感慨地認(rèn)為“她是天才的女畫家”。
通過幾年的探索,周思聰?shù)乃囆g(shù)生命中到了出現(xiàn)更大轉(zhuǎn)機(jī)的時(shí)候,可惜的是,開始于1983年的類風(fēng)濕關(guān)節(jié)炎發(fā)展到更嚴(yán)重的程度,1987年春夏之交竟至住院,之后的十年間,病情雖有時(shí)穩(wěn)定與好轉(zhuǎn),但總趨勢是逐漸惡化,全身關(guān)節(jié)由難忍之疼痛到僵直和變形,嚴(yán)重之時(shí),寢食難安,不能行走與持筆。同時(shí)并發(fā)癥也越來越多,進(jìn)出醫(yī)院成為家常便飯。
就在她的生命機(jī)能幾近廢止的那些難熬的日日夜夜里,她還要堅(jiān)持作畫,以此來寄托、沉浸與忘卻。一切忙碌停頓下來,她能面對的只能是病榻上無法移動的身體和病房窗口外那幾個(gè)固定的視野。繁重的家務(wù)不需要她了,此起彼伏的藝術(shù)革新夾雜著喧囂也離她遠(yuǎn)去了。她的生活安靜、局限、孤獨(dú)。有長達(dá)五年的時(shí)間,周思聰幾乎完全被禁錮在一個(gè)狹小的空間里,但她的內(nèi)心沒有被禁錮,而是飄向遠(yuǎn)方的彝女,飄向蒙蒙煙雨中的池塘,飄向她內(nèi)心深處的境界。
這時(shí)期,她的表現(xiàn)題材大致集中于三個(gè)方面,即彝女、小景山水和荷花。令她難以忘懷的彝女,到這個(gè)時(shí)候,已經(jīng)成為一種象征或符號,她們雖然依舊負(fù)重,但已經(jīng)不沉重,寄托著周思聰對女性命運(yùn)的思考、對大自然的渴望和對未來的詩意幻想。她的屬于女性的柔情、細(xì)敏與自我審視,也通過她們發(fā)散出來。《秋林負(fù)薪》是這個(gè)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依舊是細(xì)細(xì)的如同捻棉線一樣捻出來的線,依舊是淡淡的色調(diào),依舊是緩慢有致的節(jié)奏;六棵粗壯的樹被處理得淡極了,淡得仿佛要融化掉,背景因而顯得極為空曠、潤澤和清新,氣息令人沉醉;五個(gè)負(fù)重的女人,因?yàn)榇緲愫拓S滿而別具韻致;她們從右向左靜靜地移動著,如履仙境;地上幾片發(fā)黃的葉子和幾叢枯草點(diǎn)明了秋意,簡潔之致,多一筆不能,少一筆不得,有一種令人屏住呼吸的力量,仿佛喘一口氣都會玷污這個(gè)干干凈凈的世界。
從醫(yī)院窗外得來的《病室》和《過路雨》,透露著病魔給周思聰帶來的心理上的變化。病室里赫然一個(gè)大大的、她再也離不開的輪椅,房屋斜斜的,月光慘淡而清寂;窗外的天空飄來一片云,留下一陣雨,短短的、時(shí)斷時(shí)續(xù)的、細(xì)細(xì)的線,蒙蒙的,織就一張憂傷的網(wǎng),罩在水漬斑斑的房屋、天空和她的心上,凄涼而黯淡。這就是她的山水小景的大致樣貌,任情恣肆,圓著自己一生的山水情結(jié),而且越是被隔離于自然之外,對自然的向往便越是強(qiáng)烈。受指關(guān)節(jié)變形的限制,她無法大量使用擅長的線條,不得已轉(zhuǎn)用隨機(jī)性的潑灑點(diǎn)染,反倒別富想象和表現(xiàn)空間。煙雨迷蒙中,一棵樹,一間屋,一座山,一抹云,一些顧盼與纏綿,都是心境的確切寫照,正所謂“畫山即是畫人,畫人格、畫精神、畫自己”。技巧和手段已經(jīng)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營造出的高渺、空靈、奇逸的境界。一些代表作如《山川出云》、《云歸山色深》、《野趣》、《小屋》等,標(biāo)示著山水已經(jīng)成為衡量其藝術(shù)成就的重要方面了。
1992年創(chuàng)作的以四聯(lián)屏《自在水云鄉(xiāng)》為代表的100余幅畫荷之作,集中體現(xiàn)了她在身體強(qiáng)烈變化中心理和情緒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風(fēng)格與境界的升華,可以看做她藝術(shù)成熟的重要標(biāo)志,是她在生命幾近終結(jié)前創(chuàng)造的又一個(gè)藝術(shù)高峰。同樣受病指影響,她的荷花放棄了細(xì)節(jié)刻畫,集中于情調(diào)與氣氛的表現(xiàn),以用墨、用水、用礬和局部肌理處理而自成特色,清空獨(dú)絕,很具現(xiàn)代感。時(shí)濃時(shí)淡的墨色,忽重忽輕的筆意,模糊、虛幻的花葉,在風(fēng)雨中,在霧氣中,如夢如幻,充溢著憂傷的詩意,呈現(xiàn)著一種深沉的情懷和精微的趣味。大凡,一個(gè)成功的藝術(shù)家,或在藝術(shù)技法上有所推進(jìn),或在藝術(shù)精神上有所提升。相對而言,技法的創(chuàng)造終是有限的,精神的樣態(tài)卻可以是無限的。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周思聰以其真誠的態(tài)度為我們創(chuàng)造的這樣一種獨(dú)特的審美趣味,使她成為中國美術(shù)史上公認(rèn)的最杰出的女畫家。
1993年4月,因長期服用激素,周思聰?shù)哪_部開始出現(xiàn)潰瘍,且面積逐漸增大,再難愈合,此時(shí)后悔當(dāng)初不該服用激素,已為時(shí)太晚。她的身體越來越難以支持,畫作也越來越少。1995年歲末,只有老天知道她將度過最后一個(gè)新年。她把筆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畫了十多張自制的賀年片,寄送給師友,所畫多是彝女:“我要讓他們知道,我還能畫畫。”真的,筆觸細(xì)而勻,完全沒有不支的感覺,連她自己都少見地忍不住“不謙虛”地說:“我也沒想到能畫那么好。”同樣把筆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能畫那么好”的是默畫的白描《李可染先生像》,側(cè)身站立的可染先生一手拄杖,一手持畫夾,神情自若!線條細(xì)勁、準(zhǔn)確,控制得相當(dāng)好。這是她的最后一件作品。

1996年,周思聰用中指夾筆為《李可染畫集》作《李可染先生像》,此為周思聰最后一幅作品。
1996年1月20日,周思聰因胃部不適住院,第二天便因突發(fā)急性壞死性胰腺炎逝世于北京地壇醫(yī)院,享年57歲。盡管人生滿是苦樂和無常,但我們對于逝去的曾經(jīng)帶著體溫的生命卻總是有著相通的眷戀,特別是那些精神上有所遺留的引人追思的個(gè)體,她的音容笑貌,她的思想品格,我們懷念且神傷……但,生死往來,誕生逝去,不是永恒的規(guī)律么?如此,我們只需平靜地告別。
“我的經(jīng)歷簡單而幸運(yùn),說來話短。”這是周思聰在她的千字自傳中的開篇語,一生淡泊的謙謙君子之風(fēng)昭然,溫婉的笑容亦仿佛如在目前。“有人說畫畫是苦事,有人說畫畫是樂事。其實(shí),沒有苦哪有樂?只不過入了迷,雖苦心甘。”“世界上眾多的人為生存從事著自己并不喜歡的工作,而我不是,我很幸運(yùn)。”果真簡單亦或幸運(yùn)?相對而已。在歷經(jīng)繁復(fù)后說簡單,盡棄悲傷后說幸運(yùn),無奈也寬容。說起煩惱,人生大凡如此;說起幸運(yùn),人生唯此選擇才有味。周思聰走過了她充滿煩惱而有味的生命歷程,她留下的,是含著歡樂與苦澀的藝術(shù)。
周思聰曾說過:“父親曾希望我成為一名醫(yī)生,這職業(yè)無疑是高尚的,而我毫無興趣。從孩童時(shí)起,我只鐘情于畫畫,沒想過會干別的。今生如愿以償了,若真有來世,我仍會這樣選擇。”若我們也有來世,必定會與這個(gè)才情秀逸的女畫家再度相遇吧!那將是何等幸運(yùn)!

周思聰 長白青松112×95cm 紙本 設(shè)色 1973年鈐印:周(白) 思(白)


周思聰 人民和總理151×318cm 紙本 設(shè)色 1979年釋文:人民和總理。俺們舍不得總理走,他說:“重建家園后再來看你們。”如今災(zāi)區(qū)變成了新村,俺們大伙等啊盼啊,就盼著那一天……”—記邢臺地震災(zāi)區(qū)一位老鄉(xiāng)的哭訴。一九七九年八月初稿,思聰。鈐印:周(白) 思聰(白)

周思聰 礦工圖習(xí)作34×34cm 紙本 水墨 1980年鈐印:周(白)

周思聰 礦工圖習(xí)作34×34cm 紙本 水墨 1980年鈐印:周(白)

周思聰 同胞、漢奸和狗(礦工圖系列)(與盧沉合作)178×318cm 紙本 水墨 1980年鈐印:周(白)

周思聰 王道樂土177×236cm 紙本 水墨 1982年鈐印:周(白)

周思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102.5×103cm 紙本 設(shè)色 1982年鈐印:周(白)

周思聰 礦工子弟67.5×82cm 紙本 設(shè)色 1980年鈐印:周(白)

周思聰 秋天的素描98×102cm 紙本 設(shè)色 1983年鈐印: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