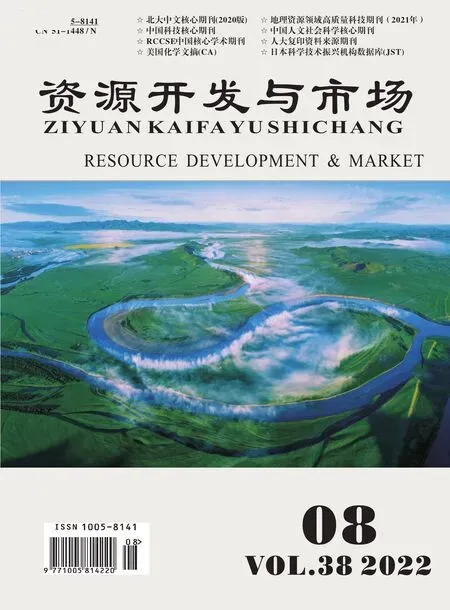黃河流域省區(qū)隱含碳排放及其碳轉(zhuǎn)移研究
康彥霞,馬 忠
(西北師范大學(xué) 地理與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70)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jīng)濟飛速增長的同時使用了大量化石能源,產(chǎn)生的碳排放帶來了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國家。我國莊嚴承諾,到2030 年實現(xiàn)碳排放達峰,2060年前實現(xiàn)碳中和,這需要各區(qū)域分擔(dān)責(zé)任共同減排。我國目前的碳排放量是各區(qū)域碳排放總和,減排必須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減排目標(biāo)由各個省份分擔(dān)實施,但是因為各區(qū)域資源稟賦、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展階段的不同,區(qū)域間碳排放存在很大差異[1],在總減排目標(biāo)下確定各省份應(yīng)承擔(dān)的減排責(zé)任是重點難題。我國各省份之間貿(mào)易頻繁,產(chǎn)生的隱含碳轉(zhuǎn)移對各省份碳排放具有重要影響,這就需要估算因省份間貿(mào)易而產(chǎn)生的隱含碳。
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供應(yīng)基地,其煤炭產(chǎn)量約占全國的70%[2],經(jīng)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之間矛盾突出,面臨的碳減排壓力巨大。2019年,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被提出并成為國家戰(zhàn)略[3]。黃河流域高質(zhì)量發(fā)展不是流域內(nèi)各省區(qū)分別實現(xiàn)高質(zhì)量發(fā)展,而是在整體上實現(xiàn)發(fā)展[4],黃河流域面臨的資源環(huán)境問題也只能通過整體治理才能得到有效減緩。因此,本文從各省區(qū)視角和黃河流域整體視角來探討黃河流域隱含碳排放及轉(zhuǎn)移特征,對合理分配黃河流域重要能源生產(chǎn)省區(qū)的減排責(zé)任意義重大。
隨著全球?qū)I(yè)化分工的發(fā)展,不同階段的產(chǎn)品在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生產(chǎn),發(fā)達國家大量進口產(chǎn)品導(dǎo)致“碳泄露”問題。我國各省份之間也存在產(chǎn)品的交換,有的省份在產(chǎn)品生產(chǎn)過程中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不僅僅為本地消費,還要滿足其他省份的消費或出口[5]。產(chǎn)品生產(chǎn)地和消費地分離對制定碳排放責(zé)任問題增加了困難。國外已有很多從隱含碳的角度分析碳轉(zhuǎn)移的研究[6,7]。研究發(fā)現(xiàn),發(fā)達國家通過貿(mào)易向發(fā)展中國家轉(zhuǎn)移了碳排放,發(fā)展中國家則為發(fā)達國家承接了部分碳排放。我國與主要貿(mào)易國之間的碳排放轉(zhuǎn)移也受到了關(guān)注[8-10]。近年來,國內(nèi)和區(qū)域隱含碳轉(zhuǎn)移的研究也廣泛開展。如:韓夢瑤等[11]基于嵌套網(wǎng)絡(luò)視角研究了我國省域碳排放國內(nèi)外轉(zhuǎn)移情況;陳暉等[12]用MRIO(多區(qū)域投入產(chǎn)出模型),從污染貿(mào)易條件、碳基尼系數(shù)等多個方面分析了我國31 省份之間的碳轉(zhuǎn)移及公平性;張紅麗等[13]對京津冀區(qū)域內(nèi)的隱含碳轉(zhuǎn)移進行了研究。目前碳減排責(zé)任分擔(dān)機制有3 種[14]:一是生產(chǎn)者責(zé)任原則,將產(chǎn)品生產(chǎn)和服務(wù)產(chǎn)生的碳排放歸于生產(chǎn)者,而沒有考慮為誰提供產(chǎn)品和服務(wù);二是消費者責(zé)任原則,從最終消費角度顯示碳排放的來源,該種核算方式對碳排放出口地區(qū)更為公平[15];三是責(zé)任共擔(dān)原則,該原則有利于促進減排公平性,其核心問題是計算責(zé)任共擔(dān)分配因子[16]。
總體來看,一方面,以往貿(mào)易隱含碳轉(zhuǎn)移大多是從最終產(chǎn)品消費的視角來計算隱含碳排放,未體現(xiàn)地區(qū)中間產(chǎn)品貿(mào)易引致的碳排放,且未對省區(qū)間碳轉(zhuǎn)移的具體流向進行探討;另一方面,以上研究多為單一年份碳轉(zhuǎn)移,沒有考慮年際變化。基于此,本文將省份排放的隱含碳分解為滿足本地最終需求引致、滿足外省中間產(chǎn)品需求引致和滿足外省最終產(chǎn)品需求引致,并揭示了省區(qū)調(diào)入調(diào)出貿(mào)易隱含碳的具體流向。本文采用多區(qū)域投入產(chǎn)出模型,從隱含碳貿(mào)易視角探討了黃河流域碳排放特征及其轉(zhuǎn)移路徑,從生產(chǎn)者責(zé)任、消費者責(zé)任視角測算了黃河流域9 省區(qū)2012 年、2017 年隱含碳排放情況,探討了隱含碳排放構(gòu)成及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隱含碳轉(zhuǎn)移來源和去向,以期為黃河流域高質(zhì)量發(fā)展和低碳減排提供借鑒與參考。
1 研究區(qū)域概況
黃河流域總面積79.5 萬km2,橫跨青藏高原、內(nèi)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四大地貌單元,涵蓋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9 個省區(qū);2020 年GDP 為24.74 萬億元,約占全國GDP 總量的25%,但人均GDP 低于全國水平[17]。9 個省區(qū)發(fā)展水平差異巨大,下游省區(qū)比上游經(jīng)濟發(fā)達。黃河流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以第二產(chǎn)業(yè)為主體,其中,能礦資源采掘業(yè)占比較高。流域內(nèi)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儲量豐富,在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成為重工業(yè)、能源及化工生產(chǎn)基地,中國“5 +1”能源基地中有3 個位于黃河流域。黃河流域是“一帶一路”重要經(jīng)濟走廊,是聯(lián)系我國東、中、西部的經(jīng)濟紐帶,也是我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和生態(tài)保護的重要區(qū)域,加強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對我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和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
2 數(shù)據(jù)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采用我國2012 年、2017 年31 個省份(因數(shù)據(jù)缺失,故研究區(qū)域未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和臺灣地區(qū))42 個部門的多區(qū)域投入產(chǎn)出表,根據(jù)黃和平[18]、李艷梅等[19]的方法,將42 個部門合并為7 個(表1)。各省份碳排放數(shù)據(jù)清單由中國碳核算數(shù)據(jù)庫(CEADs)根據(jù)IPCC 行業(yè)碳核算方法編制,該清單包括生產(chǎn)水泥過程產(chǎn)生的碳排放和17 種化石能源燃燒產(chǎn)生的碳排放[20]。

表1 部門合并結(jié)果Table 1 Departmental merger
2.2 研究方法
構(gòu)建G個地區(qū)N個部門多區(qū)域投入產(chǎn)出模型:

式中:對任一地區(qū)s,Xs表示s 地區(qū)總產(chǎn)出向量;Ass表示s 地區(qū)直接消耗系數(shù)矩陣;Yss表示s 地區(qū)生產(chǎn)并滿足該地區(qū)最終需求向量;Asr(r =1,…,G,且r≠s)地區(qū)s 和地區(qū)r 之間的相互需求系數(shù)矩陣,表示兩地區(qū)之間中間品貿(mào)易;Ysr為s 地區(qū)生產(chǎn)并滿足于r 地區(qū)的最終需求向量,表示地區(qū)s 對地區(qū)r的最終品貿(mào)易;X 和Y 為N × 1 列向量,A 為N × N列矩陣。
由公式(1)得:

表示經(jīng)典里昂惕夫逆矩陣。
在G 個地區(qū)N 個部門的經(jīng)濟系統(tǒng)中,行平衡關(guān)系式為:

隱含碳排放的測算:隱含碳排放的測算參考王安靜等[21]、王育寶等[22]的研究。本文關(guān)注黃河流域隱含碳排放及其國內(nèi)貿(mào)易隱含碳轉(zhuǎn)移,因此不計算出口隱含碳。

式中:第一項表示s 地區(qū)為滿足本地最終需求產(chǎn)生的隱含碳;第二項、第三項分別表示s 地區(qū)為滿足其他區(qū)域中間產(chǎn)品需求、最終產(chǎn)品需求調(diào)出的隱含碳。
區(qū)域s 消費側(cè)碳排放為:

3 結(jié)果及分析
3.1 各省區(qū)生產(chǎn)側(cè)和消費側(cè)碳排放
根據(jù)公式(5)、(6)對黃河流域各省區(qū)生產(chǎn)側(cè)和消費側(cè)碳排放進行測算,結(jié)果如圖1 所示。從圖1可見:①總體來看,黃河流域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大于消費側(cè)碳排放。2012—2017 年,其生產(chǎn)側(cè)和消費側(cè)碳排放均呈增長趨勢,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從2012 年的2818Mt上升到2017 年的3159Mt,年均增長率為2.3%;消費側(cè)碳排放從2067Mt 上升至2363Mt,年均增長率為2.7%。②從各省區(qū)來看,2012 年黃河流域9 省區(qū)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均大于消費側(cè)碳排放。其中,山西省和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分別為消費側(cè)碳排放的1.76 倍、2 倍。山西省和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為化石能源集中地,為外省生產(chǎn)并提供了大量能源密集型產(chǎn)品,導(dǎo)致碳排放顯著增加。2017 年,除河南省、四川省、陜西省消費側(cè)碳排放增長并超過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外,其他省區(qū)依然是生產(chǎn)側(cè)大于消費側(cè)碳排放。③從地理分布看,黃河流域隱含碳排放大致呈現(xiàn)出中下游地區(qū)高于上游地區(qū)。中下游地區(qū)的山東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河南省、山西省是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較高地區(qū),2012年和2017 年均高于400Mt,占黃河流域總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量的72%。山東省、河南省人口眾多,能源消費量大,且制造業(yè)發(fā)達,而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需要生產(chǎn)能源資源產(chǎn)品,因此產(chǎn)生的隱含碳排放大;四川省、陜西省的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也超過210Mt,而青海省隱含碳排放量最小,不足50Mt。就消費側(cè)碳排放來看,山東省、河南省消費側(cè)碳排放最大,2012年和2017 年分別占黃河流域消費側(cè)碳排放的66%、49%。2012—2017 年,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東省、陜西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呈增長趨勢。其中:山東省和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增長量最多,分別為153Mt和95Mt,年均增長量分別為4.5%、3.4%;山西省、陜西省、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增長均超過29Mt;河南省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下降了24Mt。

圖1 黃河流域各省區(qū)隱含碳排放Figure 1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為了更清晰了解各省生產(chǎn)側(cè)和消費側(cè)碳排放的產(chǎn)生原因,本文對黃河流域9 省區(qū)隱含碳排放的結(jié)構(gòu)組成進行了分析,結(jié)果如圖2 所示。從圖2 可見:①內(nèi)需碳排放和中間產(chǎn)品貿(mào)易碳排放是黃河流域各省區(qū)碳排放的主要組成部分。2012 年黃河流域各省區(qū)內(nèi)需碳排放、中間產(chǎn)品調(diào)出碳排放、最終產(chǎn)品調(diào)出碳排放分別占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的51%、42%、5%,2017年分別占52%、40%、7%。②從各省區(qū)碳排放的組成來看,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河南省、陜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qū)中間產(chǎn)品調(diào)出碳排放均大于內(nèi)需碳排放,說明這些省區(qū)生產(chǎn)并向其他省份提供了大量產(chǎn)品,從而導(dǎo)致碳排放的快速增長。山東省、四川省、青海省則以內(nèi)需排放為主要構(gòu)成部分。2012—2017 年,山東省內(nèi)需碳排放、中間產(chǎn)品調(diào)出碳排放和最終產(chǎn)品調(diào)出碳排放增長量均大于35Mt,這是該省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快速增加的原因。說明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山東省不僅自身消費能源增加,還更多地參與到國內(nèi)初級產(chǎn)品和最終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加工中。山西省和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中間產(chǎn)品調(diào)出的增加,其增長量均大于70Mt,表明山西省和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越來越多地向其他地區(qū)提供初級產(chǎn)品。中間產(chǎn)品往來產(chǎn)生的碳排放量增加,表明一個產(chǎn)品由多個省區(qū)通過生產(chǎn)鏈完成,并非單獨生產(chǎn),省區(qū)間的聯(lián)系也越來越緊密。值得關(guān)注的是河南省,2012—2017 年其消費側(cè)碳排放量增長了201Mt,中間產(chǎn)品和最終產(chǎn)品調(diào)入隱含碳均有所增加。近年來,河南省第二產(chǎn)業(yè)占比增長緩慢,而第三產(chǎn)業(yè)增長加快,其工業(yè)化也從中期向后期推進,因此該省調(diào)出產(chǎn)品減少,調(diào)入產(chǎn)品增加來滿足第三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

圖2 黃河流域各省區(qū)隱含碳排放組成占比Figure 2 Proportion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 composi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3.2 各省區(qū)產(chǎn)業(yè)碳排放結(jié)構(gòu)
2012—2017 年黃河流域各省區(qū)產(chǎn)業(yè)碳排放結(jié)構(gòu)結(jié)果如圖3 所示。從圖3 可見:①從黃河流域內(nèi)需碳排放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來看,重制造業(yè)、建筑業(yè)和服務(wù)業(yè)是隱含碳排放量最高的產(chǎn)業(yè),2012 年其碳排放分別為400Mt、377Mt、257Mt,分 別 占 黃 河 流 域 內(nèi) 需 排 放 的33%、31%、21%,農(nóng)業(yè)、能源工業(yè)、輕制造業(yè)、其他工業(yè)隱含碳排放占比均不到7%。重制造業(yè)碳排放最大的省區(qū)依次是山東省、河南省、四川省,2012 年重制造業(yè)碳排放分別占黃河流域總制造業(yè)碳排放的49%、38%、33%。建筑業(yè)和服務(wù)業(yè)碳排放最大的省區(qū)均為山東省。各省區(qū)建筑業(yè)占內(nèi)需碳排放的比重均較大,2012 年超過22%。2012—2017 年,黃河流域重制造業(yè)內(nèi)需碳排放從400Mt 下降至310Mt。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東省、河南省重制造業(yè)內(nèi)需碳排放呈下降的趨勢,下降量均大于12.9Mt。而建筑業(yè)內(nèi)需碳排放從370Mt上升至410Mt,成為內(nèi)需碳排放最大的部門。各省區(qū)的快速城市化是建筑業(yè)碳排放大且一直增長的原因,建筑業(yè)使用的金屬等材料較多,需要大量其他產(chǎn)業(yè)和產(chǎn)品的輸入。服務(wù)業(yè)碳排放量從257Mt上升至290Mt,除山西省和陜西省外,其他省區(qū)服務(wù)業(yè)碳排放均呈增長的趨勢。隨著各地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改變,服務(wù)業(yè)隱含碳需求逐漸增長。②從黃河流域調(diào)出碳排放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來看,調(diào)出隱含碳排放最大的部門是能源工業(yè),2012 年和2017 年9省區(qū)能源工業(yè)隱含碳的總調(diào)出量分別為874Mt、1187Mt,占黃河流域總調(diào)出的54%、63%。調(diào)出隱含碳最大的產(chǎn)業(yè)為重制造業(yè),2012 年和2017 年調(diào)出量分別為529Mt、459Mt,占總調(diào)出的32%、24%;農(nóng)業(yè)、輕制造業(yè)、建筑業(yè)、其他工業(yè)、服務(wù)業(yè)調(diào)出隱含碳占比均不到5%。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陜西省是能源工業(yè)碳排放調(diào)出最大的地區(qū),均超過100Mt;山東省、河南省是重制造業(yè)隱含碳排放調(diào)出最大的地區(qū)。2012—2017 年,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東省能源工業(yè)調(diào)出隱含碳排放增長量均超過73Mt。從調(diào)入隱含碳排放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來看,重制造業(yè)、能源工業(yè)依然是調(diào)入隱含碳最大的產(chǎn)業(yè),2012 年和2017 年黃河流域9 省區(qū)能源工業(yè)調(diào)入隱含碳分別為327Mt、405Mt,重制造業(yè)調(diào)入隱含碳分別為353Mt、443Mt。河南省、陜西省重制造業(yè)調(diào)入隱含碳最大,河南省、山東省能源工業(yè)隱含碳調(diào)入最大,2012—2017 年間河南省能源工業(yè)調(diào)入隱含碳增長了180Mt,這也是該省調(diào)入隱含碳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圖3 黃河流域各省區(qū)分部門隱含碳排放結(jié)構(gòu)Figure 3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per province and sector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3.3 省際貿(mào)易隱含碳轉(zhuǎn)移
省際貿(mào)易凈碳轉(zhuǎn)移時空變化:2012 年,黃河流域9 省區(qū)均為凈碳轉(zhuǎn)入地區(qū),凈碳轉(zhuǎn)入總量為817Mt。2017 年,除河南省、陜西省、四川省外,其他省區(qū)依然是凈碳轉(zhuǎn)入地區(qū),凈碳轉(zhuǎn)入總量為796Mt。其中,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和山西省凈碳轉(zhuǎn)入量最大,2012年分別占黃河流域凈碳轉(zhuǎn)入的21%、32%,說明我國生產(chǎn)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能源的消耗,導(dǎo)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西省等資源型省區(qū)碳排放的轉(zhuǎn)入。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凈碳轉(zhuǎn)入量僅次于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東省,說明寧夏為我國其他省份提供了較多資源工業(yè)產(chǎn)品。2012—2017 年,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東省凈碳轉(zhuǎn)入量迅速增加。近年來我國對資源能源的使用和依賴依然在加大,而山東省制造業(yè)發(fā)達,因此凈碳轉(zhuǎn)入大且持續(xù)增長;河南省、陜西省、四川省凈碳轉(zhuǎn)入量下降,變?yōu)閮籼嫁D(zhuǎn)出地區(qū)。

表2 黃河流域各省區(qū)隱含碳轉(zhuǎn)移量(單位:Mt)Table 2 Embodied carbon transfer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Unit:Mt)
省區(qū)間碳轉(zhuǎn)移方向:從上述分析可知,由于黃河流域凈碳轉(zhuǎn)入量較大,因此需要分析碳排放轉(zhuǎn)移地理源特征,明晰區(qū)域碳轉(zhuǎn)移去向和來源,為區(qū)域合作減排提供參考。2012 年、2017 年黃河流域9 省區(qū)隱含碳轉(zhuǎn)移的主要地區(qū)結(jié)果如圖4 所示。從隱含碳轉(zhuǎn)移整體特征看,首先,隱含碳轉(zhuǎn)移具有顯著的地理鄰近效應(yīng),在黃河流域各省區(qū)隱含碳的調(diào)入地區(qū)上表現(xiàn)更為明顯,主要是黃河流域區(qū)域內(nèi)部隱含碳相互轉(zhuǎn)移及周邊省區(qū)的調(diào)入。如2012 年河北省向河南省轉(zhuǎn)移隱含碳25Mt,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向山東省轉(zhuǎn)移31Mt,山東省向河南省轉(zhuǎn)移24Mt。其次,隱含碳轉(zhuǎn)移具有明顯的產(chǎn)業(yè)互補性[23],這在黃河流域隱含碳調(diào)出地區(qū)表現(xiàn)的更為明顯,如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向江蘇省、廣東省的轉(zhuǎn)移。

圖4 黃河流域各省區(qū)隱含碳轉(zhuǎn)移流向關(guān)系Figure 4 Flow pattern of embodied carbon transfer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山東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西省、河南省調(diào)出隱含碳較大,本文具體分析4 個省區(qū)的隱含碳調(diào)出主要去向。2012 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調(diào)出隱含碳超過
20Mt的地區(qū)有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山東省、廣東省,山西省調(diào)出超過15Mt 的地區(qū)有北京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蘇省、山東省、廣東省,山東省調(diào)出隱含碳超過15Mt的地區(qū)有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河南省、廣東省,河南省調(diào)出隱含碳超過15Mt 的地區(qū)有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河北省人口眾多、產(chǎn)業(yè)以重工業(yè)為主,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等因地理鄰近效應(yīng)向其運輸能源產(chǎn)品。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上海省等省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迅速,對能源產(chǎn)品的需求量高,消費能力強,黃河流域省區(qū)對其調(diào)出的能源資源較多。2012—2017 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西省、山東省向河北省、浙江省、河南省調(diào)出隱含碳增長較多。從調(diào)入隱含碳地區(qū)來看,河南省、山東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調(diào)入隱含碳較大。分析其具體隱含碳主要來源地區(qū),河南省調(diào)入隱含碳超過10Mt的地區(qū)有河北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遼寧省、安徽省、江蘇省、山東省;山東省調(diào)入隱含碳超過10Mt 的地區(qū)有河北省、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黑龍江省、安徽省、陜西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調(diào)入隱含碳超過10Mt 的地區(qū)為河北省、遼寧省、江蘇省和山東省。由于黃河流域內(nèi)部各省區(qū)距離鄰近、交通便捷,通過短距離運輸便可實現(xiàn)資源和產(chǎn)品的貿(mào)易,因此相互之間隱含碳轉(zhuǎn)移量大。江蘇省、山東省制造業(yè)發(fā)達,產(chǎn)品貿(mào)易量大,向黃河流域各省區(qū)提供產(chǎn)品量大,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遼寧省也是資源量較為豐富的地區(qū),它們向黃河流域也調(diào)入了資源和產(chǎn)品。2012—2017 年,河南省從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遼寧省、江蘇省、浙江省、陜西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調(diào)入隱含碳增長量均大于13Mt。
3.4 區(qū)域合作減排效果
關(guān)于如何減少貿(mào)易隱含碳對各地區(qū)減排的影響的研究,Peters 等[24]在研究中提出可以通過向其他地區(qū)進口高耗能、高污染產(chǎn)品,從而減少本地碳排放。但對于國家、區(qū)域而言,這將會加重隱含碳出口地區(qū)的減排壓力,同時不利于整體減排。因此,無論是隱含碳進口或出口地區(qū),必須從區(qū)域合作減排的角度來實現(xiàn)減排目標(biāo)。根據(jù)鐘章奇等[25]對河南省減排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各省區(qū)獨自劃分碳減排責(zé)任,該省與中部6 省區(qū)的合作有利于減小貿(mào)易隱含碳排放的影響。
本文基于前面的研究,探討了2012 年黃河流域各省區(qū)合作減排與單獨減排的效果差異。鐘章奇對合作區(qū)域的選擇有兩個原則:一是貿(mào)易隱含碳凈流出地區(qū)可能更具合作的條件;二是地理鄰近性。黃河流域9 省區(qū)基本具備這兩個條件。Peters 等[24]認為只要區(qū)域調(diào)出和調(diào)入隱含碳占該區(qū)域總碳排放量的比重下降,該地區(qū)貿(mào)易隱含碳減排責(zé)任也會相應(yīng)減小,因此區(qū)域間合作會影響貿(mào)易減排的分擔(dān)。黃河流域各省區(qū)貿(mào)易碳排放占比和黃河流域區(qū)域內(nèi)貿(mào)易隱含碳占比結(jié)果如圖5 所示,在黃河流域區(qū)域內(nèi)合作減排后,調(diào)出和調(diào)入黃河流域的貿(mào)易隱含碳分別占該區(qū)域碳排放的48%、19%。與各省區(qū)單獨減排相比,除青海省和四川省的調(diào)入、調(diào)出比例上升之外,其他省區(qū)調(diào)出、調(diào)入占本地碳排放的比重都是下降的,尤其對陜西來說,其隱含碳調(diào)出、調(diào)入占比在開展區(qū)域合作后分別下降了24.7%、38.9%,說明區(qū)域合作減排可以減小黃河流域各省區(qū)減排責(zé)任。山東省、青海省、四川省可能參與黃河流域區(qū)域貿(mào)易不明顯,因此獲益程度也最小。

圖5 黃河流域各省區(qū)在開展區(qū)域合作前后的貿(mào)易隱含碳排放Figure 5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s and imports before and after reg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4 結(jié)論與政策啟示
4.1 結(jié)論
本文采用投入產(chǎn)出模型對黃河流域各省區(qū)2012年、2017 年的隱含碳排放進行了測算,分析了2012—2017 年各省區(qū)碳排放構(gòu)成及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碳轉(zhuǎn)移量及其地理源特征,并對黃河流域合作減排效果進行了分析。
主要結(jié)論如下:①黃河流域各省區(qū)整體上呈現(xiàn)出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大于消費側(cè)碳排放,區(qū)域內(nèi)隱含碳排放異質(zhì)性較大,中下游碳排放規(guī)模比上游省份大。山東省、河南省消費側(cè)碳排放相比其他省區(qū)較為突出。2012—2017 年,黃河流域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和消費側(cè)碳排放均呈增長的趨勢,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3%、2.7%。從隱含碳排放結(jié)構(gòu)來看,中間產(chǎn)品調(diào)出和內(nèi)需隱含碳排放占比最大,也是產(chǎn)生隱含碳的主要原因。②河南省、山東省、四川省的重制造業(yè),各省區(qū)的建筑業(yè)、服務(wù)業(yè)是內(nèi)需碳排放產(chǎn)生的關(guān)鍵部門,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的能源工業(yè)和山東省、河南省的重制造業(yè)是調(diào)出隱含碳排放的關(guān)鍵地區(qū)和部門,而山東省的能源工業(yè)、河南省的重制造業(yè)是調(diào)入隱含碳的關(guān)鍵部門。③2012 年,黃河流域各省區(qū)均為凈碳轉(zhuǎn)入地區(qū);2017 年,除河南省、陜西省、四川省之外,其他省區(qū)依然是凈碳轉(zhuǎn)入地區(qū);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山東省凈碳轉(zhuǎn)入量最多,2012—2017年為增長趨勢。④黃河流域9 省區(qū)隱含碳轉(zhuǎn)移具有明顯的地理鄰近效應(yīng),向其輸入隱含碳省區(qū)主要是區(qū)域內(nèi)部或周邊鄰近省區(qū),黃河流域輸出隱含碳較大的地區(qū)具有產(chǎn)業(yè)互補性。⑤黃河流域各省區(qū)域合作減排后,可以減小貿(mào)易碳排放的影響,尤其對陜西省受益程度最大,而青海省、四川省、山東省的獲益程度最小。
4.2 政策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結(jié)論,為促進黃河流域?qū)崿F(xiàn)高質(zhì)量發(fā)展和低碳減排提出以下政策啟示:①由于資源能源的差異和地區(qū)分工的不同,黃河流域各省區(qū)尤其是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生產(chǎn)側(cè)碳排放遠大于消費側(cè)碳排放,它們通過向全國各地提供能源產(chǎn)品導(dǎo)致大量隱含碳輸入。如果按照生產(chǎn)者責(zé)任制定減排政策則有失公平原則,因此應(yīng)同時考慮生產(chǎn)者責(zé)任原則和消費者責(zé)任原則,促進共同減排的公平性,適當(dāng)減輕能源地區(qū)的減排責(zé)任。②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的能源工業(yè)是調(diào)出隱含碳最大的產(chǎn)業(yè),其他省份應(yīng)多向此行業(yè)提供節(jié)能減排技術(shù),從隱含碳排放源頭控制其轉(zhuǎn)移,同時及時舍棄附加值低、耗能高的產(chǎn)業(yè)。③黃河流域各省區(qū)在向其他省區(qū)輸出大量能源產(chǎn)品來供應(yīng)其他依賴資源型城市發(fā)展的同時,也引致了隱含碳的大量流入,加重了黃河流域的減排壓力。因此,對于能源需求量大,消費水平高的城市應(yīng)改善能源消費結(jié)構(gòu),提高能源利用率,多使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從而減小能源供應(yīng)省區(qū)隱含碳輸入;對于提供資源而產(chǎn)生大量隱含碳的山西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等地區(qū),在發(fā)展資源優(yōu)勢產(chǎn)業(yè)的同時要引進脫碳技術(shù),注重低碳開采,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提高能源利用效率。④加強黃河流域區(qū)域內(nèi)的合作減排。黃河流域9 省區(qū)間貿(mào)易密切,合作減排可促進區(qū)域內(nèi)人員、資金、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流動,相比于各省區(qū)單獨減排更具優(yōu)勢。
——山東省濟寧市老年大學(xué)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