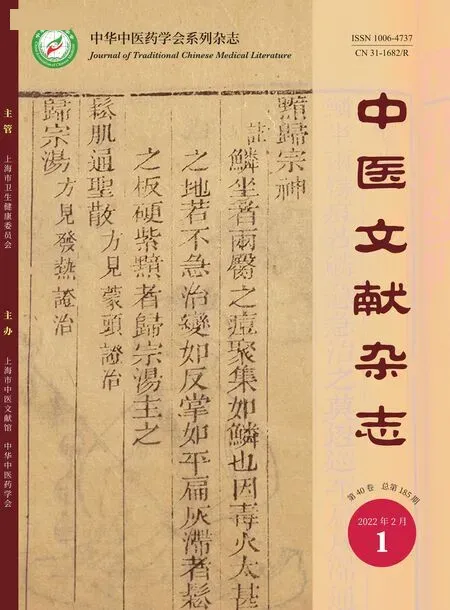淺析陳士鐸辨治痢疾思路及特色
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301617) 馮進龍 劉 毅
痢疾多發于夏秋季節,是常見病、多發病,或有一定的傳染性[1],其涉及西醫學的細菌性痢疾、潰瘍性結腸炎、阿米巴痢疾等多種疾病[2],以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膿血為主要表現[3]。《黃帝內經》最早描述了痢疾的主要癥狀為“腹痛”“便血”“下白沫”“下膿血”等,并指出病因多為“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難經》提到,“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后重”,從臟腑角度論述了痢疾的病因及表現。《金匱要略》則以“下利”統稱各種泄瀉、痢疾之病,不僅描述了下利的癥狀,還明確了治法方藥,如以白頭翁湯清腸解毒治熱痢,以桃花湯溫中澀腸治虛寒痢等,為后世痢疾的診療提供了主要依據。
現代醫學治療痢疾主要為抗生素和補液等[4],然而抗生素在一定程度上會產生耐藥性,且使用時間越長耐藥性愈發明顯[5]。中醫治療痢疾在減輕不良反應、縮短病程方面存在一定優勢[6]。陳士鐸在《辨證錄》中專設痢疾一門,其師從仲景旁參諸家,結合自己對五行生克等理論的認識,對痢疾的病因病機、臨床表現及治療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臨床療效顯著,對現代治療痢疾有一定啟迪和指導作用,現總結如下。
辨證特色
1.從因論治,獨重濕熱
中醫對痢疾從病因分類有風痢、氣痢、熱痢、疫痢、冷痢等[8]。張代釗認為,痢疾在初期常兼有表癥,尤其是疫痢及熱痢初期表證尤為明顯,故在此期應以解表為主,只要表證得解則其全部癥狀皆可隨之而去,方用人參敗毒散或葛根芩連湯[9]。林萬和依據中醫四診八綱的診斷法則,提出“審病因、明時令、究癥狀、重脈象、分證候、定證型”的臨床診痢概要[10]。

2.濕熱為重,臟腑有別
痢疾的常見病因有外感暑濕、疫毒;嗜食肥甘,釀生濕熱;脾胃損傷,濕熱內生等[7]。陳氏論述痢疾發病是由于肝克脾、胃火得濕、膀胱熱結、濕熱積脾、腎醉于酒等,病位或在臟或在腑,而病邪為濕熱,由各臟腑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濕熱,治療亦有區別。人有腹痛作瀉,變為痢疾,痢下宛如魚凍,久則紅白相間,陳氏認為此乃肝克脾土,治法急平其肝氣之怒,少佐祛邪之藥,脾胃之土自安,所以痢能自止。重用白芍、當歸、梔子以養肝平肝,重用車前子以祛邪。另案載,人有下痢晝夜七八十行,膿血黏稠,大煩渴不解,陳氏認為此為膀胱熱結水不化氣,盡趨于大腸而出,藥用豬苓、茯苓、黃芩以開膀胱之結,分消大腸之積水,又加訶子、地榆以止血水,通中有塞,塞中有和,而奏神效。人有貪酒好飲,日積月累,濕熱內積,變生痢疾,雖無崩奔之狀然溏鶩之苦終年不愈,陳氏認為此證濕熱困脾為標,實乃腎氣不足,腎醉于酒而作痢,治宜補腎健脾,分消濕熱,兼解酒毒。
3.開創新知,瘀血致痢
古之論痢疾,或認為外感暑濕、疫毒,或認為內因食積、疫毒所致,而從瘀血論治者少之又少。劉完素認為濕熱邪氣壅滯腸腑導致氣血不行進而引起下痢膿血,提出“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后重自除”的治法。陳氏在《辨證玉函》痢疾篇提出痢疾有陰陽之分,皆為濕熱所致,陽痢火重而濕輕,主要癥狀為起病急驟,便血腹痛,里急后重,噤口等。陰痢火輕而濕重,主要癥狀為腹不痛,以手按之則快,無急迫之感,能食,無便血,白痢,反復發作,遷延不愈等。而在《辨證錄》痢疾門中指出瘀血也可致痢,并強調了“食之后復加疾走,或飲酒之余更多叫號,或毆傷忍痛,或跌磕耐疼,或大怒而氣無可泄,或遇郁而愁無可解,或餐燔炙之太多,或受訶責之非分,皆能致瘀而成痢”。“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如體內產生瘀血則導致氣機不利,久之致使脾不得升提水谷精微,胃不得降瀉污垢糟粕,中焦氣機升降失常,導致日久瀉痢。故瘀血致痢臨床表現多久痢不止,日夜數十行,水谷精微下流,故下如清涕,食漸減少,內有紫黑血絲,脈沉細弦促。陳氏治法以活血化瘀為主,梳理氣機為輔,方用消瘀神丹或分瘀湯,方中乳香、沒藥、桃仁活血化瘀,兼木香、檳榔行氣利水,瘀消氣行則痢止,并提示痢久不愈者,可用消瘀神丹下其瘀血。
用藥特色
1.補澀兼施,以補為主
陳氏認為,遷延日久之痢疾應當用止法,醫者不可偏執“痢無止法”一說,而畏用止法,延誤病情,且重用補虛兼以溫澀而止痢,根據病情的具體情況,不拘于早晚,當用則用。人有下痢純血,色如陳腐屋漏之狀,肛門大開,不能收閉,面色反覺紅潤,唇似朱涂,該案癥雖見死象,而氣猶未絕,有可續之機。陳氏認為凡下痢純紅,即應用補陰兼以固澀,因人執“痢無止法”動用攻邪逐穢之劑,導致病情延誤至此,正是陽在上而陰沉下之顯征,陽宜降而反升,陰宜升而反降,陰陽兩不相交,死證顯現。治法急救其陰以引陽氣下降,兼補其陽,以提其陰氣之上升,方用補陰升提湯,方中重用人參、熟地、山茱萸、白芍等補虛的同時又配以五味子、訶子、山藥等收斂固澀。另一方更是芡實用至一兩,補澀兼施,以補為主。陳氏還指出,如服藥后痢疾之癥同前則乃陰以絕陽不能相交之死證,不必再服。
筆者統計了陳氏《辨證錄》痢疾門方劑共25首,使用藥物達49種。陳氏治療痢疾重視補法且重用補虛之藥,使用補虛藥達63次,占總數的39%,其最常用的補虛藥為白芍、甘草、人參、當歸,其中白芍用量多為二兩至三兩。陳氏對收斂固澀藥的使用頻數占比最少,只有5%,似乎不值一提。然筆者以為,其在治療痢疾的過程中突破前人“痢無止法”之說而提出該用止時亦用止法一說,值得重視。在重用補虛的同時又應當遵循“急則治其標”的原則,配伍收斂固澀藥以防其洞瀉過度,虛不受補。補澀兼施,以補為主,為日久痢疾之治法。痢疾初期,不宜使用補澀,以免閉門留寇,導致病情遷延不愈,故前人云“痢疾不怕當頭下”“痢無止法”。
2.重視理氣,納清排濁
濕熱初期當以分消濕熱、祛邪為主,納清排濁,切勿補澀。 《靈樞·針解》云“濁氣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氣上注于肺,濁溜于腸胃”,飲食入胃化生水谷精微當上輸于肺,而其所生糟粕當下歸于腸腑,納清有序,排濁有度。若濕熱作痢,胃腸氣機紊亂,當升不升當降不降,小腸做脹,里急后重。故陳氏治法重視疏理氣機,使脾胃升降有序,納清排濁,分消濕熱。“人有先瀉后痢,腹中疼痛,里急后重,口渴欲飲,小便艱澀,小腸做脹”,陳氏斷為濕熱之盛,治當分解濕熱,使糟粕穢濁趨于大腸以便排出,水谷精微歸于小腸方使吸收,不必用澀藥以止痢。其藥用車前子一兩以利水滲濕,用厚樸、枳殼、檳榔三味以梳理氣機,逐濁歸清。陳氏在分解濕熱利小便以實大便時,尤善使用車前子,且重視理氣。陳氏納清排濁的專藥當屬車前子,認為車前子“功專利水,通尿管最神,止淋瀝泄瀉,能閉精竅,祛風熱,善消赤目”,輕則用到二三錢,重則用至一兩。
筆者梳理了陳氏治療痢疾初期的13首方劑,以探究用藥規律,發現陳氏在此階段重視理氣,理氣藥物每方中使用二到四味,以三味為多,且里急后重的情況越重則理氣藥物的使用藥味及藥量也會略大,對于理氣藥物的使用劑量一般不會超過三錢。
3.五行生克,臟腑配藥
痢疾的病位責之腸腑,涉及脾、胃、腎、肝,尤以脾為主要;病邪多見濕、熱、暑熱、氣虛、陰虛、瘀血,尤以濕、熱為關鍵[11]。陳氏《辨證錄》認為痢疾的起因、發展涉及多個臟腑,且依據五行生克理論,分臟腑論處用藥,療效甚佳。夏秋之間,腹痛作瀉,紅白相間,陳氏斷為肝克脾土,夏秋之間肝遇涼風,脾受暑熱,肝激成怒,克土更甚,遂腹痛作瀉,瀉久糟粕已盡,脾乃傳肝木之氣于腎,腎見其子氣郁,乃相助而作惡,其氣必傷,肝不藏血而見紅,腎不藏精而見白,故瀉下紅白。方用平肝止痢湯,白芍、當歸、梔子以平肝疏肝,車前子以利水止瀉,枳殼、甘草以補脾理脾,使肝不能克伐脾。唯不用入腎藥,是痢之來始于肝,痢之成本于腎,平肝則肝氣緩,肝緩而腎氣亦平,故不用入腎藥。此案痢疾因肝克脾,后因肝木過急,腎母來救,病變中心在肝,故其配伍用藥入肝為主,佐以入脾治其瀉痢以治標,腎救肝子為一時之急,而其本不虧故不用入腎之藥。可見陳氏處方用藥有輕重緩急,標本兼治,配伍精當。
綜上,陳士鐸對痢疾的辨證分為暴痢、久痢,辨明陰陽寒熱虛實。其認為痢疾暴起急癥多由于濕熱所致,而濕熱所犯具體臟腑當為辨證關鍵,在腸腑多用車前子、黃連、大黃以分解濕熱,在脾多用茯苓、白術、陳皮以健脾利濕清熱,在肝多用白芍、當歸、檳榔疏理氣機,排解濕熱,緩急止痛;久痢則多辨為陰傷陽脫,主要用人參、熟地、山茱萸、山藥等急救其陰,引陽下降,兼補其陽,使陰陽相交,且兼顧收斂固澀,納清以排濁,養陰泄熱、止血止痢共進,不但清腸利濕,而且調氣和血,既無損臟腑之過,又無留邪之弊。其辨治痢疾的經驗值得同道借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