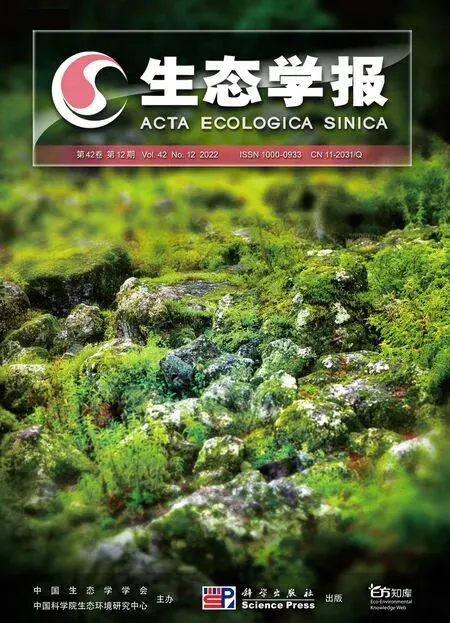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耦合協調的動態演化
——以新疆阿勒泰地區為例
羅萬云,王福博,戎銘倩
1 新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烏魯木齊 830046 2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西安 710061 3 新疆創新管理研究中心, 烏魯木齊 830046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作為主體功能區中的“限制開發區”,承擔著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以及生物多樣性等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責任。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建立在提高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的同時,卻帶來了生態與經濟社會系統的矛盾[1]:一方面,中央財政資金對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作為限制開發區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需要服從主體功能目標而受到限制,這種結果并非是中央政府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未來期待。因此,甄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經濟-社會(Ecological-economic-social,EES)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關鍵因子,深入揭示EES系統耦合協調水平與各系統間的互動關系,對解決生態與經濟社會的矛盾,推動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19世紀末,英國學者霍華德率先提出了“田園城市”的構想[2],標志著人類開始認識到生態與環境-經濟-資源系統的共軛體系。之后,著名學者Norgaard提出,耦合協調發展理論強調生態系統與經濟社會系統的共同發展[3]。Grossman和Krueger發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互斥互競的關系,即環境狀況并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一直變壞,當經濟增長到一定水平后,環境就會逐漸改善,俗稱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CK)[4]。后來,意大利學者Brown等從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相互作用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提出了可用于評估的生態技術、不可再生投資等指標[5]。Martínez等選擇全球沿海地區為研究對象,對生態、經濟、社會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6]。后來,數據包絡方法[7]和生態足跡法[8]等定量模型逐漸被應用在生態、經濟和社會協調的研究之中。實踐層面,聯合國在“2015年發展議程”中提出“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個方面的17個目標和169個子目標”[9],旨在建立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國內一些學者在國外成果的基礎之上,開始了本地化探索。理論層面,著名學者馬世俊和王如松率先提出“社會-經濟-自然符合生態系統”理論,強調社會、經濟、自然系統的整體性[10]。后來,吳傳鈞院士提出人地關系學說[11],進一步解釋了三大系統的互動機理。相比理論層面的突破,實證研究也逐漸興起,概括起來具有以下特點:第一,研究區域逐漸由國家或者省域的大尺度[12]向微觀小尺度轉換[13]。第二,方法層面逐漸由耦合協調評價模型[14]向多個方法交叉綜合應用轉換[15]。第三,靜態耦合向動態耦合的互動切換[16]。已有成果為本研究構建EES系統指標評價體系以及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的選擇提供有益借鑒,但也存在有待完善之處。例如:如何將生態、經濟、社會三大系統納入到一個整體框架下進行實證,討論耦合協調程度的動態演化趨勢?此外,如何突破現有研究范圍的經驗缺失,選擇承擔著更多“生態功能”和“生產功能”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考察其EES系統耦合機理?
截止到2021年,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有25個,分布在中西部地區的有16個,占到國土總面積的30.1%[17]。相比沿海地區,西部地區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不僅生態環境脆弱,而且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共服務滯后。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并非是淺嘗輒止地追求生態保護,而是寄希望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建設能實現生態、經濟、社會之間的平衡和充分發展。阿爾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態功能區作為西部地區最為重要的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之一,過去的幾十年里人類行為造成的生態、經濟、社會的矛盾引起了廣泛關注。論文以此為研究對象,構建EES系統評價體系,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剪刀差方法、耦合度模型以及VAR模型對EES系統耦合協調水平以及動態演化趨勢進行實證研究,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出臺更加有效的治理政策提供可靠的理論借鑒。
1 研究區域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阿爾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態功能區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區,區域行政主體為阿勒泰地區及兵團第十師(圖1),包括阿勒泰市、布爾津縣、富蘊縣、福海縣、哈巴河縣、青河縣、吉木乃縣、北屯市(下面統稱六縣二市),東部與蒙古國接壤,西部、北部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交界,總面積11.80萬km2,占全疆面積的7.2%。2007—2019年阿勒泰地區總人口由64.51萬人增加到65.95萬人,GDP從99.28億元增加到284.09億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由4157元增加到14392元,三次產業結構從21.98∶45.86∶32.16調整為16.7∶36.1∶47.2。阿勒泰地區大小河流50余條,是額爾齊斯河的發源地,境內森林、草地、冰川發育完整,2010年被明確劃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水源涵養型保護區。2014年國家林業局頒布的《阿爾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與建設規劃(2014—2020年)》(以下簡稱“保護規劃”)明確提出,增強額爾齊斯河和烏倫古河流域的水源涵養能力,建設西北干旱地區重要的生態文明示范區。

圖1 研究區示意圖Fig.1 Distribution of study area
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2008—2020年《阿勒泰地區統計年鑒》、《中國縣域統計年鑒》、《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師北屯市統計年鑒》、《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以及阿勒泰地區各縣市統計公報等資料,缺失數據通過SPSS 20.0軟件采用臨近點均值法補齊。耕地面積、林地面積和草地面積通過ArcMap 10.8軟件對2007—2019年土地利用數據計算得出,柵格分辨率為30m,數據來源為質量較好的Landsat影像(所有影像的軌道號均為141- 146/28- 32),該數據來自美國地質調查局(http:glovis.usgs.gov)。

正向指標:
(1)
負項指標:
(2)
式中,Hkij、hkij分別代表無量綱化前、后第k年第i個縣市第j個指標數值。
2 EES系統評價體系與模型構建
2.1 EES系統結構及互動關系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具有限制性色彩,生態與經濟社會之間產生了較大沖突,使得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陷于兩難境地[18]。可見EES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是國家生態功能區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鍵[19]。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系統作為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發展的基礎,為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提供土地、能源等資源,分解吸收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剩余物質和排放物(圖2)。但是生態系統有限的承載能力,又會阻礙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發展:一方面,隨著經濟系統的發展,經濟系統對資源的需求將不斷擴大,進而帶來資源的過渡消耗與環境惡化;另一方面,社會系統中人類的某些社會活動,又會給生態環境帶來負面影響。此外,良好的社會環境是經濟系統高效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反過來,經濟系統的高效可持續發展必然促進社會發展,改善民生,推動精神文明建設,進而促進社會系統對生態系統的修復與保護。綜上,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EES系統的發展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復雜耦合過程,三系統相互制約,協同共生,如果單一方面追求某個系統的發展,將會導致其他系統的失衡。

圖2 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結構與互動關系Fig.2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system in 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2.2 EES系統評價體系構建
2010年國務院正式下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按照不同國土空間的功能,分別劃分為優先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20],后兩類區域最大特征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基本公共服務薄弱,保障基礎較差,生態脆弱,但環境資源豐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屬于限制開發區,與其他功能區相比較,如果不采取差別化和“傾斜”政策照顧,很容易出現兩種極端,一是生態功能區為了獲得短時間的經濟增長與民生福祉的改善不惜破壞生態環境;二是經濟水平以及公共服務維持在低水平的生態環境改善。前者會使得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續道路,而后者會使得原本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進一步加劇,這一結果并非是中央政府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未來期待。
中央政府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定位并非是淺嘗輒止的保護與發展[21],而是以維護和改善區域重要生態功能為目標,調整區域社會經濟布局,進一步減少人類行為造成的負外部性,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將生態保護與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群眾生活水平提高有機結合起來,實現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本研究認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EES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更加側重生態環境改善,在提高生態基礎(森林、草地等生態要素好轉)的同時,推動經濟系統的結構優化(第三產業發展,生產效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鞏固民生與社會基礎(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改善),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減輕經濟社會發展對生態系統造成的壓力與脅迫,實現EES系統的協調發展。據此,本研究參考相關復合系統耦合協調的研究[15,22],選取3個宏觀系統,6個一級指標,17個二級指標,構建符合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特征的EES系統評價體系(表1),運用熵權法計算出指標權重,能較為全面地反映EES系統的發展水平。

表1 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評價體系Table 1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system
2.3 研究方法
2.3.1耦合協調模型
為了更好地反映阿勒泰地區EES系統間相互作用、相互脅迫的動態演化進程。本研究采用耦合協調模型對阿勒泰地區EES系統的耦合協調水平進行定量評價。但是,在計算耦合度C值時,國內外學者所采用的方法存在較大差異,同時存在一定使用誤區以及表述不當等問題。因此,本研究采用從曉男[23]糾正后的耦合度模型來計算EES系統的耦合度C值。具體步驟如下:
計算耦合度C值。
(2)

(3)
式中,U1、U2、U3分別表示同一縣市、同一年份不同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C為耦合度(0≤C≤1),C越大表示耦合度越高,系統間的關聯越明顯。
計算耦合協調度D值。
T=αU1+βU2+γU3
(4)
(5)
式中,D表示表示同一縣市、同一年份的EES系統的耦合協調度,T為綜合發展值,其中α=β=γ=1/3[24],并參照熊曦等[25]的劃分標準,將阿勒泰地區EES系統的耦合協調度D值劃分為極度失調、嚴重失調、中度失調等十個亞類,失調衰退區間、過渡調和區間以及協調發展區間三大區間(表2)。

表2 耦合協調類型劃分表Table 2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partition table
2.3.2剪刀差方法
在耦合協調模型的基礎上,本研究采用剪刀差進一步反映阿勒泰地區EES系統間的演化速率差異。剪刀差最初主要用來衡量工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換,后來被用來反映兩個系統之間演化速率的差異[26],通過分析系統之間的變化速率在二維平面上構成的投影軌跡的夾角θ,來判斷和分析EES系統之間演化趨勢的差異。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演化速率V(x)、V(y)和V(z)可通過其曲線的切線斜率F′(x)、F′(y)和F′(z)來表示:
(6)
兩系統間變化速率的剪刀差值θ可按照式(7)、式(8)、式(9)計算:
(7)
(8)
(9)
式中,θ是系統之間在給定時刻的兩切線夾角,θ越小,表明兩系統間的變化趨勢差異越小,反之,則越大。
2.3.3EES系統的耦合度模型
為了更好探究兩系統之間的耦合關系,本研究采用耦合度模型進一步分析。耦合度模型是根據兩系統各自的耦合元素產生相互影響的程度,來判定兩者之間的協調關系及表現[15]。若把兩系統作為一個整體考慮,假定這個系統只有F(x)與F(y)兩個元素,按照貝塔蘭菲的一般系統論[27],當系統內各元素協調時,整個系統也是協調發展的,整個系統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作是V(x)與V(y)的函數,所以有V=f(V(x),V(y))。同時系統之間的影響又具有周期性,所以可以用兩維平面[V(x),V(y)]來描述V。即V(x)與V(y)的夾角β滿足:tanβ=V(x)/V(y),即β=arctanV(x)/V(y),根據β的取值,可以判定整個系統的演化狀態以及F(x)與F(y)協調發展的動態耦合程度。參照馬亞亞等[15]的分類標準,將阿勒泰地區EES系統耦合度水平劃分為低級協調共生階段、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和諧發展階段等六大發展階段,Ⅰ、Ⅱ、Ⅲ、Ⅳ四大區域(表3)。

表3 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耦合度類型劃分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degree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system
2.3.4向量自回歸(VAR)模型
VAR模型被國內外學者[28]廣泛用于時間序列分析,主要用于研究無約束下聯合內生變量之間的交互影響。本研究采用VAR模型對各系統與耦合協調度的互動效應和貢獻程度進行分析,模型如下:
Yt=C+Φ1Yt-1+Φ2Yt-2+…+ΦpYt-p+εt
(9)
式中,Yt表示n×1維的向量時間序列,C表示n×1維的常數向量,Φi(i=1,2,…,p)表示n×n維的自回歸系數矩陣,n表示時間序列變量個數,t表示年份,p表示VAR模型階數,εt代表n×1維的向量白噪聲。
3 結果與分析
3.1 EES系統耦合協調水平的時間演進分析
3.1.1EES系統耦合協調水平
2007—2019年,阿勒泰地區整體耦合協調水平呈現上升趨勢,由2007年的中度失調(0.271)逐漸調整到輕度失調狀態(0.371),而中度失調的持續時間為2007—2010年,2011年整體耦合協調水平進入輕度失調狀態,一直持續到2019年。
從各縣市的耦合協調類型來看(表4),EES系統耦合協調水平并沒有呈現出與整體趨勢一致的態勢,其中阿勒泰市由輕度失調(0.362)逐漸上升為瀕臨失調(0.453),布爾津縣由輕度失調(0.308)逐漸上升為瀕臨失調(0.426)。富蘊縣由中度失調(0.284)逐漸上升到輕度失調(0.364),但是初期的耦合協調水平存在較大波動性,2010年后其維持在輕度失調狀態。福海縣的耦合協調水平并未發生較大幅度變化,但是從具體得分數值來看,從2007年的0.229上升到2019年的0.299。哈巴河縣初期表現(2007—2008年)為波動上升,但是到2009年之后處于輕度失調狀態,并且哈巴河縣(2008年)進入輕度失調的時間明顯早于整體水平(2010年)。值得注意的是,青河縣、吉木乃縣、北屯市雖從中度失調進入到輕度失調狀態,但是進入時間均依次滯后于整體水平。

表4 2007—2019年阿勒泰地區各縣市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耦合協調度Tabl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system in counties and cities of Altay region from 2007 to 2019
3.1.2EES系統綜合發展水平
2007—2019年生態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呈現略微下降趨勢(圖3),由2007年的最高點(0.115)下降到2019年的最低點(0.093),略微下降這一趨勢可能的原因是:阿勒泰地區是以犧牲生態環境質量為代價來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圖3 2007—2019年阿勒泰地區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發展水平Fig.3 The level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system development in Altay region from 2007 to 2019
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整體呈現出穩步上升趨勢。2007—2019年經濟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大體上呈“增長-波動下滑-回升”的發展趨勢,經濟系統由2007年的0.057持續上升到2017年的0.156,在2018年呈現略微下降之后在2019年達到峰值(0.170),拉動其達到頂峰的是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其權重最高達12.49%,其次是地區GDP(7.75%)和人均固定資產投資(7.38%),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自2007年以來阿勒泰地區人民消費水平顯著提高,消費與需求的增加正逐漸推動阿勒泰地區經濟系統穩步發展,而2018年經濟系統略微下降主要是由結構優化準則層中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下降所致。
社會系統總體上呈現持續上升的發展趨勢,由2007年的0.077上升到2019的0.205,年均增長率為8.87%,社會系統的持續增長主要源于公共基礎和民生改善準則層,人均財政支出(年均增長率為25.77%)和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為20.40%)是促進社會系統增長的核心因子。此外,每100人擁有床位數量(年均增長率為7.93%)也是社會系統持續上升過程中的重要驅動因子。
2007—2019年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社會系統的發展水平呈現較為明顯的“X”型變動趨勢,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呈現持續上升趨勢,而生態系統一直處于低水平且呈現略微下降趨勢。2007—2011年,生態系統水平高于其他兩個系統,而社會系統與經濟系統在2012年超過生態系統后呈現持續上升趨勢。
3.2 EES系統間演化速率的剪刀差及耦合度分析
3.2.1EES系統間演化速率的剪刀差
為了進一步探究各系統演化速率的差異,本研究采用剪刀差方法對EES系統相互之間的演化過程進行分析(圖4)。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演化速率的剪刀差在2008—2013年呈現穩步上升趨勢,但到2013后呈現波動下降趨勢,并在2019年呈現快速上升趨勢。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演化速率的剪刀差呈現出先平緩上升后倒“U”的趨勢,于2017年以后呈現快速下降趨勢。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演化速率的剪刀差呈現出左低右高的“M”型波動趨勢。EES系統相互之間的演化過程大體可以分為3個階段,即2007—2013年的波動上升、2013—2014年的快速下降、2014—2019年的劇烈波動。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演化速率的剪刀差在2014年以后突然增大,并出現劇烈波動,而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演化速率的剪刀差趨于穩定態勢。從波動趨勢來看,2014年后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經歷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并且這一劇烈變化逐漸影響了生態系統,而生態系統演化遞減趨勢在2015年以后的逐漸上升則進一步印證了這一結論。

圖4 2008—2019年阿勒泰地區生態-經濟-社會系統演化速率的剪刀差變化趨勢Fig.4 The changing trend of scissors difference in the evolution rate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system in Altay region from 2008 to 2019
3.2.2EES系統耦合度分析
2008—2015年,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耦合角度在共同發展階段(45°<β≤90°)波動,即經濟系統的演化速率逐漸加快,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開始相互影響,社會系統對經濟系統發展的約束與限制矛盾開始顯露,但尚不突出(圖5)。在2016—2018年間出現了短期調整,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耦合角度由Ⅱ區域向Ⅰ區域過渡,耦合度水平從共同發展階段下降到低級協調共生階段(-90°<β≤0°),說明社會系統的演化速率逐漸加快,進而超越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對經濟系統發展的約束與限制的矛盾得到緩和。2017年以后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耦合角度出現先快速下降又快速上升的大幅度波動,在2018年到達谷底,這可能是經濟系統的劇烈波動所致。從具體指標來看,2018年阿勒泰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呈現快速下滑趨勢,全年完成投資90.17億元,比上年下降39.6%,從產業分類來看,第一產業下降39.6%和第三產業下降46.5%,阿勒泰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不足與新疆整體發展水平具有較高一致性,同年新疆固定資產投資下降25.2%,第一產業下降42.1%、第三產業下降32.6%,經濟系統對社會系統發展的約束與限制矛盾逐漸減弱。

圖5 2008—2019年阿勒泰地區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耦合度演化趨勢Fig.5 The evolution trend of coupling degree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system in Altay region from 2008 to 2019
2008—2017年,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耦合度處于低級協調共生階段(角度范圍值為-90°<β≤0°),說明生態系統發展緩慢,且基本不受經濟系統的限制和約束,經濟系統發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也幾乎為零。直到2018年,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耦合度由Ⅰ區域上升到Ⅱ區域,角度范圍值相應調整到45°<β≤90°(共同發展階段),說明生態系統的演化速率逐漸加快,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開始相互影響,經濟系統對生態系統發展的約束與限制矛盾開始顯露,但尚不突出。2019年,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耦合度再次回到低級共生階段,經濟系統對生態系統發展的約束與限制有所減弱。而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耦合度一直處于低級協調共生階段,說明生態系統發展緩慢,且基本不受社會系統的限制和約束,社會發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也幾乎為零。
從EES系統耦合度整體演變趨勢來看,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耦合度趨于穩定(一直處于低級協調共生階段),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耦合度以及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耦合度,呈現先穩定后大幅波動的趨勢。而這一現象可能與2014年頒布的“保護規劃”有較為緊密的聯系,2014年后,阿勒泰地區開始加大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促使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進行調整,而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耦合度的此消彼長的關系也進一步說明EES系統的耦合度呈向好趨勢,復合系統呈現出由無序到有序的初始過渡。
3.3 EES系統耦合協調的脈沖響應分析
3.3.1構建脈沖效應函數
首先,在進行檢驗之前,先對時間序列數據取對數,來消除異方差的影響。再對模型中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并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差分處理,進而保證數據的平穩性(表5)。其次,確定最優滯后階數(1階)以及格蘭杰因果檢驗(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具有因果關系)。再次,對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經檢驗模型是穩定的)。最后,構建耦合協調度D值對生態系統、經濟系統以及社會系統的脈沖響應函數(圖6)。

表5 平穩性檢驗Table 5 Stationarity test
3.3.2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可以對相關變量的動態關系進行分析,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判斷出EES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對三系統沖擊的動態響應過程(圖6)。EES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對經濟系統的響應呈現“上升-略微下降-略微上升”的波動趨勢,前3期逐漸加強,第4期以后逐漸減弱,呈現略微下降趨勢,到第8期,響應開始略微增強。EES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對社會系統的響應在第2期達到最低值(-0.002),此后一直處于持續上升趨勢,呈現“下降-上升”的 “U”型趨勢。而對生態系統的響應同樣在第2期達到極值(0.008),此后,正向響應轉向負向響應,一直持續到第15期(-0.133)。整體來看,EES系統耦合協調度在第3期之前主要受經濟系統、生態系統的影響較為顯著,而第3期后對社會系統響應力度逐漸增強,并且在第7期超越經濟系統。從長期來看,EES系統耦合協調度對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響應具有相似趨勢,而對生態系統則具有顯著相反的趨勢。

圖6 耦合協調度對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的脈沖響應 Fig.6 Impulse respons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o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為進一步明晰阿勒泰地區各系統發展水平對EES系統耦合協調度的貢獻程度,本研究在脈沖響應函數的基礎上對EES系統耦合協調度進行方差分解(圖7)。第1期三系統對阿勒泰地區EES系統耦合協調度的貢獻度存在顯著差異,社會系統的貢獻度高達67%,其次是經濟系統貢獻度為26%,生態系統貢獻僅為6%。初期(第1期到第3期),經濟系統對EES系統耦合協調度的貢獻程度快速提高,達到63%,此后貢獻程度處于持續緩慢下降的過程,直至第15期(10%),整體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生態系統對EES系統耦合協調度的貢獻度由第1期的6%持續上升到第2期的14%,到第3期之后趨于快速上升趨勢,在第6期生態系統的貢獻度明顯超越了經濟系統,可以得出生態系統的貢獻度明顯強于經濟系統。而社會系統的貢獻度在第1—4期呈現緩慢下降趨勢,自第4期以后,社會系統的貢獻度穩步上升,在第11期超過經濟系統。整體來看,各系統對阿勒泰地區EES系統耦合協調度的貢獻度存在明顯的前后階段差異,初期的主要是社會系統與經濟系統驅動,到了后期逐漸向生態系統過渡。

圖7 耦合協調度D值的方差分解Fig.7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 value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首先,本研究通過對2007—2019年EES系統耦合協調的動態演化趨勢進行分析,發現阿勒泰地區EES系統耦合協調水平整體呈現上升趨勢,由2007年的中度失調(0.256)逐漸過渡到輕度失調狀態(0.371),這一結論與徐潔等[29]得出國家生態功能區的生態系統質量在2000—2010年有所提升的客觀生態事實相符合。但是,在整體耦合協調水平提升的背景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還存在內部發展不均衡問題,例如:從EES系統內部趨勢變動來看,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呈現“X”型演化趨勢,生態系統在2007—2019年間變化幅度有限,而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發展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兩個系統在2012年超過生態系統,可能是過度強調人類主體在經濟-社會系統的中心地位所致;阿勒泰地區在“經濟建設為中心”政策推動下,通過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等經濟環節,實現了由資源到產品的價值轉換,尤其是在“十三五”期間阿勒泰地區憑借資源優勢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有色金屬、水電等資源性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其次,從EES系統間演化速率的剪刀差以及耦合度來看,阿勒泰地區在2014年以后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經歷了較大浮度的調整,并且這一劇烈變化逐漸影響了生態系統,例如:2015年后EES系統間演化速率的剪刀差與耦合度出現較大波動,尤其是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耦合度從低級協調共生階段向共同發展階段過渡。這一結論的原因可能是:2014年國家林業局頒布《阿爾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與建設規劃(2014—2020年)》,中央政府實施生態工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等措施取得了較大成效,符合李玥等[30]認為生態修復工程與EES系統具有緊密協同性的觀點。此外,本研究初步判斷生態修復工程的外部干預也會顯著影響EES系統的內部結構調整,尤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產生的反饋較為明顯,但這一結論還需要結合具體的生態保護工程建設加以考察和驗證。
再次,本研究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及方差分解判斷出三系統對阿勒泰地區耦合協調水平的貢獻具有明顯的前后階段差異,初期主要依靠社會系統與經濟系統驅動,后期逐漸向生態系統過渡,這一結論也符合著名學者葉俊[31]提出的系統狀態是由于漲落運動或隨機擾動在不停演變的這一觀點。然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與其他功能區具有顯著區別,即政策設計之初的本意是以提高生態環境質量,弱化經濟增長為前提,同時強調公共服務水平改善[32],通過干預物質交換、能量和信息流動,實現EES系統處于更高水平的耦合協調,由此進入一種良性循環過程。如圖7,三系統對耦合協調水平的貢獻并沒有呈現“協同性”,這也進一步印證了Li等[33]認為阿勒泰地區存在的“功能協同”障礙的觀點,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要想獲得高水平的系統穩定狀態,除了需要堅持樊影等[34]強調的山水林田湖生態系統各要素耦合協調以外,還需要在經濟層面構建一個行之有效的約束與激勵補償機制,實現三系統間的功能協同,一方面實現生態環境改善達到新高度,另一方面還需要注重經濟激勵與公共服務投入,扭轉地方政府長期在生態保護中形成的機會主義,避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陷入“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兩難困境。
最后,本研究重點在于關注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EES系統耦合協調水平以及動態演化趨勢,而中央政府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未來期待不僅僅局限在提供生態產品,還試圖運用多種組合政策達到區域發展以及減貧的目標。因此,以后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考慮構建基于服務與福祉的復合系統評價體系,考察長周期下不同空間尺度的動態演化特征,深入揭示耦合過程與傳導機制,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可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理論支撐。
4.2 結論
本研究構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EES系統評價體系,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剪刀差方法、耦合度模型以及VAR模型對2007—2019年阿勒泰地區EES系統耦合協調水平的動態演化趨勢進行分析。結果表明:
(1)2007—2019年阿勒泰地區整體耦合協調水平呈現上升趨勢,2011年阿勒泰地區EES耦合協調水平整體進入輕度失調狀態,并一直持續到2019年。
(2)2007—2019年阿勒泰地區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發展水平呈持續上升趨勢,而生態系統則呈現下降趨勢,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社會系統的發展水平呈現出較為明顯的“X”型變動趨勢。
(3)EES系統相互之間的演化過程可以分為3個階段,即2007—2013年的波動上升、2013—2014年的快速下降、2014—2019年的大幅波動。從EES系統耦合度的演變趨勢來看,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耦合度一直處于低級協調共生階段,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耦合度以及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耦合度,呈現先穩定后大幅波動的趨勢。
(4)2007—2019年阿勒泰地區各系統對EES系統耦合協調度的貢獻具有顯著的階段性差異,初期主要由社會系統、經濟系統驅動,后期生態系統的貢獻度不斷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