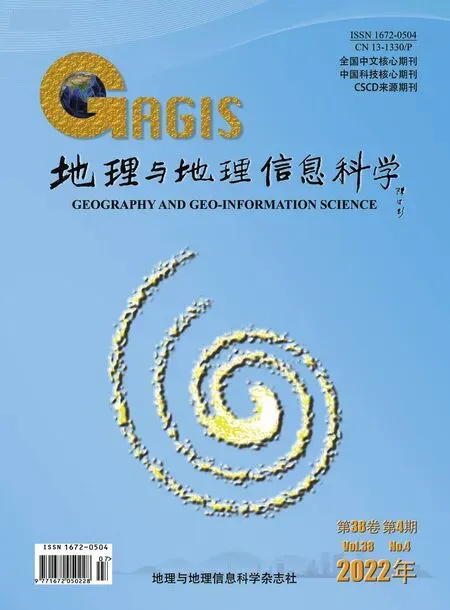地方依戀對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影響研究
周 曉 麗,唐 承 財
(1.長治學院歷史與旅游管理系,山西 長治 046000;2.山西省太行文化生態研究院,山西 長治 046000;3.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科學學院,北京 100024;4.北京旅游發展研究基地,北京100024)
0 引言
發展紅色旅游是創新、傳承與弘揚紅色文化的重要方式[1]。國際上革命遺址旅游與我國紅色旅游相對應,其依靠國家歷史標志物展現民族精神和國家歷史[2],有助于旅游者構建國家和民族認同[3];我國紅色旅游亦屬于革命遺址旅游,發展紅色旅游有助于堅定紅色文化自信、增強政黨和國家認同及推動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大量研究關注發展紅色旅游的積極社會和政治效應,亦證實了紅色旅游在傳播中國共產黨革命理念、展現其光輝歷史、實現旅游者政黨和國家認同教育等方面效應顯著[4,5]。
紅色旅游效應的發揮以紅色旅游市場的繁榮為前提,然而研究顯示,我國紅色旅游市場以黨員干部和團員學生為主體[6],普通群眾關注熱情不高,主動參與和重游意愿不強[7],且紅色旅游市場亦存在部分旅游者的非理性訴求,盲目追求紅色旅游的休閑性、娛樂性和趣味性,忽視紅色文化內涵,致使部分紅色景區規劃建設存在去紅色文化底蘊、突出娛樂氛圍營造的錯誤傾向,造成紅色文化資源的嚴重濫用,阻礙紅色旅游高質量發展。紅色旅游者的忠誠度有助于擴大紅色旅游的有效市場需求,而其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能夠有效促使其旅游訴求和行為回歸理性,助力紅色旅游高質量發展。因此,如何提高紅色旅游者的忠誠度并引導其踐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成為當前紅色旅游研究亟須關注的課題。
地方依戀作為地方理論的核心概念,有助于培育依戀主體的積極態度和行為,對提高旅游者忠誠度[8]、滿意度[9,10]和親環境行為傾向[11,12]等效應顯著。紅色旅游情境下的實證研究亦顯示,旅游者的情感依戀能夠顯著正向影響其環境責任行為[13],然而,將地方依戀理論整體應用于紅色旅游情境的相關研究較少。鑒于此,本研究在紅色旅游情境下,探討地方依戀對紅色旅游者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影響和作用機制,期望在理論上拓展地方依戀理論的應用情境,實踐上為我國紅色文化基因傳承及紅色旅游高質量發展提供依據。
1 文獻回顧與理論模型構建
1.1 地方依戀與紅色旅游忠誠度
1989年,Williams等最早提出地方依戀的概念,將地方依戀定義為人們與其居住地之間的情感聯結[14]。學者認同地方依戀是一個多維概念,但有二維[15]、三維[16]和四維[17]等之分。本研究借鑒Jorgensen等對地方依戀的三維劃分觀點[16],將旅游者對紅色旅游地的地方依戀分為地方依賴、地方認同和地方情感:1)紅色旅游情境下,地方依賴代表旅游者對紅色旅游地行為層面的功能依賴和行為忠誠,即部分紅色旅游體驗,如追憶敬仰革命英雄、悲痛、惋惜及憶苦思甜等,只有在紅色旅游地才能體會得如此深刻;2)地方認同代表旅游者認知層面的地方感,即旅游者對紅色革命精神(如革命英雄為國家利益犧牲自我等)的認同,為一種自我本體的表達和確認,從而對承載紅色文化記憶和紅色英雄事跡的目的地產生認知上的認同;3)地方情感則代表旅游者情感層面的感覺和情緒,紅色旅游感知有助于人們反思當下,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產生更大的奮斗動力等,這能給旅游者帶來更大的幸福與滿足感[3],使旅游者對紅色旅游地產生不同程度的熱愛。可見,地方依戀反映了旅游者對紅色旅游地行為、認知和情感層面的關系強度。
大量研究認為,旅游者忠誠度包括重游意愿和積極的口碑推薦意愿[18,19],且部分學者認為重游意愿包括其未來游覽其他同類型旅游目的地的行為意愿[19,20]。因此,本研究認為,紅色旅游者忠誠度包括旅游者積極推薦他人參觀游覽紅色旅游目的地的口碑意愿和未來重游本紅色旅游地及其他紅色旅游地的積極行為意愿。可見,旅游者的紅色旅游忠誠度能有效擴大紅色旅游市場需求,對繁榮紅色旅游市場具有重要意義。如上所述,地方依戀能影響旅游者在紅色旅游地的一系列態度和行為,非紅色旅游情境下的大量研究均證實地方依戀能有效提高旅游者忠誠度[8,9]。基于此,本研究認為地方依戀亦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的紅色旅游忠誠度,提出研究假設H1a-c:地方依戀(地方依賴、地方情感、地方認同)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
1.2 地方依戀與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
研究者普遍認為旅游者的負責任行為是以其行為或行動為基礎,強調旅游者為減少其行為對旅游業的負面影響,而采取的對旅游業多方面負責的旅游實踐方式[21,22]。當前,旅游者負責任行為研究主要聚焦于旅游者的生態、經濟和社會環境負責任行為[23,24]。例如,張朝枝依據遺產和遺產旅游的本質屬性,提出“遺產責任”的概念[25],在此基礎上,凌歡等提出旅游者的遺產負責任行為,將其界定為旅游者對遺產資源保護負責的行為[26]。依據旅游者行為或行動的實踐領域差異,旅游者的負責任行為涉及不同方面。
狹義的紅色文化資源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所形成的物質、精神、制度等資源的總和,蘊含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建設方式、政治綱領和文化追求,內化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基因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密碼[27]。紅色文化資源是目的地發展紅色旅游的重要資源客體,是目的地紅色基因、價值理念的外化[28],具有重要價值,旅游者的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有利于紅色文化資源的保護、傳承和合理利用。基于此,本研究認為,紅色旅游情境下,旅游者采取的對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的行為即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反映了旅游者為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紅色文化資源的負面影響,本著尊重、保護和學習的態度而非普通觀光游中的最大化享樂態度參觀凝視紅色文化資源,有助于促進旅游者在紅色旅游地的利益訴求和行為方式回歸理性,增強紅色旅游教育的實效性、公信力和紅色文化自信,亦有助于紅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地方依戀與旅游者環境負責任行為的關系得到了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11,12],本研究期望在紅色旅游情境下進一步探討地方依戀與旅游者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之間的關系,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2a-c:地方依戀(地方依賴、地方情感、地方認同)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的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
1.3 紅色精神共情的中介作用
共情最初源于德語einfuhlung一詞,表示人們將自己真實的心靈感受投射到所看到的事物和他人身上的一種現象[29],是個體對他人感受的一種情感體驗[30,31]。紅色精神共情源于旅游者對紅色旅游地宏大革命事件、艱辛革命歲月及紅色英雄革命精神的心靈理解和情感體驗,強調旅游者情感體驗中的認同感與替代參與感。在旅游地莊嚴肅穆的紅色氛圍下,借助對展品的凝視、儀式體驗等活動,旅游者能穿越時空,感受革命事件的宏大、革命年代的艱辛和英雄的奉獻等紅色精神,即紅色精神共情。如筆者曾在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偶遇一位老人,當聽到解說員講無名英雄事跡時,老人跪在碑林前,淚流滿面,久久不能平靜,此情此景即是其紅色精神共情。
依戀和共情的關系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周春秀等梳理了國內外關于“依戀和共情關系”的研究,發現多數學者認同依戀是共情的前因,爭議存在于影響程度和作用機制上[32]。關于共情的研究亦證實,共情具有強利他性[33],能影響消費者的一系列行為傾向,特別是親社會行為傾向[34]。研究顯示,自然共情是旅游者環境負責任行為的前因[35,36]。依據“共情—利他”假說,借由情景遷移,本研究認為,紅色精神共情在地方依戀影響旅游者的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中發揮中介作用,據此提出研究假設H3a-c:地方依戀(地方依賴、地方情感、地方認同)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紅色精神共情;H4:紅色精神共情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H5:紅色精神共情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
1.4 紅色教育感知的中介作用
紅色旅游具有發展經濟、教育旅游者、保護環境及扶貧等功能。紅色旅游的教育功能區別于其他旅游活動,主要體現在對旅游者的紅色教育上[37]。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發展紅色旅游的根本目的是進行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等紅色教育,紅色旅游是傳播紅色文化和主流價值觀的重要載體[38]。基于此,學者將旅游者紅色教育界定為以紅色旅游活動為載體而對旅游者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39],主要通過對與紅色旅游地有關的革命歷史、革命事跡和革命精神等的展示、宣說和弘揚,達到提高旅游者思想政治素養及其對政黨和國家認同的目的[4,5,40]。紅色教育感知即旅游者在紅色旅游地,通過參觀游覽革命遺址、聆聽紅色故事、瞻仰標志性建筑、觀看歷史照片和紀錄片、主動參與儀式體驗等方式,直觀感受、接受的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41]。紅色教育感知使旅游者獲益匪淺:在參觀紅色旅游景區的過程中,旅游者對我國的革命歷史、革命事跡和革命精神等有了更深刻的認知和理解,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認同感與依戀感也顯著增強[4]。這些認知與情感方面的變化,能夠有效增加旅游者對未來生活的熱情與信心,提升人們的幸福感,更加感恩和珍惜當下生活。“認知—情感—意動”理論模型[42,43]認為個體認知、情感、態度與行為密切相關,因此,本研究認為旅游者的紅色教育感知與紅色旅游態度和行為密切相關。已有研究發現地方依戀有助于促進自然教育感知[35],紅色教育感知有助于促進旅游者在紅色旅游地的親環境行為[37]。因此,為深入探討紅色教育感知在地方依戀影響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中的作用,提出研究假設H6a-c:地方依戀(地方依賴、地方情感、地方認同)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紅色教育感知;H7:紅色教育感知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H8:紅色教育感知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假設,本研究構建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模型Fig.1 Theoretical model
2 研究設計
2.1 案例地選取
山西長治的“抗戰圣地·紅色武鄉”擁有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如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八路軍文化園、王家峪八路軍總部舊址、百團大戰磚壁指揮部舊址、太行干部學院和太行少年軍校等,2017年2月,武鄉被評為首批“中國紅色地標”,亦是山西省太行文化旅游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太行山片區紅色旅游資源核心聚集區。然而,與眾多紅色旅游目的地類似,目前武鄉的紅色旅游以團體組織參觀游覽者為主,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本研究選取武鄉為案例地,探究有助于促進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機制,有利于武鄉紅色文化基因的傳承和愛國主義教育功能的發揮。
2.2 變量測量
本研究所有變量的測量均參考和借鑒已有研究中的成熟量表,且采用7點式李克特量表測量。地方依戀的測量參考Tonge等的研究[12],紅色教育感知借鑒李文明等[37]的研究,并將量表的適用情景修正為太行山片區的武鄉紅色旅游地;紅色精神共情的測量參考李文明等對自然共情的研究[35],但將共情的對象修正為紅色精神;紅色旅游忠誠度的測量采用拓展的旅游者忠誠度量表[19,20],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量表來源于紅色文化資源情境下修正的旅游者遺產負責任行為量表[26,44]。
2.3 數據收集
正式調研前,對問卷進行試測。首先,邀請近期去武鄉見習的大學生閱讀問卷,確保題項不存在歧義;然后于2020年11月對研究人員熟悉的、近期出游過武鄉的親友進行預調查,回收有效問卷84份;最后,對問卷進行信(效)度測試,其中紅色教育感知構念下的一個題項,即“武鄉紅色旅游的展覽和表演是一種高尚的藝術形式”因子載荷低于0.5,予以刪除,其余題項信(效)度符合標準。
正式調研選擇現場采集數據,于2020年11月24日至2021年1月10日的周末和2021年4月10-11日,一名研究人員帶領某高校旅游管理專業的兩名學生,在武鄉紅色旅游景區出口及停車場等位置邀請游覽結束的旅游者填寫問卷,共收集問卷436份,其中有效問卷409份,有效率為93.8%。有效問卷中,男性樣本占44.55%,女性樣本占55.45%;年齡在18~30周歲的樣本占67.3%,18周歲以下及51周歲以上的旅游者較少;本科學歷者占59.27%,高中學歷者占17.13%;首次參觀者占51.01%,參觀3次及以上者占35.51%,超過50%的旅游者來武鄉是為緬懷革命先烈、了解革命歷史等。
3 結果分析
3.1 信(效)度檢驗
采用SPSS 23.0和AMOS 24.0對問卷的信(效)度進行檢驗。由表1可知,各構念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2~0.946,組合信度為0.911~0.947,問卷信度充分。各構念觀測題項的因子載荷為0.824~0.942,滿足大于0.6的推薦值,量表的收斂效度得到驗證。構念平均方差提取AVE值為0.719~0.847,符合大于0.5的要求。一階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模型總體擬合效果為:df=254>0,GFI=0.845,CFI=0.934,NFI=0.922,IFI=0.935,TLI=0.922,除GFI略小于0.9外,其余指標均符合理想標準,PGFI=0.664,達到大于0.5的標準,RMSEA=0.078,符合小于0.08的標準。各構念AVE值的平方根大于與其他構念間的相關系數,變量的區別效度得到驗證(表2)。

表1 量表的信(效)度結果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measurements

表2 構念區別效度Table 2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constructs
3.2 結構方程模型檢驗
采用AMOS 24.0對結構方程模型的路徑系數及其顯著性進行檢驗(表3),除假設H1c、H2b和H2c外,其余假設均得到驗證。地方認同對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直接影響不顯著,地方情感對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直接影響亦不顯著,這與已有研究“地方認同、地方情感直接顯著影響旅游者忠誠度及其環境負責任行為”的結論[8,9,11,12]不一致。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案例地偏差,雖然武鄉在太行山片區紅色旅游發展優越,但相比井岡山、延安、瑞金和韶山等知名紅色旅游勝地,武鄉在激發旅游者地方認同和地方情感中的作用相對較弱;另一方面可能源于樣本偏差,本次問卷收集時間介于2020年年底至2021年4月份,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樣本中有較多的集體組織參觀者,并非受武鄉作為紅色旅游地的吸引而來,因此其對武鄉的地方情感不強,亦談不上地方認同。

表3 結構方程模型路徑系數及檢驗結果Table 3 Path coefficients and test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3 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中介效應檢驗
以地方依賴、地方情感和地方認同合并的一階構念地方依戀為自變量,檢驗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在地方依戀作用于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中的中介效應。使用SPSS宏中的PROCESS 3.4.1對中介效應進行95%置信區間檢驗[43],結果(表4)表明,地方依戀作用于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兩條路徑中,直接和間接效應均顯著,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對比二者的間接效應值可發現,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在地方依戀作用于紅色旅游忠誠度的路徑中,中介效應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在地方依戀作用于旅游者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路徑中,紅色精神共情的中介效應顯著優于紅色教育感知。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是源于紅色精神共情、紅色教育感知、旅游者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時空差,旅游者的紅色精神共情、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更多地存在于旅游者的紅色旅游過程中,紅色教育感知既存在于旅游過程中,亦反映了旅游者出游后的獲得感,而紅色旅游忠誠度更多地反映了旅游者出游后的態度和行為傾向。因此,紅色精神共情能夠更好地在旅游過程中的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上發揮作用,表現出優于紅色教育感知的中介效應;而在旅游者出游后的紅色旅游忠誠度中,并未表現出與紅色教育感知顯著差異的中介效應。

表4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Table 4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4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紅色文化基因傳承和紅色旅游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構建了地方依戀影響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理論模型,經實證檢驗得到以下結論:1)地方依賴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的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地方認同對二者的直接影響均不顯著,地方情感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的紅色旅游忠誠度,但對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直接影響不顯著。紅色旅游情境下,地方依戀不同維度對旅游者忠誠度和負責任行為的影響與普通觀光旅游情境下結果存在差異,原因需進一步研究。2)地方依賴、地方情感和地方認同反映了旅游者對紅色旅游地行為、認知和情感層面的關系強度,均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的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但相比地方情感和地方認同,地方依賴的影響程度更大;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的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3)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在地方依戀影響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在地方依戀影響旅游者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作用路徑中,紅色精神共情的中介效應顯著優于紅色教育感知。紅色精神共情是旅游者在紅色旅游地參觀游覽中非常容易產生的一種情感共鳴,然而,當前鮮有研究引入紅色精神共情這一變量,本研究創新性地引入這一變量作為地方依戀作用于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中介變量,并驗證了其優于紅色教育感知的中介效應,為紅色旅游目的地及紅色旅游景區激發引導期望的旅游者態度和行為提供了新思路。另外,本研究在紅色旅游情境下,探討地方依戀對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影響及作用機制,與李文明等關于地方依戀對韶山紅色旅游者親環境行為的影響研究[37]共同拓展了地方依戀理論的應用情境。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為提高旅游者的紅色旅游忠誠度并引導其踐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促進我國紅色文化基因傳承和紅色旅游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建議:1)基于地方依戀有助于提高旅游者對目的地的忠誠度,強化旅游者的負責任行為,目的地管理者要重視借助硬件設施的完善、服務的提升、特色紅色旅游活動的開展、紅色革命精神標志性景觀的打造及紅色精神的展示和宣講等手段,加深旅游者對紅色目的地的地方依戀水平。如武鄉作為太行革命精神的重要載體,可以將太行兒女在中華民族危亡之際不怕犧牲、無私奉獻等革命故事通過敘事、藝術創作等方式進行宣傳展示,突出武鄉作為弘揚傳承太行精神的獨特性,提高旅游者對武鄉的地方依戀水平。2)重視對旅游者紅色精神共情的喚醒和紅色教育效果的提升。紅色旅游屬專項旅游活動,解說員的解說質量是喚起旅游者紅色精神共情和獲得紅色教育感知的重要因素,然而,當前紅色旅游目的地部分解說員紅色知識水平有限,且工作積極主動性不高,僅機械復述紀念館展板上的解說詞,不利于旅游者紅色精神共情的喚醒和紅色教育感知的提升。因此,紅色旅游目的地必須重視從業人員特別是解說員的專業化培訓,重視融情式信息和情緒線索的提供,喚起旅游者的紅色精神共情,不斷提升紅色旅游的教育效果,更好地促進旅游者的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
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影響因素眾多,然而,本研究僅探討了地方依戀這一重要因素的影響作用和機制,后續可進一步研究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的其他影響因素及其可能的作用路徑,為旅游者紅色旅游態度和行為的培育和引導提供更加豐富的理論依據。本研究驗證了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在地方依戀作用于旅游者紅色旅游忠誠度和紅色文化資源負責任行為中的部分中介作用,但是否存在其他中介機制以及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之間的鏈式中介有待后續研究進一步檢驗。另外,訪談中發現解說員解說有效性對紅色精神共情和紅色教育感知有重要影響,然而本研究并未檢驗解說員解說有效性的作用,有待后續進一步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