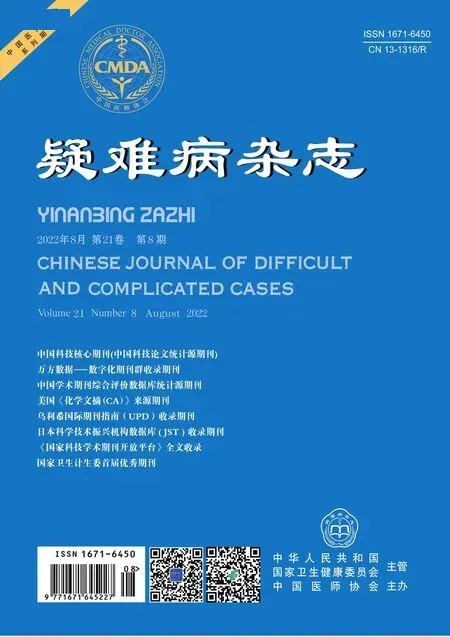狼瘡足細胞病1例并文獻復習
范佳,雷靜,孫廣萍,何平,劉大軍
患者,男,38歲,因“發現蛋白尿1周”于2019年7月2日入院。患者1周前擬行膽囊切除術,術前常規檢查發現尿蛋白(+++),低蛋白血癥,腎功能正常,追問近2周無明顯誘因出現雙眼瞼水腫,尿色偏暗,后逐漸有泡沫尿,夜尿增多,尿量較前稍增多。患者近半年嚴重脫發,母親患有干燥綜合征。查體:T 36.5℃,P 80次/min,R 18次/min,BP 130/80 mmHg。顏面水腫,心肺腹查體無明顯異常。實驗室檢查:WBC 2.84×109/L,Hb 130 g/L,PLT 118×109/L;Alb 21.9 g/L,TG 1.66 mmol/L,TC 5.53 mmol/L,SCr 61.6 μmol/L,UA 550 μmol/L;尿蛋白(++++),24 h尿蛋白定量13.30 g/d;抗dsDNA抗體(-),抗Sm抗體(+)>8.0 IU/ml,抗SSA抗體(+)>8.0 IU/ml,抗核抗體(ANA)(+)≥1∶640,補體C3 0.423 g/L,C4 0.077 g/L。行腎臟穿刺活檢,免疫熒光檢查:IgG(-),IgM(-),IgA(-),C3(-),C1q(-)。光鏡檢查:15個腎小球中可見2個腎小球球性硬化,1個腎小球節段性硬化,節段性硬化的腎小球位于尿極處,伴周邊足細胞肥大,其余腎小球基本正常;腎小管上皮細胞空泡變性,小灶狀萎縮(萎縮面積約5%),腎間質小灶狀炎性細胞浸潤,無明顯纖維化,小動脈管壁輕度增厚,管腔輕度狹窄,符合局灶節段性腎小球硬化(FSGS)頂端型。電鏡檢查:腎小球基底膜無明顯增厚,上皮細胞腫脹,空泡變性,足突彌漫性融合;系膜細胞和基質輕度增生,未見確切電子致密物沉積;上皮下、內皮下未見電子致密物;個別毛細血管管腔內可見紅細胞聚集(見圖1)。最終診斷:(1)狼瘡足細胞病;(2)系統性紅斑狼瘡。于2019年7月13日給予強的松(潑尼松)60 mg,每天1次口服,聯合環磷酰胺0.6 g 靜脈滴注治療,患者癥狀好轉后出院。2019年8月1日復查尿蛋白(+),Alb 33.4 g/L,TG 2.33 mmol/L,TC 6.69 mmol/L,SCr 64.5 μmol/L,UA 359 μmol/L,24 h尿蛋白定量2.18 g/d,后每15 d予患者靜脈滴注環磷酰胺0.6 g,強的松遵醫囑規律減量。因新冠疫情患者近3個月未及時到醫院累計環磷酰胺,2020年3月16日實驗室檢查示24 h尿蛋白9.98 g/d,Alb 20.8 g/L,此時強的松減量至22 mg,每天1次,環磷酰胺累計5.6 g。遂將強的松增量到40 mg,每天1次,并繼續規律累計環磷酰胺到8.4 g后,患者病情得到明顯控制,尿蛋白明顯減少。2020年7月1日復查患者病情穩定,24 h尿蛋白定量<1 g/d,將強的松規律減量至20 mg,每天1次,應用環磷酰胺1.0 g,累積量為9.4 g。現患者每月按時返院復查,嚴格遵醫囑激素減量。

注:A.光鏡下示硬化的腎小球(HE染色,×400);B.光鏡下示腎小球內無明顯嗜復紅蛋白沉積(Masson染色,×400);C.電鏡下示上皮下、內皮下未見電子致密物(×1 500);D.電鏡下示足突彌漫性融合(×1 200)
討 論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種以多種自身抗體、多器官損害為特征的自身免疫病,約50%以上的SLE患者出現腎臟損害的臨床表現,幾乎100%出現腎臟病理異常。SLE的病因尚不清楚,但目前認為其病因主要涉及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1]。狼瘡足細胞病(lupus podocytopathy, LP)是SLE患者臨床表現為腎病綜合征,腎活檢病理表現為系膜增生(MsP)、腎小球輕微病變(MCD)或FSGS,超微結構為足細胞足突廣泛融合,毛細血管袢內皮下及上皮側無免疫沉積物的腎損害。
LP的發病機制尚不清楚,在LP中,腎小球毛細血管壁上缺乏免疫沉淀物和存在嚴重的足細胞足突彌漫性融合(FPE),與MCD或原發性FSGS的發病機制類似,可能是由細胞因子、淋巴因子或T細胞功能障礙介導的足細胞損傷,不同于典型的免疫復合物介導的損傷[2]。足細胞也作為抗原提呈細胞,參與免疫介導的腎小球疾病[3]。
LP的診斷尚無正式指南,但其最常用的診斷標準如下[4-8]:(1)臨床表現,滿足SLE診斷,表現為腎病綜合征,常伴急性腎損傷;起病前無非甾體抗炎藥(NSAID)等藥物使用史。(2)光鏡:腎小球病變輕微或系膜增生,或局灶節段性腎小球硬化,無內皮下或上皮側免疫沉積物。節段硬化者需與增生型狼瘡性腎炎(LN)遺留的疤痕鑒別。(3)免疫熒光:血管袢無免疫復合物,伴或不伴系膜區免疫球蛋白和補體沉積。(4)電鏡:足細胞足突融合≥70%,可伴系膜區電子致密物沉積而無內皮下或上皮側電子致密物沉積。本例患者早期以腎病綜合征起病,并出現白細胞及血小板減少、脫發等腎外表現,ANA、抗Sm抗體陽性,補體C3、C4降低等血清學改變,且在腎病發作前無腎毒性藥物使用史;腎活檢后組織學形態為FSGS,腎小球沒有免疫球蛋白和補體沉積,電鏡下可見足突彌漫性融合>50%,上皮下、內皮下未見電子致密物。結合本例患者的臨床和病理表現,滿足LP的診斷。
絕大多數LP患者對激素治療敏感,預后良好,但復發率高。Wu等[9]報道的LP患者首先接受類固醇和環磷酰胺治療,然后服用環孢素和其他藥物,腎功能完全恢復,臨床表現改善,出院后定期隨訪,病情穩定。本例患者使用激素聯合環磷酰胺治療,臨床癥狀逐步緩解,蛋白尿顯著降低,腎功能穩定,效果良好。
LP治療后的復發率可高達30.80%~42.86%,研究發現,單用激素維持治療的患者復發率可高達90%,與其他免疫抑制劑聯合使用可顯著降低復發率[10-12]。本例患者在激素聯合環磷酰胺治療緩解后,因未及時累計環磷酰胺出現復發,及時調整激素劑量并且累計環磷酰胺后,病情得到緩解,提示激素聯合免疫抑制劑對于LP的復發治療有效。此外,由于鈣調神經磷酸酶抑制劑(CNIs)對足細胞損傷有穩定作用,對頻繁復發的患者也可使用CNIs[13]。研究報道,頻繁復發的LP會發生病理轉型,但LP患者總體遠期腎臟預后良好[8]。
總之,LP患者激素治療敏感,但其復發率較高,激素與免疫抑制劑聯合使用可降低其復發率。本例患者采用激素聯合環磷酰胺治療,效果良好,復發后調整激素用量及繼續規律累計環磷酰胺治療效果明顯,但其臨床療效及有效治療方案仍需大樣本進一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