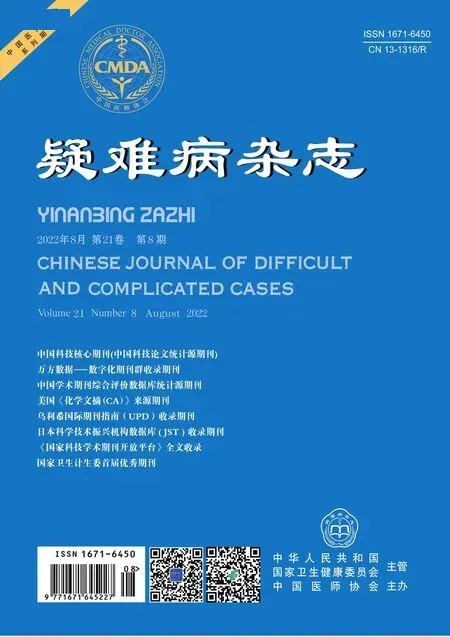孕婦胎膜厚度、外周血Th17/Treg變化及預測早產價值的ROC分析
陳秀敏,吳熊軍,許文彬,鄧乾葆
早產是圍生兒致死重要原因之一,發病率為5%~15%,部分產婦經保胎可繼續妊娠,但部分產婦可進展至難免流產[1-2]。早產是多因素、多過程參與作用的結果,盡管其確切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但近年相繼有研究提出,早產與宮內亞臨床性感染、炎性免疫應答關系密切[3-4]。輔助性T細胞17(T helper cell 17,Th17)、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Treg)是CD4+T淋巴細胞家族成員,二者分化過程呈互相依賴性,但其免疫調節作用完全相反,共同維持機體免疫穩定及平衡[5]。近年越來越多研究顯示,Th17、Treg作為效應及調節細胞參與妊娠的建立及維持過程,若Th17/Treg失衡可能會導致妊娠失敗[6-7]。另外,胎膜是確保胎兒發育環境穩定性的主要結構之一,而感染及炎性因素均會致胎膜水腫增厚;同時有研究證實,Th17細胞因子可通過激活活性氧/核因子κB而促進細胞外基質膠原降解,降低胎膜韌性,增加破裂風險[8]。鑒于此,現分析孕婦胎膜厚度、外周血Th17/Treg變化在預測早產中的價值,為臨床完善相關機制提供參考,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1月—2021年8月海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婦產科就診的先兆早產孕婦102例為觀察組,選取同期正常產檢孕婦102例為對照組。2組年齡、孕周、體質量指數(BMI)、產婦類型、人工流產史、早產史、飲酒史、吸煙史等基礎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K20191223321),受試者及家屬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對照組與觀察組臨床資料比較
1.2 病例選擇標準 (1) 納入標準:①先兆早產參考《婦產科學》[9]診斷標準;②孕周28~36+6周;③無妊娠期綜合征。(2)排除標準:①胎膜早破;②伴嚴重肝、腎、心功能不全者;③胎兒畸形;④前置胎盤;⑤低置胎盤。
1.3 觀測指標與方法
1.3.1 超聲檢查:采用邁瑞DC-70S型超聲儀,腹部探頭1~5 MHz,探頭與腹壁垂直,掃描臍帶入口宮頸方向≤3 cm部位,測量羊膜、絨毛膜結構外緣3次,取平均值作為胎膜厚度。常規觀察胎兒發育情況,測生物物理參數,評估胎兒發育。
1.3.2 外周血Th17、Treg水平檢測:產婦入院后采用肝素抗凝真空管采集晨起空腹肘靜脈血2 ml,應用美國BD FACS calibur流式細胞儀檢測CD4+T細胞內Th17、Treg細胞占比,并計算Th17/Treg比值。
1.3.3 新生兒并發癥發生率:記錄新生兒并發癥發生情況,包括高膽紅素血癥、呼吸窘迫綜合征、貧血、感染、腦室內出血等。

2 結 果
2.1 2組胎膜厚度、外周血Th17/Treg水平比較 觀察組胎膜厚度、外周血Th17、Th17/Treg水平高于對照組,Treg低于對照組(P<0.01),見表2。

表2 對照組與觀察組胎膜厚度、外周血Th17/Treg水平比較
2.2 觀察組孕婦不同亞組臨床特征比較 觀察組102例孕婦早產65例(63.73%,早產亞組),非早產37例(非早產亞組)。早產亞組孕婦年齡≥30歲、孕周28~33周、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占比及胎膜厚度、Th17/Treg水平高于非早產亞組(P<0.05),見表3。

表3 觀察組孕婦是否早產在不同臨床特征中比較
2.3 相關因素的多重共線性檢驗 將表3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項(年齡、孕周、妊娠期高血壓疾病、胎膜厚度、Th17/Treg)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發現上述因素容差在0.380~0.736,方差膨脹因子(VIF)在1.358~2.631,因此認為多重共線可能性低,見表4。

表4 相關因素的多重共線性檢驗
2.4 影響早產的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 經多因素回歸分析顯示,胎膜厚度、Th17/Treg升高均是增加早產風險的危險因素(P<0.01),見表5。

表5 影響早產的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
2.5 胎膜厚度、Th17/Treg對早產風險的預測價值 ROC曲線分析發現,胎膜厚度、Th17/Treg水平及二者聯合預測早產的AUC分別為0.791、0.766、0.861,二者聯合預測早產的價值高于單項指標預測(Z/P=2.586/0.010,2.806/0.005),見圖1、表6。

圖1 胎膜厚度、Th17/Treg水平預測早產風險的ROC曲線

表6 胎膜厚度、Th17/Treg水平對早產風險的預測價值
2.6 觀察組中足月與早產新生兒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觀察組102例孕婦(雙胎3例),活產胎兒105胎,早產兒68胎。早產兒高膽紅素血癥、呼吸窘迫綜合征發生率高于足月兒(P<0.05),而貧血、感染、腦室內出血與足月兒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7。

表7 觀察組中足月與早產新生兒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例(%)]
3 討 論
早產誘發因素眾多,其中胎兒因素、母體因素均可能引起早產[10]。目前陰道指檢是臨床了解宮頸情況的主要手段,并可以此評估早產風險,盡管操作簡單且可為臨床提供一定參考依據,但也存在一定不足,尤其是在評估先兆早產患者進展至難免流產風險方面缺乏客觀性[11]。因此,需積極完善相關風險評估機制以指導臨床積極制定干預策略。
胎膜屬于胎兒重要附屬物,具有包裹及保護胎兒作用。近年研究證實,感染引起羊膜、絨毛膜炎性反應及其所致的胎膜早破可誘發早產,破膜孕婦7 d內發生早產幾率高達50%~70%,早產胎兒胎膜厚度高于正常分娩胎兒,且早產胎膜厚度與繼續妊娠胎齡間呈負相關[12-13]。本研究也發現,先兆早產孕婦胎膜顯著增厚,與上述研究結果一致。此外,本研究還發現,經保胎治療仍進展至難免早產的孕婦胎膜厚度高于保胎成功孕婦(P<0.01)。分析主要是因正常情況胎膜厚度隨孕周增加而增加,并在一定合理范圍內(<5 cm),若胎膜受感染、免疫應答異常等影響出現水腫增厚可能會誤導機體過早的激活分娩機制,且胎膜厚度越大,此效應越強烈以致保胎失敗[14-15]。但還有研究表明,個體間胎膜厚度存在一定差異,受孕周影響較大,且檢測位置不同可能對結果評定有一定影響[16]。本研究選取距臍帶插入位置3 cm且靠近宮頸處檢測胎膜厚度,主要是此處上行感染風險較大,局部圖像放大后較易測量,所測結果更能代表胎膜病理性改變情況[17]。同時本研究發現,在對早產的影響方面,孕周、胎膜厚度間不具有共線性,胎膜厚度每增加1個單位,早產風險增加2.683倍,且經ROC分析,胎膜厚度高時在預測保胎失敗方面具有一定價值。上述研究均提示,胎膜厚度或可應用于先兆早產病情轉歸的評估。但不難發現,胎膜厚度變化屬病理性改變,當其出現顯著異常時可能先兆早產已進展至較嚴重階段。因此,單純從此方面評估可能會錯失最佳保胎時機,而先兆早產進展所涉及的生化層面改變或能為臨床更早評估先兆早產轉歸情況提供依據。
妊娠的本質是“同種異體移植”過程,其攜帶來自母體50%的抗原組織,其中免疫耐受調節是此過程的重要調節機制之一,妊娠成功需母—胎間免疫耐受[18-20]。以往研究指出,Th1/Th2細胞平衡穩定是妊娠維持的必要條件[21]。但近年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發現,Th1/Th2細胞平衡無法完全解釋母—胎間免疫平衡機制[22-23]。有研究顯示,人早期蛻膜內富含Treg細胞,其在孕24周即滋養細胞侵入母體達最大限度時達到高峰,待分娩后逐漸回歸較低水平[24]。Th17是與自身免疫、炎性疾病、移植排斥等密切相關的一種CD4+效應細胞,在機體防御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發揮重要作用。多項研究證實,Th17細胞在器官移植、類風濕性關節炎等患者外周血中含量升高[25-26]。另外,Treg細胞是控制機體自身免疫反應的一類T細胞亞群,主要介導免疫抑制。正常情況,Th17/Treg處于動態平衡,共同維持機體正常的免疫功能。本研究推測,Th17/Treg異常可能與先兆早產發生發展有關。經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Th17/Treg水平升高是早產的獨立危險因素。主要是母體被感染后,Th17細胞啟動免疫應答致Th17/Treg平衡向Th17偏移,繼而激活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等炎性細胞的增殖及成熟機制,并向感染部位聚集,通過上述細胞的活化及相關炎性介質釋放形成炎性級聯反應,若感染持續存在則最終造成胎膜增厚,發動分娩[27-28]。但結合現有研究分析[29-30],Th17/Treg水平異常并非早產的必然條件。因此,單純Th17/Treg生化檢驗難免存在片面性,而與病理性檢驗相結合或更具客觀性。本研究經ROC分析發現,胎膜厚度、Th17/Treg聯合預測早產的AUC為0.861,具有較高的預測效能。此外,先兆早產孕婦早期Th17/Treg及胎膜厚度異常并不同步,提示臨床在孕婦孕檢中若發現Th17/Treg水平異常則需加強先兆早產防控意識,積極干預并定期檢測胎膜厚度,若異常則需加強干預策略,盡量延長孕周,降低早產兒并發癥發生風險。
綜上可知,胎膜厚度增加、外周血Th17/Treg水平升高是先兆早產孕婦進展至難免早產的獨立危險因素,二者聯合檢測可提升早產的預測效能,對指導臨床完善干預策略、減少新生兒并發癥具有重要意義。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無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
陳秀敏:實施研究過程,論文撰寫;吳熊軍:提出研究思路,論文審核;許文彬:課題設計,實施研究過程;鄧乾葆:實施研究過程,分析試驗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