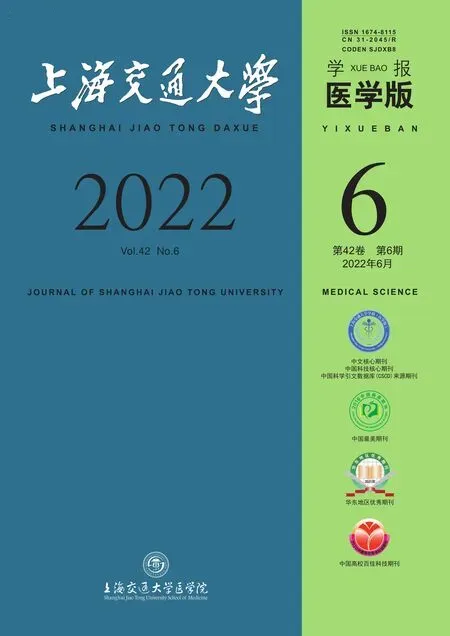體質量與C1q 腫瘤壞死因子相關蛋白1 在心肌梗死患者中的交互作用
胡 曉,張 鑫,谷 陽
南京醫科大學附屬淮安第一醫院心內科,淮安 223300
1997 年,世界衛生組織首次將肥胖定義為疾病。肥胖是由基因、環境、社會、心理等多種因素引起的慢性代謝性疾病。研究[1-3]表明,肥胖與胰島素抵抗、血脂異常及高血壓等疾病密切相關,是動脈粥樣硬化的危險因素之一。在肥胖與動脈粥樣硬化等疾病的相關性研究中,多采用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作為肥胖的界定標準[4]。然而,由于脊柱退行性變、佝僂等原因,基于直接測量的身高計算出來的BMI 并不能準確反映身體脂肪含量[5],使得研究結論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目前,鮮少有以體質量為切入點,探討肥胖與心肌梗死患者預后的相關性研究。
C1q 腫瘤壞死因子相關蛋白1 (C1q 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protein 1,CTRP1)是一種脂肪細胞因子,參與機體的炎癥反應、新陳代謝等病理生理過程,其表達水平與冠狀動脈的狹窄程度呈正相關[6]。有研究[7]表明,CTRP1 可刺激醛固酮的生成;而ENGELI等[8]發現,體質量降低5%可顯著降低血漿和脂肪組織中的醛固酮水平。以上研究提示,CTRP1 與體質量之間或存在一定的關系。基于此,本研究對心肌梗死患者的基本資料及檢測指標進行分析,探討影響患者預后的相關因素、體質量和血清CTRP1 水平之間的交互作用,以期為該類患者的預后評估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雙盲法。選取2018 年1 月—2020 年1 月于南京醫科大學附屬淮安第一醫院救治的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200 例。納入標準:①符合《急性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診斷和治療指南》[9]診斷標準。②在急診介入治療時間窗內,已行急診冠狀動脈造影+支架植入術。排除標準:①合并嚴重的肝腎功能不全。②合并活動性出血。③合并急性腦血管疾病。④合并惡性腫瘤。⑤合并嚴重感染。
1.2 研究方法
1.2.1 基本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的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體質量、BMI、既往史[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冠狀動脈性心臟病(冠心病)家族史、吸煙史等]以及梗死相關動脈(infarction related artery,IRA)情況。其中,IRA 為患者本次罹患心肌梗死的罪犯血管,經冠狀動脈造影術確認,包括左前降支動脈(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LAD)、左回旋支動脈(left circumflex artery,LCX) 和右冠狀動脈(right coronary artery,RCA)。
1.2.2 實驗室指標及心功能指標測定 于患者入院后第2 日清晨,抽取靜脈血5 mL,行實驗室指標及心功能測定:①采用日立76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肌酐、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水平。②采用酶聯免疫檢測試劑盒檢測血清CTRP1 水平。③采用二維超聲心動圖測量左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
1.2.3 院外藥物治療、隨訪及分組 根據《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診斷和治療指南》[9],所有患者出院后需繼續口服藥物進行治療,如無使用禁忌證,其口服藥物包括阿司匹林腸溶片、替格瑞洛/氯吡格雷、瑞舒伐他汀/阿托伐他汀、倍他樂克緩釋片、貝那普利/纈沙坦、螺內酯等。遵循個體化治療的原則,患者如發生消化道出血、低血壓等情況,需及時調整用藥。
同時,患者出院后需每月行門診或電話隨訪1 次。記錄患者自出院后1 年內有無發生嚴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SAE),即是否發生預后不良。SAE定義為再發心肌梗死、再次血運重建(植入支架或冠狀動脈搭橋)、發生嚴重出血、發生卒中以及心源性死亡。根據有無發生SAE,將患者分為SAE組和無SAE組。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 22.0 軟件處理。定量資料經單樣本K-S 檢驗后均符合正態分布,以±s表示并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比較;定性資料以頻數(百分率)表示,使用χ2檢驗進行比較。采用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SAE 發生的影響因素。使用GraphPad Prism 9.0 軟件繪制森林圖,分析患者的性別、年齡、體質量與血清CTRP1 水平的交互作用。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隨訪結果及其分組
截至2021年1月,本研究完成了對所有研究對象出院后的隨訪工作;其中,因患者失聯、自行退出等原因,失訪8 例。在192 例患者中,有24 例患者發生SAE,發生率12.5%。同時,基于該情況將患者分為SAE組(n=24)和無SAE組(n=168)。
2.2 2組患者的基本資料、實驗室指標和心功能指標比較
對2 組患者的基本資料、實驗室指標和心功能指標進行比較,結果(表1)顯示,與無SAE 組相比,SAE 組患者的年齡更大、體質量偏低、CTRP1 水平較高,且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表1 2組患者的基本資料、實驗室指標和心功能指標比較Tab 1 Comparison of basic data,laboratory indexes and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3 SAE發生的相關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是否發生SAE 作為因變量,以上述分析篩選出來的年齡、體質量、CTRP1 等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作為自變量;同時,根據體質量中位數(70.75 kg)將患者分為低體質量組和高體質量組,根據CTRP1 水平中位數(17.95 ng/mL)將患者分為低CTRP1 組和高CTRP1 組,根據年齡中位數(63 歲)將患者分為低齡組和高齡組,再行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經校正了性別、年齡后,結果(表2) 顯示,高CTRP1 水平與STEMI 患者發生SAE 密切相關(P=0.003),而體質量不影響患者SAE 的發生(P>0.05)。隨后,行亞組分析的結果(圖1)顯示,體質量與CTRP1 之間存在交互作用(P=0.011);對于低體質量患者而言,CTRP1 水平是其發生SAE 的危險因素(HR=22.303,P=0.003)。

圖1 發生SAE的交互作用分析Fig 1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SAE occurrence

表2 影響SAE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校正性別、年齡后)Tab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AE occurrence(after adjusting for gender and age)
3 討論
據2010年國民體質監測公報[10]顯示,我國成年居民的超重率為32.1%,肥胖率為9.9%。近10 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增長和生活方式、飲食結構的改變,我國各年齡段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有了快速增加。據《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 年)》顯示,成年居民的超重肥胖率超過50%,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體質量分別為69.6 kg 和59.0 kg,且體質量增幅大于身高。KERSBERGEN 等[11]研究發現,肥胖人士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非人性化侮辱,這將對其生理、心理產生不良后果。因此,正確認識肥胖對人群健康的危害,探索其內在病理生理機制,對人口健康素質的提高和慢性病的防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肥胖引起的糖代謝異常、脂質代謝異常、高血壓及睡眠呼吸障礙等是動脈粥樣硬化發生、發展的病理生理學基礎[1-3]。SONG 等[12]研究發現,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冠心病的死亡率均隨BMI 的升高而增加。SHIGA 等[13]對6 216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進行了平均時長為(3.6±1.4)年的隨訪,結果發現,肥胖患者發生心源性猝死的風險是非肥胖患者的2.78倍。但就肥胖對冠心病患者的預后影響方面,學術界仍存在爭議,不少研究得出了“肥胖悖論”,即肥胖冠心病患者的預后比非肥胖患者更好[14-16]。所以,BMI 是否能夠準確評估肥胖與冠心病間的關系仍有待商榷。本研究發現,與無SAE 組相比,SAE 組STEMI 患者的年齡更大、體質量偏低、CTRP1水平較高,而2組患者的BMI 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校正了年齡、性別等混雜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并未發現體質量與SAE 的發生具有直接的相關性;而亞組分析發現,在低體質量患者中,高CTRP1 組的SAE發生風險是低CTRP1 組的22.303 倍,而在高體質量患者中則沒有這一效應。
目前,關于體質量與CTRP1 水平間的關系研究相對較少。KANEMURA 等[17]發現,CTRP1 作為保護性因素,可抑制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從而改善病理性血管重構;而另有研究[18]發現,在肥胖條件下CTRP1 的表達出現了上調,提示這可能是“肥胖悖論”的機制之一。個體體質量的增加以脂肪組織積聚增加為主;其中,脂肪組織不僅具有儲存能量的作用,其內分泌功能也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脂肪組織分泌的細胞因子如脂聯素、瘦素、抵抗素、CTRP1 等,均參與了冠心病的發生與發展過程[6,19-20]。其中,CTRP1和脂聯素結構相似,均具有C1q 球形結構域,因此該2 種因子在脂肪組織中可能存在競爭性抑制。有研究[21]顯示,使用腫瘤壞死因子-α 刺激已分化的SGBS 前脂肪細胞,CTRP1的mRNA 表達水平有明顯升高,而脂聯素的mRNA 表達有所下降。相關研究[22]發現,脂聯素水平與脂肪組織含量呈負相關,因此我們推測CTRP1 水平與體質量之間或可存在一定聯系。MUENDLEIN 等[23]對539 例冠心病患者隨訪8 年發現,CTRP1 水平與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發生具有顯著相關性,這與我們的研究結果相一致。且相關研究[24]顯示,CTRP1 可促使血管平滑肌細胞中白細胞介素-6、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細胞間黏附分子1 等表達增加,從而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其促炎作用是冠心病患者預后不良的機制之一。本課題組在前期研究[25]發現,小鼠發生心肌梗死后,其心臟組織和血清中的CTRP1 水平有明顯升高,且在心肌梗死4 周后小鼠體質量有所減輕;而C1qtnf1-KO 小鼠發生心肌梗死后,體質量較對照組有增加。因此,血清CTRP1 水平與體質量之間或存在一種負反饋機制,但具體如何發生將是我們未來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①為單中心、橫斷面研究,樣本量較少。由于我國人群的體質量和國外間存在種族差異,導致結論可能有一定的偏倚,尚需國內外更大樣本量、更長隨訪時間的隨機對照研究加以驗證。②未涉及體質量與CTRP1 的內在聯系及作用機制分析,這也將是我們未來研究的方向。綜上,本研究發現在不同體質量的患者中,血清CTRP1 水平對心肌梗死患者的預后影響有所不同。因此,探尋通過CTRP1 影響心肌梗死患者預后的作用靶點,對改善心肌梗死患者特別是低體質量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或可為個性化的體質量管理提供科學佐證。
利益沖突聲明/Conflict of Interests
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All authors disclose no relevant conflict of interests.
倫理批準和知情同意/Ethics Approval and Patient Consent
本研究涉及的所有試驗均已通過南京醫科大學附屬淮安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核批準(文件號YX-2017-245-02)。所有試驗過程均遵照南京醫科大學附屬淮安第一醫院制定的《臨床研究倫理守則》的條例進行。受試對象或其親屬已經簽署知情同意書。
All experimental protocols in this study were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Affiliated Huaian No. 1 People'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Approval Letter No. YX-2017-245-02),and all experimental protocols were carried out by following the guidelines ofEthical Principle of Clinical Research.Consent letters have been signed by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or their relatives.
作者貢獻/Authors'Contributions
胡曉、谷陽參與試驗設計;胡曉、谷陽和張鑫參與論文的寫作和修改。所有作者均閱讀并同意最終稿件的提交。
The study was designed by HU Xiao and GU Yang. The manuscript was drafted and revised by HU Xiao, GU Yang and ZHANG Xin.All the authors have read the last version of paper and consented for submission.
·Received:2022-01-20
·Accepted:2022-06-01
·Published online:2022-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