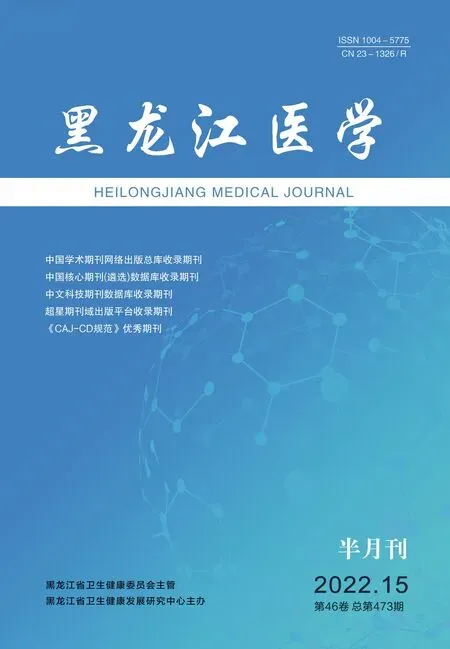外周血凝血酶-抗凝血酶復合物、血栓調節蛋白、組織纖溶酶原激活物-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復合物在膿毒癥患者中的檢測意義探析
李一璞
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檢驗科,河南 南陽 473000
膿毒癥因較高的發病率、病死率及預后并發認知障礙受到相關學術界的重點關注,其發病機制主要為機體無法正常抵抗有害感染引發各組織、器官病變,進而出現發熱、寒戰、心慌、精神異常等癥狀,病情加重時甚至導致器官衰竭與循環障礙,危及生命安全[1]。提高膿毒癥早期確診率為及時提供科學合理的針對性治療,提升膿毒癥患者生存率至關重要[2]。臨床醫學工作者不斷嘗試各種治療手段以實現膿毒癥的有效治療,主要包括液體復蘇、血液透析以及抗生素等,雖然膿毒癥相關治療手段不斷先進化且起到一定療效,但流行病學研究[3]發現,截止目前,膿毒癥存活的患者中大部分存在認知功能障礙。鑒于膿毒癥發生、發展過程繁瑣,涉及因素復雜,且具有高發病率、相關臨床癥狀嚴重、致死性強以及治療費用昂貴等劣勢,膿毒癥發生、發展相關標志分子的研究與確立迫在眉睫[4]。凝血酶-抗凝血酶復合物(TAT)可反映機體凝血酶含量,血栓調節蛋白(sTM)為模型血栓調節蛋白的脫落可溶物,組織纖溶酶原激活物-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復合物(t-PAI-C)能反映纖溶系統情況,此三項指標均與凝血、纖溶狀態有關,本研究通過回顧性收集2019 年5月—2020 年5 月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ICU 接受診治的66 例膿毒癥患者資料,獲取其外周血TAT、sTM、t-PAI-C 檢測數據并進行分析,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收集2019 年5 月—2020 年5 月在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ICU 室接受診治的66 例膿毒癥患者資料,男41 例,女25 例,年齡55~70 歲,平均年齡(62.83±7.17)歲。納入標準:(1)根據相關診斷標準確診膿毒癥,且可分為一般膿毒癥、嚴重膿毒癥及膿毒癥休克[5]。(2)性別不限,年齡≥18 周歲。(3)入院時間≥24 h,臨床資料完整。(4)無合并其他危及生命的急癥。排除標準:(1)確診神經類精神疾病。(2)確診先天凝血功能障礙、合并自身免疫疾病或血液疾病。(3)近期服用抗血栓等藥物或存在外科手術史。(4)經檢查存在惡性腫瘤。根據3 個月內死亡情況分為存活組與死亡組,分別對應46例、20例。
1.2 方法
(1)治療:主要包括積極液體復蘇、早期抗感染、給予血管活性藥物和器官支持等對癥治療預防各種并發癥等,其中預防并發癥措施主要包括機械通氣、鎮痛鎮靜、血糖控制以及腎臟替代等。(2)收集臨床資料:具體包括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身體質量指數(BMI)、各感染發生位置、基礎疾病,計算患者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狀況(APACHEⅡ)評分[6]、序貫器官衰竭(SOFA)評分[7]、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發生情況、C反應蛋白(CRP)水平、降鈣素原(PCT)水平、常規凝血指標[凝血酶原時間(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D-二聚體(D-D)、血小板計數(PLT)]等,并進行統計整理與分析。(3)外周血TAT、sTM、t-PAI-C檢測數據:收集所有患者2 mL 外周血(枸櫞酸抗凝管),常溫離心10 min(3 000 r/min)后,通過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定量檢測并計算血栓分子標志物濃度,包括TAT(參考值:<4.0 ng/mL),Stm(參考值:3.8~13.3 TU/mL),T-PAI-C(參考值:男:<17 ng/mL;女:<10.5 ng/mL)。
1.3 觀察指標
(1)對比不同預后患者基本臨床資料,具體內容包括各感染發生位置、APACHEⅡ評分、SOFA 評分、休克發生率及CRP、PCT 水平。(2)對比不同預后患者各項凝血指標水平,包括PT、APTT、DD、PLT、TAT、sTM、t-PAI-C 等。(3)分析外周血TAT、sTM、t-PAI-C 水平與膿毒癥患者炎癥因子(CRP、PCT),APACHEⅡ評分、SOFA評分及預后死亡的關系。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基本臨床資料情況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BMI、各感染發生位置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病情程度、SOFA評分、APACHEⅡ評分、DIC 發生率、CRP、PCT 水平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死亡組患者病情程度較存活組更嚴重,SOFA 評分、APACHEⅡ評分、DIC 發生率高于存活組,CRP、PCT 水平低于存活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基本臨床資料情況
2.2 兩組患者各項凝血指標情況
兩組患者PT 水平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死亡組APTT、DD、TAT、sTM、t-PAI-C 水平均明顯高于存活組,PLT 水平明顯低于存活組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各項凝血指標水平情況(±s)

表2 兩組患者各項凝血指標水平情況(±s)
指標常規凝血指標PT(s)APTT(s)DD(μg/mL)PLT(×109/L)血栓分子標志物TAT(ng/mL)sTM(TU/mL)t-PAI-C(ng/mL)存活組(n=46)死亡組(n=46)t值P值14.18±1.97 35.21±2.66 2.94±0.87 166.27±20.14 15.02±1.24 37.82±2.57 6.78±2.39 115.15±22.93 1.757 3.700 9.605 9.086 0.084 0.001 10.94±2.16 11.26±2.49 15.13±3.06 15.06±3.65 18.47±2.91 22.17±4.16 5.718 10.268 7.678 00 0 0 0
2.3 外周血TAT、sTM、t-PAI-C 與膿毒癥患者炎癥因子,APACHEⅡ評分、SOFA評分的相關性
Spearman 相關性分析顯示,膿毒癥患者外周血TAT、sTM、t-PAI-C 與CRP、PCT 水平及SOFA 評分、APACHEⅡ評分均呈明顯正相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外周血TAT、sTM、t-PAI-C與炎癥因子,APACHEⅡ評分、SOFA評分的相關性
2.4 外周血TAT、sTM、t-PAI-C 與膿毒癥患者預后死亡的多因素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
logistic 多因素回歸分析顯示,外周血TAT、sTM、t-PAI-C 與膿毒癥患者預后死亡密切相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外周血TAT、sTM、t-PAI-C與膿毒癥患者預后死亡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誘發膿毒癥病變的因素較多,具體包括嚴重肺炎、泌尿系統感染、嚴重創傷、腹膜炎等,致病微生物侵入人體組織后,促使炎性因子大量分泌,引起異常炎癥反應,使免疫調節功能失常,因此炎性因子與凝血指標分子對膿毒癥的診斷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8]。通過不斷分析膿毒癥患者凝血功能變化情況,可及時檢測其凝血功能紊亂征兆,有助于早期開展針對性治療,提高患者生存幾率[9]。膿毒癥患者常見并發癥狀為凝血功能障礙,此病變影響范圍較廣,具體包括全身凝血系統、纖溶系統受抑、內皮有關組織等,進而造成機體大面積衰變[10]。
為探尋一定信度的凝血預測指標,為膿毒癥早期診斷、預防、治療等工作提供理想參考依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死亡組患者病情程度較存活組更嚴重,SOFA 評分、APACHEⅡ評分、DIC發生率高于存活組,CRP、PCT水平低于存活組,表示病亡的膿毒癥患者器官衰竭急性變化程度更嚴重,體內凝血與纖溶功能異常發生率更高,兩組患者PT 水平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死亡組APTT、DD、TAT、sTM、t-PAI-C 水平均明顯高于存活組而PLT 水平明顯低于存活組,證實了治療病亡的膿毒癥患者凝血功能紊亂更嚴重,間接提示在膿毒癥檢測與預后監測過程中,可將以上凝血指標作為參考目標,為及時發現膿毒癥患者病情變化提供臨床依據。此外,Spearman 相關性分析顯示,膿毒癥患者外周血TAT、sTM、t-PAI-C 與CRP、PCT 水平及SOFA 評分、APACHEⅡ評分均呈明顯正相關,其中SOFA評分、APACHEⅡ評分可直接反映膿毒癥患者病情及器官功能受損[11]。CRP的異常表達在誘導線粒體損傷、炎癥損傷等發面發揮作用,可加劇器官、免疫功能障礙和凝血障礙。PCT 是一種糖蛋白,在內毒素等細胞因子誘導下,其濃度可在6~8 h 內迅速升高,通過結合膿毒癥患者機體內的糖蛋白配體,可加劇氧化應激損傷,導致膿毒癥患者病情惡化。logistic 多因素回歸分析顯示,TAT、sTM、t-PAI-C 與膿毒癥患者預后死亡密切相關,以上結果進一步證實TAT、sTM、t-PAI-C 作為血栓分子標志物,與膿毒癥患者病情程度及炎癥反應程度有密切關聯,能夠為膿毒癥預后病變情況提供可靠的臨床反饋。分析原因,TAT、sTM、t-PAI-C 通過敏感度、準確度更高的化學發光方法檢測,其測定速度更快,且操作便捷,而sTM 作為模型血栓調節蛋白的脫落可溶物,是反映內皮細胞受損最早期的一種指標,TAT 可反映凝血酶含量,當其含量上升則考慮機體發生DIC 癥狀,t-PAI-C 既能反映纖溶系統情況又能反映血管內皮細胞水平,當其含量升高則考慮機體發生血管內皮受損、動靜脈血栓或DIC 預兆等,這些標志物均在機體發生凝血等功能障礙早期出現變化,因此建議對膿毒癥患者盡早開展外周血TAT、sTM、t-PAI-C 監測,以進一步幫助判斷病情發展,并及早采取相關救治措施。
綜上所述,外周血TAT、sTM、t-PAI-C 可作為膿毒癥患者早期病情評價及預后分析的參考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