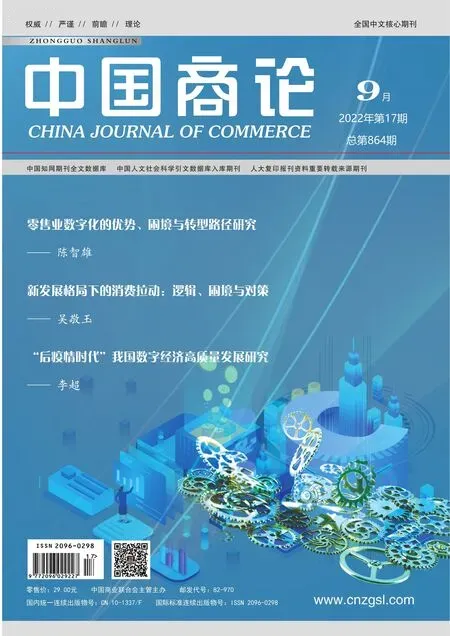“后疫情時代”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
李超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上海 200444)
2020年對我國乃至世界都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場疫情席卷全國,給經濟社會發展等帶來一定的沖擊與挑戰。在新冠疫情影響下,雖然我國農業、制造業、旅游業等受到了一定的沖擊,但數字經濟得到了強有力的發展。數字經濟在新冠疫情期間的運作方式不僅表現在患者診療、疫情地圖、人群追蹤等抗疫方面,還在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生活生產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重要作用。比如,疫情期間的在線學習、在線辦公、網絡直播、線上購物等,都成為應對疫情危機的重要方法,也刺激著我國 5G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數字產業的不斷發展。
夏杰長等(2021)研究指出,數字經濟規模能顯著促進創新投入,從而提高創新產出能力。姚維瀚、姚戰琪(2021),李英杰、韓平(2021)也指出,數字經濟發展能通過促進地區創新最終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任保平(2020),王曉紅、李雅欣(2021)也指出,數字經濟通過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發展和數字普惠金融三個維度顯著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由此可以發現,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基于此,本文對后疫情時代背景下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情況進行系統研究,分析其目前發展進程中的機遇與存在的挑戰和問題,更好地推動數字經濟的良性發展。
1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情況
1.1 數字經濟發展規模不斷增大
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數字經濟在技術創新、科技進步等影響因素的作用下,發展規模總體上不斷增大,呈現了從小到大、從發展不穩定到規范化發展的過程。由圖1可以看出,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受到全球金融風險的影響,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規模相對較小,占GDP的比重不是很高,處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隨著科技創新趨勢的不斷增強,數字經濟規模也在不斷擴大,2011年與2008年相比,其產值增加至9.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由15.2%上升至20.3%。2016年,數字經濟規模和比重也在不斷上升,并實現雙突破,其中規模突破20萬億元、比重突破30%。隨著技術創新對我國數字經濟的作用不斷增強,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受到社會的認可,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在此機遇下得以快速發展,發展規模在2018年達到了30萬億元以上,并且在之后的2019年和2020年,數字經濟的總體規模還是呈一個繼續增長的態勢,所占比重也不斷上升。

圖1 中國數字經濟規模與比重
1.2 產業數字化對數字經濟的影響進一步增強
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由于技術創新水平低下等問題,我國大多數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對數字技術的運用存在一定的欠缺,產業數字化發展相對較慢。由圖2可以發現,2005年我國數字經濟剛剛起步時,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各占一半的構成比例組成,之后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并與其他產業不斷融合,產業數字化在該比例的作用不斷凸顯。與此同時,其數字產業化的作用不斷弱化,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其所占比重不斷下降,在2019年所占比重跌出20%,反而產業數字化占比高達80.2%。這種變化趨勢恰恰反映了隨著經濟、技術創新等的不斷發展,產業數字化的比重越來越高,正不斷優化數字經濟的內部結構。

圖2 中國數字經濟內部組成部分比重
2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機遇
2.1 國家大力支持
對于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大力支持。習近平總書記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指出,要不斷加快促進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雙向推進,帶動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相互深入交融,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同時,為了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在其他階段我國政府實施了關于助推數字經濟發展的積極政策,例如早期政府實施的“先試水、后監管”的寬容政策,使得很多數字企業在積極政策的刺激下不斷擴大規模,為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2.2 數字經濟綜合市場廣闊
與歐盟、美國相比,我國在互聯網群體上數額較大,目前互聯網群體早已超過9億人,遠超歐盟與美國,且互聯網的普及率也達到64.5%以上。受新冠疫情影響,雖然我國經濟社會和產業受到了一定的沖擊,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同時,受新冠疫情影響,醫療供給緊張、人員就醫困難等問題,社會性問題不斷凸顯,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線上診療的發展,疫情期間在線診療App使用人數的快速增長足以證明此觀點。此外,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許多學生和上班族無法繼續線下上學辦公,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在線辦公、網課學習教育的不斷發展,也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2.3 具備較強實力的數字市場主體
在數字經濟領域發展過程中,我國不斷凸顯一大批出色的、具有引領作用的企業標桿,這些企業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此次疫情中,根據防疫需要,我國數字企業紛紛研發創新疫情防控所需相關產品,與世界其他數字企業相比處于領先地位,不斷彰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受新冠疫情影響,原有線下工廠的工人人數不斷減少,對智能化無人生產的需求不斷增大,推進我國數字企業不斷向智能工廠方向轉型。我國數字經濟在這些強有力的數字企業的帶領下,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3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的相關問題
3.1 產業數字化水平差異大
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受行業利潤水平、規模化程度的影響,三次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速率呈現較大差異,第三產業明顯高于第二產業、第二產業高于第一產業,發展規模具有較大的差異。除此之外,在同一產業內,數字化水平也差異較大,比如在服務業內部,我國生產性服務業數字化水平要高于生活性服務業;在工業生產過程中,一般資本密集型企業要比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數字化水平高,重化工業的企業數字化水平高于輕工業。進一步說明了我國目前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產業間差異化較大的問題。
3.2 “數字鴻溝”現象依然嚴峻
與傳統行業類似,數字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呈現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成為我國“數字鴻溝”的一個重要體現,也制約著經濟的發展。除此之外,我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呈現由東部向西部逐漸遞減的狀態,與GDP的發展態勢幾乎相同,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也恰恰說明了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密切。根據胡煥庸線對我國數字經濟進行劃分,在數字經濟指數加總得分項中,東南地區為887.7分,在全國省份的占比高達89.5%,而與之對應的西北地區情況并不樂觀,加總得分僅為104.4分,相當于東南地區指數加總得分的11.8%,在全國省份占比也僅為10.5%,進一步表明了東南沿海是我國數字貿易發展勢頭良好的主要集中區,而中西部與之差距甚大。
3.3 數字企業國際化程度嚴重不足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企業雖然在快速發展,但將其置于國際領域,與世界上的數字企業相比,我國數字企業的弱項還很大,國際化程度和競爭能力還不強,并且呈現國際市場份額小等現象。一方面,由于國內外市場環境、競爭模式的差異,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方式差異很大,適應國內市場的企業經營方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無法適應國際化要求。另一方面,我國數字企業缺乏國際化經驗,很多企業國際化運營的原動力不強,只可局限在國內市場的競爭中,不會選擇具有一定風險性的國際市場。
4 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
4.1 數字經濟創新能力不足
在技術創新的不斷驅動下,我國數字經濟得以穩步發展,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不難發現,我國在核心技術與基礎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許多關鍵性數字技術仍然依靠西方國家,數字創新能力遠遠落后于發達經濟體,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從根本上改變。這就意味著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卡脖子”問題仍然存在,技術創新水平、高質量發展程度、生產力水平等還有一定的差距,有待進一步加強與提高。
4.2 數字經濟領域人才缺乏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雖然是人口大國,在勞動力方面占據一定的優勢,但對于數字經濟創新人才而言,我國的挑戰和弱項十分明顯,并且對該領域的創新人才、高端研發技術人才等還不能滿足數字經濟發展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其培養周期長等問題的困擾。目前,我國很多高校雖開設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專業,但相對而言,起步較晚,并且培養一個合格的數據工程師周期較長,使得我國數字人才的培養速度明顯低于數字技術發展與應用的速度,導致了數字經濟領域人才供給不足。
4.3 全球數字經濟中的話語權不強
近年來,數字經濟的日益發展已成為各國在國際競爭中爭奪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雖國際地位和話語權有所提高,并提交關于數字貿易的相關議案,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數字經濟起步較晚,還存在一定的缺陷,在關于數字貿易等相關法律建設方面相對滯后,使得我國提出的貿易交易標準與其他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異,在交易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是被動適應別國完善的貿易準則,也就使得我國在數字貿易中的國際話語權不斷降低,無法得到大家的認可與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