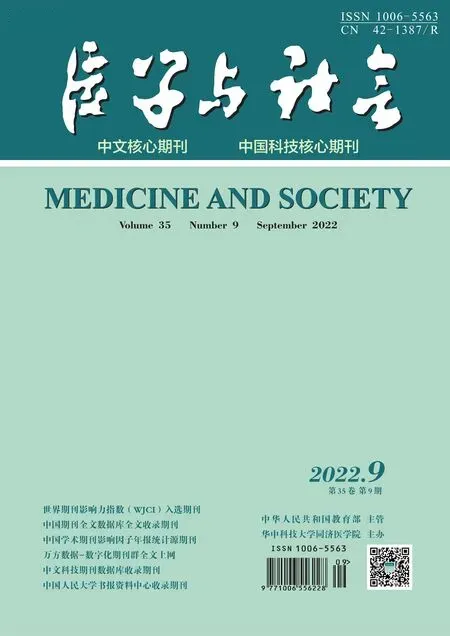我國急性主動脈夾層院前救治延遲現況及原因
方 瑜,胡 濤,嚴 麗,羅嘉臻,肖亞茹,黃素芳,李樹生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急診科/ICU,湖北武漢,430030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逐年上升,死亡率也居高不下,給人類健康帶來極大危害。《“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心腦血管疾病是我國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國家要求到2030年我國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到190.7/10萬以下。急性主動脈夾層(acute aortic dissection,AAD)是最復雜兇險的心血管疾病之一,病死率僅次于急性心肌梗死,是急診死亡的常見原因之一。如何提高AAD患者的生存率、救治效率至關重要。
AAD作為一種嚴重的心血管疾病,具有起病急進展快的特點,病死率高從30%到60%不等[1],同時疾病救治難度大。未經及時治療的AAD患者早期死亡率會以每小時1%-2%的速率增加[2]。由于疾病的救治效果與時間強相關,院前救治延遲的產生會導致消耗大量寶貴的救治時間,造成患者死亡率增高及并發癥增多。
在我國急救工作中仍存在院前延遲現象[3],其中AAD的院前延遲報道也逐漸增多[4],分析AAD院前延遲原因并采取相應對策對提高疾病救治意義重大。近年來國內關于院前延遲的研究多圍繞急性心肌梗死和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等疾病展開[5-6],但對于同樣是治療獲益程度與搶救時間強相關的疾病的AAD的研究較少。本文通過Pubmed數據庫、Cochrane 圖書館、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維普數據庫及國家衛健委網站,搜索AAD院前延遲相關內容,結合我國AAD院前救治現狀分析我國AAD院前延遲的相關原因,擬對目前問題主體要素進行完善以及基于現有主體要素現狀假設下的診療體系優化,從這兩個層面上探索目前 AAD 診治流程中的瓶頸環節及初步對策。
1 AAD院前救治延遲概念及現狀
急診醫學里院前時間一般指患者出現癥狀至患者到急診科的時間,由決定就醫時間和轉運時間共同組成[4-5]。決定就醫時間是指患者從發病到決定就醫的時間;轉運時間則指患者從決定就醫到達首診醫院的時間[4]。院前延遲一般指患者從發病至到達首診醫院的時間延遲。然而與急性心肌梗死和缺血性腦卒中相比,AAD癥狀更復雜多樣,更具有隱匿性和欺騙性,導致大部分的AAD患者常常需要轉輾于同一醫院內多個科室甚至多個醫院才能確診。又因其治療復雜,難度大,要求的手術條件更高,導致患者需要轉至高級別的醫院進行治療。也就是說,首次就診的醫院和科室不一定能提供有效的診療。在這一情境下,院前時間的傳統定義對AAD而言顯得未必適用。
如果我們僅僅關注從患者出現癥狀至到達首診醫院或急診科的時間,并將其作為院前延遲進行研究[5, 7],則在科學研究上可能混淆了首診醫院、轉診醫院和有效救治醫院三個不同的概念。結合文獻和前期的管理經驗[5],我們梳理了中國AAD患者常用就診途徑并簡化成圖1。

圖1 AAD患者不同的就診路線及部分時間節點
中國AAD患者的就診路徑可以總結為以下三條:①路線1(典型直達路線),在這條路徑上患者首診醫院(或首診科室)即可提供有效救治;②路線2(典型的二甲轉診路線),患者到達的首診醫院無法進行提供有效的救治,患者需要轉診至路線1中的醫院;③路線3(典型社區醫院轉診路線),在這條路徑上患者從首診醫院到最終進入有效治療醫院耗時最長,就診過程中可能歷經了數次的轉診和延誤;從圖中可以非常直觀的發現,路線2或路線3的患者與路線1的患者相比,即便他們的院前時間相同(到達首診醫院的時間),但他們得到的救治質量卻存在巨大的差異。僅僅干預基于這個時間界定篩選出的危險因素,而忽略了圖中所示的路線1(最優路線)和路線3(最差路線)之間的巨大時間空隙及背后的原因,也許才是造成目前AAD死亡率下降不理想的原因。因此,對于AAD而言,院前救治延遲時間窗口概念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本文認為將其定義為患者出現癥狀至到達有效救治醫院的時間也許更為合理。
AAD是一種治療獲益程度與搶救時間強相關的疾病,其死亡率及傷殘率與救治時間長短有密切的關系。救治越晚,預后越差,未經及時治療的AAD早期死亡率以每小時1%-2%的速率遞增[2],24 h內、1周、2周死亡率分別為50%,66%和80%[1]。患者錯過最佳救治時間將嚴重影響疾病救治和患者的生存質量。因此,控制救治時間對于降低AAD死亡率而言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國的急診AAD院前急救的臨床科研工作仍比較薄弱,國內尚缺乏標準的院前AAD患者數據庫。而國外的研究顯示高達 28%的患者在尸檢時才明確AAD診斷[8],這表明相當一部分的AAD患者尚未到達醫院就已經死亡,對該人群統計中可能出現數據丟失,這可能導致死亡病人數量的低估。
近年來,我國對AAD的有效救治進行了一定探索,其組織體系主要依賴于胸痛中心。胸痛中心是一種基于區域協同的醫療急救服務模式,是急診急救體系建設的其中的一種重要形式,橫向通過多學科整合,縱向通過建立院前急救、院中治療、院后康復及預防的一體化醫療服務模式[9]。截至目前,中國胸痛中心注冊單位達到4766家,通過認證1672家,已經全覆蓋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9],能夠對于胸痛的常見疾病(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主動脈夾層等)進行快速有效的急診救治。
AAD作為胸痛類疾病的一種,胸痛中心的建設縮短了AAD患者院內診療時間,對于救治時間的控制起到了一定的幫助,但仍存在許多問題[10-11],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各種因素導致的院前延遲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并且AAD的救治研究主要集中于院內救治,然而院前救治的重要研究工作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為提高AAD救治的效率,迫切需要控制總體救治時長,特別是重視院前救治延遲問題,這是AAD救治過程中的關鍵性問題之一,也是我國急診醫學中急需解決的瓶頸問題。
2 AAD院前救治延遲研究和原因分析
2.1 AAD院前救治延遲研究的梳理
進入現代醫學時代,新醫療技術的運用提高了AAD的救治效率,但總體上AAD患者的死亡率并沒有明顯的改善[12],有臨床研究報道AAD由于其病情的特殊性導致其院前延遲現象仍十分普遍[13]。通過文獻檢索可以發現目前問題的難點及熱點集中于AAD院前延遲的關鍵時間窗的確定及影響因素的影響。
目前,對于急性心肌梗死和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院前延遲時間窗界定非常明確[5-6],但AAD院前延遲的時間窗卻十分模糊。關于時間窗的研究,國內幾乎處于空白狀態。在國外的研究中,我們發現研究者們多自行定義院前延遲的時間窗口,將文獻進行梳理發現,目前一般取院前時間的50%-75%百分位數作為時間截點,大于時間截點者被認為存在院前延遲,大多數研究均用中位數(時間非正態度分布)表示患者院前時間的平均情況,說明數據呈非正態分布,且時間跨度相當大,范圍在1.25 h-18.1 h[14]。因此如何界定AAD的患者院前延遲的時間窗,是繼院前延遲概念后又一需要明確的問題。
國內學者們還針對AAD的轉診延遲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何瑜媛等發現Stanford A型夾層、血壓控制欠佳、疼痛、恐懼心理等是主動脈夾層患者轉診的風險因素[15],金立貝等人對轉診過程中血壓和心率控制等方面的臨床意義進行相關研究[16]。郭志軍用CTA結合臨床指標評估轉運風險,發現假/真腔比值與休克明顯相關,對轉運風險評估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17]。其他研究多是護理體會,且病例數不多,原始研究相對比較匱乏。
在管理層面,南京鼓樓醫院以心胸外科為中心,聯合江蘇省大血管疾病診療中心,以6小時現代工具路程為輻射半徑構建AAD急救輻射平臺[18],利用團隊資源管理概念組建了多學科的AD救護團隊,從而將患者從入院到術前時間縮短至12小時內。該研究初步肯定在國內構建跨區域AAD急救管理平臺降低院前延遲的積極意義。
從文獻梳理的結果來看,學者們普遍認可AAD院前救治延遲對于疾病有效治療的意義,但是由于缺乏大數據的支持,對造成AAD院前救治延遲的前因并未進行規范性的整合研究,進而也未能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特別是未對AAD院前救治延遲時間窗口給出科學明確的界定,這些都將成為將來研究的理論基點。
2.2 AAD院前救治延遲的原因
目前國內外關于AAD院前延遲的分析較少。考慮到AAD本身的特點,借鑒急性心肌梗死和急性缺血性腦卒中(在急診醫學范疇都屬于救治過程有強時效性的疾病)的經驗,本文根據疾病共性的特點,分析可能造成AAD院前延遲的因素如下:
2.2.1 患者就診延遲。決策延遲是急性心肌梗死延誤病情最常見的原因,受患者的文化程度、年齡、收入等影響[5],這一點同樣在AAD患者中表現明顯。不同類型患者的院前延遲也不一樣,而同樣是心臟病史,有心臟手術史的患者比無心臟手術院前延遲的比例較高,而有心力衰竭的患者院前延遲比例較低,其次AAD患者的自覺癥狀嚴重程度、發病后采取的措施、選擇的入院方式及發病癥狀等都會對院前延遲有一定的影響[4];此外,公眾對疾病的認知不夠也是導致患者就診延遲的原因之一,如對于急性心肌梗死的認識不足,有研究顯示就診延遲患者高達32.6%[19]。患者的就診延遲,究其原因在于急救知識的不足和“諱疾忌醫”的就醫心態,同時AAD昂貴的治療費用也對患者的治療決策產生影響[20],總體上會導致救治時間的浪費,對于AAD這類與急救時間密切相關疾病,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嚴重的后果。
2.2.2 診斷延遲。一部分AAD患者起病隱匿,缺乏典型特征,臨床表現呈多樣化,且發展迅速。該疾病的臨床診斷對臨床經驗及檢查設備要求較高。在我國很大一部分患者的初步就診在一級醫院或門診,這就會導致診斷延遲。診斷延遲是造成AAD院前延遲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研究的最多的風險因素。在國外利用風險評分來節約評價時間,如主動脈夾層風險評分等。多中心前瞻性的ADvISED的研究發現,初篩時ADDRS=0或≤1加上D-D二聚體<500 ng/mL的敏感性較高,但特異性僅有18.2%和57.3%[21],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增加了胸片或CTA的結果,初始診斷正確率有所提高[22]。但影像學檢查的實施往往是在醫生考慮到患者具有AAD的可能的前提下才會進行,這需要醫生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這一點恰巧是基層醫療的薄弱環節,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此外,預判環節的增多往往伴隨著醫療費用的增加、醫療資源的消耗、醫療耗時的延長。臨床經驗不豐富的醫生在AAD的診療過程中容易出現兩個極端:①應該立即檢查的高危患者被忽略,造成了漏診;②部分低危的患者做了過多的檢查,增加了患者的負擔和風險。總而言之,病情的復雜性和確診的要求較高導致了不同程度的診斷延遲,進一步導致治療延遲。
2.2.3 轉診延遲。AAD在醫療欠發達的地區的發病率遠高于發達地區[23],這就導致大部分的患者第一就診醫院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由于手術的高復雜性及高風險性,往往需要在三級醫療機構進行對應的手術。據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共1022922個,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社區衛生院/鄉鎮衛生院/診所/醫務室/村衛所)有970036個,醫院35394個,其中三甲醫院1580個,占比僅為4.46%[24]。這種醫療資源不均勻分配直接導致大量的患者需要轉診到更高一級的醫院。然而目前尚缺乏與高轉診率相匹配的成熟的AAD轉診體系。雖然國家急診專業質控中心2022年發布了《危重癥患者院際轉運專家共識》[25],但對于AAD患者的轉診治療依據、轉診方式、轉診半徑與目的等關鍵性問題并沒有具體的統一流程和方案,實際指導價值有所欠缺。共識的發布也反應了國內對AAD轉診相關的原始研究不足,如何進行高效的轉診減少轉診延遲也是目前急診面臨的重要課題。
2.2.4 其他因素導致的延遲。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地理環境、天氣、使用的交通工具等條件)的不同,也會導致院前延遲。例如在轉運過程中常見的地理差異就是導致A型AAD患者院前延遲的因素之一。這點與急性心肌梗死和急性腦梗死患者情況一致。研究發現居住地點、發病地點與首診醫療場所的距離、首診醫療場所的等級是腦卒中患者院前延遲的主要因素[26]。有研究對冀中地區腦卒中急救工作的分析顯示發病地點與醫院距離>20 km是院前延遲重要的原因[6]。同樣對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而言,距離也是導致院前延遲的主要因素[11]。雖然對于AAD的院前研究目前仍比較匱乏,但在臨床工作中觀察到AAD患者達到居住地最近機構的時間也是造成院前時間延長的原因之一。此外采用的交通方式,交通路況,天氣的變化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轉運效率,導致院前延遲的產生。
總之,影響AAD患者院前延誤的原因涉及到疾病本身、患者、醫務人員、醫療機構、甚至天氣地理條件等。如何厘清多維度多角度的因素之間的相關作用以及對院前延遲的作用途徑和方式,是解決AAD院前救治延遲這一瓶頸問題的理論基礎。
3 AAD院前救治延遲的對策
針對上文所歸納出導致AAD院前救治延遲發生的原因,本文認為其解決思路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個層次:對現有主體要素進行完善、基于現有主體要素維持現狀假設下的診療體系優化。
3.1 對現有主體要素進行完善
3.1.1 針對患者就診延遲。由于患者對疾病的認知程度等會對院前延遲有一定的影響,加強對疾病的宣傳教育工作就尤為重要;目前在我國AAD患者具有年輕化趨勢,基礎保健及教育工作需要進一步提前普及。在政府機構的主導下,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可以多樣化和多媒體化,以增加在新形勢下的醫學教育成效。例如孫慧等人提出利用互聯網+三位一體護理模式加大科普力度,通過這種形式能夠更好的提升患者對疾病的認知和應對方式[27]。同時針對患者治療費用問題,需要國家衛生部門在醫保制度上進行深度改革,增加醫保投入,提高醫保使用效率,減輕患者治療負擔,進而讓患者出現癥狀時能夠積極及時的就診。
3.1.2針對診斷延遲。在AAD診斷延遲中基層衛生醫療機構救治經驗不足,缺少有效快速的確診手段的問題最為突出。提高基層醫院的診療水平,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①可以通過加強繼續教育教育、提高資質標準等傳統的方式,提高基層醫療人員的對疾病的認識和診斷水平。②除了增加基層的檢驗檢查醫療器械外,還可通過現代化診療工具來提高診斷準確率,如借助人工智能技術構建輔助決策系統、利用5G技術實現遠程會診、區域資源共享等方式來實現[28-29]。
3.1.3 針對轉診延遲。目前醫療資源分配不均,AAD患者的轉診仍然很普遍的現象,院前延遲十分普遍。為了患者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這就需要在政府領導下集中現有醫療資源,進一步加強管理水平,優化資源配置,完善轉運路徑,提高救治效率。如鄧先鋒等學者提出多學科聯合專病急救綠色通道的模式以及江蘇打造的AD急救輻射平臺整合了醫療資源、提高了急診救治效率[30],這在局部區域實現流程優化,減少轉運,經驗值得推廣。
3.1.4 針對疾病診療過程中的其他原因。對于地理環境、天氣、交通工具等因素,應該進行全面系統評估,結合區域情況,做好轉運預案,納入患者轉診轉運過程的關鍵點進行控制,優化轉診半徑和轉診方式,節約轉運時間。比如對于在地理環境中,陸地交通不方便的地區可采用直升機轉運,目前AAD患者的航空轉運工作正在起步探索階段[31],且取得一定的初步經驗。
不難看出,上述主體要素的完善都需要較多的資源投入,需要較長時間去執行和調適。誠如202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推動優質醫療資源向市縣延伸,提升基層防病治病能力,使群眾就近得到更好醫療服務”,但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較長時間和較大投入進行建設和完善。其中一些主體要素短期內可能無法解決,比如地理因素和氣候原因所造成的院前救治延遲需要診療機構地理布局的優化,這些可能需要政府更多的醫療資金投入,在更大范圍內協調,較長的時間去調整優化,短期內難以完成。因此,在進行對于AAD主體因素進行優化時,目前較為現實和有效的解決方案可能是對主體第二層次的診療體系優化。
3.2 基于現有主體要素維持現狀假設下的診療體系優化
基于現有主體要素維持現狀假設下的診療體系優化,可以從技術方面和管理方面進行優化,以加強系統性風險控制和醫療資源潛能釋放。
3.2.1 采用新技術推動醫療的進步,加強系統性風險控制,提高AAD的診治效率。目前急需建立或完善院前AAD患者的臨床數據庫,利用現代技術進一步分析院前的具體環節,探討AAD院前延遲的時間窗,尋找院前延遲的關鍵點,加強系統風險控制以優化救治效率。目前人工智能在臨床運用越來越廣泛,研究者團隊曾成功的利用卷積神經網絡構建了COVID-19臨床輔助決策系統[32],解決了多專科醫生深入一線,對疾病診治能力參差不齊的問題,提高了診斷能力并進行精準分級治療。筆者以為可借鑒該方法,以構建智能化的AAD院前救治延遲的風險預測及評估模型,設計人工智能輔助診斷及轉診系統。具體可以從患者延遲/診斷延遲/轉診延遲/地理等其他因素造成的延遲四個類別設計到多個維度的指標。如在醫學(疾病本身的特點)、心理學(如患者發病時的反應,決定就醫的方式、態度和選擇等)、社會學(如患者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等)、氣象學和地理學(地理位置,海拔以及天氣對轉診的影響)、醫療費用(經濟水平,費用支持主要來源)等方面對疾病在特定時間段內預后(痊愈、死亡或者后遺癥等)進行數字化處理,進行計算機分析預測,決定轉診的時間窗口和方式等。利用構建基于控制AAD院前救治延遲風險的人工智能輔助診斷及轉診系統等方式,最大程度的減少基層的診治水平的差異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優化提高現有的診療體系的效率。
3.2.2 利用現代的管理方法,優化AAD的轉運流程,釋放醫療資源潛能。采用合適的管理方法,可以利用多種管理工具來提高AAD患者轉運效率,最大程度緩解我國醫療不均勻的問題,充分釋放我國的醫療資源潛能。例如針對患者轉運延遲的問題上,可在深入推廣急性主動脈夾層院前救治延遲風險控制管理模型的基礎上,使用計劃評估和審查技術(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PERT)網絡分析法、圖論等方式來設計急性主動脈夾層的轉運流程[33-34],尋找醫療最安全,耗時最短,成本最低的臨床路徑。這也能夠快速縮小基層與上級醫院診療和管理上的差距,并可以借助計算機智能系統對患者預后準確分級,根據患者嚴重程度及可能需要的治療方式,結合當地醫療服務能力實施精準轉運,減少院前延遲。最終實現在基于現有主體要素下最大限度地減少院前救治延遲這一目標,提高急診救治效率。
總之,在我國主動脈夾層的院前延遲的現象仍比較普遍,其嚴重性被普遍低估,目前AAD院前救治延遲研究仍比較匱乏,分析表明患者延遲、診斷延遲、轉診延遲、和地理天氣等其他因素是其重要的影響因素。基于中國國情和AAD院前救治的現狀,從對現有問題主體要素進行完善和基于現有主體要素現狀假設下的診療體系優化兩個層面著手,針對性處理現有主體要素問題,加強系統性風險控制和醫療資源潛能釋放,對減少院前延遲提高AAD 診治效率有較大的臨床意義和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