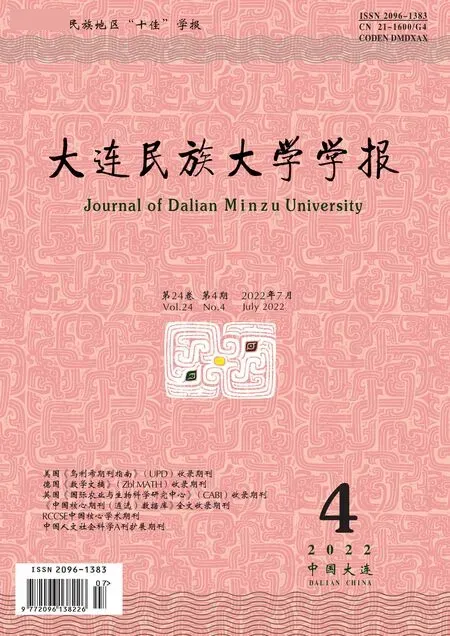原深度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可行能力的提升路徑探析
——以甘肅省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為例
田 甜,王 艷
(大連民族大學 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遼寧 大連116605)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的問題,進入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發展階段。在后扶貧時期,相對貧困的問題仍然存在,并在區域和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性,而少數民族女性作為特殊貧困群體和相對貧困群體,是鞏固脫貧成果、接續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對象,也是反貧困的重要力量,需要政府、社會重點、持續的關注與幫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到新時代,在解決溫飽問題之后,人們對于貧困的認識不僅局限于經濟收入,而更加重視發展能力的提升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諸如兩性平等、性別公正等。著名的倫理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將貧困界定為對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和社會排斥。可行能力則指的是一個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的組合[1]社會排斥則是指個體獲取發展資源的機會受限。不同于以往只關注單一經濟指標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將目光聚焦于人的發展能力,不斷擴大信息基礎,擴展以工具性自由和建構性自由為基礎的可行能力去實現人的自由發展,即發展的過程就是擴展人類以可行能力為基礎的自由的過程。在阿馬蒂亞·森看來,工具性自由涵蓋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保障和防護保障等多個方面;建構性自由則是強調作為行為主體的人,在謀求自身發展、擴展可行能力過程中的主動性。以阿馬蒂亞·森有關可行能力的論述為理論基礎,引入社會性別的概念,用以分析臨夏縣麻尼寺溝鄉少數民族女性在脫貧過程、謀求發展時所面臨的制約因素。不僅能使評估能力貧困現狀時所涵蓋的內容更加全面,還能提供一個嶄新的分析視角。
一、麻尼寺溝鄉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可行能力缺失現狀分析
麻尼寺溝鄉位于中國“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之一的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南部山區,現轄13個行政村,5054戶25742人(臨夏縣統計年鑒(2010-2020))。該地區為多民族聚居地,主要有漢族、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等6個民族,其中回族人口占68.39%,生產方式以農業為主,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傳統文化氛圍濃厚。自精準扶貧工作開展以來,通過“黨建+扶貧車間”“產業扶貧資金”“危房改造”“易地搬遷”等惠民項目,取得了可喜成效:全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從2013年的2314戶11305人減少到2018年底的590戶2364人,于2020年底所有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目標。同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2815元增加至2020年的6934元。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惠民項目、扶貧政策大都以戶為單位,多以當地男性參與為主,女性更多的是在反貧困實踐中扮演輔助性角色,其主體地位、主動性難以得到充分發揮。盡管巾幗家美積分超市的成立、公益性崗位、拖鞋鉤編勞動技能培訓等有效提高了當地少數民族女性在脫貧實踐中的參與度。但就總體而言,仍在扶貧政策制定和惠民項目設計時缺乏性別敏感度,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當地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可行能力相對匱乏的現狀。
1.工具性自由的缺失
在阿馬蒂亞·森看來,工具性自由旨在促使幫人們按照自身的意愿過有價值的生活,直接表現在對人們發展可行能力的擴展。為了進一步貼合當地的實際情況,筆者將從教育、經濟、防護性保障、公共生活與家庭生活的話語權四個方面進行工具性自由缺失的現狀分析。
在教育方面,該地區教育事業發展水平較低,歷史欠賬多。根據表1的人口結構比較可以得知,該地區群眾文化構成以小學為主,且比例不高,僅占總人數的27.8%,與全省相差9.11個百分點;高中程度人口僅占1.1%,大學程度出現斷層。盡管鄉、村、家長、幫扶干部、學校多方聯動制度的推進,“兩免一補”、營養餐、雨露計劃等各項政策的落實有效推動義務教育的優質發展,實現了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有學上,上得起,然而全縣常住人口中,15歲及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由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6.36年上升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6.61年(1)數據來源于《臨夏縣統計年鑒(2010-2020)》。。可見,歷史上整體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現實已成為該地區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之一。

表1 第五次人口普查:甘肅全省與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比較表[2]
此外,由于“男孩偏好”和當地盛行的家長男性專權使得人們對少數民族女童教育的重視程度不足。這一觀念造成的影響在以往和現今有著近乎相同的表現:過去,“近80%左右的回族女童集中在小學1-2年級,4-5年級尤其是五年級回族女童占校園女生總數的比例極低。”[3]接受教育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持續接受教育的時間短導致了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教育滯后的歷史,也決定了其文化程度不高的現實;現今,通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教師、村干部、婦聯工作人員等協作勸學,有效提高了當地少數民族女童的受教育年限。但由于部分家長對其接受教育的重視度、關注度不足,以及當地“早婚早孕”的習俗,在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后,部分少數民族女童便不繼續接受教育,這也進一步導致她們難以進入、應對信息化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
在經濟方面,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可行能力的缺失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由于傳統觀念的束縛,難以獲得外出工作的機會;二是由于自身文化素質較低,難以獲得適合的工作崗位;三是由婦女經濟收益所產生的福利更多的流向家庭。隨著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當地多數男性選擇外出工作,留守在家中的少數民族女性則需要負擔起照顧老人、孩子以及農業種植的重荷,并進一步表現出農業女性化的趨勢。對此,當地婦女表示:“不是不想出去干活,走不開。尕娃們長大了,公公婆婆還是需要人照顧的嘛!政府給幫,掌柜的現在擱城里跑車,有時候凌晨2點多還在跑,我總得把家照顧好,把老人伺候好,再忙些地里的活,不得閑。”(2)受訪人:DXW,女,41歲,回族,2022年6月6日在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M鄉訪談。;其次,有機會外出務工的少數民族女性也多選擇在就近的城鎮做一些技術含量低、服務類型的短期工,始終以家庭為生活和工作的重點,并不能使自己擁有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當這些少數民族女性有外出長期務工念頭時,多數將會遭遇來自家庭的阻力,如丈夫以離婚為要挾。多數將會遭遇來自家庭的阻力,并選擇妥協。最后,當地少數民族女性通過參與巾幗就業車間、做零工等獲得經濟收益,更多用于支付家庭成員消費,如購置設備、子女上學、贍養老人等。并且由于對智能手機、銀行卡等接觸較晚,操作不嫻熟,這些經濟收益可能并不是直接掌握在個人手中。對此,一位賣“碾轉”(3)碾轉:臨夏農家特色美食,“嘗新”的青物之一,俗稱青稞麻麥。的婆婆表示“城里年輕人喜歡吃這個。沒事的時候,我就做一籃子拿來賣,也掙些錢花花。十元一斤,賣的挺好的,四五點鐘的時候差不多就快賣完了。那個先進的手機我不得用,不會。我還是愿意收些現錢,踏實。我的這個碼是掌柜手機上的,那個妹子的收款碼是她尕娃的。”
在防護性保障方面,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所從事的是非價值化的家務勞動、農業勞動,其為家庭所付出的辛勞極易被忽視或被邊緣化。由于沒有直接性的經濟收入,她們的生活大多依賴于丈夫,一旦遭遇風險便陷入生活貧困的窘境。通常情況下,幫扶措施以戶為單位,較少有針對少數民族女性的項目。加之,由于受教育水平低、社會參與度低,她們獲取信息得意識與能力也相當有限。
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話語權方面,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可行能力的缺失表現為:外出活動需要丈夫同意、家庭事務由丈夫決策。由于西北民族地區傳承的家長男性專權和男性繼承制,絕大多數女性游離于公共生活領域和家庭生活中重大事務的決策之外,甚至沒有參與商討的機會。盡管現代化進程加快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歧視性的性別觀念,農業女性化的趨勢也使得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有參與家庭農業事務商討、決策的權利,但在公共生活領域中,話語權和決策權仍由男性所壟斷。
2.建構性自由的缺失
建構性自由側重于強調自由是人們價值觀中與生俱來的一部分,是人們天生的追求,強調突出人的發展主動性、主體性地位,成為自由的建構者進而獲得更好的發展,擴展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的自由。
“三從四德”“男主外,女主內”是西北少數民族社區理想女性不可缺少的品質或能力。可以見得,現行的社會性別觀念仍朝著有利于男性的方向發展。當地的部分男性認為,“只有家里條件實在揭不開鍋,才會讓婦女出去打工掙錢。把她們留在家里的初衷是保護、照顧,女的都很‘金貴’,不能隨便出去,照顧好老人、孩子就行了”(4)受訪人:MXL,女,62歲,東鄉族,2022年6月5日在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H鎮訪談。。這種充滿偏見的性別原則也逐漸內化為少數民族女性自身思想觀念的一部分,使她們深受其累而不自覺,進而構成自我覺醒、自身發展的內在障礙。她們往往集傳統性別歧視制度的受害者身份與捍衛者身份于一體,即使現代社會為其提供了新的角色和發展機遇,但她們還是傾向于認同傳統的身份形象。也正是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依附心理強化了現行社會中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秩序。因此,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些少數民族女性不單只是接受“發展”的對象,更應是擺脫貧困、謀求自身發展的主體,激發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發展的內生動力顯得尤為重要。
二、制約麻尼寺溝鄉少數民族女性發展的深層原因分析
“文化是一個集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任何人類作為社會成員所擁有的能力和習慣的綜合體。”其核心意涵為“任何人類作為社會成員所擁有的”[4]。泰勒有關于文化定義的重點是:人類在某種特殊社會條件下的成長過程中,受到該社會的特定文化傳統的影響所具有的屬性。即自然人成長為社會人的關鍵在于接受社會文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發揮的作用巨大,不僅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而且還是特定社會環境下,人類精神文化的整體,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并且,文化的顯著特征是其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在不同文化進行持續不斷的直接接觸時,這些不同文化之間會發生相互適應,并作出一定的改變。因此,從文化、文化適應機制的角度去分析制約麻尼寺溝鄉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可行能力提升的深層原因是具有現實意義和可行性的。
以當地回族社區為例。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歷史表明,它所采取的是一種相適應、相嫁接的方式。在實際傳播的過程中,伊斯蘭教為了進入并適應帶有強烈父權思想的中國社會,將經義中有關婦女問題的消極因素同中國傳統封建禮教雜糅在一起,成為限制少數民族女性思想、行為的桎梏。這些封建思想隨著回族社會的發展得到進一步強化。同時,處于宗教發展的現實需要,一些學者,如明清時期的王岱輿、劉智等,通過“以儒詮經”活動推動伊斯蘭教中國化。這種以傳統儒家思想為載體,再加之著述學者自身的性別觀念,使回族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男女性別差異獨具特色的社會文化結構。并且在文化適應機制運作過程中,作為社會行動主體的人們,通過一代代人的歷史實踐強化了性別差異、性別偏見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并將其世代延續。
此外,與中東部地區相比,麻尼寺溝鄉所處的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且宗教文化氛圍較為濃厚。受伊斯蘭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被牢牢禁錮于家庭之中,社會文化賦予的性別角色使她們的受教育權利受限、勞動技能缺失、進而無法有效參與社會生產,競爭意識下降,服從于傳統觀念的束縛,難以實現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自身價值的追尋。
三、麻尼寺溝鄉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可行能力提升的路徑探析
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在雜糅封建禮教思想的伊斯蘭文化與民族社區傳統文化的雙重形塑下,當地少數民族女性難以獲得良好發展環境、產生迫切發展愿景。因此,需在適應當地文化機制的前提下,四方面著力提升當地女性的發展可行能力。
1.落實九年義務教育、推行教育現代化、引進優質人才,建立少數民族女性反貧困長效機制
國際社會與中國反貧困實踐證明,人口文化素質較低往往是導致貧困的關鍵性因素和深層次原因,貧困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少接受教育和知識的機會,缺乏與現實社會的信息溝通,無法利用現代文明和科技進步的結果。因此,大力發展西北農村少數民族女性教育,尤其是女童教育,有利于控制該地區人口數量、均衡性別比例、提高人口素質,更是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發展可行能力持續性提升的關鍵。
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教育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條件是進入當地的文化機制中,即充分尊重民族性。充分挖掘、整理民族傳統文化中尊重知識的文化資源和伊斯蘭教義中鼓勵求知的論述,在尊重民族特色與習俗的基礎上,大力宣傳女性教育,特別是女童教育對個人成長、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確保九年義務教育落實的同時,重視提升教育質量,以西部人才引進戰略為契機,優化教師隊伍結構;加大對教育基礎設施的投入經費,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同時,合理規劃教育內容,重視對其傳統文化進行重塑,幫助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樹立自尊、自強、自立的觀念,使她們重新認識并爭取優秀傳統文化賦予她們的各項權利,成為可行能力提升的推動者。
2.基于專業技能培訓、結合區位特點進行項目開發有效提高少數民族女性就業率
結合麻尼寺溝鄉區位特點進行產業開發,制度化、組織化的對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進行專業技能培訓和就業引導,是現階段提高其發展可行能力的有效路徑。并且通過精準化的就業技能培訓能切實提高該地區少數民族女性的就業成功率,幫助其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進而有利于建構平等、和諧的性別關系。
為了實現高質量的就業幫扶,需要充分考慮當地少數民族女性的擇業、就業需求。首先,由于文化素質較低、勞動技能欠缺,因此在就業前的培訓十分有必要,并且技能培訓內容的選擇應充分考慮當地少數民族女性的擇業傾向,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她們參加培訓的熱情與積極性。技能培訓的時間安排應是周期性的、持續性的,一定程度上要配合當地少數民族女性的勞作時間。其次,當地男性大多外出務工,家庭中老人與孩子對女性的依賴程度較大。長期外出就業可能對于多數少數民族女性來說,并不現實。基于此,就近進行扶貧項目開發,就業引導將成為首選。最后,當地政府的勞動部門和婦聯機構在幫扶引導過程中要增強社會性別敏感度,做好對接工作,打破“玻璃天花板”效應,為工作能力強的少數民族女性提供良好的發展平臺。在引導和幫助就業的過程中,要保障少數民族女性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受到充分的尊重,同時做好后續工作,持續關注、及時解決她們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難。
3.基于性別視角完善政策措施,多方合力為貧困女性提供社會防護網
阿馬蒂亞·森認為,防護性保障是為那些遭受天災人禍或其他突發性困難的人、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殘疾的人,提供扶持的社會安全網。在家庭生活中,絕大多數西北農村少數民族女性沒有財產所有權和支配權。由于不平等的性別文化規范和村規民約,西北農村社區內部土地流轉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女性的土地權利。這種以男權為中心的傳統觀念對內部土地分配和再分配有著極大的約束力,嚴重影響當地少數民族女性獲得土地資源,使其常以赤貧者的身份進入或離開不同的生活場域。防護保障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少數民族女性窘迫的經濟條件,為她們提供一系列防護性質的保障,進而為當地少數民族女性可行能力的提升提供一個可靠的兜底保障。
為了充分發揮防護保障的兜底作用,應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到幫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之中,增加少數民族女性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生產資本等資產占用、控制及使用的支持,以實實在在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等利益導向機制將對少數民族女性的扶持落到實處。如西北農村回族婦女養羊專項減貧項目,以當地少數民族女性為扶持對象,提供小額借款,鼓勵她們參與實踐;巾幗扶貧車間等布鞋工廠,定期對當地女性進行培訓、引導就業。其次,當地少數民族女性遭遇家庭暴力或經濟權益侵害時,沒有尋求相關單位以及法律保護的意識,往往選擇默默忍受。對此,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顯得尤為重要。如當地婦聯組織,由于女性工作人員多且熱心于婦女兒童事業,往往更容易與少數民族女性建立信任。并且這些工作者對當地少數民族女性的處境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同理心,能夠站在幫助對象的角度思考問題,引導她們樹立自我保護的意識,用法律武器捍衛合法權益。
4.增強女性話語權,挖掘民族文化中有關兩性平等的積極因素,提升女性自我發展能力
話語權僅僅從字面上理解為,說話權、發言權,即擁有表達自身訴求的資格與權利。在公共生活場域,話語權往往與人們獲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位和權益的話語表達密切相關。無論是在公共生活領域還是在家庭生活領域,女性均被排斥在事務商討、決策過程之外,甚至沒有參與權。這將會忽視她們在社會發展中貢獻及自身參與發展訴求,使其淪為現代化進程中的被動參與者。
對此,應首先鼓勵當地少數民族女性走出家門、參與就業。直接性的經濟收入能夠使她們對家庭的貢獻顯性化,而不再只是非價值化的家務勞動。并且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也使她們擁有一定的財產支配權,增強在家庭生活中的話語表達權。其次,不平等的性別制度往往以傳統禮教思想、民族文化為外衣,為了打破對伊斯蘭教義解讀時以男性利益為主的慣例,應充分挖掘并整理教義中有關女性地位、權益保護、性別平等等內容的闡述,鼓勵當地少數民族女性主動打破依附心態和自縛心理,培養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和自主、自立、自強、自信的精神,發出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