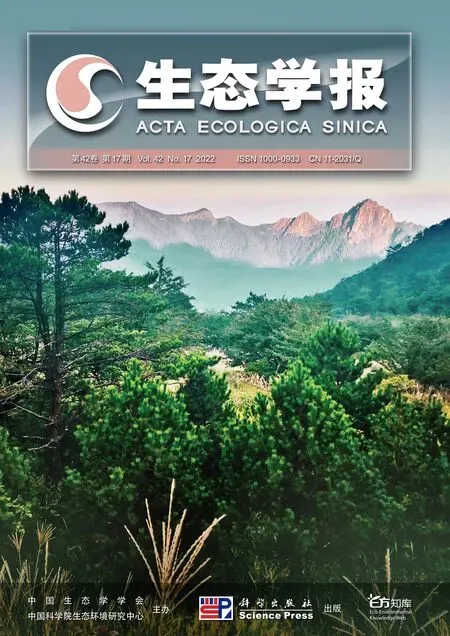大都市區生態源地識別體系構建及國土空間生態修復關鍵區診斷
屠 越,劉 敏,高嬋嬋,孫彥偉,蔡超琳,蘇 玲
1 華東師范大學生態與環境科學學院,上海 200241 2 自然資源部大都市區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工程技術創新中心,上海 200241 3 上海市建設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務中心,上海 200003 4 上海廣境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上海 201822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維持生態安全與城市發展的平衡成為新時代目標,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成為國家戰略工程[1]。構建生態安全格局作為維持城市生態安全的重要方法,能夠有效提升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是識別國土空間生態修復關鍵區域的重要手段[2]。
生態源地指在維持生態功能及生態過程中起重要意義的斑塊,不僅是本地種的重要棲息地,也是維持生態系統服務、保障其完整性與連通性,并提供給人類生產生活豐富產品的重要區域[3—4]。科學和準確識別生態源地是生態安全格局構建與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重要目標,構建因地制宜的生態源地識別體系是技術核心,各地因生態安全需求不同,生態源地識別體系差異較大。研究初期多采用提取自然本底較佳的自然保護區等作為源地[5],后發展為通過多指標體系識別的方法[6—7]。生態安全格局構建與優化的研究起源于景觀生態學背景下的自然資源保護措施[8],對生態系統功能及過程進行探究[9—13],近年來逐漸將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因素考慮其中[14],以期實現人地耦合目標。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相關研究逐漸形成“源地-阻力面-廊道”范式[15—17]。
目前生態源地評價體系相互包含、錯綜復雜,沒有統一標準。已有研究多以基于生態源地定義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7,18]、生態敏感性[19]、粒度反推法[20]、熱點分析法[21]、政府決策或居民意見[22],或結合以上多種方法[23—24]識別生態源地。研究多選取近自然區域[7],或疊加社會經濟因素識別生態源地,較少提及人類需求與自然因素的耦合及指標權重的選取。現有研究多針對生態本底較佳區域,較少以人口高聚集性為特點的大都市為研究對象,探究大都市生態安全格局構建與優化。在構建生態阻力面體系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僅考慮某一類指標層,如僅根據土地利用類型構建阻力面[7]。此外,已有研究針對生態保護與生態修復關鍵區域的概念與識別方法闡述較為模糊[20]或直接混談[18,24],導致生態保護與修復重點區域與生態網絡構建優化等概念互相關聯,關系不甚明確。
本研究以高度城市化的上海市為例,結合基于自然的生態系統服務格局與基于人類的生態環境安全格局與環境友好格局,探究不同土地利用數據源與各格局指標權重對生態源地識別的影響,構建上海市生態源地識別體系,并疊加《上海市生態保護紅線》識別生態源地;在此基礎上,構建綜合生態阻力面,通過最小累積阻力模型及電路理論識別生態保護優先區域(廊道、優先點)與生態修復優先區域(生態障礙點、需優化的非生態用地),構建上海市生態安全格局[25],并提出修復策略,以期為上海市國土空間生態保護與修復及未來城市規劃提供參考,為其他高度城市化區域,以及處于高速城市化發展進程城市的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工作提供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上海市(30°40′—31°53′ N,120°52′—122°12′ E)地處華東地區,長江與黃浦江匯入東海處,北接江蘇省,西鄰浙江省。上海市總面積6340.5 km2,平均海拔約4 m,地勢較平坦,年均氣溫17.3 ℃,年均降水量1649.1 mm,氣候濕潤溫和。2019年上海市常住人口2481.34萬(約為全國1.76%),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37987.55億元(約為全國3.86%),經濟發展促使城市快速擴張,2019年上海市城市化率高達88.10%,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0.60%), 2004年至2017年建設用地面積上漲69.21%,從1825 km2增長至3088 km2[26]。雖然上海市城市化水平較高,但自然資源豐富,是典型的河口濕地城市,具有較高的生態保護研究價值。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研究采用的基礎數據包括土地利用數據集、生境威脅因子數據集、植被因子數據集、水資源環境數據集以及興趣點數據集。
土地利用數據是生態源地識別和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關鍵數據源,由于解譯單位或技術手段不一致,目前不同土地利用產品間存在一定差異。同時,由于遙感數據和解譯方法的局限性,目前土地利用數據的質量存在不確定性(分類精度[27]、分辨率[28]及分類方法[29]等),進而對大都市區生態源地和國土空間生態修復關鍵區的準確識別產生影響。為客觀識別大都市區生態源地,選取4個土地利用主流產品,探究不同土地利用數據對生態源地準確識別的影響。土地利用數據分別來源于清華大學宮鵬團隊(FROM-GLC10[28], 10 m, 2017年;FROM-GLC30[29], 30 m, 2017年)、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GLC-FCS30, 30 m, 2020年, https://zenodo.org/record/4280923#)及中科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CAS-LUCC30, 30 m, 2020年, http://www.resdc.cn/data.aspx?DATAID=335)。
生境威脅因子數據來自OpenStreetMap平臺(2020年);植被因子數據中植被凈初級生產力(NPP)來自美國航天局(2017年, http://reverb.echo.nasa.gov);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來自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2017年);水資源環境數據集中年累積降水量來自中國氣象數據網(2017年),河網密度來自OpenStreetMap平臺(2020年);興趣點數據集中污染性工廠數據來自百度地圖API(2020年),公園數據來自OpenStreetMap平臺(2020年);社會因子數據集中人口密度(POP)及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自中科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2015年),夜間燈光數據來自全球光污染地圖(2020, https://www.lightpollutionmap.info)。
2.2 生態源地識別指標及方法
基于生態安全的廣義層面概念[6],生態源地要滿足人類-自然耦合的目標。本文分別從基于自然的生態系統服務格局及基于人類的生態環境安全、環境友好格局識別生態源地(表1)。生態系統服務格局代表傳統自然環境的生態價值,生態環境安全格局代表人類對空間藍綠資源需求的生態價值,環境友好格局代表人類活動造成自然環境變化(包括負向和正向)的生態價值。從自然需求出發,生態源地要滿足維持生態過程完整、生態系統服務可持續,并預防生態系統退化[30]。生物多樣性價值代表區域物種豐富度,生境質量代表區域生物生存的環境質量,植被凈初級生產力(NPP)反映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而景觀連通性指數代表斑塊對整體景觀生態過程與完整度的貢獻。從人類需求及影響出發,生態環境安全格局通過NDVI、年累積降水量及河網密度代表區域藍綠資源的分布情況;環境友好格局則通過提取人類活動造成自然環境變化的污染性工廠分布(負向)及公園分布(正向)兩個因素構建區域人類活動影響分布。
考慮到植被凈初級生產力與歸一化植被指數高度共線,為盡量消除重復計算的誤差,并保留二者的差異性表達,統籌考慮已有文獻指標權重,降低植被凈初級生產力權重(生物多樣性服務價值∶生境質量∶植被凈初級生產力∶景觀連通性=1∶1∶0.3∶1),以確保同類型/相似指標權重之和與已有研究較為一致。
不同權重代表自然環境與人類需求對大都市區生態源地識別重要性的不同占比:權重一(1∶1∶1)到權重三(5∶2∶1)逐漸增加自然環境相對于人類需求的重要性,對照組為不加入人類需求指標的傳統源地識別方法。結合源地識別效果及已有生態資源分布,確定大都市區人類需求指標添加的有效性及源地最佳識別效果的指標比重。將三個格局按照不同權重賦值疊加,經自然斷點法分為五級,一級至五級賦值之和逐漸升高,取四級、五級區域為生態源地。

表1 基于生態安全格局的生態源地識別的指標及方法
2.2.1生物多樣性服務評估
根據生物多樣性服務當量評估生物多樣性服務價值[31]。其中,林地為4.51,濕地為3.69,水體為3.43,灌叢取林地與草地平均值,為3.19,草地為1.87,耕地為1.02,不透水面和裸地為0。
2.2.2生境質量評估
生境質量指生態環境能夠維持生物生存繁衍的能力,影響因素為土地利用類型與生境威脅因子。本文使用InVEST模型的生境質量(Habitat Quality)模塊評估研究區域的生境質量[18,24]。模型將不同土地覆被與脅迫因子建立聯系,評估生境質量分布特征,公式如下:
(1)
式中:Qxy是土地覆被類型j區域柵格x的生境質量;Dxy是土地覆被類型j區域柵格x的生態環境脅迫程度;Hj為土地覆被類型j的生態環境適宜度;k為半飽和常數。
2.2.3景觀連通性分析
景觀連通性代表生態系統中物質、能量及信息流動的困難程度。可能連通性指數(PC)既可以表征區域整體連通性,也可以表征各斑塊相較整體的連通性高低[32],故本文選取PC進行景觀連通性分析,其范圍為0到1,隨值增大連通性增強,公式如下:
(2)

斑塊重要值代表現有斑塊對于維護景觀連通性的性,以百分比表示。針對PC指數,斑塊重要值(dPC)公式為:
(3)
式中,PC為所有斑塊均存在于研究區域時的可能連通性指數值,PCremove為移除某斑塊后的可能連通性指數值。
2.3 生態阻力面設置
生態系統中物質、能量與信息的傳遞需要克服阻力[33],本文通過最小累積阻力模型構建生態阻力面,模型公式如下:
(4)
式中:MCR為最小累積阻力值;f代表最小累積阻力與研究區域生態過程的函數;min為最小值;Dij為源j到柵格i的空間距離;Ri為柵格i對生態流動的阻力值。
綜合生態阻力面由人類活動格局與自然環境格局組成。人類活動格局下的綜合阻力由不透水面、污染性工廠、道路、POP與GDP為指標構建[24,34—35]。傳統研究多以土地利用類型直接定義阻力值,未考慮物質與能量間的相互影響[20],故本研究加入基于空間自相關的克里金插值法,作為表征氣體、液體或微小固體運動擴散的隱性阻力[36],將基于土地利用類型的顯性阻力面與隱性阻力面疊加形成自然環境格局阻力面。克里金法公式如下:
(5)
其中,Z(si)為第i個柵格的數值;λi為第i個柵格權重;s0為預測的柵格;N為柵格總數。
2.4 生態保護優先區域識別
生態系統的物質與能量流動在景觀尺度上通過斑塊-廊道結構進行[37—38]。研究利用基于最小累積阻力模型與電路理論的Linkage Mapper工具識別生態廊道,并判斷廊道寬度,單位長度阻力低(前10%)的生態廊道為需保護的低阻力廊道,反之(后10%)為需修復的高阻力廊道;生態節點是重要生態廊道的交點/折點[39—40];生態夾點是景觀連通性較高區域,有著重要的生態保護價值[41—42],使用Pinchpoint Mapper工具識別。由于夾點與節點分布高度一致,合并作為生態保護優先點,包含重要廊道的交點、折點為一級點,非重要廊道間的交點與折點為二級點。
2.5 生態修復優先區域識別
生態障礙點指修復后能夠提升區域整體連通性、區域生態系統功能與生態安全的區域,是生態修復優先區,使用Linkage Mapper工具識別。通過設置低阻力移動搜索窗口判斷提升窗口內生態環境對研究區域整體連通性的提升作用[24]。比值越大,窗口區域生態修復優先程度越高。最小成本距離公式如下:
LCD′=CWD1min+CWD2min+(L×R′)
(6)
式中,LCD′為將障礙移除后的最小成本距離,CWD1min和CWD2min分別為窗口至兩個源地的最小累積阻力值,L為移動窗口的長軸長度,R′為窗口新阻力值。
粒度反推法基于反證法,通過構建不同粒度下的生態用地結構,確定最佳景觀連通性的粒度,反套回原始數據識別重要生態斑塊(最佳粒度與原始資料一致的斑塊)與轉換為生態用地后能夠增加景觀連通性的斑塊(最佳粒度相連,原始資料不相連的斑塊)[20]。
3 結果與討論
3.1 生態源地診斷與識別
上海市四種數據源土地利用類型占比如圖1,不透水面、裸地及耕地面積之和占比均超過75%。四種土地利用數據中FROM-GLC10的不透水面面積占比最高(43.02%),與同年中國統計年鑒的上海市建設用地面積占比(48.70%)最接近[43],耕地面積(2566.75 km2)與基于Landsat遙感數據解譯結果(2784 km2)最接近[44]。草地面積占比存在較大差異,FROM-GLC10(8.61%)遠高于其他三種(0.39%、0.48%及1.38%),且與通過Landsat TM為數據源人機結合解譯所得的2015年上海市林地面積占比(7.00%)較為接近[45]。造成草地面積差異的可能原因為分辨率提升導致斑塊面積較小的草地被識別出來,或較低分辨率三種數據源的部分草地斑塊被錯誤歸類為林地。綜上,FROM-GLC10對草地、耕地及建設用地/不透水面的識別效果與已有研究或已發表報告最為接近;數據分辨率主要影響草地識別,其識別效率隨分辨率增加而提升。

圖1 上海市四種土地利用/覆蓋數據源土地利用類型占比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types in four land use/cover data sources in ShanghaiFROM-GLC10與FROM-GLC30為清華大學宮鵬團隊等發布的全球土地覆蓋數據集,GLC-FCS30為中科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發布的首個全球(除南極洲)的土地利用數據集,CAS-LUCC30為中科院建立的多時期土地利用遙感信息庫
上海市生態安全綜合賦值五級分布如圖2所示。權重一(1∶1∶1)識別出的生態源地面積較大,其中面積較多的較高值區域(四級)在權重二(3∶1∶1)中被兩極化,部分轉化為高值區域(五級),如淀山湖、滴水湖與周邊林地區域以及崇明區北部灘涂,部分轉化為低值區域(一至三級),如崇明區、金山區及奉賢區。較高值的兩極化轉變有效提升了生態源地提取的便捷性。
不同權重下生態源地識別效果差異較大。權重一(1∶1∶1)對于自然本底環境較佳的區域(淀山湖、滴水湖以及崇明區灘涂)識別效果不佳,且部分行政區(金山區、奉賢區、浦東新區及崇明區)源地識別面積過大,有悖生態源地選取原則,故認為選取權重一識別生態源地不適宜。權重二(3∶1∶1)與權重三(5∶2∶1)生態源地分布相似,差異主要集中于耕地,由于大都市區耕地能夠體現出更多生態價值[46],權重三(5∶2∶1)能夠提取部分高生態價值耕地,而權重二(3∶1∶1)卻將大片耕地無差別保留,不能有效識別出高價值耕地,故選擇權重三(5∶2∶1)作為識別源地的最佳權重。
不同土地利用數據源對源地識別也存在顯著差異,主要體現在中心城區的源地識別效果、重要藍綠資源識別完整性、提取出源地面積的適宜性三個方面。FROM-GLC10與FROM-GLC30對中心城區源地的識別效果優于CAS-LUCC30與GLC-FCS30;CAS-LUCC30未能識別出淀山湖,FROM-GLC30、GLC-FCS30未能識別出崇明區北部的灘涂;GLC-FCS30在部分行政區(金山區、奉賢區)識別出的四級區域面積過大,保護效益較低。綜上,識別上海市生態源地效果最佳的土地利用數據源為FROM-GLC10,三種格局權重為權重三(5∶2∶1)。

圖2 上海市生態安全綜合賦值五級分布Fig.2 Five-level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valua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Shanghai
3.2 現狀生態源地空間分布

圖3 上海市生態源地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sources in Shanghai
研究識別上海市生態源地202個,總面積920.96 km2,主要分布在非中心城區范圍,呈現南北較多、東西較少的規律(圖3)。非中心城區共198個生態源地,其中浦東新區最多(39),崇明區(32)次之,松江區、奉賢區、金山區均超過20個,寶山區僅5個;中心城區僅4個生態源地,楊浦區2個,普陀區與長寧區各1個,其余無生態源地。嘉定區生態源地雖然數量(18)高于閔行區(10),但面積(26.70 km2)小于閔行區(31.34 km2),說明區域斑塊破碎程度較高;金山區生態源地面積較大(97.51 km2)而數量(23)相對較少,斑塊破碎程度較低,連通性較佳。將直接提取自然保護區、公園及林地等生態本底較佳區域作為源地[47]的識別效果與本文進行對比,二者大體分布趨勢相似,但本研究識別的源地在更小斑塊、更多元化用地類型方面具顯著優勢,差異集中在崇明區北側與東南側(濕地與水體)、青浦區西側(淀山湖水體)、金山區西北側(耕地)及浦東新區中部(草地)。對比直接識別法,多指標生態源地的識別結果與本研究更為相似,如Bai等基于生態系統服務、生態脆弱性、生物多樣性及政府與居民意見識別的生態源地[22],不同的是Bai等識別出了更多崇明區的耕地與浦東新區的草地,這與加入碳儲量與固碳功能、生態脆弱性等指標有關。
按面積規模將上海市生態源地分為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表2)。生態源地的數量隨規模減小而快速上升,微型生態源地數量高達167個,占82.67%,而大型及特大型生態源地均僅3個。上海市微型生態源地數量遠超于其他規模源地,生態源地破碎化程度嚴重,保護與修復任務迫切。
上海市生態源地的空間分布受到城市化水平的顯著影響(表3)。城市化水平較低區域(外環以外)生態源地數量及面積相較外環內大幅增加,數量從5個上升到92個,總面積從11.10 km2上升到167.02 km2,但平均面積略有降低;郊環以外區域(102)及外環-中環區域(92)生態源地數量差異較小,但郊環以外源地總面積是外環-郊環的4.4倍,即城市化水平最低的郊環以外區域生態源地連通性最佳。綜上,上海市生態源地的數量與面積與城市化水平高度相關,以外環為界,以內源地數量與總面積極少,分別為3.96%與1.69%;生態源地的平均面積以郊環為界,以外(7.24 km2)遠超以內(0.96 km2—2.22 km2)。

表2 上海市生態源地面積分類統計

表3 上海市城市四個環線劃分區域的生態源地分布
3.3 生態保護與修復優先區域識別
上海市自然環境格局阻力、人類活動格局阻力與綜合生態阻力分布基本一致,高值區域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圖4)。中心城區中,長寧區與楊浦區在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格局的高阻力面積較低于其余行政區;由于寶山區周邊豐富的綠地資源將中部不透水面包圍,其中部阻力值較高而周邊阻力值較低。與已有研究相比,在總體阻力面分布趨勢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突出了人類活動對綜合阻力的貢獻,豐富了中心城區阻力面的變化[47]。

圖4 基于“人類-自然”耦合的上海市生態阻力面空間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esistance surface in Shanghai based on coupling of “Human-nature”

圖5 上海市生態保護優先區域Fig.5 Priority area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Shanghai
上海市生態保護優先區域由“面(源地)-線(廊道)-點(優先點)”組成(圖5),生態源地及生態廊道的分布與上海市政府2021年6月批復的《上海市生態空間專項規劃(2021—2035)》中“九廊十區”分布較為一致[48]。研究識別出生態廊道共計442條,根據已有研究[49—50],廊道寬度取400 m時整體生態效益較高。高阻力廊道圍繞中心城區分布,少部分位于浦東新區中部;低阻力廊道主要分布于遠離中心城區的上海市行政區邊界附近,包括崇明區北部、浦東新區東部、奉賢區南部及青浦區南部。本研究生態廊道的空間分布特征與已有研究類似[47,51],且較好的彌補了已有研究針對中心城區生態廊道匱乏的不足。上海市生態保護優先點共306個,浦東新區最多(87),奉賢區(43)、松江區(35)、青浦區(33)、崇明區(32)及嘉定區(30)數量較多,金山區(18)、寶山區(14)及閔行區(13)數量較少,中心城區除長寧區(1)外均沒有分布。
上海市生態修復優先區域由生態障礙點與需優化的非生態斑塊組成(圖6),二者分布差異顯著,嘉定區及浦東新區較多。生態障礙點區域共309.78 km2,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區外東、西、南側,浦東新區面積最大,為96.14 km2,崇明區及中心城區不存在障礙點區域或極少分布,區域景觀一致性較強;上海市最佳生態景觀組分為400 m,需要優化的非生態斑塊主要集中在嘉定區北部與浦東新區中部,主要為耕地與不透水面,共95個,占地15.69 km2。
需優化的非生態斑塊與生態障礙點作用均為提升連通性。基于粒度反推法提取的需優化區域通過合并或剔除生態斑塊,減少斑塊間隔,目的為提升研究區域整體的景觀連通性;生態障礙點通過減少高阻力斑塊增加源地間生態流動,目的為提升生態源地間的連通性。已有研究鮮有將二者進行比較或疊加討論,或僅考慮對研究區域整體連通性的提升[3,20,34],或以提升生態斑塊/源地間連通性為目的[7,18,24,51],而二者對于生態安全提升均存在重要意義,且針對上海市研究發現其互不重疊,或針對生態安全提升具有疊加效應。
生態保護與修復區域存在重疊情況,即作為現狀生態本底較佳的保護區,依然具有很大修復提升潛力,應作為重點修復對象。主要集中在嘉定區南部、寶山區中南部、浦東新區中部及長寧區北部,大多為草地與耕地。對比上海市近40年土地利用變化狀況發現,大多重疊區在周邊城市化程度逐漸加深的情況下自身生態并未發生較大惡化,即大都市的生態修復重點區域應聚焦于城市化擴散的阻力區域,且應多關注生態價值適中的草地與耕地。
4 結論
以高度城市化的上海市為對象構建生態源地識別體系,探究不同土地利用數據源與各指標權重對生態源地識別的影響,輔以《上海市生態保護紅線》確定生態源地。在此基礎上構建適宜大都市的綜合生態阻力面,識別生態保護與生態修復的優先區域。結論如下:
(1) 生態源地識別結果受生態系統服務格局、生態環境安全格局與環境友好格局權重的綜合影響。綜合考慮藍綠資源分布與上海市生態保護紅線,當三個格局的構成權重為5∶2∶1時上海生態源地識別效果最優。基于該識別體系,最終識別上海市現狀生態源地202個,面積920.96 km2,總體呈沿中心城區向外輻射遞增趨勢,南北向分布較為密集。生態源地破碎化較為嚴重,微型生態源地(面積<3 km2)數量占主導地位(167/202)。浦東新區與嘉定區破碎化程度高,崇明區與金山區連通性強。城市化水平影響生態源地分布,其集中分布于外環以外(194個, 167.02 km2),外環以內僅8個微型源地(15.53 km2),郊環以外源地平均面積增幅較大(7.24 km2)。
(2) 上海市生態保護優先區域由“面(源地)-線(廊道)-點(優先點)”組成,其中,生態廊道442條,生態保護優先點306個。上海市生態修復優先區域由障礙點區域和需優化的非生態斑塊組成,面積325.47 km2,其中,障礙點區域309.78 km2,需優化的非生態斑塊95個,占地15.69 km2。大都市的生態修復重點區域應聚焦于城市化擴散的阻力區域,且應多關注生態價值適中的草地與耕地。
本文基于多源數據與“人類-自然”耦合理念構建適宜上海市的生態源地識別體系,并構建阻力面識別生態保護與修復優先區域,形成“面-線-點”的生態安全網絡。目前研究在構建生態源地及阻力面指標體系時,針對多項指標間的重疊與沖突考慮不夠全面,多指標優化將是下階段的研究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