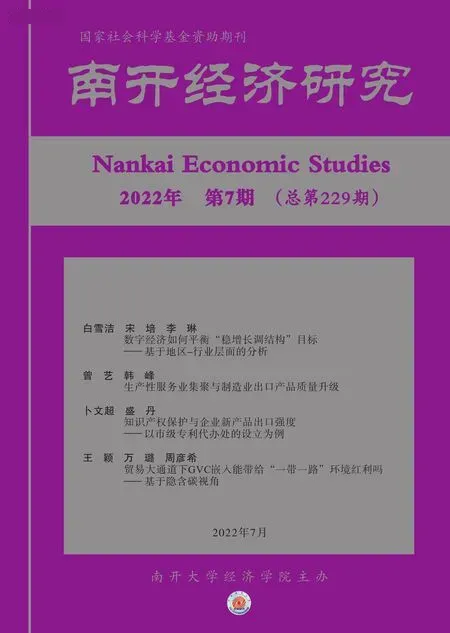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
——以市級專利代辦處的設立為例
卜文超 盛 丹
一、引 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總量的不斷增加,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隨之產生了一系列的貿易爭端問題。美國從最初對華產品實行337 調查,到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再到華為芯片禁售。實際上是以知識產權保護為名,禁止中國企業產品出口,從而對我國進行技術封鎖。可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關鍵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出口產品自身也存在著生產環節較為低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等問題,產業結構亟待轉型和升級。在這一大背景下,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優化出口商品質量和結構,穩步提高出口附加值”。為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開展以高附加值或高技術為典型特征的新產品出口,可能是推動我國實現高質量出口和貿易轉型升級的破局之舉。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政府就意識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為了方便專利申請人申請專利,1985 年,我國在長沙設立了第一個專利代辦處。截至2020 年,共計有34 個城市設立了專利代辦處。實際上,專利代辦處的設立,緩解了原有審查單位的業務壓力,大大縮短了專利審批時間,提升了專利申請效率,增強了知識產權保護,促進了企業研發、自主創新(Chen 和Puttitanun,2005;Qian,2007)和出口新型產品,實現了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為此,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背景下,本文以市級層面的專利代辦處設立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準自然實驗,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視角,考察了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和作用機制,不僅為我國企業提高新產品出口,改善出口結構提供理論支持;也為我國政府制定貿易政策,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政策依據。
目前,國內外學者已經關注了知識產權保護與中國企業出口行為之間的關系,探究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出口的種類、規模、質量、技術復雜度等的作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考察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但遺憾的是,現有研究較少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視角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的出口產品結構的影響。Vernon(1966)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新產品、成熟產品和標準產品三個階段。發達國家在開發新產品和采用新技術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擁有高附加值的新產品,由此可以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頂端,獲得國際貿易中的大部分利益。相比而言,發展中國家只能通過生產和出口舊產品,從國際貿易中獲得較少的利益(劉竹青和盛丹,2021)。因此,本文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視角,探討知識產權保護與中國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之間的關系,對促進中國企業出口產品結構升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事實上,知識產權保護主要通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來影響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專利代辦處的設立會大大縮短專利審批時間,提高專利審批效率,增強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會減少新技術被模仿的風險(Kiedaisch,2015),促進企業研發和自主創新(Chen 和Puttitanun,2005;Qian,2007),有效促進出口(Guan 和Ma,2003;王剛波和官建成,2009)。那么,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的最終效果如何,是否通過企業研發創新對新產品出口強度產生作用?本文以專利代辦處的設立為例,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并探討其作用的微觀機制。
鑒于此,本文利用2000—2006 年中國工業企業和海關數據庫,運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方法,探討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在研究視角上,本文以產品生命周期為研究視角,探討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了其作用機制。這不僅為理解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出口產品結構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還對中國企業出口產品結構優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具體而言,本文借鑒Xiang(2014)的研究方法,對產品生命周期進行量化,將中國企業出口的5000 多種HS 六位產品劃分成794 種新產品和4450種舊產品,以此來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
第二,從研究對象來看,本文用專利代辦處的設立作為衡量知識產權保護的指標,具有一定的新意。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強度難以進行直接測度,雖然現有文獻從不同緯度衡量了知識產權保護(Weng 等,2009;余長林,2011;Maskus 和Yang,2013;吳超鵬和唐菂,2016;鄭長云,2017),但鮮有文獻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進行直接度量。而專利代辦處的設立縮短了專利審批時間,提高了專利審批效率,增強了對企業專利保護的強度。為此,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借助專利代辦處的設立這一政策沖擊,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
第三,從研究結論來看,本文實證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增強顯著提高了我國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提升了新產品的出口地位,改善了我國企業的出口產品結構。同時,影響機制分析發現,知識產權保護主要是通過激勵企業創新來促進企業新產品出口的。此外,知識產權保護還具有一定的異質性,更能促進非國有企業和高生產率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這對我國制定和實施如何增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具有重要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20 世紀60 年代,Vernon(1966)關于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提出,開啟了產品生命周期與貿易的研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包括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Vernon 用產品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解釋了國際貿易的形成原因及方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表明,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上的產品為企業帶來的出口附加值差異明顯,新產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而舊產品具有較低的附加值。所以研究新產品出口對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及對外貿易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Hummels和Klenow(2005)將出口貿易的增長分為廣義邊際(即新產品出口)與集約邊際(即現有產品出口),通過對121 個出口國家和56 個進口國家的進出口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大經濟體中,60%的出口貿易增長是由新產品出口推動的。相反,一部分研究得出不同的觀點,Evenett 和Venables(2002)認為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增長的1/3 貢獻來自現有產品出口,而新產品出口的作用僅為1%左右。Amurgo-Pacheco 和Pierola(2008)通過研究1990—2005 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數據,得出86%的出口貿易增長來自集約邊際,主要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擴展邊際不斷增加。隨后對中國出口貿易的研究中,李坤望(2008)、錢學鋒(2008)、Amiti 和Freund(2010)、陳勇兵等(2012)也均得出出口貿易的主要增長原因是集約邊際,而擴展邊際的作用較小。
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產品生命周期與貿易的文獻相對較少。大部分文獻通過構建理論模型探討了知識產權保護與貿易之間的關系。Chin 和Grossman(1990)最早對該領域進行研究,通過構建南北方的貿易模型,考察了知識產權保護與貿易之間的關系,認為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過強會抑制本國創新,從而不利于本國企業的發展與貿易往來。更強的知識產權保護也會增強創新者的壟斷力量(Deardorff,1992;Chin 和Grossman,1990;Maskus 和Penubarti,1997),如果這種力量足夠強大,那么北方產品的出口將會下降。之后,Ginarte 和Park(1997)也得到類似結論。相反,Taylor(1993)、Maskus 和Penubarti(1997)則認為更強的知識產權保護會促進北方產品的出口,從而說明知識產權保護能促進貿易發展(Wang,2004;Fink 和Maskus,2005)。
隨著1994 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Trips)協議的生效,部分學者開始運用國家和行業等層面的數據,對加強進口國知識產權保護與出口國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Maskus 和Penubarti(1995)通過對1984 年OECD 成員國的28 個制造業行業分析得出,進口國增強知識產權保護促進了OECD 成員國對最低專利敏感性行業的出口,而對最高專利敏感性行業無影響;此外,也促進了OECD 國家對模仿能力強和市場規模大的進口國的出口,而對模仿能力弱和市場規模小的進口國恰恰相反。在之后的研究中,Smith(1999)運用1992 年美國制造業出口截面數據、Weng 等(2009)運用美國出口到48 個國家的出口數據、Awokuse 和Yin(2010)利用向中國出口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和細分制造業行業出口貿易數據、Branstrtter 等(2011)運用美國出口到16 個國家的數據,均得出加強進口國知識產權保護能顯著促進出口國出口的結論。此外,Ivus(2010)還使用1962—2000 年貿易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對發達國家來說,加強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可以大大提高其高技術行業的出口。
然而,在加強本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研究中,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本國知識產權保護對國內自主創新的影響(Park,2008;Chen 和Puttitanun,2005;Qian,2007;Fu 和Yang,2009),較少文章直接考察出口國知識產權保護對本國出口的影響。Rafiquzzaman(2002)對加拿大制造業的出口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促進了本國企業的出口。Raizada 和Dhillon(2017)對從1996—1997 年和2013—2014 年的印度數據進行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余長林(2016)運用中國制造業行業出口數據考察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出口的影響,發現知識產權保護顯著促進了中國總體制造業行業出口的增長。之后,何文韜(2019)考察了中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對本國企業出口強度的影響,發現企業積極申請知識產權保護提升了企業出口強度。
此外,對于新產品的定義,現有統計實踐和學術研究爭論不一。例如,Feenstra 和Kee(2007)采用1990—2001 年中國和墨西哥對美國出口的產品數據,構建的相對產品種類指標就是基于時間和國家對比確定了兩國對美國新產品出口的情況;劉慧和綦建紅(2014)為了考察中國企業對美國新產品出口的策略選擇,以1997—1999 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數據為參照,把1997—1999 年任何一年出口的產品界定為舊產品,把1997—1999 年從未出口、2000—2006 年新出口且至少連續出口三年的產品界定為新產品。但是上述的研究僅僅將某一特定國家或企業首次出口的某一特定時期的產品定義為新產品,無法精確地描述其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的真實階段。而新產品的定義應當以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為基礎,而非局限于某一國家或某一企業(劉竹青和盛丹,2021)。雖然這是第一次向某一國家或企業出口,但是從世界范圍來看,這個產品很有可能早就由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生產并出口,只不過隨著這一產品的技術成熟或價值鏈轉移,才第一次向這個國家或企業出口。該產品很可能在其生命周期中處于衰退期,早已經成為舊產品。
為此,本文參考Xiang(2014)、劉竹青和盛丹(2021)的研究量化了產品生命周期概念,區分了中國企業出口的新產品和舊產品。以專利代辦處的設立作為準自然實驗,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視角考察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作用及可能的影響機制。
三、政策背景與理論分析
(一)政策背景
為了促進我國科技發展,適應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1985 年我國《專利法》正式實施,標志著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實現了質的飛躍。為了方便全國各地的專利申請人申請專利,根據各省份省會距離首都的遠近、各省份對專利侵權案件的審理情況,以及各地區專利的申請情況,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全國范圍內開始設立專利代辦處。1985 年在長沙、濟南、沈陽三個城市設立專利代辦處,隨后,在成都、南京、上海等地逐漸設立專利代辦處,到目前為止在全國各地共設立了34 處專利代辦處,基本覆蓋全國。
專利代辦處是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業務派出機構,是國家知識產權局和地方知識產權局共同的對外服務窗口。《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代辦處管理規定》對專利代辦處的職責和業務做了明確規定。代辦處的工作職能為執行專利法的公務行為,負責專利局授權和委托的專利業務工作及相關的服務性工作。
在未設立專利代辦處之前,專利申請人只能到北京當面遞交或以郵寄等方式提出專利申請。但隨著全國范圍內與日俱增的專利申請,將對單一的專利審查單位形成巨大的審批壓力。而各地專利代辦處的逐步設立,可以分散化審批各地的專利申請,緩解了原有單一審查單位的業務壓力,降低了審批時間,提高了專利審批效率。專利代辦處的設立,承擔了專利申請、專利審批、專利費用繳納等一系列工作,專利申請人可以到當地專利代辦處進行專利申請。這提升了專利申請效率,有助于企業盡快實現創新成果的認定和轉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企業既有的創新成果。而且為地方知識產權宏觀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使其能夠快速、高效和高質量地完成專利審批和專利監管。為此,本文采用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可以有效度量知識產權保護。據專利局統計,到2008 年,我國專利代辦處受理全國2/3 以上的專利申請,收繳的專利費用筆數也占全國的1/2 以上。
為解決內生性問題,本文有效識別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實施效果。由于專利代辦處在各地區設立的時間有先有后,且多選取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這種在地區和時間上的差異便構成了準自然實驗,所以我們可以采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法來識別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影響。
(二)理論分析
實際上,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主要通過促進企業研發創新來影響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可以大大縮短專利審批時間,提高專利審批效率,進而增強知識產權保護。在沒有專利代辦處時,很多企業因距離較遠、成本較高、單一審批單位業務壓力巨大、效率低下等因素無法及時進行專利審批,從而造成專利審批時間過長,專利無法受到保護,大大增加了專利被模仿的風險;而當專利代辦處設立之后,企業可以就近選擇專利代辦處進行專利申請。通過分散化審批各地的專利申請,有利于緩解原有單一審查單位的業務壓力,大大縮短了專利的審批時間,提高了專利的審批效率,從而企業的專利等創新發明在短時間內得到了保護。
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降低創新產品和技術產品被模仿的可能,從而提高創新的回報(Kanwar 和Evenson,2003)。增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有助于提升發達國家的研發創新能力(Park,2008;Fu 和Yang,2009;Krammer,2009),同時,知識產權保護增強還增加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顯著促進了當地企業的研發投入力度和專利數量(Lo,2011),進一步增強技術研發能力,促進中國的技術創新(李蕊和鞏師恩,2013)。
任何一種新產品都是企業研發創新的結果。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初期,產品創新是出口貿易的主要力量,然而到了后期,則是以生產創新為主導(Klepper,1996)。這說明新產品的研發和生產對出口貿易產生重要的影響,技術創新對出口貿易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Sanyal,2004)。技術創新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的出口,改善我國的出口貿易(Guan 和Ma,2003;楊波,2008;王剛波和官建成,2009)。一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將促使本國企業開展自主研發活動(Chen 和Puttitanun,2005;Qian,2007)。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可以提高企業的研發創新能力,促進企業對新產品的研發和生產,從而有利于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并改善新產品的出口地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知識產權保護的增強大大降低了新技術被模仿的風險,提高了企業的創新能力,有利于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提高。
四、計量模型、數據及變量說明
(一)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多時點雙重差分的方法來評估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本文參考Xiang(2014)的研究方法,將中國企業出口產品劃分為新產品和舊產品,構建了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來檢驗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行為的影響,估計的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i、c、j 和t 分別代表企業、城市、行業和年份。Newexport為被解釋變量,代表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本文采用企業新產品出口額占企業總出口額的比重來衡量新產品出口強度,該指標衡量了新產品出口在企業出口中的地位。MPA( treat×post)為核心解釋變量,代表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本文采用是否設立專利代辦處來衡量。X代表一組控制變量,包含了影響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其他指標。ν、ν和ν分別代表了時間固定效應、城市固定效應和行業固定效應。ε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2000—2006 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海關進出口貿易數據庫。我們參考Brandt 等(2012)、Brandt 等(2017)的做法,對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進行處理。由于這兩個數據庫中同一企業的代碼是不一樣的,我們借鑒Upward 等(2013)、田巍和余淼杰(2013)等的匹配方法,采用三步匹配法,將工企庫與海關庫進行匹配。
(三)變量說明
1. 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新產品出口強度。如何確定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識別新產品,是本文的關鍵,也是學術界爭論不一的話題。為此,本文根據Xiang(2005)、Xiang(2014)的做法,將中國企業出口的產品識別為新產品和舊產品。
具體來說,我們根據 Xiang(2014)提供的新產品名錄和代碼,借鑒 Chen 等(2017)、劉竹青和盛丹(2021)的做法,將中國出口產品進行劃分:首先,由于Xiang(2014)提供的新產品名錄中美國的HS 代碼為HS1996 版本,為此我們將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提供的HS 代碼也統一到HS1996 版本,將兩者進行匹配;然后,根據新產品名錄和代碼,將中國制造業出口產品分為新產品和舊產品。最終,我們將2000—2006 年中國制造業企業出口的產品在HS1996 六位碼上劃分為794 種新產品和4450種舊產品。雖然Xiang(2014)對新產品的劃分與本文數據相比早了近20 年左右,但這不會明顯影響本文對中國出口的新產品和舊產品的識別結果。因為新產品大約花費18年才能趨于成熟(Chen 等,2017),并將生產和出口轉移到發展中國家(Antràs,2005),正好符合本文所選擇的時間。
本文選擇中國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用企業新產品出口額占企業總出口額的比重來衡量。其中,表1 匯報了2000—2006 年中國企業的新產品出口情況。由表1 第(1)列可以看出,從2000 年以來,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但2005 年之后略有下降。但總體上中國企業出口新產品的占比較低,所占比重為1/3 左右,說明中國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地位較低。表1 中第(2)列和第(3)列分別報告了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相比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明顯較高。進一步,我們將非國有企業分為非國有民營企業和非國有外資企業,可以發現,非國有企業中的外資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遠遠高于民營企業。表明國有企業新產品出口<民營企業新產品出口<外資企業新產品出口。

表1 2000—2006年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及其變化趨勢(單位:%)
2. 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是否設立專利代辦處MPA( treat×post)。其中,treat為在城市c 是否設立專利代辦處的虛擬變量。如果該城市設立專利代辦處,則該城市為實驗組,treat取1,否則,為對照組,treat取0。經過手工搜集,目前全國共在34 個城市設立了專利代辦處,在2000 年前設立了9 處,在2000—2005 年共設立了10 處,在2006 年及以后設立了15 處。所以將2000 年以前設立專利代辦處的城市從樣本中刪除掉,將2000—2005 年設立專利代辦處的10 個城市設為實驗組,其他城市中的企業設為對照組。post為時期虛擬變量,若城市c 的專利代辦處在第t 年設立,則第t 年及之后時期post等于1,設立之前時期post等于0。與對照組相比,估計系數β的大小反映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的影響。
3. 控制變量
為了避免遺漏變量對本文估計結果產生的影響,本文在多時點DID 模型中加入了影響企業新產品出口的企業層面和行業層面因素。
(1) 企業層面的影響因素。企業資本勞動比(kl),采用企業年末固定資產凈值與年平均從業人員數比值的對數值來衡量;企業規模(scale),采用年平均從業人員數的對數值來衡量;企業投入產出比(input),采用企業中間投入品與產出比值的對數值來衡量;企業工人平均工資(lnwage),采用企業每年應付工資總額與年平均從業人員數的對數值來衡量;企業年齡(lnage),采用企業在市場上存在的時間的對數值來衡量。
(2) 行業層面的影響因素。行業集中度(hhi4),采用四位數行業的赫芬達爾指數來衡量,該值越大,表示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壟斷程度也就越高;行業規模(size),采用四位數行業就業規模的對數值來衡量。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 所示。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根據方程(1)進行了計量檢驗。考慮到方程中的隨機擾動項在同一城市可能存在序列相關等問題,為此,本文參照Hering 和Poncet(2010)的做法,在城市層面對所有的回歸進行聚類調整。表3 匯報了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對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估計結果。其中,在控制了年份、城市和行業固定效應后,第(1)列~第(4)列分別依次加入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發現交叉項MPA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且估計系數依次增大。我們將第(4)列作為比較基礎,結果顯示,交叉項MPA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與對照組企業(企業處于未設立專利代辦處的城市)相比,處理組企業(企業處于設立專利代辦處的城市)的新產品出口強度實現了更大幅度的增長,即知識產權保護會顯著提高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改善新產品在企業出口中的地位。第(5)列在此基礎上加入行業層面的影響因素,交叉項MPA的估計系數依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再次證實了知識產權保護提高了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占比,提升了新產品出口在企業中的地位。

表3 基本回歸結果
(二)DID 有效性檢驗
為證明本文基準回歸結果的準確性,本文從兩個方面進行了DID 有效性檢驗。第一,參考Jacobson 等(1993)的做法,采用事件分析法,考察專利代辦處設立的動態效應;第二,采用人為設定和隨機設定來構造虛假實驗組,實施安慰劑檢驗。均說明了本文基于多時點DID 得到的回歸結果是有效的,即我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提升確實是由于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帶來的。
(三)穩健性檢驗
本部分,我們對基準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主要包括:控制專利代辦處設立的決定因素、縮尾處理以及控制外生政策沖擊等三個方面。
1. 控制專利代辦處設立的決定因素
為了有效識別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的影響,剔除其他可能影響因素的干擾,本文還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控制了決定專利代辦處設立的影響因素。本文發現各城市專利申請數量、省會距離首都的距離和各省份侵權程度是影響專利代辦處設立的決定因素。其中,各省份侵權程度采用各省份侵權立案數與專利授權數之比來衡量。將以上三個變量納入基本回歸模型中進行控制,再次檢驗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回歸結果報告在表4 的第(1)列~第(3)列。
從表4 第(1)列~第(3)列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決定專利代辦處設立的因素之后,交互項MPA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與表3 的基本回歸結果相一致,說明本文基本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2. 縮尾處理
為了排除基本回歸結果受樣本極端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將被解釋變量上、下1%的極端值進行縮尾處理,回歸結果顯示在表4 中。從表4 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交互項MPA的估計系數為0.0233,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專利代辦處的設立顯著提高了我國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回歸結果與表3 中基本回歸結果相一致,這說明在縮尾處理之后,本文的回歸結果依然是穩健的,知識產權保護增強提高了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

表4 穩健性檢驗(Ⅰ)
3. 外生政策沖擊
在2000—2006 年,在設立專利代辦處的同時,還存在著增值稅改革、設立經濟特區、國有企業改革和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政策和事件沖擊。如果不考慮上述因素,我們就難以將新產品出口強度的提高完全歸因于專利代辦處的設立。
為排除外生政策沖擊對本文基準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將是否進行增值稅改革(tax×t)、是否位于經濟特區(tq)、是否發生國有企業改革(state×t)和最終品關稅(tariff)四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基本回歸中,回歸結果見表5 所示。可以發現,MPA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且估計系數的大小在0.0188~0.0233。這表明在控制了增值稅改革、經濟特區、國有企業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沖擊后,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對中國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的政策效應依然存在,進一步說明本文的基本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表5 穩健型檢驗(Ⅱ)
(四)異質性分析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企業新產品的出口還依賴許多其他因素,例如企業所有制和企業生產率等。鑒于此,本文進行分樣本檢驗,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影響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的特點。
1. 區分企業所有制類型
由于國有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國有企業更易于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所以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對國有企業的影響程度可能會降低。為此,相比于非國有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可能對國有企業新產品的出口的影響較小。為檢驗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是否會因企業所有制而存在差異,本文構建企業所有制的虛擬變量(SOE),若企業是國有企業,則SOE=1,否則SOE=0。通過分組回歸的方法考察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對不同所有制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的影響。
表6 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別表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非國有企業的交互項MPA估計系數為0.0231,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專利代辦處的設立顯著提高了非國有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改善了非國有企業中新產品的出口地位。相反,國有企業的交互項MPA估計系數并不顯著,這表明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對國有企業的影響并不大。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因受到政府政策的保護居于壟斷地位(張杰等,2014)。國有企業憑借壟斷地位不斷獲取壟斷利潤,從而減少對新產品進行學習、模仿和研發的動力,所以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對國有企業的影響不大;相反,為了在市場中獲取一定的市場份額,非國有企業需要不斷進行產品創新,不斷研發和生產新產品。專利代辦處的設立縮短了專利審批時間,提高了專利審批效率,從而增強了非國有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提高非國有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
2. 區分企業生產率差異
企業生產率的高低對企業新產品的生產和出口會產生影響。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新產品出口的影響很可能與企業生產率高低有關。本文選取企業生產效率來衡量企業的生產率水平。企業的生產率水平采用企業人均工業增加值的對數值來度量。為此,我們設立企業生產率的虛擬變量(tfp_dum),若企業生產效率大于中位數,則為高生產率企業,tfp_dum 取1,否則為低生產率企業,tfp_dum 取0。基于企業生產率的中位數我們把樣本分為高生產率企業和低生產率企業,通過分組回歸的方法來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對不同生產率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的影響。表6 匯報了回歸結果。其中,第(3)列和第(4)列分別是對高生產率企業和低生產率企業檢驗的結果。

表6 異質性檢驗
從表6 第(3)列、第(4)列可以看出,高生產率企業交互項MPA的估計系數為0.025,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相反,在低生產率企業中,交互項MPA的估計系數較小,且顯著性水平僅為10%,并未通過常規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知識產權保護對低生產率企業的影響不大。知識產權保護顯著提高了高生產率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改善其出口結構。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當設立專利代辦處后,專利審批時間縮短,審批效率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增強,高生產率企業由于自身生產率優勢會加大專利研發,通過創新成果轉化增加新產品的生產和出口。低生產率企業因生產率低下等原因,難以形成有效的創新成果轉化,甚至缺乏研發創新的能力,因此表現為新產品生產和出口能力相對低下。
(五)影響機制檢驗
以上的計量分析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產品出口具有一定的影響。知識產權保護顯著提高了中國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改善了新產品在中國企業出口中的地位,這對我國企業提高出口競爭力、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有著重要的意義。
實際上,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大大縮短了專利審批時間,增強了知識產權保護。由于企業的研發和創新在短時間內受到保護,新技術被模仿的風險大大降低(Kiedaisch,2015),企業便會加大研發投入,使企業更有能力學習和掌握新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及時搶占國際市場。據此,我們推測知識產權保護可能通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來影響企業新產品的出口強度。因此,我們構建如下回歸模型來檢驗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

其中,lnrd代表企業的創新能力,我們用企業的研發投入的對數值來衡量,研發投入越多的企業越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和研發。其中,表7 中第(1)列報告了對公式(1)估計的基本回歸結果。對公式(2)的估計結果報告在表7 第(2)列,交叉項的MPA顯著為正,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創新能力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專利審批時間的縮短加強了知識產權保護,而專利保護增強會促進企業進行創新(Park,2008;Fu 和Yang,2009)。

表7 影響機制檢驗
第(3)列匯報了對公式(3)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MPA的估計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我們注意到,第(3)列與第(1)列基準回歸結果相比,在加入企業創新能力變量之后,MPA的估計系數有所下降。可見,企業創新能力確實是知識產權保護促進企業新產品出口的渠道。這其實并不難理解,根據前文的檢驗,知識產權保護增強會導致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創新能力。為了提高競爭力,增強國際地位,創新能力的提高又會促進企業對新產品的生產和出口。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卻面臨國外專利封鎖、國內產業結構急需轉型的壓力。在這種新的國內外嚴峻形勢下,推動中國企業出口產品結構優化對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雖然關于知識產權保護與中國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一直都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但鮮有文獻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角度,系統探討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鑒于此,本文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入手,準確識別了中國企業出口的新產品和舊產品,并采用專利代辦處的設立作為準自然實驗,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及作用機制。這對理解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的制定、中國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等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基于2000—2006 年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微觀出口數據,把專利代辦處的設立作為準自然實驗,從產品生命周期這一獨特視角,準確地將中國企業出口產品分為新產品和舊產品,采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法考察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企業新產品出口的影響和特點。本文研究發現,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對中國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知識產權保護促進了中國企業新產品的出口,有利于出口產品結構優化和升級,同時,這一結果還有時間持續性。在控制其他外生政策沖擊、控制影響專利代辦處設立的決定性因素、縮尾處理后,我們的結果依然穩健。此外,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還會因企業所有制、企業生產率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經異質性分析,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更能促進我國非國有企業和高生產率企業的新產品出口強度的提升。進一步機制研究分析發現,知識產權保護主要通過促進企業研發創新提高了新產品出口強度。
本文研究充分說明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新產品出口強度的影響,為有效實施專利審批和專利保護政策,促進我國企業出口產品結構升級提供了一定的啟示。第一,專利代辦處的設立大大縮短了專利審批時間,提高了專利申請效率。為此,我國政府要明確專利代辦處的職責,加大對專利代辦處的人員培訓,促進專利審批效率的進一步提升。第二,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中國政府要加大創新投入和創新補貼,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加大產品結構轉型和升級。第三,要充分考慮不同的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差異,對非國有企業采取政策獎勵、財政補貼等措施,激勵其改善出口產品結構,而對國有企業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激發其創新活力。第四,加大對低生產率企業的資金、設備和科研人員的支持,幫助其改善生產效率,提高創新動力,不斷生產擁有高附加值的新產品。第五,提高企業的研發能力和創新水平,改善企業創新環境,加大對企業創新的資金投入,不斷提高企業的生產率,促進企業研發并生產新的產品。此外,我國要抓住“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積極向國外出口新產品,不斷開拓我國國際市場,逐步優化我國出口產品結構,提高我國新產品出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