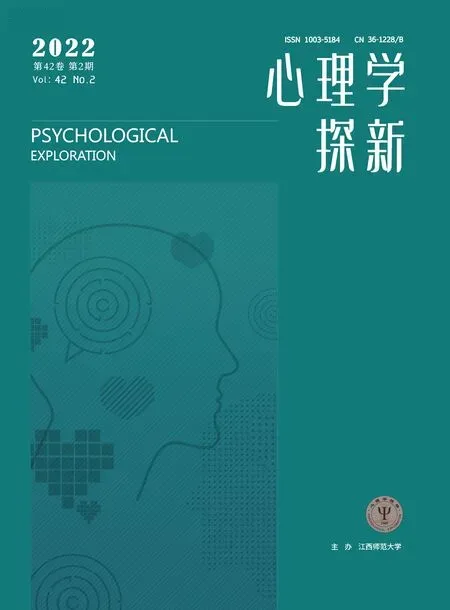先前知識經驗對遠距離水平映射規則內隱學習的限制*
姜 珊,周 楚,郭秀艷,鄭 麗
(1.上海政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上海 201701;2.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上海 200062; 3.復旦大學心理學系,上海 200433;4.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上海 200433)
1 引言
內隱學習是一種無目的、無意識的學習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體通過與環境接觸,能夠自動地獲得事件或者客體間的結構關系和規則(Reber,1967;Reber,Batterink,Thompson,& Reuveni,2017;郭秀艷,2003)。內隱學習在人類認知的許多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例如語言獲得(Kovacs & Endress,2014;Paciorek & Williams,2015)、音樂認知(Rohrmeier & Widdess,2017)、動作技能的掌握(Rose,Haider,Salari,& Büchel,2011;Zhang et al.,2020)等。
既往內隱學習研究大多采用兩類自然語言中存在的語法規則——限定狀態語法和遠距離映射規則。這兩類語法均來自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的語法層級體系,是自然語言中存在的重要語法規則。早期的內隱學習研究更多關注限定狀態人工語法的習得。1967年,Reber首次采用相鄰元素間有順序限制的限定狀態人工語法證明了內隱學習的存在。實驗中,Reber 首先要求被試記憶一系列符合人工語法的字母串,然后要求被試對一些新字母串進行分類判斷,結果發現被試的分類正確率顯著高于隨機水平,且言語報告表明被試沒有發現規則,表明被試內隱地獲得了語法規則,證明了內隱學習的存在。目前,研究者對于存在內隱學習這樣一種無意識的學習過程已經達成了共識,但對于內隱學習的機制問題還存在爭論。爭論點在于,內隱學習獲得的知識究竟是相鄰元素之間的表面特征(Knowlton & Squire,1996;Servan-Schreiber & Anderson,1990),還是底層的語法結構,即抽象規則(Reber,1967)。
近年來,內隱學習研究常采用另一種相鄰要素間沒有順序限制的遠距離規則(non-adjacent dependency,Wilson et al.,2018)。這種結構廣泛存在于自然語言中,例如英語中助動詞和詞素之間存在遠距離的對應關系(“is writing”);包含嵌套結構的定語從句(“the rat the cat ate stole the cheese”);漢語中詩歌的遠距離平仄映射結構(例如,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等。喬姆斯基(1956)指出,相對于限定狀態人工語法,遠距離規則是人類語言所特有的、最為關鍵的成分。跨物種研究也發現了猴子被試只能習得限定狀態語法,而人類被試卻能夠很容易地習得兩種語法。因此,從進化的角度,人們獲得遠距離結構的能力反映了這一結構是人類語言進化的重要轉折(Fitch & Hauser,2004)。從遠距離結構本身的特點來看,它能夠很好地分離底層規則和相鄰相似性的組塊信息,有助于澄清內隱學習的機制問題。人工語言領域的研究發現在特定的情況下,人們能夠習得遠距離映射規則,但是與學習相鄰規則相比,遠距離規則的習得更困難,且包含很多限制條件,如停頓(Pen?,Bonatti,Nespor,& Mehler,2002)、刺激之間的相似性(Newport & Aslin,2004)、刺激元素的變異性(Gómez,2002)、分階段輸入(Poletiek et al.,2018)、先前的學習(Zettersten,Potter,& Saffran,2020)、長期的訓練和鞏固(Uddén,Ingvar,Hagoort,& Petersson,2012,2017)等。
音樂領域遠距離規則的研究同樣發現遠距離規則的習得存在限制。Dienes和Longuet-Higgins(2004)探討了四種音樂遠距離規則的習得,結果表明只有具備音樂背景的被試才能夠內隱地習得這些規則,而沒有音樂背景的被試只有在有意學習(Kuhn & Dienes,2006)和采用喜好度評分這種測驗形式(Kuhn & Dienes,2005)的情況下,才能夠習得音符的遠距離映射規則。Cheung等(2018)采用具有至少7年樂器訓練背景的被試,探討了音樂遠距離嵌套規則的習得,結果發現被試對規則的敏感性和他們接受音樂訓練的年限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上述研究結果表明遠距離規則能夠被習得,但是這一規則的習得似乎會受到先前知識經驗的限制。
采用漢語聲調遠距離映射范式的研究,探討了遠距離映射規則的內隱習得(Jiang et al.,2012;Li et al.,2013;姜珊,郭秀艷,楊靖,馬聞笛,2014;姜珊,關守義,2018)。Jiang等(2012)首次采用漢語語音體系中獨有的語言特征——聲調,在平衡了組塊和重復結構等表面特征的情況下,獲得了聽覺通道遠距離映射規則的內隱學習中分類判斷的成績高于隨機水平的結果。隨后的研究發現這一聽覺通道獲得的遠距離映射規則可以靈活遷移到不同的聲調(姜珊等,2014)以及不同長度(姜珊,關守義,2018)的材料上,進一步為內隱學習的抽象性和規則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由于上述研究采用的平仄遠距離映射符合被試先前關于平仄分類的經驗,這是否意味著符合經驗的平仄遠距離映射規則才能夠被內隱地習得呢?這種漢語聲調遠距離映射規則的習得是否會受到過去經驗的限制呢?跨文化的比較研究為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了初步的證據。Ling等(2018)采用同樣能夠分辨漢語聲調的中國和外國被試,在平衡了組塊這一表面特征的前提下,發現兩組被試都能夠內隱地習得漢語聲調的水平映射規則,但是當更為精準地操縱測驗材料的局部表面特征和整體抽象規則后,發現中國被試在習得整體抽象規則上更具有優勢。這一結果一方面表明,漢語聲調的水平映射規則的習得具備普遍性,不僅僅局限于中國被試;另一方面,也似乎表明先前的知識經驗,即文化導致的注意偏向差異(整體VS局部)影響了不同規則類型的習得。
有研究采用不同的范式直接探討了先前知識經驗對內隱學習的限制問題。例如,Chen等(2011)采用形—義聯結的內隱學習范式,探討了在漢語中,被試是如何獲得限定詞和名詞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被試不能夠內隱地習得限定詞和名詞的任意對應關系,只有限定詞和名詞的對應關系符合語言特征(符合被試具備的知識經驗)時,才能夠被內隱地習得。內隱概念學習的研究也表明在概念學習過程中,類別中包含的特征與先前知識經驗相一致時,會促進這一概念的獲得(Ziori & Dienes,2006,2008)。采用限定狀態人工語法的研究同樣證明當刺激結構與先前知識經驗相一致時,會促進語法知識的學習(Ziori,Pothos,& Dienes,2014)。但是很少有研究直接探討先前知識經驗是否以及如何限制了遠距離映射規則內隱習得。
基于此,該研究將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精細的操縱漢語聲調材料,探討先前知識經驗是否限制了漢語聲調水平映射規則的內隱學習以及遷移。具體來說,我們將采用與姜珊等(2014)的研究相類似的方式,考察聲調水平映射規則的習得和遷移。為了探討漢語聲調水平映射規則的內隱習得和遷移,姜珊等(2014)創設了兩種符合先前經驗的平仄聲調水平映射規則,分別是1聲和3聲的映射以及2聲和4聲的映射,在學習階段讓被試學習其中一種映射規則,而在測驗階段分別測驗兩種映射規則(見圖1),結果發現被試能夠內隱地習得學習階段的映射規則,并且能夠將其靈活遷移到另一種映射規則上。這一結果表明被試內隱地習得了更為抽象的平仄映射,而非具體的聲調映射,揭示了內隱學習確實能夠獲得底層的抽象規則,為內隱學習的抽象性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

圖1 兩種符合先前經驗的平仄水平映射規則的樣例,分別為一聲和三聲的映射以及二聲和四聲的映射。(注:采自姜珊 等,2014)
為了直接探討先前知識經驗是否限制了遠距離映射規則內隱習得和遷移。該研究將在姜珊等(2014)的研究基礎上,創設兩種不符合先前經驗的聲調映射規則:分別是1聲和2聲的映射以及3聲和4聲的映射,在學習階段讓被試學習其中一種映射規則,而在測驗階段分別測驗兩種映射規則,探討不符合經驗的映射規則的習得和遷移。此外,我們還將先前研究中(姜珊 等,2014)的學習效應與該研究的學習效應進行直接比較。如果被試能夠習得這種任意聲調的映射規則并將其靈活遷移,則表明先前知識經驗并不影響被試對遠距離映射規則的內隱習得;如果不能,則表明內隱學習會受到先前知識經驗的限制,只有符合特定語言特征的遠距離水平映射規則才能夠被內隱地習得,平仄聲調分類是漢語中重要的語言特征。
2 方法
2.1 被試
采用單樣本t檢驗,Power=0.95,參考先前研究中的效應量d=0.66(姜珊 等,2014)(1)先前研究中,實驗組被試在遷移條件和非遷移條件下的分類判斷矯正正確率均為0.54(0.06),且均高于隨機水平50%(非遷移條件:t(31)=3.73,p<0.01,d=0.66;遷移條件:t(31)=3.80,p<0.01,d=0.67)。,以GPower3.0來估算總樣本量為32個。選取32名來自大學校園的學生,男性7人,女性25人,年齡在18~26歲之間,平均年齡19.59歲,標準差為1.36。所有被試的母語為漢語,聽力正常,實驗結束后每人獲得一定的報酬。
2.2 材料
選取和姜珊等(2014)相同的24個音節,其中12個音為平聲,包含6個1聲和6個2聲,為“cān,jū,huī,shēng,bīng,yīng,níng,lái,qín,bó,wán,méi”;12個音為仄聲,包含6個三聲和6個四聲,為“guǒ,ěr,zhǎn,tiě,kǒu,xǐ,zòu,jùn,tù,fù,wèi,ruò”。給被試呈現的材料是一串長度為10 的聲音串,每串中的10個音不重復,前五個音和后五個音遵循下述的兩種不符合經驗的聲調水平映射規則:(1)1聲和2聲的映射:如果第一個音為2聲,那么第六個音就為1聲,如果第二音為1聲,那么第七個音就為2聲,以此類推;(2)3聲和4聲的映射,即如果第一音為3聲,那么第六個音就為4聲,如果第二音為3聲,那么第七個音就為4聲,以此類推(見圖2)。

圖2 兩種不符合先前經驗的聲調水平映射規則樣例:(1)上圖:1聲和2聲的映射:如果第一音為2聲,那么第六個音就為1聲,如果第二音為1聲,那么第七個音就為2聲,以此類推;(2)下圖:3聲和4聲的映射:如果第一音為3聲,那么第六個音就為4聲,如果第二音為3聲,那么第七個音就為4聲,以此類推。
采用上述的兩種映射規則,每種規則各生成了32個聲調串,16個作為學習階段的材料,16個作為測驗階段的合法串。此外,16個測驗階段使用的非法串是由上述16個測驗階段的合法串修改生成的,修改的方式是保證每個非法串只有兩個位置不符合規則。
對于1聲和2聲映射規則,學習階段的16個聲調串重復3次,共48個聲調串,將12個音(6個1聲和6個2聲)按照1聲和2聲的映射規則填入這48個聲調串中,生成48個學習聲音串。測驗階段的32個聲調串重復兩次,共64個聲調串,同樣,將12個音(6個1聲和6個2聲)按照規則填入測驗階段的32個合法的聲調串和32個非法的聲調串,生成64個測驗聲音串。由于12個音為隨機選擇的,并且將12個音填入聲調串中的方式也是隨機的,所以,每個聲音串都是無意義的。對于3聲和4聲映射規則,采用上述同樣的方式生成材料。
此外,同姜珊等(2014),需要對重復結構和組塊等表面特征進行平衡。首先,對于兩種聲調映射規則而言,學習階段和測驗階段的聲調串沒有相同的重復結構(repetition structure);其次,測驗串的中的合法串和非法串的平均特征頻率(mean feature frequency,MFF)、總體組塊強度(global ACS)以及前后組塊強度(anchor ACS)在聲調類型和音節維度上都進行了平衡,ps>0.05(見表1)。

表1 兩種聲調映射規則的合法串和非法串在聲調和音節維度上的平均特征頻率(MFF)和組塊強度(ACS)
對于每一個聲音串,前5個音節和后5個音節之間有600ms的時間間隔,構成聲音串的每個音節的持續時間為450ms。因此,每個聲音串共持續5100ms。實驗程序運用E-prime 2.0編寫。
2.3 實驗程序
實驗包含兩個階段:學習階段和測驗階段(見圖3)。

圖3 學習串和測驗串的呈現流程圖
2.3.1 學習階段
本實驗包含兩套學習材料:1聲和2聲映射材料以及3聲和4聲的映射材料。在學習階段,每個被試隨機分配只學習其中一套材料。對于每套材料,48個學習串重復3次,共144個聲音串,隨機呈現。每個聲音串播放前會有一個450ms的提示音,提示被試聲音串即將開始播放,播放完畢后有5000ms的空白時間,被試的任務是仔細聽每個聲音串,并在5000ms的空白時間內在心中默默復述聲音串。學習階段持續時間約30分鐘。
2.3.2 測驗階段
在測驗階段,所有被試均測驗兩套材料(1聲和2聲映射、3聲和4聲的映射),其中一套材料測驗被試對規則的學習情況,另一套材料測驗被試對規則的遷移。測驗開始前,被試被告知先前在學習階段所聽到的聲音串都是由一套復雜規則生成的,要求他們對一些新的聲音串進行分類判斷,即判斷這些新的聲音串是否符合規則。測驗包括兩部分,每部分64個聲音串,共128個串。兩部分測驗的先后順序采用被試間平衡。對于每個測驗串,被試首先需要判斷其是否符合規則,隨后給出他們的判斷依據,即從“猜測、直覺、記憶和規則”四個選項中給出本次判斷所依據的結構知識。
3 結果
3.1 分類判斷的正確率

由于被試在學習階段只學習一種聲調映射規則,而在測驗階段測量了兩種聲調映射規則。因此,測驗包含兩種條件:非遷移條件(和學習階段相同的聲調映射規則)和遷移條件(和學習階段不同的聲調映射規則)。
被試在非遷移條件和遷移條件下的分類判斷矯正正確率分別為0.49(SD=0.05)和0.50(SD=0.08)。兩種條件下的分類判斷矯正正確率均和隨機水平50%差異不顯著(非遷移條件:t(31)=1.10,p>0.05,d=0.19;遷移條件:t(31)=0.28,p>0.05,d=0.05)。此外,遷移條件和非遷移條件的分類判斷矯正正確率不存在差異,t(31)=0.36,p>0.05,d=0.06。這一結果表明與隨機水平相比,被試不能夠習得不符合平仄分類經驗的漢語聲調的水平映射規則,并且不能夠將其遷移到新的材料上。
3.2 意識和無意識的結構知識
將結構知識中的“猜測”和“直覺”合并作為內隱結構知識,“記憶”和“規則”合并作為外顯結構知識。
為了考察被試在測驗過程中的分類判斷的依據以及正確率是否會隨著測驗的進行而發生變化,將測驗分為前后半部分。被試在非遷移和遷移測驗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四個結構知識上的判斷比例以及矯正正確率見表2和表3。除了在非遷移條件下,實驗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在記憶這一結構知識上的反應比例存在顯著差異外(t(31)=3.79,p<0.01,d=0.67),其余各條件下,實驗前后半部分的分類判斷依據以及正確率不存在差異,ps>0.05。這可能由于隨著測驗的進行,被試對整個或部分聲音串特征的記憶會存在消退的現象。

表2 非遷移和遷移測驗的前后半部分各結構知識上的反應比例(M±SD)

表3 非遷移和遷移測驗的前后半部分各結構知識上的矯正正確率(M±SD)
被試在內隱和外顯結構知識上的分類判斷矯正正確率見圖4。在非遷移條件下,被試在內隱和外顯結構知識上的分類判斷矯正正確率分別0.49(SD=0.05)和0.51(SD=0.18),均和隨機水平差異不顯著(內隱結構知識:t(31)=1.32,d=0.23;外顯結構知識上:t(16)=0.32,d=0.08)。在遷移條件下,被試在內隱結構知識上的分類判斷矯正正確率為0.50(SD=0.78),和隨機水平差異不顯著,t(31)=0.22,d=0.04;由于僅有6名被試選擇了外顯的結構知識,所以外顯結構知識不能進行統計。這一結果進一步表明,被試不能夠內隱地習得這種不符合平仄分類經驗的漢語聲調的水平映射規則,并且不能夠將其遷移到新的材料上。

圖4 非遷移和遷移測驗中被試在內隱和外顯結構知識上的分類判斷矯正正確率(Error bars:+/-SE)
3.3 與先前研究的學習效應比較
為了進一步考察先前知識經驗是否限制了漢語聲調水平映射規則的內隱習得和遷移,我們選取了姜珊等(2014)研究中非遷移和遷移條件的總體學習效應以及內隱結構知識上的學習效應與該研究結果進行了比較。


3.4 關于零結果的貝葉斯統計分析
采用貝葉斯因子(Bayes Factors)對姜珊等(2014)的結果和研究中得到的零結果進行進一步的分析(2)貝葉斯因子在線計算工具網址:http://pcl.missouri.edu/bayesfactor。在假設檢驗中,貝葉斯因子代表的是當前數據對零假設(H0)與備擇假設(H1)支持的強度(胡傳鵬 等,2018)。
在姜珊等(2014)的研究中,被試在非遷移條件下的矯正正確率為0.54(SD=0.06),且與隨機水平差異顯著,t(31)=3.73,p<0.01,d=0.66。計算此時的貝葉斯因子分,B10=41.09。這一結果表明當前數據在H1為真的情況下出現的可能是H0為真的條件下出現可能的41.09倍。被試在遷移條件下的矯正正確率為0.54(SD=0.06),且與隨機水平差異顯著,t(31)=3.80,p<0.01,d=0.67。計算此時的貝葉斯因子分,B10=48.72。這一結果表明當前數據在H1為真的情況下出現的可能是H0為真的條件下出現可能的48.72倍。采用Wagenmakers和Love等(2018)對貝葉斯因子的大小所代表的意義進行劃分的標準,在姜珊等(2014)的研究中,對于非遷移條件和遷移條件,當前數據提供了非常強的證據支持備擇假設,即被試能夠習得和遷移符合先前平仄分類經驗的漢語聲調水平映射規則。
而在該研究中,被試在非遷移條件下的矯正正確率為0.49(SD=0.05),且與隨機水平差異不顯著,t(31)=1.10,p>0.05,d=0.19。計算此時的貝葉斯因子分,B01=3.05。這一結果表明當前數據在H0為真的情況下出現的可能是H1為真的條件下出現可能的3.05倍。被試在遷移條件下的矯正正確率為0.50(SD=0.08),且與隨機水平差異不顯著,t(31)=0.28,p>0.05,d=0.05。計算此時的貝葉斯因子分,B01=5.11。這一結果表明當前數據在H0為真的情況下出現的可能是H1為真的條件下出現可能的5.11倍。采用Wagenmakers和Love等人(2018)提出的標準,對于非遷移條件和遷移條件,當前數據提供了中等程度的證據支持零結果。因此,貝葉斯因子對零結果的分析進一步表明被試不能夠習得不符合平仄分類經驗的漢語聲調的水平映射規則,并且不能夠將其遷移到新的材料上。
4 討論
該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精細地操縱漢語聲調材料,直接考察先前知識經驗是否限制了漢語聲調水平映射規則的內隱學習以及遷移。具體來說,我們創設兩種不符合先前經驗的聲調映射規則:1聲和2聲的映射以及3聲和4聲的映射,在學習階段讓被試學習其中一種映射規則,而在測驗階段分別測驗兩種映射規則,探討規則的內隱習得和遷移。結果發現,當破壞了符合先前知識經驗的平仄映射規則后,被試不能夠內隱地習得規則以及將規則靈活地遷移,這一結果表明先前知識經驗在漢語聲調遠距離映射規則內隱習得中的重要作用。
現有的內隱學習計算模型(Boucher & Dienes,2003;Servan-Schreiber & Anderson,1990)很少涉及知識經驗的作用,然而,探討先前知識經驗對內隱學習的影響對于豐富和完善內隱學習的理論模型是十分重要的。雖然先前研究表明漢語聲調的平仄水平映射規則能夠被內隱地習得并且遷移,但這些研究使用的平仄聲調映射是符合被試先前知識經驗的。結合該研究結果,進一步表明遠距離水平映射規則的內隱學習會受到先前知識經驗的限制,只有符合特定語言特征的映射規則才能夠被內隱地習得,平仄聲調分類是漢語中重要的語言特征。與該研究結果相一致,采用形意聯結范式(Chen et al.,2011;Leung & Williams,2011)、內隱概念學習范式(Ziori & Dienes,2006,2008)、限定狀態人工語法范式(Ziori,Pothos,& Dienes,2014)以及音樂遠距離規則內隱學習(Kuhn & Dienes,2005)的研究,都揭示了先前知識經驗對內隱學習的影響。
不同種類遠距離規則習得的比較研究也似乎證明了先前知識經驗的重要作用。Uddén等(2012)采用人工語法學習范式比較了兩種遠距離規則(交叉結構和嵌套結構)的習得。結果表明,經過9天的學習,被試能夠習得兩種結構,并且交叉結構的成績好于嵌套結構的成績。由于該研究采用荷蘭被試,荷蘭語的語法結構中存在大量的交叉結構可能導致被試對交叉結構的加工更加容易。li等(2013)采用漢語聲調的平仄音為材料,比較了水平映射和垂直映射規則的內隱習得。結果發現,被試能夠內隱地習得兩種結構,且水平映射規則的學習效應好于垂直映射,這可能由于水平映射類似于詩歌中的對仗規則,更符合中國被試的經驗。隨后的神經網絡模擬研究(李菲菲,劉寶根,2018)進一步考察了簡單循環網絡(Simple Recurrent Network,SRN)對上述兩種漢語聲調遠距離規則的學習,結果發現SRN能夠學會兩種規則,且與人類學習效應相一致,SRN學習水平映射規則比學習垂直映射規則更好,這一結果表明SRN可以模擬人類遠距離規則的內隱學習。神經網絡模擬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即通過設置不同的學習材料,訓練神經網絡學習符合先前知識經驗的材料以及打破先前知識經驗的材料,考察神經網絡的學習效應,并將這一結果與人類被試的結果進行比較,進一步從建模的角度為先前知識經驗在內隱學習的作用提供新的匯聚性證據。
此外,從更大的范圍來講,學習是存在限制的。這種限制可以來自于內部認知機能,例如個體內部有限的記憶容量、計算能力、已有的知識經驗等,也可以來自于外部的信息輸入方式,例如由短到長、由簡單到復雜的信息輸入。已有研究表明,限制并非對學習不利,反之,很可能使學習過程受益(Jost,Brill-Schuetz,Morgan-Short,& Christiansen,2019;Poletiek et al.,2018)。本項研究結合先前研究結果,表明先前知識經驗對語法規則內隱學習的促進及限制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從更廣泛的視角進一步探討其他因素對學習過程的促進和限制。
5 結論
該研究在控制組塊和重復結構等表面特征的條件下,通過創設不符合平仄知識經驗的任意聲調水平映射規則,探討先前知識經驗是否限制了遠距離水平映射規則的內隱學習和遷移。結果發現相對于符合平仄經驗的漢語聲調水平映射規則,被試不能夠內隱地習得和遷移任意的聲調水平映射規則,表明先前知識經驗在遠距離水平映射規則內隱學習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