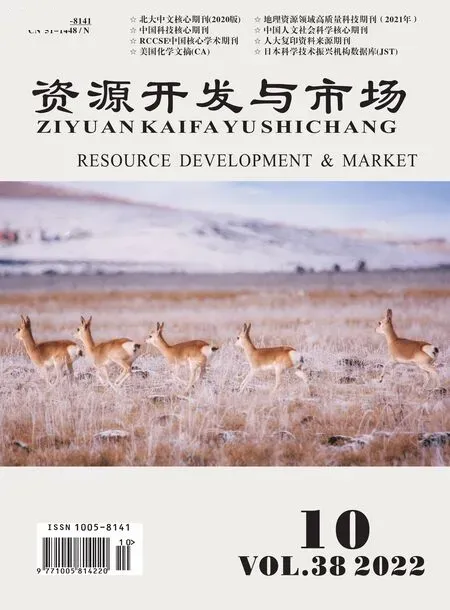西部脫貧地區農旅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及實現機制
——基于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準自然實驗
任紅穎,邱守明,夏 凡
(西南林業大學a.地理與生態旅游學院;b.經濟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4)
0 引言
2020 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西部地區作為脫貧攻堅時期的“主戰場”和“硬骨頭”,具有資源短缺、環境脆弱、基礎設施落后等特點,因此在新階段西部地區仍然是推進、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重點區域,而促進農民增收是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關鍵環節。阻礙西部地區農民增收的原因之一是地區產業結構問題。西部地區以農牧業為支柱產業并保留傳統農業生產特征,綜合生產力和產業附加值較低,難以帶動農民持續和較快增收。但西部地區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深厚的人文資源稟賦,為農業和旅游業融合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條件,在西部地區大力推動農旅融合發展有利于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從而帶動當地農民收入增長[1]。分析西部脫貧地區農旅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及其異質性特征,探究其實現機制可為西部脫貧地區優化農旅融合發展政策提供參考依據,有助于鞏固西部地區脫貧攻堅成果,推動鄉村振興發展[2]。
農旅融合是指農業與旅游業相互交叉滲透,逐步形成新型業態的發展過程。旅游業與農業之間具有較高的耦合性,相互關系可歸納為:農業為旅游業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和產業支撐,旅游業為農業發展提供思路和市場平臺,進而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3]。近年來,學術界對農旅融合的研究逐步從概念、特點等延伸至影響效果[4-6],對影響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 個方面:一是對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農旅融合發展可通過獲取財政支持的途徑推動地區經濟發展[7]。二是減緩農民的貧困。農旅融合發展可產生減貧效應,有助于農民脫貧,脫貧效率與農旅融合發展水平高度相關[8-10]。三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農旅融合發展對糧食生產效率、農業生態效率和農業產業機構優化升級具有顯著影響[11-13]。測度農旅融合影響效果的方法主要分為3 類:一是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探索農旅融合的作用效果[14,15];二是在農旅融合政策影響下,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評估農旅融合影響效應[16];三是構建計量模型對農旅融合影響效應進行測度,常見的模型有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10,17]、PSM - DID 模型[7]、SBM模型[12]、Probit 和Tobit 模型[8]等。綜合分析國內外現有文獻,農旅融合對地區經濟發展和減緩貧困的影響效果是近期研究熱點,研究視角多集中在宏觀經濟水平和微觀減貧效果的測度,對于農旅融合的宏觀增收效應及作用機制、異質性特征鮮少研究。農旅融合影響效果的測度方法普遍為倍差法、多元線性回歸、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容易存在由于調查對象個體異質性造成的樣本選擇偏誤問題,由不可觀測變量引發的內生性問題也難以避免。綜上所述,本文以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設立作為準自然實驗,選取我國西部地區247 個脫貧縣2010—2019 年的宏觀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采用PSM-DID模型評估設立示范縣所帶來的增收效應,構建中介效應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示范縣帶動農民增收的作用機制及區域異質性,嘗試厘清農旅融合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聯系。
1 政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政策分析
為了推動農旅融合發展和拉動農民就業增收,2010年農業部和國家旅游局聯合開展了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創建活動,并陸續推出扶持政策。截至2021 年,西部地區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達到74 個,為農旅融合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本文系統梳理了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相關政策(表1),并總結出促進農民增收的3 條作用路徑:一是通過產業扶持推動農業和旅游業協同發展,依托“百縣千鄉萬村”、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等試點工程和項目,投入大量經費以改善休閑農業種養條件,推動旅游產業提檔升級;二是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施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提升工程,開展休閑農業村莊道路、停車場、農事景觀觀光道路等基礎服務設施建設,美化農村環境,提高接待能力;三是加強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人才培養,提高創業資金和就業補貼,為農旅融合創業者提供金融和稅收方面優惠政策,完善從業培訓[18]。

表1 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政策Table 1 Policies for recreational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counties
1.2 研究假設
內生式發展理論認為,社會的綜合發展只能從內部來推動,最好的方法是把當地人作為開發主體,讓當地人成為主要的參與者和受益人[19,20]。要從根本上帶動西部脫貧地區經濟增長需要對當地現有產業進行轉型升級,讓當地農民成為主要參與者,從而提升脫貧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實現收入的穩步提升。農旅融合可充分利用農村閑置土地、剩余勞動力和農民閑暇時間發展休閑農業,在提升農民內生式發展能力的同時形成產業支撐,不斷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為此,本文提出假設H1:在西部脫貧地區設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可以促進農民增收。
空間地域分異是自然環境地域分異和社會經濟地域分異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同區域因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差異,在相同經濟活動下也會有著不同的發展程度[21]。2017 年,《國土資源部關于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實施意見》將“三區三州”和貧困發生率超過18%的貧困縣和貧困發生率超過20%的貧困村認定為深度貧困地區。深度貧困地區的自然條件較其他貧困地區更為惡劣,經濟基礎更為薄弱,在深度貧困地區實施農旅融合政策所產生的增收效應可能與其他貧困地區產生顯著差異[22]。為此,本文提出假設H2: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在西部原深度貧困地區和其他脫貧地區所產生的增收效應具有異質性。
依據前文政策分析,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設立可以通過提高農業和旅游業的財政扶持,增強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發展能力;通過提高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扶持力度,提升示范縣的可進入性,進而帶動產業融合及快速發展;通過提高就業創業的財政扶持,拓展增收渠道,促進西部貧脫貧地區農民增收。為此,本文提出假設H3: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能夠通過提高農業的財政投入促進西部脫貧地區農民增收;假設H4: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能夠通過提高旅游業的財政投入促進西部脫貧地區農民增收;假設H5: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能夠通過提高基礎設施的財政投入促進西部脫貧地區農民增收;假設H6: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能夠通過提高就業補貼的財政投入促進西部脫貧地區農民增收。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模型選擇
本文主要采用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來評估農旅融合的增收效應。PSM—DID由Heckman首次提出,運用DID 必須滿足平行趨勢假設這一前提條件,在不滿足平行趨勢假設的情況下可以借助PSM 方法構造一個與處理組具有平行趨勢的對照組,以有效降低樣本選擇性偏差對分析結果帶來的影響[23]。結合研究目的,西部地區貧困縣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存在顯著差異,不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故適合運用PSM—DID 方法進行評估。首先,劃分處理組和對照組,處理組為設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西部脫貧縣,對照組為非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西部脫貧縣,并依據控制變量對處理組和對照組進行傾向得分匹配,然后引入雙重差分模型作進一步分析[24]。考慮到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設立為多期且發生在不同年份,所以將一般雙重差分模型變形為雙向固定效應差分模型來驗證假設H1,模型為:

式中:Yit為西部脫貧縣i 在第t 年的增收效應;treati為處理組的虛擬變量,用以區分處理組和對照組;postt為處理期的虛擬變量,用以區分處理組政策實施前后;Xit為控制變量;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γi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非觀測的隨機干擾項。
為了驗證研究假設H2,本文參照姚耀軍[25]對三重差分模型的構建方法,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是否為深度貧困縣”這一虛擬變量Deepj,討論示范縣在原深度貧困地區和其他脫貧地區的增收效應差異。如果該縣屬于原深度貧困縣,則Deepj= 1,否則,Deepj=0。Deepj× treati× postt為該模型關注的交互項,也是ddd[25],模型為:

根據前文理論分析,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設立可以通過提高農業和旅游業的財政支出、基礎設施和就業補貼的財政投入來推動脫貧縣農民增收。因此,為驗證假設H3—H6,本文采用Baron &Kenny提出的逐步回歸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中介效應模型[26]:

式中:Mit為中介變量。檢驗步驟如下:首先,檢驗方程(1)中的回歸系數α1的顯著性,反映的是自變量對因變量的總效應。其次在α1顯著的基礎上,檢驗模型(3)中的回歸系數φ1和模型(4)中的回歸系數θ2。若二者都顯著,表明間接效應顯著;若φ1或θ2不顯著(或兩者都不顯著),表明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不是通過該中介變量實現的。最后檢驗模型(4)中回歸系數θ1。若θ1顯著,表示該中介變量起到的是部分中介作用;若θ1不顯著,表示該中介變量起到的是完全中介作用,即政策效應全部是通過該中介變量實現的。
2.2 變量選擇
由于本文重點研究的是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縣的增收效應,因此反映地區農民收入水平的指標為核心變量。考慮到其他社會經濟因素也會影響到核心變量,故納入其他控制變量進行分析。①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Yit代表當地農民收入水平。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反映農民收入水平,因此選取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it)這一變量來衡量西部脫貧縣的增收水平。②核心解釋變量。虛擬變量(treati)用于區分處理組和對照組。參照2012年國家鄉村振興局發布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名單》和2010—2017 年國家旅游局和農業部聯合發布的《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市、區)名單》,處理組為設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貧困縣,賦值為1,對照組為沒有設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貧困縣,賦值為0。虛擬變量(postt)用以區分處理組政策實施前后。本文將脫貧縣評定示范縣之前的年份設置為對照期,賦值為0,將脫貧縣評定示范縣之后的年份設置為處理期,賦值為1。交互項(did)為該模型關注的核心變量,是treati和postt的乘積,表示處理組在處理期的真正效應。③控制變量。本文選取能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其他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經濟增長帶來的涓流效應會影響居民收入水平,由乘數效應可知固定資產投資可以直接促進經濟增長[27],因此選取能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固定資產投資(investit)作為控制變量之一;產業結構調整可以通過勞動力轉移影響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選取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primaryit)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thirdit)來衡量產業結構[28];政府財政在促進農民收入增長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選取地方財政支出比重(financeit)來衡量。④中介變量。根據研究設計,檢驗農業與旅游業的財政投入是否為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機制,選取農林水務支出(farmingit)、文化傳媒和旅游支出(tourismit)作為檢驗指標;檢驗基礎設施和就業補貼的財政投入是否為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機制,選取交通運輸支出(transit)、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jobit)作為檢驗指標。
2.3 數據來源
本文根據國家統計局劃分的西部地區10 個完整省份作為分析樣本。由于西藏和新疆擁有特有的專項扶貧政策,為避免專項扶貧政策對增收效應的影響,故剔除出樣本范圍。最終選取云南、貴州、四川、廣西、甘肅、青海、寧夏、陜西8 個省份,共247 個貧困縣作為樣本數據,包括102 個深度貧困縣和145個普通貧困縣。將設立為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23 個貧困縣作為處理組,其他224 個貧困縣作為對照組(圖1),樣本時間設為2010—2019 年,數據來源于中國各省份歷年的統計年鑒和各縣歷年的財政決算報告,部分缺失數據通過各縣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補齊。實證分析中,為剔除極端值影響對變量進行1%的縮尾處理,為消除異方差所有數值指標均取對數值。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 所示。

圖1 樣本分布情況Figure 1 Sample distribution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3 結果及分析
3.1 增收效應測度
首先采用PSM匹配處理組和對照組,各協變量得分匹配平衡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有變量標準偏差絕對值均小于10%;同時,T 檢驗結果均不顯著,表明匹配后處理組和對照組不存在顯著性差異,滿足平衡趨勢假設。

表3 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檢驗結果Table 3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balance test results
通過PSM匹配到相似的處理組與對照組樣本,采用模型(1)評估貧困縣設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帶來的增收效應。表4 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別為沒有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分析結果,did 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設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對于貧困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起到正向促進作用。在未控制其他經濟變量時,處理組在設立示范縣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對照組60%,控制其他經濟變量后,處理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對照組12%。上述結果表明,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設立顯著提高了西部地區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驗證了假設H1。

表4 雙重差分分析結果Table 4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analysis result s
利用雙重差分分析政策效應需要處理組和對照組必須滿足共同趨勢假設,如果不滿足該假設,會在分析中產生估計偏誤問題,導致政策效應被低估或者高估[29]。另外,在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設立階段,除了受示范縣的影響之外,貧困縣的發展可能還會受到其他政策或隨機事件的影響,若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會錯誤地判斷示范縣產生的增收效應。為確保分析結果的穩健性,分別進行平行趨勢假設檢驗和安慰劑檢驗。參考龍小寧等[30]平行趨勢假設檢驗法,加入示范縣設立之前年份的虛擬變量與是否屬于示范縣的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作為解釋變量,再次進行估計。表5 中,變量pre1、pre2、current 和time1、time2、time3分別為示范縣設立前1年、前2 年、設立當期和設立后1 年、后2 年、后3 年的年份虛擬變量與虛擬變量(treatment)的交互項,變量的系數用來測度因變量的增長率是否相同。結果顯示,示范縣設立前1 年和前2 年的系數幾乎不存在顯著性差異,相反設立當期和設立后三年的系數顯著,說明符合平行趨勢的前提假設。參考蔣靈多等[31]的安慰劑檢驗方法,將政策實施年份向前調整一年進行反事實檢驗。我國西部脫貧縣最早在2012年設立第一批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將年份調整至2011 年進行分析。若估計系數不顯著,說明示范縣設立不存在預期效應,貧困縣的增收效應是由示范縣的設立引起;反之,貧困縣的增收效應不是由示范縣的設立引起的。從表5 可見,did 的系數不存在顯著差異,表明示范縣設立前不存在顯著的預期效應,即示范縣的設立產生了增收效應。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3.2 增收效應異質性分析
現有研究表明,政策影響具有異質性,不同的地區因其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的差異會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相比其他貧困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薄弱的產業基礎增加了深度貧困地區的增收難度,在深度貧困地區推行農旅融合發展所產生的不同效果值得分析與探討[32,33]。本部分關注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設立在原深度貧困地區和其他脫貧地區產生的增收效應是否存在異質性,構建三重差分模型(DDD)對樣本中102 個原深度貧困縣和145 個其他脫貧縣進行分析驗證,表6 為異質性模型的回歸結果。從表6 可見,ddd 和ddd1的系數在1%、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增收效應在原深度貧困縣和普其他脫貧縣之間存在異質性,驗證假設H2。ddd1的系數為負值,說明原深度貧困縣設立示范縣產生的增收效應低于其他脫貧縣,原因可能有3 點:一是原深度貧困縣資源稟賦較差,對比其他地區農業與旅游業發展基礎較薄弱;二是原深度貧困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缺口較大;三是原深度貧困縣勞動力流失嚴重,難以為產業融合發展提供足夠的人力和智力支持。

表6 三重差分分析結果Table 6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analysis results
3.3 增收效應作用機制分析
通過上文分析,已驗證了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可帶動西部脫貧地區農民增收,那么設立示范縣實現增收效應的作用機制究竟是什么?根據前文政策分析,選取農林水務支出(farmingit)、文化傳媒與旅游支出(tourismit)、交通運輸支出(transit)、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jobit)4 個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效應模型,采用逐步回歸系數法進行驗證,分析4 個中介變量是否存在中介效應及作用程度。
表7 為農業財政投入的中介效應檢驗回歸結果,第(1)—(3)列依次表示中介變量的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同理,表8—10 分別為旅游業財政投入、基礎設施財政投入、就業補貼財政投入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7—10 中的第(1)列反映了中介變量的總效應,此處仍然采用雙重差分回歸模型(1),故表7—10 中第(1)列的結果與雙重差分結果一致。表7—10 中的第(2)列反映了中介變量的直接效應,為模型(2)的回歸結果。表7 中第(2)列的did 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示范縣的設立能夠顯著增加當地農業財政支出,對農業財政支出產生正向促進作用。同理,表7、表10 中的did 系數分別在1%和5%上顯著為正,表明示范縣的設立能夠顯著增加當地財政支出和就業補貼財政支出,對旅游業財政支出、就業補貼財政支出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表9 中的did 系數不顯著,表明示范縣政策未能對基礎設施財政支出產生影響,研究假設H5不成立。表7—10 中的第(3)列反映了中介變量的間接效應,即中介效應,為模型(3)的回歸結果。表7 中第(3)列的did 系數顯著為正,農業財政支出對增收效應的估計系數為0.131,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農業財政支出投入會隨著示范縣的設立產生部分中介作用,促進西部脫貧地區農民增收。同理,表8 和表10 中的did 系數與中介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旅游業財政投入與就業補貼財政投入對農民增收具有部分中介效應。為檢驗中介效應,采用系數乘積項檢驗法,原假設為H0:φ1×θ2=0,若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說明中介效應顯著;反之,說明中介效應不顯著,3 個中介變量皆拒絕原假設,表明中介效應成立[34],驗證了假設H3、假設H4和假設H6。最后,估算中介效應。農業、旅游業、就業補貼財政投入作為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促進增收的機制,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中介效應分別為0.0559(0.427 × 0.131)、0.0615(0.526 × 0.117)、0.0469(0.634 × 0.074)[35]。其中,旅游業財政投入產生的中介效應的占比最大,其次為農業財政投入與就業補貼財政投入。

表7中介效應檢驗 農業財政投入Table 7 Mesomeric effect test agricultural fi nancial investment

表8中介效應檢驗 旅游業財政投入Table 8 Mesomeric effect tourism financial investment

表9中介效應檢驗 基礎設施財政投入Table 9 Mesomeric effect infrastructure fina ncial investment

表10中介效應檢驗 就業補貼財政投入Table 10 Mesomeric effect eployment subsidy f inancial input

(續表10)
4 結論、討論與建議
4.1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設立作為準自然實驗,選取2010—2019 年我國西部地區247個脫貧縣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PSM—DID 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探究了農旅融合發展為西部脫貧地區農民帶來的增收效應和區域異質性,并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分析了農旅融合發展帶動農民增收的作用機制。主要結論如下:①設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對于西部地區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起到正向促進作用,示范縣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非示范縣12%,表明農旅融合發展能有效帶動西部脫貧地區農民增收。②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在西部原深度貧困縣和其他脫貧縣設立后所產生的增收效應存在不同,在原深度貧困地區產生的增收效應低于其他脫貧地區,表明農旅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具有區域異質性。③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設立能顯著增加農業財政投入、旅游業財政投入和就業補貼財政投入,并通過三者的增長產生中介效應,帶動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增長。其中,旅游業財政投入產生的中介效應最大,其次為農業財政投入與就業補貼財政投入,而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的設立并不會對基礎設施財政支出產生影響,表明農旅融合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機制為旅游業、農業和就業財政投入。
農旅融合正處于蓬勃發展階段,政府針對農旅融合發展的政策種類較多,本文僅選取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政策為例進行探究,后續研究可考慮將多種農旅融合政策納入研究范圍,以進一步討論農旅融合發展的影響效果。本文從區域異質性角度出發,驗證了農旅融合發展在原深度貧困地區和其他脫貧地區產生的增收效應的差異性,在后續研究中可結合增收效應的作用機制,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探討其產生區域異質性的具體原因。
4.2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①政府及相關部門應充分認識到農旅融合對脫貧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通過科學編制農旅融合發展規劃,制定農旅融合發展扶持政策,給予項目申報、前期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推動貧困地區農旅融合高質量發展。②政府部門應充分重視西部脫貧地區農旅融合項目的資金投入,在加大財政投入的同時創新籌集資金渠道,用于農旅融合相關項目建設、集群發展、設施改造升級、宣傳推介等,推進特色農業基地、農業園區、休閑農莊建設,形成一定規模的農旅融合產業帶或集聚區,以實現農旅產業深度融合。③政府部門加強對農旅融合相關產業的創業與就業支持,積極支持返鄉下鄉人員開展農旅融合經營項目,采用貸款貼息、以獎代補等方式進行創業扶持,定期組織對農旅融合經營主體負責人和合作社管理人員開展常規技術服務培訓,為農旅融合發展提供必要的人才儲備。④各地政府部門應因地制宜地選擇農旅融合政策方案,針對資源稟賦沒有優勢的原深度貧困地區,優先推動傳統農業轉型升級,加快農業由生產功能向休閑、生態功能拓展,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的可進入性和旅游接待服務功能,以此帶動農旅融合發展。
(致謝: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了云南省農業農村廳政策研究處陳聰老師的指導,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