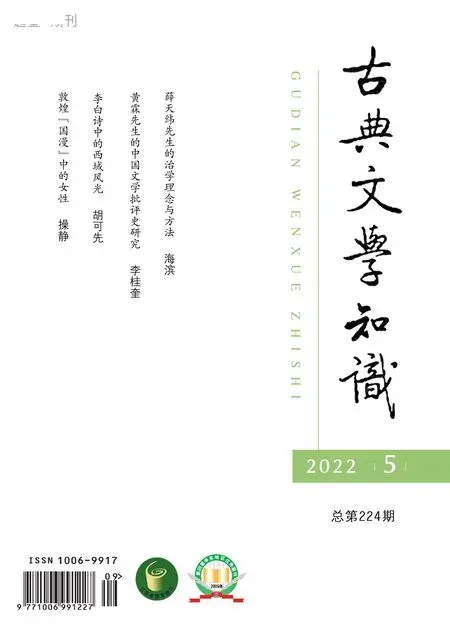唐代的鬼詩(上)
陳尚君
《全唐詩》卷八六五至卷八六六有兩卷鬼詩,標目作者凡七十多鬼,相應附錄的還有幾位,其他各卷及《全唐詩》以外還有一些,總的作者估計不超過百鬼。相對今存唐詩作者超過三千人來說,陰間的創作隊伍稱不上繁榮。
什么是鬼?是人死后在陰間生存狀態的簡稱。什么時候開始有鬼?大約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巫鬼時代。佛教東來后,隨著五道輪回、因果報應學說之盛行,享受現世生活的人們也相信黃泉之下還有另一個世界。唐人多能寫詩,鬼應該也稍解風雅,故有如此多的鬼詩存在。不過雖然匯編于一處,統名曰“鬼”,其實每個鬼也各有個案,獨成故事,曲折離奇,匪夷所思。如我之天生好奇不讓于太史公,勇于斷案更甚于新老偵探名家,對各鬼亦不免窮源竟委一番,偶有一些新的認知,寫出來與讀者分享。
一、 真相不明皆屬鬼
今人常因遇到意外而不可解釋之事,概括為“今天真是遇到鬼了”,即指鬼是不可預料、出乎預期的。古人也經常如此。
比方“峽中白衣”,《本事詩》載,馬植罷安南都護,又除黔中觀察使,二處雖屬方鎮,但最是荒寒偏遠之處,因此而“殊不得意”。其間“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了一首詩:“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第一句頗有西南民族音樂的特色,次句則說高人自有輝煌前途,后二句說你此行雖然辛苦,過此即可以入為宰臣。“陶鈞萬類”是說可以做到宰相。詩很平實,借土風勸慰馬植,不要埋怨眼前的不順。如《本事詩》所述,月明林暗,只有馬植聽到,也就是說這一故事最初即源出馬植本人敘述。馬植在開成五年(840)除黔中,大中二年(848)入相,其間懸隔八年,兩度轉官,并非從黔中入相。推測最初僅是友人送赴黔中詩,后來馬植入相,便故意神秘其詞,因有此詩此事,其間未必有神秘處。
再如“巴峽鬼”,《太平廣記》三二八引牛肅《紀聞》載,唐高宗調露年間,有人夜泊巴峽,聽有人高聲吟詩:“秋徑填黃葉,寒催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而且“其音甚厲,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數十遍”。其人認為是舟行未寢者所吟,天明訪之,并無舟船,“詠詩處有人骨一具”。從詩意說,就是一首行客悲秋之詩,十分傷感。將其渲染為峽中枯骨所吟,更增加了吟者人生的悲劇意義。當然,也僅出于聞者之揣度。
再如“冢中人”,《太平廣記》三五四載,河北人鄭郊,下第游陳蔡間,見一冢上有竹二竿,青翠可愛,乃駐馬吟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久而未能續出后二句,乃聞冢中有聲續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似乎有些白日見鬼的意味。今人得讀王梵志詩,其意屢有所見,且從長沙窯瓷器題詩,到敦煌學郎抄詩,“青竹林”與“百年人”也屬常見詞語,如“上有千年鳥,下有百年人”之類,恐有人不免因此附會為冢中孤鬼成詩。類似故事,如世傳賈島《過海聯句》,即是當時民間流傳很廣的俗詩。
再如“隔窗鬼”,《太平廣記》卷三五二引《聞奇錄》載,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窗借筆,于窗上題詩:“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其后寂然無聲,王紹乃知其非人。以其為是鬼,其實僅屬揣測,詩確還有味道。
再如“長安中鬼”,《長安志》卷七引《輦下歲時記》載:“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曛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干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月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長安既是京師,也曾用為年號,鬼市其地確在長安務本坊西門,似乎以《萬首唐人絕句》卷六九作長安二鬼詩更為恰當。詩雖然有些鬼氣,但相信還是由生人所作,有些穿透兩界的感慨而已。
二、 迷離怳惚信為鬼
還有一些所謂的鬼,其生前事跡歷歷可考,但存詩則有些迷離,世傳為死后所作,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太平廣記》卷三四一引《玄怪錄》,說建州刺史魏朋任滿后,客居南昌,遇病迷惑失心,仿佛有人相引接,忽索筆抄詩云:“孤墳臨清江,每睹白日晩。松影揺長風,蟾光落巖甸。故鄉千里余,親戚罕相見。望望空云山,哀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愿言敦疇昔,勿以棄疵賤。”且說魏素無詩思,而此詩詩意似亡妻所贈朋。后十余日,魏卒。因為有蘇颋之制文,可知他確有其人,且死在南昌,大約即是從建州歸京之半途。由蘇颋撰制,到牛僧孺撰《玄怪錄》,將近百年,不知此一故事如何曲折流傳。《全唐詩》卷八六六收此詩于魏朋妻下,題作《贈朋》,似乎并不恰當。就詩看,更像是魏將終之際寄給親友之作。清江即在南昌附近,詩寫自己客死異鄉,無緣回到故鄉,更無從與親人面別,設想孤墳凄涼,無限傷感,淚隨情落,愿親人不要相棄。很可能其家族有過一些變故,而有末句的規誡。
《太平廣記》卷二七九引《廣異記》載,大歷初,監察御史李叔霽卒。他曾與兄仲云俱進士擢第,有名當時。今人編《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收天寶三載(745)撰《范志玄墓志》,署“前國子進士趙郡李叔霽撰”,就是他進士及第還未授官時的作品。他死后歲余,其妹夫夢中與叔霽相見,語及仲云,音容慘愴,讀出一詩,讓妹夫誦呈仲云。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余。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兄弟情深,未及與兄告別就意外身亡,一直為無從告兄而遺憾。后兩句,平淡中含有許多離恨。
這些孤魂野鬼之詩,有些是保存了生前的真實經歷的。《太平廣記》卷三三八引《宣室志》載,大歷中進士竇裕,落第后將往成都,行至洋州,無疾而卒。竇裕生前與淮陰令沈生熟悉,分別后不通消息。后沈生補金堂令,舍于洋州館亭,夜半有白衣男子入內,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吟詩云:“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沈生由此確定是竇裕,次日在數里外找到他的殯宮,方得致奠拜泣而去。唐人有一習俗,即死在遠方的親友,應盡可能地使之歸葬故土,至少應該有人設奠祭祀,亡者之魂魄方得將息。竇裕客死遠方,故友至此方能傾訴相思,一灑塵淚。故事看似傳奇,其實只是基本的人情。
再說些名家鬼事。唐末詩人邵謁,出生在南方,少為小吏,發憤讀書,艱難應試,登第赴官后下落不明,命運確實很不幸。他日縣民祠神,振鈴持幘者忽自稱邵先輩降,寫成二十八字云:“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當時別故鄉。惆悵不堪回首望,隔溪遙見舊書堂。”這是一位寒苦詩人一生不得志的悲苦之辭,世人可以將其理解為發憤讀書而未必有大的前途,客死異鄉而難以回歸故土,離家之際是如此失意,一生回顧更不堪說來,末句無限悲涼。說是鬼托身巫者而唱出,也許就算一種傳聞吧。
南唐后主李煜是天才的詩人,“不巧”做了國主,國亡后客居汴京而卒,遭遇值得同情。宋太宗時名臣賈黃中出守金陵,這里本是南唐國都,當然會有人懷想舊日時光。據說某日恍惚間有人遞上名刺,云:“前國主李煜祗謁。”賈黃中也不敢怠慢,立即接見,乃一清瘦道士。賈也不慌,禮貌問候:“太師安得及此?”太師是李煜降宋后,宋廷給的虛官。道士說:“今為師子國王,適思鐘山,故來相見。”師子國王為冥間之位。道士說著就從懷里拿出詩稿:“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未閑。風濤千萬里,無復見鐘山。”道士倏忽不見。賈閱畢,詩稿也隨手灰滅。賈黃中在《宋史》卷二六五有傳,于太平興國二年(977)知升州,即宋收金陵后二年,那時李煜還在人世。如果事情發生在他任職后期,也是李煜逝后不久之事。即便坐實了有道士冒李煜之名見賈,其中也包含有對李煜命運的同情。更可能是李煜晚年本有此詩,好事者據以編造故事,實質也大體近似。
未知人,安問鬼?先圣早有明訓,鬼事是無法究明的,那就點到為止吧。
三、 平生幽冤死不瞑
人生在世,春風得意、人生美滿的畢竟是極少數人,大多數人回顧一生,難免艾怨難平。存有幾首這樣的詩,我寧可相信為其人生前所作,傳著傳著就成為黃泉訴怨之作了。
韓弇是韓愈的兄長,德宗建中間任河中節度掌書記,隨節度使渾瑊與吐蕃會盟,吐蕃背信劫盟,渾瑊奪馬逃回,韓弇不幸遇害。據說他與櫟陽尉李績為友,績因晝寢,夢弇被發披衣,面目盡血,自稱憔悴困辱,不可盡言,乃有一詩呈李績:“我有敵國讎,無人可為雪。每至秦隴頭,游魂自嗚咽。”是說被敵國所殺,銜冤塞上,游魂孤苦,嗚咽隴上。又告李績,“吾久饑渴”,希望李績為自己置酒饌錢物祭奠。此可能為李績思念友人慘死邊塞而夢得之詩,表達的是韓弇的悲苦遭遇和憤怨之情。無論如何形成,都包含對韓弇之同情和懷念。武元衡有《酬韓弇歸崖見寄》,知韓弇亦能詩。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三說到他的遠房叔父曾在瓜洲舟中聞外有嗟嘆聲,還寢夢一女子,自稱鄭瓊羅,因父母早亡而到揚子尋姨,在逆旅中為人逼辱,因自殺。其后抱恨四十年,無人為雪。其叔父后至洛北,內弟樊元則說他有女鬼相隨,作法遣之。女鬼請紙筆書之,述遭際冤情,末附雜言七字詩,辭甚凄恨:“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這是一位受害女子極度冤恨的控訴,雖托言鬼書,其間自可知悉世情。

鬼的要求不高,有些關心和理解即可令他在黃泉釋然。
四、 人生感悟死后知
人生多歧途,不斷面臨選擇,每一次選擇都面臨風險與不幸,然身在局中,一葉障目,當時未必清楚,到生命將盡時,回顧往事,不免有感慨與哀傷。留下記錄,警戒后人,也不失為珍貴的憬悟與提醒。
唐代最為名家欣賞的鬼詩,是與蘇州虎丘有關的兩組詩。

另一組是虎丘山石壁鬼的傳說。其事原委以《唐詩紀事》卷三四所載最為詳盡。大歷十三年(778),李道昌為蘇州觀察使。虎丘山有題詩二首,隱于石壁上。其一為《示幽獨君》:“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壟,幽壟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其二為《答處幽子》(題據《太平廣記》三三八引《通幽記》):“神仙不可學,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顯,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生問枯骨,三樂成虛言。”這是兩個鬼魂之間的對話。前一首是處幽子作,說冥間景色蕭條,夜臺寂寞,雖然知道生者為樂,但怎么也回不去了,內心悲哀,思及所親,痛苦無可名狀。后一首為幽獨君之答詩,首句即顯斥神仙長生之學不可憑信,到了冥間,游魂寂寞,更思及子孫。他勸慰處幽子,萬物有生必有死,不必過分悲惋,但要寄言世間之人,盡量享受人生樂趣,不然死后后悔也來不及了。這些都是參透生死者之通達感悟。道昌以其事奏聞,奉敕致祭,乃為文云:“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侄?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哀哉,嘆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愿當生兮事明君。”這是一篇很動人的人鬼對話,作為地方官,李道昌奉旨祭鬼,不知被祭者為誰,有何遭際委屈,對他或她的冤屈充滿同情和安慰。據說祭后數日,再有詩一絕顯于石上:“幽明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詩據《松陵集》卷二)。按其指示,乃于寺后見二墳,荊榛叢茂,無人知曉為誰。皮日休、陸龜蒙皆曾和此組詩,這里就從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