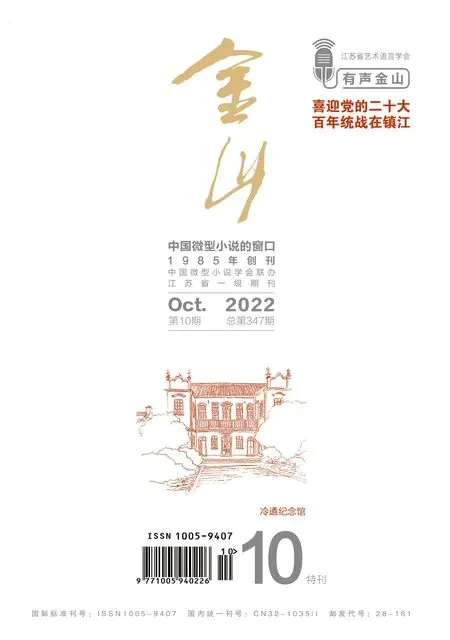朱易經·茅山道教掌門人
江蘇/趙 華

朱易經(1917—2007),俗名朱樹金,江蘇金壇人。曾任中國道教協會名譽理事,江蘇省道教協會會長,鎮江市政協委員、常委,市道教協會名譽會長,句容市道教協會會長、名譽會長。
出身寒微 志存高遠
朱易經出生鄉村,父親朱寶銀,生有四子一女,其排行第五,長年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清苦日子。1925年,8歲的孩子該是背著書包進學堂的年齡了,由于家境貧寒,朱易經只身一人離開家鄉,來到茅山乾元觀出家,成為一名小道士,皈依趙容海道長,屬全真龍門派復字岔支閻祖派第二十四代弟子。
初入山門,“從未進過孔子門,一腳跨入老子門”的朱易經什么也不懂,什么都感到新奇。窮人的孩子懂事早,朱易經憑借著勤奮和刻苦,識字、念經、打水、掃地、種莊稼,樣樣學在前,干在前。經過十年的清修和錘煉,朱易經不僅學會了道教的經文,而且對道教音樂也頗有靈性,吹拉彈唱樣樣拿得起放得下,很得師傅們的賞識、師兄弟們的尊重。在師傅趙容海道長的悉心調教下,并得益于師公惠心白大師傳授道教科儀,18歲的朱易經就任主壇法事,長期往來于乾元觀與溧水城隍廟之間,從事齋醮科儀活動,成長為一名出色的道長。
朱易經出生在軍閥割據、社會動蕩的舊社會,其出家是家庭貧寒的無奈之舉,但一入道觀門便是道家人。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發源地,被譽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曾經道教文化氛圍濃厚,名師高道輩出,卻幾度輝煌幾度衰落。在源遠流長的茅山道教文化的滋養下,朱易經學了知識,長了見識,越發清醒地認識到舊社會的茅山道教日漸衰微,僅僅維持了法派傳承的師徒關系,道場法事及科儀活動仍維持舊制,沒有任何創新。
抗戰洪流 心懷愛國
1938年6月14日,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來到茅山,建立蘇南抗日革命根據地,一支隊司令部和政治部就設在乾元觀內。師公惠心白道長諄諄教誨全觀道士:新四軍是救國軍,保家衛國,大家應積極配合。乾元觀道士自覺投入抗戰洪流,為新四軍提供住宿,燒菜做飯,觀察敵情,通風報訊,救治傷員,配合新四軍打擊日本侵略者。惠心白道長和陳毅司令員經常在觀內的宰相堂和松風閣對弈、撫琴、交談。此時的朱易經,總是不聲不響地為陳毅奉上一杯茅山青茶,有時還靜立一旁聆聽陳毅暢談抗日的道理。1938年9月間,為了更好地聯合各方力量打擊日本侵略者,組織群眾抗日隊伍,陳毅召集了茅麓茶葉公司老板紀振綱、樊玉林及周圍各地方鄉長等進步人士在乾元觀大客堂舉行抗日宣傳大會,安排抗日戰略部署。在革命先輩的鼓舞和革命志士的感召下,朱易經的愛國主義熱情也在心中點燃。
這次大會之后,陳毅率新四軍離開了乾元觀。10月6日,日軍侵入乾元觀,火燒松風閣、宰相堂、大羅寶殿等殿堂,只剩下幾間沒有燒完的東西道眾齋房、庫房和客堂,千年古觀幾成廢墟。侵略者還殘忍地殺害了惠心白、陳容富等12名道士和5個打柴人,師傅趙容海、師叔陳容君和朱易經當日被安排外出,幸免于難。接下來幾天里,日軍又火燒白云觀、仁祐觀、德祐觀、玉晨觀、九霄萬福宮、元符萬寧宮,殺害道職人員。天在悲,雨在泣,短短幾日,失去賴以生存的宮觀和師公、師叔伯、師兄弟的朱易經,帶著對道眾們的深切懷念和對侵略者的深仇大恨,連夜投奔新四軍江南抗日根據地溧陽。他和幸存的道友們繼續投身抗日斗爭,利用在廟觀問道傳經的身份作掩護,經常冒著生命危險,為新四軍傳遞情報。
抗戰勝利后,曾經香火繚繞的道教圣地茅山瓦礫遍地,到處是一片荒涼景象。朱易經來到溧水、杭州等地道觀居住,以做道場維持生活,盡力化緣積攢重振茅山道院的資金和人脈。后又參訪學道于南京斗母宮、二郎廟,蘇州伍子胥廟,上海桐柏宮、三茅宮等地道觀,直至1949年全國解放。
興業弘道 慈儉愛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茅山三宮五觀合并組建茅山道院。1952年成立茅山道院互助組,朱易經任組長,1957年至1970年任茅山道院生產組長。在此期間,朱易經積極參加學習和生產勞動,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努力適應新社會,服務新中國。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中共中央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朱易經和7位老道長先后回到茅山九霄萬福宮。1982年,成立茅山道院管理小組,朱易經任組長,開始恢復道觀修建,重塑神像。1985年3月10日,茅山道教協會成立,朱易經任會長和茅山道院住持。協會成立后,朱易經和道友們齊心協力,四方奔走,為宮觀的恢復和建設灑下了辛勤的汗水,幾乎是在殘垣斷壁的基礎上,修建了一座嶄新的茅山道院。他組織道眾喜迎茅山“四寶”歸山,舉行宗教活動,從事自養事業,使茅山道院煥發新的生機。
茅山道院恢復建設初期,日子過得十分清苦,即使日子過得再苦再難,朱易經都不斷地告誡自己,要堅持,不僅要咬緊牙關生活下去,還要把道院建設起來,更要建設好,因為這里是自己的家。幾十年的道教生活中,朱易經道長真正感悟到了“知足者富”的內涵,在清苦的歲月中“知足常樂”。
時光進入21世紀,道院經濟條件有了很大改善,朱易經個人生活仍然保持著簡樸的風范,一間十分擁擠的臥室,一張極其普通的床鋪,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外出參訪期間,也是一切從簡,從不向別人提要求、講條件。
朱易經一生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慈儉愛人。他平生積蓄非常有限,卻經常接濟他人,為道院的建設做功德。其個人為茅山道院和地方建設捐款30余萬元,所接受的供養費也大多交給了道院用于宮觀修繕,現在的隱仙道院就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
傳道授業 培養后學
朱易經從小出家入道,沒有讀過書,但卻虛心好學,對道教的義理悟性極強,年輕時就能登臺做高功法師,一生富有道教內涵和道門精神。他謙和、居下,與其他宗教大師一起參加宗教會議時,從不搶先發言,總是謙讓于別人。與普通宗教人士在一起,也總能親切交談,友好相處。
1982年,茅山道院招收了8名有文化、有信仰、愛國愛教的青年道徒,朱易經很是高興,對這些剛上山的道徒說:“茅山道教后繼有人了,我們這些老道士解放前苦啊,都沒上過什么學,你們來了,茅山道院就有了希望。”朱易經吃了沒讀過書的苦,所以特別注重培養道教人才。1983年,中國道教知識專修班第一期招生,他親自送去2名學員,此后二期、三期、四期直至1990年道教學院開辦,茅山道院每期都選送2~3名學員,先后有21位青年道友被送出去學習、深造。1987年,茅山道院辦起了道教經懺培訓班,朱易經親自負責,言傳身教,為茅山培養了第一批道教科儀方面的人才,這在全國道教宮觀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些專修班以及道教學院結業或畢業回來的學員大部分都成長為道協、道院的主要負責人和骨干。
1999年鎮江句容市道協換屆,朱易經執意要求退下來,讓年輕人上。他說:“人都是要老的,趁我還在,讓年輕人放手去干,干得好是你們的成績,干得不好是我的責任。”語言樸實無華,意味深長。
老驥伏櫪 壯心不已
隨著茅山道教事業的蒸蒸日上,朱易經并沒有躺在功勞簿上安享晚年,即使從道協會長的位置退下后,依然在道教傳承上兢兢業業,為道院事業發展奔波。
1998年10月,茅山道院元符宮露天老君像開光前夕,老君像左手掌心出現了一個蜂窩,群蜂漫天飛舞。神像開光在即,屆時將有幾萬人出席開光盛典,一旦發生野蜂蜇人事件,后果不堪設想。大家正在考慮如何搗毀蜂窩之時,朱易經道長拄著拐杖來到現場,泰然若定地開導大家:道教崇尚自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放心,野蜂不會蜇人。說來也是奇怪,老君像開光那天人山人海,不但沒發生野蜂蜇人事件,還成就了茅山景區一處“蜂擁而至”的自然奇觀。這種道教生態文明理念深深地影響著茅山生態道觀建設,如今,“青山與我為鄰,白云常來作伴”已然成為茅山道院的真實寫照。
2001年11月16日,84歲高齡的朱易經出資購買了兩棵銀杏樹,親自與乾元觀的小道士一起把樹栽在三清殿前。看著高高的銀杏樹,他深有感觸地說:“我現在年事已高,為乾元觀也做不了更多貢獻,親手植下這兩棵銀杏樹,以表達我對乾元觀的一往深情,希望乾元觀今后的發展像銀杏樹一樣越長越高大,越長越茂盛。”2007年6月,病榻上的朱易經委托二子朱松林為乾元觀捐贈了一幅老子石刻畫像,了卻其最后的心愿。
晚年的朱易經在道教修為上率先垂范,雖年事已高,也勤修不輟。他每日堅持閉目養神,打坐修行,一心為道,信仰虔誠。他經常在簡陋的觀舍誦讀《清靜經》《八大神咒》《玉皇心印妙經》等道教經典,為青年道眾釋疑解惑,并將他“外想不入,內想不出”的修道之法悉數傳授徒子徒孫。直到2007年11月26日,朱易經道長在茅山道院元符萬寧宮仙逝,享年90歲。
斯人已逝,話卻鏗鏘。朱易經發自內心的幾句話,還在茅山上空縈繞:“感謝共產黨,感謝政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沒有人民政府就沒有茅山道院的現在,共產黨是我們最大的護法,人民政府是我們最大的靠山。”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精美的語言,但句句實在,愛國愛教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