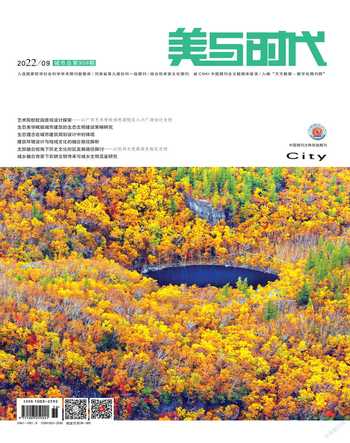路易斯·康建筑現象學精神及其設計學意義
張藝瀚
摘 要:源于對羅馬廢墟與古典秩序的認同,路易斯·康的建筑靜謐而樸實,充滿純粹的幾何形式與沉穩厚重的體量感。路易斯·康對建筑“本源”的探討使他不斷地在結構與功能之間嘗試建立新的聯系,秩序、結構、材料與光線在他的建筑中形成了人與萬物的溝通,最終呈現了其獨特的建筑精神。作為一位直到最后一刻都不會停止改變的藝術家,路易斯·康自我獨特的建筑精神于20世紀50年代開始形成,并隨著項目的進行逐漸發展成熟。基于此,以時間順序列舉了路易斯·康在20世紀50年代后設計的四座建筑,并從這些建筑的結構、材料、光線等角度出發,探究路易斯·康的建筑世界,探尋路易斯·康建筑中蘊含的思考與理想,明確路易斯·康建筑精神的演進歷程,為當代建筑設計提供思想啟示與實踐指南。
關鍵詞:路易斯·康;建筑精神;建筑現象學
一、路易斯·康的建筑精神演進
20世紀20年代末,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建筑師們開始重新審視建筑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在歐洲建筑哲學變革、現代主義興起的背景下,路易斯·康受到當時價值意識的影響,設計的建筑以現代主義風格為主到了20世紀50年代,路易斯·康受益于兩次多國游歷之行,明確了其對歷史偉大建筑品質與秩序的興趣20世紀50年代后,路易斯·康開始將埃及、希臘與古羅馬廢墟上強有力的磚石體量與純粹的幾何材料應用于他的建筑中。
(一)耶魯大學美術館——幾何秩序
1950—1953年,返回美國的路易斯·康完成了他人生中最著名的建筑作品之一——耶魯大學美術館擴建項目。在這個項目中,路易斯·康第一次嘗試了構建廢墟之上的建筑精神。很大程度上,路易斯·康仍然依靠當時流行的現代主義風格建筑的構成手法完成對作品的設計。諸如平面上,美術館以“流動空間”的形式劃分室內空間,空間與空間的界限顯得模糊;立面上,路易斯·康用大面積的玻璃與鋼材窗框覆蓋建筑的西側墻體與北側墻體,而美術館的南側墻體由傳統的紅磚覆蓋,這源于路易斯·康對秩序的遵循,他不希望打破這所學校中的“文化結構”;在美術館的入口形式上,路易斯·康受到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影響,將入口設置在順著墻壁拐入建筑凹槽的位置,偏離建筑的中軸線,這與賴特的建筑作品拉金大廈的入口處理方式近似。
盡管路易斯·康此時并沒有完全擺脫現代主義的枷鎖,但他第一次將羅馬與埃及之旅對他的影響融入建筑結構之中:館內的天花板以網格狀的重復三角形桁架方式排列,燈具放置于三角形的桁架空間內,桁架之上是設備管線通過的空間,裸露的混凝土構成的三棱錐在天花板重復排列后宛如羅馬的穹頂,充滿了原始的力量感;在美術館的中部,放置了空心的圓柱狀核心筒,三角形的樓梯在核心筒中盤旋而上,頂端是巨大的三角形吊頂。路易斯·康開始嘗試利用純粹的幾何形式暴露建筑內部的結構與材料,這個形式在路易斯·康過去的建筑中鮮有出現。這不僅是埃及金字塔與羅馬廢墟帶給路易斯·康的建筑靈感,也是路易斯·康與他的妻子安妮·唐共同的精神產物。
耶魯大學美術館展現了路易斯·康所期望的結構與材料的意志力,三角形與圓形這種純粹的幾何形式開始在建筑中出現。值得一提的是,類似于三角形與圓形這種簡單的幾何形式貫穿了路易斯·康接下來的所有建筑設計。也正是從耶魯大學美術館項目開始,幾何元素開始頻繁出現在路易斯·康的建筑中。耶魯大學美術館中的混凝土結構有著傳統的力量感與純粹的幾何體量,將空間以一種仿佛新的規則進行劃分與安排,自由平面的劃分方式在路易斯·康的建筑中開始瓦解。總的來說,耶魯大學美術館是路易斯·康的自我建筑精神形成的開始。
(二)猶太社區中心浴場(特倫頓浴室)——帕拉第奧的秩序
1949年,魯道夫·維特科夫爾的《人文主義時代的建筑原理》作為《瓦爾堡學院研究》第19卷出版,路易斯·康受到書中關于帕拉第奧理念的影響,產生了對于秩序的思考。在1954年的阿德勒住宅方案中,路易斯·康對住宅平面的草圖繪制是十足的帕拉第奧風格,草圖的形式與16世紀50年代的圓廳別墅無異。到了1955年,特倫頓浴室的總體平面被劃分成了完全帕拉第奧式的幾何關系。浴室的平面結構相互對稱,以中間正方形的公共空間為中心,在上下左右分別布置了四個正方形的獨立空間,頂部是木質構造的金字塔形屋頂,獨立空間的四個角再以“中空柱子”相連接。
后來,路易斯·康在筆記中寫道:“我發現了別人或許已經發現的東西,那就是一個開間的系統就是一個房間的系統。一個房間就是一個明確的空間,通過它的建造方式被定義……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可以看出,這個時候的路易斯·康已經成功地將獨立空間的理念和帕拉第奧的精神相融合,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在我設計了理查德大樓之后,全世界都認識了我,那么在我設計了特倫頓的那間小公共浴室之后,我認識了我自己。”
(三)理查德醫學研究所——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
在1955年建成的特倫頓浴室中,路易斯·康放置了兩種形式的空間,第一種是“屋頂下的空間”,第二種是“中空柱子空間”。“屋頂下的空間”用于洗浴和更衣,“中空柱子空間”供人穿行和容納衛生間。在用途上,“中空柱子空間”中的功能都是為“屋頂下的空間”服務的,于是“中空柱子空間”成為服務空間,“屋頂下的空間”成為被服務空間。特倫頓浴室中兩種功能空間的出現第一次明確地體現了路易斯·康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的理念。
“服務”與“被服務”的理念是路易斯·康建筑精神中最重要的設計元素之一,貫穿路易斯·康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設計。從耶魯大學美術館與特倫頓浴室中,可以窺見路易斯·康對其使用的痕跡,但“服務”與“被服務”的規則并不清晰。而在路易斯·康1957年設計的理查德醫學研究所中,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之間的關系則變得非常明確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耶魯大學美術館重復排列的三角形桁架上方,路易斯·康為設備管線預留了專屬的存放空間,從這可以看出路易斯·康對管線設備這類服務性設施空間的規劃要求已經出現,對服務空間進行了“被服務的規劃”。針對這一點,路易斯·康在1959年的薩爾克生物研究所項目中用2.7米高的桁架孔洞完善了對管線空間的處理。
從平面空間規劃上看,理查德醫學研究所一期工程將中央的小空間集合為一個整體的設備空間,在功能上成為服務空間;然后在設備空間的東側、西側與南側分別放置一間研究室,形成三處被服務空間,設備空間與三間研究室各自只通過一條走道連接;二期工程在一期的平面基礎上于東側增加了兩處平齊的圖書館,并且圖書館的外墻同樣附著了服務空間。總體來看,理查德醫學研究所平面空間從內到外以“服務空間—被服務空間—服務空間”的順序遞進。值得一提的是,路易斯·康于這個項目中刻意地暴露了建筑構件之間的層級關系,這是他對結構秩序的追求。如二期工程墻面外所用的“T形窗”,這個手法后來在諸如論壇回顧報社大樓等各個項目中也有體現,路易斯·康利用這個形式告訴觀者:這片墻體不支撐梁柱。
1959年,在荷蘭奧特洛的國際現代建筑會議中,路易斯·康曾反思道:“在耶魯美術館中,我運用了一點點的秩序觀念,所完成的是自由空間的美術館,我必須承認,當時有一些是我尚未能完全‘理解的。”而在理查德醫學研究所中,路易斯·康以趨近成熟的建構邏輯完成了空間秩序的規劃,清晰地呈現了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的關系,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建筑精神。
(四)金貝爾藝術博物館——結構是光的給予者
1966—1972年,路易斯·康在金貝爾藝術博物館項目上實現了對光線最成熟的控制,在這個項目中,能看出路易斯·康獨立空間的設計手法,但他不再以純粹的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的秩序進行空間劃分,服務空間與被服務空間的區分在這個項目上開始相對隱晦。在平面上,路易斯·康劃分出十六個獨立的單元空間,并將單元空間相互連接,源于羅馬式建筑給予的靈感,在遞予博物館館長理查德·法戈·布朗的第一版方案中,確立了金貝爾藝術博物館拱頂的形式。1967年10月,在事務所同事馬歇爾·梅耶的推薦下,路易斯·康采用了一個充滿美感與人性的曲線——用擺線的方式處理拱的曲率,于是十六個單元空間的屋頂被構建為半筒狀拱頂。
金貝爾藝術博物館中最動人的部分來源于路易斯·康對陽光的引入和處理,為了讓陽光在不同方向與不同時間都能自然地灑入金貝爾藝術博物館內,路易斯·康在每個拱的頂部劃出一條縫隙,并在結構師科門登特的幫助下,在拱的內部加入預應力的鋼筋以應對由縫隙導致的拱的壓力與張力。在拱頂縫隙的下側,路易斯·康懸吊了長條的鋁制穿孔板對陽光進行削弱與散射處理,以使展品不會受到直射光的傷害。同時,各個時段的陽光在穿過這些鋁制板孔后在混凝土的墻壁上發生折射,成為銀白色的光線,這些光線正如路易斯·康自己期望的那樣:當身處金貝爾藝術博物館中,人們能夠感受到一天內時間的變化。1972年,路易斯·康談及金貝爾藝術博物館的天窗采光系統時曾說:“結構是光的制造者,因為結構釋放其中的空間,那就是采光。”在耶魯大學美術館中,路易斯·康以重復排列的三角形桁架覆蓋屋頂,使自然光只能從窗戶進入室內,而在金貝爾藝術博物館中,拱頂的縫隙讓自然光沒有阻隔地進入室內,采光的重心從人工光源轉到了自然光源,光線與結構之間的聯系變得明顯了。路易斯·康曾說:“空間是建筑的開始,也是精神的場所。你處在空間里,就和它的尺寸、它的結構、對它的特征起作用的光線、它精神的光芒在一起。你會意識到,不管人類的訴求是什么,創造了什么,它都是有生命的。房間的結構在房間中必須很明顯。我相信,結構是光的給予者。”值得一提的是,在隨后的耶魯大學英國藝術中心項目中,路易斯·康再一次對屋頂結構進行了特殊的處理,用以引入自然光。
二、現象學方法與設計學意義
如前文所述,路易斯·康的建筑始終貫穿著秩序原則,從早期的廢墟秩序、幾何秩序到服務與被服務關系的空間秩序,這種秩序原則是路易斯·康的建筑精神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對于秩序從何而來,秩序如何被發現,路易斯·康與其同時代的其他建筑師則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路易斯·康反對秩序單純來自自然,他認為“秩序是一種文化結構,可以在人類歷史中找到它的原型”。路易斯·康曾贊揚柯布西耶建筑中的美,但是他也批評它們是“脫離文脈、沒有重要位置的”。這樣看來,路易斯·康追尋的建筑秩序“是一種與環境有關的行為”,既非純主觀性,又非純客觀性。“自然物依循著自然的法則而產生;相對地,人造物是人為意志的展現,遵循著人的規則而形成。”路易斯·康的設計既受環境影響或“意向性對象”(場所)支配,又依賴于自身的意向性能力,是一種意向性能力與意向性對象之間的量子式的互動關系,也就是一種“場所精神”。因此,路易斯·康的設計理念和方法是一種典型的現象學方法。
路易斯·康建筑現象學給予了人們重要啟示。第一,建筑現象學作為一種方法值得借鑒的就是回到“生活世界”,即到生活世界中去發現意義。建筑設計作為一種創造性的活動,設計過程就是賦予場所和建筑以意義,但是,不同的場所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可以形成不同的意義理解,那么如何讓設計者的意義成為雇主的意義,這需要設計者能超越一般人的意義理解。因此,需要設計者從“生活世界”中去理解環境和人的關系。第二,從現象學來看,設計既非單純是自然的結果或人的主觀感受,而是“意向性能力”和“意向性對象”之間的“碰撞”形成的特定的場所與特定的意義存在,所以建筑設計者要善于提高自己的意向性能力。所謂意向性能力,即對意義的理解力,這依賴于一定的文化素養。因此,建筑設計者更應當是一個哲學、文學、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方面的高深造詣者。第三,現象學強調自然對人的“喚醒”,路易斯·康的建筑現象學啟發我們在師法自然的過程中,不可完全被自然左右,重要的是從自然中發現特定的“場所精神”,即設計者要善于從一般場所中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意義。這需要設計者深入實地感受,而不是僅僅靠想象和臆想去進行設計。
綜上所述,路易斯·康是一位執著的藝術家,是一位難以交流的完美主義者,但他固執地將建筑看作一種信仰,畢生不懈地追求建筑的永恒品質。他在建筑中已經找到了自我的精神歸宿。“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可以從路易斯·康的智慧中獲得更多啟示,學會從事物本質出發,探索設計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斷地追問自己:‘它自己希望成為什么,而不是:‘我想讓它成為什么。”
參考文獻:
[1]KAHN L I, LATOUR A.Louis I. Kahn:Writings, Lectures, Interviews[M].New York:Rizzoli,1991.
[2]施植明,劉芳嘉.路易斯·康:建筑師中的哲學家[M].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3]威廉姆森.路易斯·康在賓夕法尼亞大學[M].張開宇,李冰心,譯.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
作者簡介:
張藝瀚,安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環境藝術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