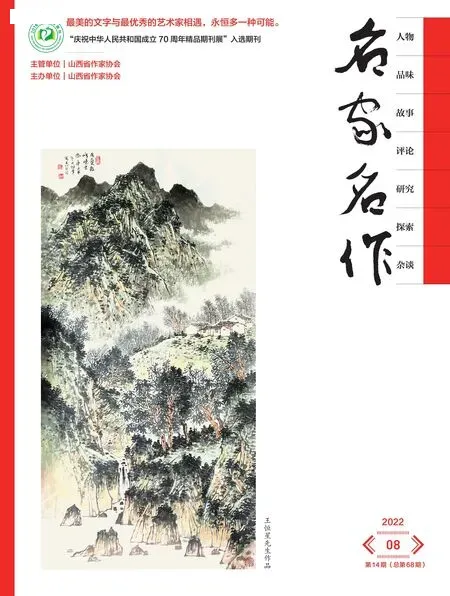林風眠與北京藝術大會
黃 藍
一、北京藝術大會的舉辦
林風眠是我國近現(xiàn)代著名的藝術家,曾赴法國留學,回國后受到蔡元培的賞識,擔任北京藝術學院院長,留學法國的這段經歷對他影響很大,他希望在中國也能舉辦一場令人印象深刻、具有創(chuàng)新意識的藝術展覽。1926年3月,林風眠初步確定了藝術大會的時間和展覽內容,并且開始籌備,他提出:“這次藝術大會將集繪畫、音樂、表演等多種藝術形式為一體,不僅是老師,學生的作品同樣可以參展。”之后他確定了大會的名字為“北京藝術大會”,宗旨是追求進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藝術精神和素養(yǎng)。
北京藝術大會開幕時,《晨報》對此進行了跟蹤報道。展覽期間,記者紛紛在藝術世界第六版專欄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報道和意見被收集起來,裝訂成冊并出版。
北京藝術大會的第一次開幕式是在5月1日,但由于陸續(xù)還有作品從各地送過來,林風眠決定推遲10天,最終數(shù)量增加到3500件,對此《晨報》記者也進行了報道。
對于首場開幕式,《晨報》記者寫道:此次北京藝術大會的所有作品都經過專家仔細挑選,審查,并對作品進行編號,數(shù)量共計有2000余件,規(guī)模之大,前所未有,今日上午10點進行開幕式。
對于第二次開幕式,記者則寫道:“由于作品數(shù)量還在擴充,北京藝術大會時間臨時變更,決定11日開幕,原本學校準備了10個展廳,現(xiàn)在擴充到14個展廳。作品數(shù)量達3000多件,校園里會有路標指示,同時給每位參觀者分發(fā)地圖冊,沿途小路種植鮮花綠草,景色優(yōu)美,聲樂系、舞蹈系的同學和教師將現(xiàn)場帶來精彩表演。”
開幕式上,全體師生高唱校歌,隨后教師代表宣讀了藝術大會的口號:“打倒模仿的傳統(tǒng)藝術!打倒貴族的少數(shù)人獨享的藝術!提倡全民的各階級共享的藝術!提倡民間的表現(xiàn)十字街頭的藝術!全國藝術家聯(lián)合起來!東西藝術家聯(lián)合起來!人類文化的倡導者、世界思想家藝術家聯(lián)合起來!”
本次藝術大會共有14個展廳,包括藝術學院展廳、美術館、會議廳、學院廳、公共教室、第一教室、第二教室、第三教室、左側內教室等。每個展廳都采用混合展示方式,打破中西風格和格局的界限。作品不區(qū)分“山水、花卉、工筆”等類型,均標有編號,以免打廣告。本次大會不僅展出和拍賣了齊白石、李苦禪、克羅多、陳師曾、林風眠等著名藝術家的名貴畫作,初出茅廬的年輕學生的作品也同樣受到關注。
本次藝術大會開幕式,從演出現(xiàn)場就已經體現(xiàn)出了中西融合的思想,不僅有古琴、琵琶、簫等中國傳統(tǒng)樂器的演奏,還有西方歌劇表演。畫家克羅多是林風眠從法國邀請到藝專任教的老師,他在開幕式中進行了長篇演講,振奮人心。《晨報》記者認為,北京藝術大會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中西的界限,不但可以看到繪畫、雕塑、建筑等多種藝術形式,還可以看到中國古樂和西方戲劇的同臺表演”。
本次藝術大會吸引了大批參觀者,《晨報》寫道:“藝術大會原計劃是舉辦20天,門票一共售出了18000張,最終決定再延期3天閉幕,每個場館都掛了一個意見簿,參觀者可以暢所欲言,閉幕時每一本意見簿都寫滿了評語,可見參觀群眾對此次藝術大會的重視程度很高。”
北京藝術大會的舉辦無疑是近代中國藝術歷史進程中的一大壯舉,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這次大會最終呈現(xiàn)出的效果,并沒有完全達到林風眠的預期,“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還存在差距。
二、林風眠對北京藝術大會的期望
首先,林風眠期望藝術大會能做到藝術的集中。從藝術大會的口號中就可以看出,藝術大會的目標非常明確:打破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形式,讓中國藝術家走出去,與全世界的藝術家聯(lián)合,實現(xiàn)藝術的集中。“聯(lián)合”和“集中”是林風眠對藝術大會的期待,這樣的期待源于他“調和中西”的思想。林風眠認為,“繪畫不應該過分強調中西的界限,中西藝術家不是對立的,不應該相互排斥,正確的做法是融合中西,尋找出藝術發(fā)展新的路徑。”
1924年,林風眠等人在巴黎成立了“霍普斯會”,之后提出的《霍普斯會宣言》更是強烈體現(xiàn)出了“調和中西”“藝術集中”的主張。北京藝術大會的重要參與者克羅多宣稱:“藝術沒有國界之分,中國畫、法國畫、美國畫等這類名詞不應該出現(xiàn),這樣的分類是對藝術的限制,‘繪畫’就是‘繪畫’而已。”作為林風眠的得力外援,克羅多的這句話與《霍普斯會宣言》中的“在未來,中西方都會產生新的藝術,兩方的新藝術亦可調和、再生,無窮無盡,這就是世界藝術未來的新生之路”是相通的,以林風眠為主的這批藝術家,希望藝術大會為中國藝術界帶來新鮮血液,尋找出一條世界主義的創(chuàng)造之路。
其次,林風眠期望藝術大會能啟迪民智。在開幕式演講中他說:“此次北京藝術大會能舉辦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它給毫無生氣的北京藝術界帶來了新的活力,普通民眾根本不知道究竟何為藝術,也沒有接受藝術教育的機會,我認為藝術是‘人生’的,但是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所以只能依靠極少數(shù)的先覺者,慢慢帶領民眾,一步步地嘗試,在潛移默化中讓民眾知道藝術的偉大之處。”林風眠將藝術視為照耀在頭頂?shù)奶枺瑥V大藝術家應該擔負起拯救社會的重任。他在《為藝術而藝術》一文中寫道:“藝術是屬于全人類的,絕不是某一個人的,藝術家應該有相當高的修養(yǎng),應該做大眾的啟蒙者,做社會的領路人,藝術是創(chuàng)造的精神,在這個混亂黑暗的年代,我們需要有創(chuàng)造力的人。”
藝術大會的一張海報上畫著排排相連的床,床上是睡熟的人,圖畫的下方寫著一行字:“藝術就像晨鐘,準備喚醒睡夢里的人民,藝術就像太陽,在這個黑暗的社會給人曙光。”
林風眠對藝術大會寄予了厚望,然而當時的民眾還不能接受這樣“懸浮在頭頂”的藝術,在談到藝術大會參觀者時,林風眠憤怒地說:“這些來參觀的群眾,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在留言簿上亂寫亂畫,甚至還說留戀展館的模特,這就像你要請人喝酒,對方卻偷你的酒杯一樣,藝術大會應該是引導民眾欣賞藝術,但現(xiàn)在看來還遠遠沒有做到。”林風眠期望用藝術來拯救大眾的理想,但在當時的社會中難以實現(xiàn)。
三、北京藝術大會受到的質疑
北京藝術大會除了沒有達到林風眠的期望外,還受到了多方面的質疑。首先是來自藝術家群體的質疑。藝術大會的籌劃者之一楊適生就提出質疑,他認為此次藝術大會沒有出現(xiàn)太多有創(chuàng)造精神的作品,大會僅僅做到了作品數(shù)量的集中,只是把所有作品混合陳列出來了而已,楊適生對藝術大會寄予厚望,他希望大會能真正做到作品創(chuàng)造性風格的集中,但是這樣的想法過于理想主義,在當時的北京還無法出現(xiàn)如他所想的集中性作品。
克羅多也承認了藝術大會質量上的不足,他說:“此次大會優(yōu)秀的作品有很多,但壞的也不少,最大的缺點就是青年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激情,被壓在了傳統(tǒng)的方法之下,還是只會一味地模仿傳統(tǒng)。”此外還有李樸園批評說:“老藝術家的確是無法再讓他們做出改變了,但是青年藝術家應該好好睜開眼睛,看看世界,看看未來,不要只知道一個勁兒地跟著你們的老前輩走,要學會判斷,別人走過的路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的,要有自己的判斷。”朱應鵬也發(fā)文:“藝術大會就不應該加入傳統(tǒng)古畫、古樂,古畫提倡歸隱山林的思想已經不符合時代的前進方向了,古樂家也只能替孫傳芳這類人去‘潤飾鴻業(yè)’,這是我們應該明白的。”
以上這些主張革新的藝術家認為,藝術大會并沒有做到“藝術集中”,大部分的作品仍然在走傳統(tǒng)繪畫的路子,林風眠所期望的“調和中西”作品少得可憐。臨摹傳統(tǒng)是中國畫發(fā)展歷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項,想要畫家完全跳出傳統(tǒng)進行創(chuàng)新是很難的。另外,“調和中西”的思想雖然在理論上具有重要價值,但實際操作不如“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tǒng)”更為直觀、明確。
取西方繪畫的長處,補中國繪畫的短處,但是究竟哪部分算“長處”,哪部分算“短處”,具體又該如何融合,這個問題尚不明確。林風眠期望全世界的藝術家聯(lián)合起來,做到藝術作品風格的“集中”,這樣的想法只是“空中樓閣”,難以實現(xiàn)。當時中國藝術的發(fā)展之路還處于摸索階段,林風眠自己的理論思想也在不斷構建之中,融合中西這類模糊的概念無法指導廣大藝術家的實踐。
藝術家群體的質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林風眠還面對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北京藝術大會的舉辦引起了北洋軍閥的警惕。藝術大會舉辦期間,校園里貼滿了帶有“打倒”字樣的標語和口號,北洋軍閥認為林風眠是在挑釁政權,此外,藝術大會上出現(xiàn)了全裸的人體像,藝專教師在教學中有時也會使用人體模特,這些都讓北洋軍閥大為不滿,他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林風眠,把林風眠舉辦藝術大會的行為看作是一場政治反叛。
一年前,上海美專的教師上課使用人體模特的行為就遭到了北洋軍閥的口誅筆伐,孫傳芳給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發(fā)去警告信,要求其必須停止使用人體模特。一年以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北京,認為北京藝專和上海美專一樣,對中國美術界的發(fā)展造成了不良影響,甚至要查封北京藝專。在“人體模特的風波”和“北京藝術大會”以后,林風眠的辦學已陷入嚴重困境,北京藝專被強行查封,北洋軍閥甚至派人追殺林風眠。
面對如此磨難,林風眠依舊身懷希望,他就像寒風中綻放的梅花,寒風越是凜冽,花香越是濃烈。1928年,林風眠發(fā)表了《致全國藝術界書》,他把筆桿和文字作為武器,繼續(xù)著戰(zhàn)斗,面對北洋軍閥的重重壓迫,他奮起反抗,從留學歸來的那一刻他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改革中國藝術學校,他身體力行,不畏艱險,不懼質疑,面對藝專被查封的現(xiàn)狀,他哀嘆道:“藝術運動剛見到希望的曙光,就被撲滅,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
林風眠苦苦地思索著,冷靜地觀察、分析中國當時的藝術教育狀況:“中國人缺乏藝術的熏陶,也缺乏藝術欣賞的趣味,在這個混亂的時代,藝術失去了地位,前途可危,不堪設想。放眼全國經費充足,人才健全,成績昭著的藝術教育機構有一個嗎?在以前,無論多困難、人才多缺乏,但總歸有個國立的藝術學校!然而,自從北洋殘余軍閥盤踞京都以后,蒙昧可憐的同胞們竟然當起軍閥的走狗,把藝專說成是一無是處的東西,現(xiàn)在,這個唯一的國立藝術教育機關,也被他們蹂躪殆盡了!”
教育總長劉哲也對藝術大會提出質疑,他認為藝術大會口號中的“打倒”等詞過于極端,會造成不良影響。1927年9月2日,劉哲約林風眠談話,面對劉哲的質詢,林風眠以藝術家的思維回答:“口號里的‘打倒’,是指鏟除舊的思想,促進新思想的發(fā)展,用這兩個字只是因為它們比較惹人注目,絕無別的作用。”在林風眠心里藝術是純凈、至高無上的事業(yè),不夾雜任何世俗的東西。
1927年的北京藝術大會雖然使林風眠在中國畫壇上聲名鵲起,但也讓他的政治處境走向了險惡。就像林風眠與劉哲的對話,體現(xiàn)出的是當時林風眠在藝術領域中的革命精神與封建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根本沖突。
林風眠的藝術思想深受西方影響,“反叛”是西方近現(xiàn)代藝術最為鮮明的特征,“反叛”精神與林風眠的文人天性相結合,成為他終身的藝術個性。但是,這樣的個性讓他在當時的社會寸步難行。他不諳世事,不懂人際交往,不關心政治,最后只能被迫辭職,南下去尋求新的庇護。他有一腔沸騰著的改革熱血,政治生涯卻屢屢受挫,他想為中國藝術尋找一條新出路,拯救那些被逼入死路的藝術家,但不知不覺中自己也深陷困境,他雖然奮起反抗,但最終還是被裹挾在了歷史的洪流之中。
誠如布迪厄所言:“文學場也是一個權力場,大部分的文學策略由多種條件決定,既關乎美學也關乎政治,既是內部的,也是外部的。”
20世紀初的藝術變革最終并非決定于藝術史內部的風格競爭,而是直指藝術史外部的權力運作。在藝術與政治一體化的歷史邏輯中,理想主義的林風眠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的碾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