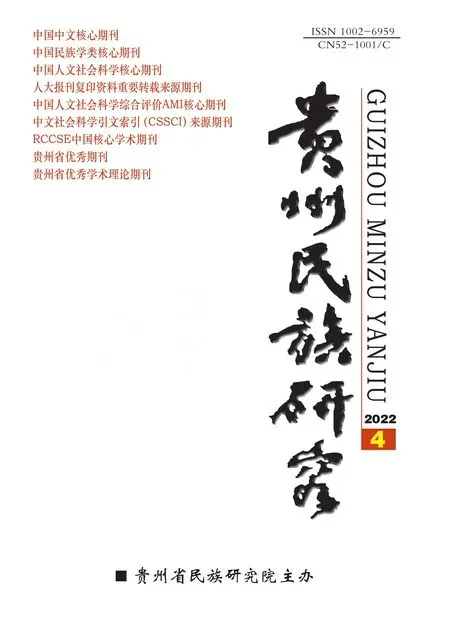鄉(xiāng)村振興背景下貴州少數(shù)民族村落共同體重建研究
安治民 李文鋼 孫 娟
(1. 貴州理工學(xué)院,貴州·貴陽550003;2. 貴州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貴州·貴陽550025;3.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貴州·貴陽550028)
前言
村落共同體以地域空間為基礎(chǔ)實(shí)現(xiàn)村寨內(nèi)部人群的社會整合,維系村民對村寨的認(rèn)同感、歸屬感,促進(jìn)村寨的存續(xù)和發(fā)展。在多民族聚居的民族村寨中,以地域?yàn)榛A(chǔ)的村落共同體超越了以血緣、宗族、族群認(rèn)同、民族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社會整合。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一直在削弱維系村落共同體存續(xù)的種種力量,導(dǎo)致村落共同體在社會變遷的進(jìn)程中走向衰敗。賀雪峰認(rèn)為,新時(shí)代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實(shí)施總體上是基于中國鄉(xiāng)村大量青壯年外移,導(dǎo)致了以村落空心化、家庭空巢化、人口老齡化為表征的鄉(xiāng)村衰敗,進(jìn)而造成了鄉(xiāng)村失序和村落共同體崩解。因而,有學(xué)者認(rèn)為當(dāng)前中國鄉(xiāng)村發(fā)展最為嚴(yán)重的問題不是經(jīng)濟(jì)的不發(fā)展,而是村落社會的坍塌,在鄉(xiāng)村建設(shè)中需要直面鄉(xiāng)村社會如何復(fù)興的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提出了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不同學(xué)科的學(xué)者就如何實(shí)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已有諸多討論。有不少人類學(xué)、社會學(xué)方面的研究認(rèn)為,鄉(xiāng)村振興的首要任務(wù)是重建已經(jīng)走向崩解的村落共同體。因?yàn)椋迓涔餐w具有整合鄉(xiāng)村社會,解決鄉(xiāng)村社會問題的作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所要求的“產(chǎn)業(yè)興旺、生態(tài)宜居、鄉(xiāng)風(fēng)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離不開村落共同體的支撐,村落共同體的崩解加速了鄉(xiāng)村的衰敗,阻礙了鄉(xiāng)村振興的步伐。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實(shí)施過程中,應(yīng)“找回村落共同體”,實(shí)現(xiàn)重塑鄉(xiāng)村社會秩序與文化、增進(jìn)鄉(xiāng)村社區(qū)凝聚力,進(jìn)而促進(jìn)鄉(xiāng)風(fēng)文明和治理有效。
貴州民族地區(qū)鄉(xiāng)村普遍缺乏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在地化發(fā)展能力較低,造成了民族村民常常離開村寨到外地尋求工作機(jī)會。當(dāng)人口流動(dòng)加劇后,民族地區(qū)鄉(xiāng)村呈現(xiàn)出空心化,“三留守”問題突出,村落共同體難以維系。此外,“十三五”時(shí)期,貴州易地扶貧搬遷人數(shù)超過180萬,易地扶貧搬遷使原來的村莊組織結(jié)構(gòu)和內(nèi)部社會關(guān)系迅速解體,村落生活空間和村落邊界開始重組,村民對村莊的認(rèn)同感降低。人口頻繁流動(dòng)和易地扶貧搬遷引發(fā)的村莊失序及活力不足等問題,凋敝而無生機(jī)的鄉(xiāng)村社會也違背了民族地區(qū)鄉(xiāng)村振興的目標(biāo)。對貴州民族地區(qū)村落共同體崩解的原因展開分析,探討村落共同體重建的理論基礎(chǔ)和實(shí)踐機(jī)制,對于在貴州民族地區(qū)有效推進(jìn)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實(shí)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政策意義。
一、貴州民族地區(qū)村落共同體走向崩解的原因
(一) 鄉(xiāng)村人口流動(dòng)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鄉(xiāng)村的人口流動(dòng)日益頻繁,對鄉(xiāng)村居民之間的交往行為造成了顯著影響。學(xué)術(shù)界在討論中國鄉(xiāng)村走向衰敗時(shí)將人口流動(dòng)看成是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gè)最為重要的原因,村落共同體走向崩解已是社會學(xué)關(guān)于中國鄉(xiāng)村研究的一個(gè)核心診斷。人口流動(dòng)并不會直接影響少數(shù)民族村寨的社會整合,而是人口流動(dòng)作用于村寨的社會生活之后才會導(dǎo)致村落共同體走向崩解。當(dāng)人口流動(dòng)導(dǎo)致不同民族村民之間的交往機(jī)會變少,不再有彼此需要的那種生活感受時(shí),就難以維系村落共同體意識。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縣塔石瑤族水族鄉(xiāng)喬央村,是一個(gè)以瑤族、水族、苗族、侗族為主的少數(shù)民族村寨。在2020年時(shí),村寨總?cè)丝谟?45人,長期在外務(wù)工的村民就達(dá)到了350人。由于外出務(wù)工的人數(shù)超過了全村人數(shù)的一半,村寨空心化、家庭“空巢化”十分明顯。大量青壯年外出務(wù)工,使得整個(gè)村寨看起來沒有生氣。村民感受最為明顯的是,過去水族、瑤族、布依族、侗族村民過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的積極性很高,在過節(jié)時(shí)不同民族村民交往互動(dòng)的機(jī)會還比較多,但隨著大量村民外出務(wù)工,傳統(tǒng)的民族節(jié)日沒有以前熱鬧了。
畢節(jié)市金沙縣的柳塘鎮(zhèn)淹壩村,居住著彝族、苗族、漢族和布依族村民。盡管淹壩村離縣城較近,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也較為完善,但大部分村民的生計(jì)方式仍然以外出務(wù)工為主。在2020年時(shí),全村1627 人,長期外出打工的村民就超過了600人。淹壩村的村寨空心化、家庭空巢化的問題也十分突出,村落共同體同樣處于解體過程中。很多村民對當(dāng)前鄉(xiāng)村生活的感受是散,幾個(gè)民族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對集體活動(dòng)都失去了興趣,村民最在乎的事情是如何通過外出打工增加家庭經(jīng)濟(jì)收入。
(二) 地方政府的脫貧攻堅(jiān)策略
在脫貧攻堅(jiān)時(shí)期,地方政府最為核心的工作是使貧困家庭達(dá)到“一達(dá)標(biāo)、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標(biāo)準(zhǔn)。為了使貧困家庭的經(jīng)濟(jì)收入達(dá)到脫貧標(biāo)準(zhǔn),地方政府除了幫助貧困人口發(fā)展種植業(yè)和養(yǎng)殖業(yè)之外,一種更為迅速和穩(wěn)妥的脫貧方法是勞務(wù)輸出。筆者在多個(gè)少數(shù)民族村寨中與村干部交談時(shí),村干部一致認(rèn)為一戶貧困家庭只要有一個(gè)勞動(dòng)力在外務(wù)工,這戶貧困家庭脫貧就不成問題。在脫貧攻堅(jiān)工作中,便存在“外出務(wù)工一人,脫貧一戶”的說法。
脫貧攻堅(jiān)時(shí)期地方政府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通過鄉(xiāng)村自治組織發(fā)展、集體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公共生活重建來提升鄉(xiāng)村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內(nèi)生動(dòng)力,但地方政府在如期完成脫貧攻堅(jiān)任務(wù)的壓力下,強(qiáng)調(diào)短期內(nèi)增加貧困人口家庭收入,導(dǎo)致了村莊公共性流失,進(jìn)一步影響到了村寨內(nèi)部的社會整合。很多貧困地區(qū)的地方政府認(rèn)識到靠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發(fā)展帶動(dòng)貧困人口脫貧存在很大的困難,便積極組織勞務(wù)輸出,鼓勵(lì)青壯年勞動(dòng)力外出務(wù)工。這種做法可以比較迅速地增加貧困人口的家庭經(jīng)濟(jì)收入,但也導(dǎo)致了村寨人口流動(dòng)加劇,客觀上助推了少數(shù)民族村寨村落共同體解體的進(jìn)程。
除了勞務(wù)輸出導(dǎo)致村寨人口外流,易地扶貧搬遷也同樣導(dǎo)致了村寨人口外流。在喬央村和淹壩村,均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在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實(shí)施后永久性地離開了長期生活的村寨。搬出去的村民認(rèn)為,易地扶貧搬遷影響到了他們的社會交往。過去生活在村寨中時(shí),生產(chǎn)勞動(dòng)中的換工、村民之間頻繁的人情往來在很大程度上促進(jìn)村民的交往互動(dòng),也維系了村落共同體的存續(xù)。易地扶貧搬遷后已經(jīng)不存在換工,人情往來也要比以前少得多。總的來看,脫貧攻堅(jiān)時(shí)期的勞務(wù)輸出和易地扶貧搬遷加劇了貴州少數(shù)民族村寨的人口流失,也進(jìn)一步導(dǎo)致了村落共同體走向崩解。
(三) 交通狀況改善影響了村民的社會生活
當(dāng)村民的社會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地域范圍有限時(shí),使得他們的社會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大多是發(fā)生在村寨內(nèi)部,村民過著一種內(nèi)向型的社會生活。山區(qū)鄉(xiāng)村的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落后,導(dǎo)致村民難以得到外部市場資源支持,山區(qū)村民為了生存下去,就內(nèi)生出一套緊密而有效的“社會化幫工”組織方式,以應(yīng)對單家獨(dú)戶無法完成的事情。“社會化幫工”本質(zhì)上指的是村民在生產(chǎn)生活中的勞動(dòng)力交換,促進(jìn)了村民的交往互動(dòng)和社會聯(lián)結(jié),也形成和維系了村落共同體。隨著山區(qū)交通條件的改善,村民的社會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范圍擴(kuò)大,必然會影響到村寨內(nèi)部村民之間的交往互動(dòng)頻率。
交通條件的改善,有效削弱了山區(qū)農(nóng)村的空間隔離程度,提高了要素流動(dòng)和經(jīng)濟(jì)交流,使村民融入了更為廣泛的外部市場之中。在喬央村,交通狀況改善對村民社會生活的影響就十分明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村民之間的勞動(dòng)力交換,使得村寨內(nèi)部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像以前一樣有強(qiáng)烈的彼此需要的生活感受。在2018年以前,村民在新建房屋時(shí),都需要通過勞動(dòng)力交換的方式請親戚和周圍的鄰居幫忙建造。2018年以后,喬央村借助扶貧資金,將2米寬的土路擴(kuò)展為4米寬的水泥路,交通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運(yùn)輸成本和與外界交流的成本也大幅下降。筆者在村寨中訪談時(shí),很多村民認(rèn)為水泥路通了以后,對他們?nèi)粘I钣绊懽蠲黠@的是村民之間的勞動(dòng)力交換比以前少了很多。
村民以前修建房屋時(shí)必須要請親戚和鄰居幫忙,這樣的勞動(dòng)力交換無疑促進(jìn)了村民之間的交往互動(dòng)。自從水泥路修通以后,很多村民在修建房屋時(shí)不再請親戚和鄰居幫忙,而是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承包給榕江縣城里的專業(yè)建筑施工隊(duì)。很多村民認(rèn)為,過去通過勞動(dòng)力交換的形式建造房屋,表面上是不需要出錢請建筑工人,減少了建房時(shí)的現(xiàn)金支出。但自己以后也要不斷地還人情,幫親戚和朋友建造房屋,導(dǎo)致沒有多少時(shí)間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家庭經(jīng)濟(jì)收入。交通條件改善以后,村民對外溝通交流成本下降,村民可以依靠市場力量來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降低了對親戚和鄰居的依賴程度,自然也就降低了村民之間交往互動(dòng)的頻率。
(四) 民族文化變遷導(dǎo)致村寨公共性流失
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中的儀式、唱歌、跳舞等集體歡騰,發(fā)揮著整合村民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后,民族地區(qū)的社會文化經(jīng)歷了快速變遷,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hù)與傳承面臨許多困境,直接導(dǎo)致了民族文化習(xí)俗與儀式的社會整合力量越來越弱。
民族傳統(tǒng)文化變遷在很大程度上導(dǎo)致了村民不再重視本民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村莊公共性流失。一些村民認(rèn)為,現(xiàn)在很多人在外打工,從年頭忙到年尾,只有春節(jié)期間才會回家過節(jié),都已經(jīng)不重視本民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在多年以前,每遇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時(shí),大家都會放下手中的事情,經(jīng)常聚在一起吃飯飲酒,或是唱歌跳舞。大家聚在一起的時(shí)間多,自然就會有一種親密感,不僅會認(rèn)為我們是一個(gè)民族的人,還會認(rèn)為我們是一個(gè)村的人,對村寨有很高的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喬央村離鄉(xiāng)政府和縣城都比較遠(yuǎn),瑤族、水族、侗族和布依族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保留相對較好,但很多村民也是常年在外打工,除了春節(jié)期間回家外,參與本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的積極性并不高。
二、貴州民族地區(qū)村落共同體重建思考
(一) 村落內(nèi)生互惠秩序視角
莫斯認(rèn)為,禮物贈予—接收—反饋3個(gè)緊密關(guān)聯(lián)的行為過程,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社會聯(lián)結(jié)與社會團(tuán)結(jié)是鄉(xiāng)村社會的一種重要的社會整合力量。在人口流動(dòng)的背景下,互惠機(jī)制的存在與運(yùn)作是村落共同體得以存續(xù)的重要基礎(chǔ)。市場經(jīng)濟(jì)的交換原則已經(jīng)滲透進(jìn)入中國鄉(xiāng)村社會,造成了村民之間的關(guān)系由過去的互惠關(guān)系轉(zhuǎn)變?yōu)榻?jīng)濟(jì)交換關(guān)系,導(dǎo)致了村落共同體走向崩解。要想重建村落共同體,就必須要?jiǎng)?chuàng)造條件,重新恢復(fù)過去村民之間長期存在的互惠關(guān)系。村民之間穩(wěn)固的互惠關(guān)系確實(shí)能夠維系村落共同體的存續(xù),但忽視了中國鄉(xiāng)村人口流動(dòng)對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改變。賀雪峰的研究早已指出,中國鄉(xiāng)村的人口流動(dòng)不只是在城鄉(xiāng)之間往復(fù)循環(huán),還有大量的村民永久性地離開村莊,意味著他們會選擇退出過去的人情圈和互惠圈。在中國鄉(xiāng)村人口大流動(dòng)的時(shí)代背景下,試圖重建村民之間傳統(tǒng)的互惠機(jī)制,對于促進(jìn)村落共同體重建所能發(fā)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二) 村落公共事業(yè)視角
自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實(shí)施以后到現(xiàn)在“半工半耕”農(nóng)村社會結(jié)構(gòu)形成,特別是在農(nóng)業(yè)稅費(fèi)全面取消后,村集體喪失了收入來源和資源再分配能力,村莊也喪失了公共性,無法讓村民對村集體組織產(chǎn)生認(rèn)同感,對村落產(chǎn)生歸屬感,村民變得個(gè)體化和功利化,導(dǎo)致了村落共同體解體。這就需要以社區(qū)公共財(cái)力為依托,圍繞著社區(qū)公共物品的供給與管理、社區(qū)合作以及社區(qū)公共意識培育和公共行為引導(dǎo)為核心的社區(qū)互動(dòng)及其形成的秩序。如果要以社區(qū)公共財(cái)力為依托,通過向村民提供公共服務(wù)的形式將村民重新組織起來,就必須要解決社區(qū)的公共財(cái)力從哪里來的問題。
(三) 民俗文化視角
奧格本提出的“文化墮距”理論認(rèn)為,物質(zhì)文化變遷的速度要遠(yuǎn)遠(yuǎn)快于精神文化變遷的速度。人們之所以會認(rèn)為中國鄉(xiāng)村走向衰敗,村落共同體走向崩解,主要是基于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經(jīng)濟(jì)變遷的認(rèn)識,忽視了在中國鄉(xiāng)村中仍然廣泛存在的民俗文化還具有整合鄉(xiāng)村社會的能力。孫慶忠的調(diào)查研究就發(fā)現(xiàn),在某些鄉(xiāng)村中盡管年輕人大量外出務(wù)工,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喪失生機(jī),但留守在村寨中的老年人仍然在實(shí)踐民俗儀式,讓漂泊在外的年輕人不要忘記村寨中的家園。民間的文化儀式能夠在個(gè)體、家庭、宗族之間進(jìn)行有效社會整合,促進(jìn)鄉(xiāng)村公共性重建,有利于維系村落共同體的存續(xù)。鄉(xiāng)村文化振興、民俗儀式復(fù)興無疑有助于加強(qiáng)村民之間的凝聚力,有利于重建村落共同體。
(四) 居住空間重組視角
“鄉(xiāng)村過疏化”現(xiàn)象不僅包括人口流出、易地扶貧搬遷導(dǎo)致的鄉(xiāng)村人口減少,還反映在鄉(xiāng)村居住空間的變遷方面。“鄉(xiāng)村過疏化”使得村民的空間分布愈發(fā)分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村民之間的交往互動(dòng)。筆者在最近幾年的田野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隨著人口流出加劇,山區(qū)鄉(xiāng)村由三五戶村民組成的聚居點(diǎn)已經(jīng)十分常見。村民普遍認(rèn)為人少了以后在生產(chǎn)生活中感到十分不便,家里有個(gè)急事也找不到鄰居幫忙。在“鄉(xiāng)村過疏化”已經(jīng)不可逆轉(zhuǎn)的情況下,通過對鄉(xiāng)村居住空間進(jìn)行規(guī)劃,將分散的村民重新整合在一起生活,有利于促進(jìn)村民之間的交往互動(dòng),培育村民的村落共同體意識。國家作為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擔(dān)綱者需要一種新的方式進(jìn)行合理的規(guī)劃安排,創(chuàng)造新的組織方式實(shí)現(xiàn)群體的再組織,進(jìn)而推動(dòng)共同體生活的再生。
當(dāng)前,中國社會已經(jīng)進(jìn)入后鄉(xiāng)土?xí)r期,不流動(dòng)的鄉(xiāng)村演變?yōu)槿丝诖罅鲃?dòng)鄉(xiāng)村,鄉(xiāng)村的社會結(jié)構(gòu)分化和多樣化,鄉(xiāng)村社會性質(zhì)已經(jīng)受到現(xiàn)代化和市場化的深刻影響。費(fèi)孝通先生論述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dòng)是基于倫理、道德、血緣等關(guān)系構(gòu)成的鄉(xiāng)土已經(jīng)式微,鄉(xiāng)村受到現(xiàn)代化和市場化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guān)系正在深化和拓展。因此,在后鄉(xiāng)土中國時(shí)期,村民之間的交往互動(dòng)必然是建立在契約關(guān)系、合作關(guān)系之上,所要重建的村落共同體也是村民之間走向合作的合作共同體。
三、貴州民族地區(qū)村落共同體重建的路徑
當(dāng)前,村莊公共性重建依靠的是基層政府為各民族村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wù),以此培育村民對村寨的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國家層面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規(guī)劃強(qiáng)調(diào)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興旺和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可以從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和推動(dòng)農(nóng)民組織化建設(shè)兩個(gè)方面重建村莊公共性,進(jìn)而促進(jìn)少數(shù)民族村寨的村落共同體重構(gòu)。同時(shí)也要發(fā)掘、改造和利用有利于村落秩序生成和民族關(guān)系和諧的民族文化要素,如民間儀式的社會整合功能、村落內(nèi)部互惠秩序的重建和維護(hù)等。
(一) 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
一般而言,在缺失集體經(jīng)濟(jì)支撐的村莊,村級黨組織的組織動(dòng)員能力和行動(dòng)能力比較單薄,而且組織軟弱渙散,缺乏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難以發(fā)揮黨組織對農(nóng)村工作特別是鄉(xiāng)村建設(shè)事業(yè)進(jìn)行全面協(xié)調(diào)和領(lǐng)導(dǎo)的能力。從制度變遷角度看,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實(shí)施后,很多地方對集體經(jīng)濟(jì)“統(tǒng)”的功能在鄉(xiāng)村發(fā)展中的作用認(rèn)識不足和矯枉過正,不少農(nóng)村從“大一統(tǒng)”走向集體資產(chǎn)被分光賣光,導(dǎo)致了村集體經(jīng)濟(jì)解體,很多村落蛻變?yōu)闆]有集體經(jīng)濟(jì)來源的空殼村。由于沒有集體經(jīng)濟(jì)支撐,村集體尤其是基層黨組織缺乏經(jīng)濟(jì)基礎(chǔ),難以向村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wù),村寨喪失了公共性。
喬央村的村支書兼村委會主任盤應(yīng)海在2018年成立了喬央村兄弟原生態(tài)種養(yǎng)殖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還成立了喬央村級集體經(jīng)濟(jì)有限公司,走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道路,2020年時(shí)村集體經(jīng)濟(jì)收入達(dá)到了3 萬元。村集體經(jīng)濟(jì)收入增長后,每年村子里有考上大學(xué)的學(xué)生獎(jiǎng)勵(lì)1000元,也幫助村里容易返貧的邊緣戶繳納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費(fèi)用。盤應(yīng)海指出,過去村里的集體經(jīng)濟(jì)收入太少,村委會無法向村民提供公共服務(wù),村民認(rèn)為村委會可有可無,都自顧自地在外打工,對村里的大小事情漠不關(guān)心,對村寨的認(rèn)同感越來越低。通過這幾年大力發(fā)展村集體經(jīng)濟(jì),為一些村民解決了生產(chǎn)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村民開始關(guān)心村里的大小事務(wù)。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好了,農(nóng)民在家里收入比較可觀,就沒有多少村民愿意外出打工,村寨也會恢復(fù)過去的生氣,“三留守”問題自然也就解決了。
(二) 推動(dòng)農(nóng)民組織化建設(shè)
新時(shí)代的鄉(xiāng)村振興,必須以農(nóng)民的組織化重建鄉(xiāng)村的主體性,以鄉(xiāng)村為主體吸納整合各種資源要素,培育鄉(xiāng)村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重塑城鄉(xiāng)關(guān)系。鄉(xiāng)村振興固然離不開外部的資金、技術(shù)、人才的支持,但鄉(xiāng)村振興的主體只能是生活于鄉(xiāng)村之中的廣大農(nóng)民,也只有組織起來的農(nóng)民才能將國家輸入鄉(xiāng)村的資源轉(zhuǎn)化為建設(shè)美好生活的能力。賀雪峰認(rèn)為,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實(shí)施的時(shí)代背景下,將農(nóng)民組織起來的最重要制度基礎(chǔ)是農(nóng)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及建立在該制度基礎(chǔ)之上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
在現(xiàn)代社會,人的“原子化”決定了人們在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必須以契約為基礎(chǔ),在社會分工的前提下,也只有契約才能使人們在社會活動(dòng)中開展合作。因此,要以現(xiàn)代社會的契約為基礎(chǔ),圍繞著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利益的分配和使用建構(gòu)鄉(xiāng)村社會組織,引導(dǎo)農(nóng)民重新走向社會合作,加強(qiáng)農(nóng)民之間的社會連接,重構(gòu)現(xiàn)代意義上的村落共同體。就此而言,鄉(xiāng)村振興背景下的貴州民族地區(qū)村寨村落共同體重建,需要圍繞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培育村民的公共意識、公共合作、公共精神,繼而增強(qiáng)村寨的凝聚力和村民對村寨的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
(三) 發(fā)揮民族文化的社會整合能力
中國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功能上的弱化,并不等于鄉(xiāng)村文化也在走向衰敗,中國鄉(xiāng)村正在經(jīng)歷的是一個(gè)社會文化轉(zhuǎn)型過程。貴州民族村寨經(jīng)歷了持久的社會文化變遷,但很多民族村寨仍然保留了濃郁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要素,這些文化要素在村民的生產(chǎn)生活中還在發(fā)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討論民族地區(qū)鄉(xiāng)村振興和村落共同體重建時(shí),不僅需要大力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也需要利用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社會整合作用來重建村落共同體。傳統(tǒng)的民間文化儀式能夠在個(gè)體、家庭、宗族之間、村落之間、甚至跨越省域的空間之間進(jìn)行有效社會整合,進(jìn)而促成鄉(xiāng)村社會公共性的重建。鄉(xiāng)村公共性的重建不僅需要新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還可以借助民族傳統(tǒng)文化要素。同時(shí),對于歷史上的少數(shù)民族而言,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往往是嵌入在社會體系之中,并非單純地以營利和財(cái)富積累為目的。在多個(gè)少數(shù)民族社會中,“正是社會交際的需要讓生產(chǎn)的動(dòng)力超越了基本生存需求界限,并客觀地實(shí)現(xiàn)了共同體的持續(xù)社會整合,從而讓村寨經(jīng)濟(jì)的目標(biāo)極大程度地指向村寨的整體存續(xù)保障”。
四、結(jié)語
貴州民族地區(qū)在村落共同體重建過程中,應(yīng)該重點(diǎn)探索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依托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將分散的農(nóng)民重新組織起來,重建鄉(xiāng)村公共性。并圍繞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在村民之間建立利益聯(lián)結(jié)機(jī)制,培育村民對村寨的歸屬感和認(rèn)同感,重建現(xiàn)代意義上的合作共同體,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鄉(xiāng)村全面振興問題的解決思路。貴州民族地區(qū)在經(jīng)歷了快速的社會文化變遷之后,民族傳統(tǒng)文化仍然在他們的生產(chǎn)生活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促進(jìn)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利用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有利于村民開展社會合作的文化要素,可為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尋找民族文化支點(diǎn),也成為維系村落共同體存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