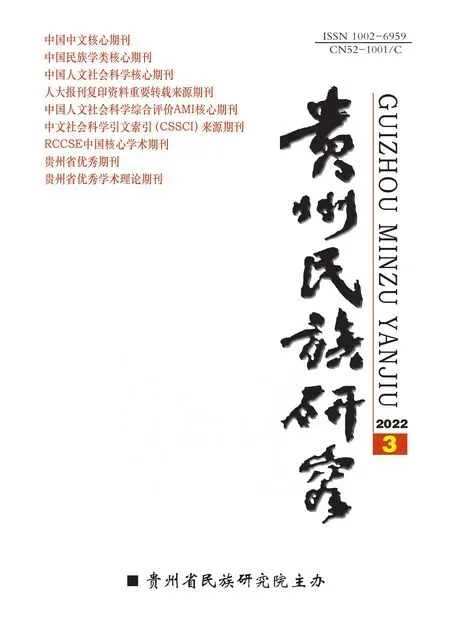革命語境下中國共產黨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歷史演變
王金玲
(貴州民族大學 多彩貴州文化協同創(chuàng)新中心,貴州·貴陽 550025)
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作為中國共產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一項基本政策,在黨的百年民族工作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由于這一政策的確立,中國共產黨經歷了艱難的探索歷程,因而其發(fā)展演變的脈絡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部分學者以某一次會議或某一綱領性文獻的發(fā)表為轉折點,標志中國共產黨民族區(qū)域自治的確立。有學者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作為中國共產黨民族區(qū)域自治確立的標志;有學者以1941年《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的發(fā)布為標志;也有學者以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頒布作為黨的民族區(qū)域自治確立的標志。這樣的研究視域可以讓我們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實中抓到問題的主旨。通過對中國共產黨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歷史演變的詳細梳理和闡釋,不僅可以對其發(fā)展演變的軌跡給予客觀清晰地認識與正確審視,而且有助于深化對我們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從而達到在新時代更加堅定中國共產黨民族區(qū)域自治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的目的。
一、中國共產黨早期對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摸索與初步嘗試(1921—1936)
由于這一時期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以及國情掌握的局限,中國共產黨早期對民族問題的處理主要堅持民族自決、聯邦制的主張。但黨對民族自決、聯邦制的運用,始終根據革命中心問題的發(fā)展變化而進行調整,由此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探索之路。
(一)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就明確自己是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主張民族平等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由于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掌握的局限,黨在一大期間并沒有提出明確的革命綱領和解決民族問題的綱領原則。經過一年的革命錘煉,黨在二大宣言中不僅明確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還提出了解決民族問題的綱領原則:“只有打倒資本帝國主義以后,才能實現平等和自決……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由于這一綱領原則中同時出現了“自決”“自治”和“聯邦”的表述,因而有部分學者認為該時期黨在民族問題的處理上完全照抄照搬蘇聯模式,事實上這一說法有失公允。黨在二大宣言中明確提出:“聯邦的原則在中國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我們黨認為聯邦制原則只適用于地處邊疆的蒙古、西藏和新疆,因為這些邊疆少數民族地區(qū)既受到帝國主義瓜分的威脅,又遭受中國各派封建軍閥武力鎮(zhèn)壓和大漢族主義的壓迫,若將它們強行統(tǒng)一于軍閥混戰(zhàn)的中國本部,不但不能實現他們渴望民族自決自治的愿望,反而擴大了軍閥統(tǒng)治的地盤,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革命的發(fā)展。這表明,黨在聯邦制的運用上是經過深度思考的,而非全盤接收。
(二) 在國共合作背景下,黨在民族自決的表述上呈微妙委婉之勢
國民黨在一大宣言中提出了“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這一點似乎是國共兩黨的共識,但若深究國共兩黨民族政策的主張,就會發(fā)現兩種民族政策之間在內涵與價值取向上的對立。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政策,而國民黨卻一味地堅持大漢族主義民族同化政策,始終寄希望于實現資產階級單一民族國家的構想,正如孫中山所言:“使藏、蒙、回、滿同化于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也就是說,國民黨一大宣言所倡導的“承認民族自決權”完全是從國民黨自身利益出發(fā),希望少數民族與之一起抗擊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待革命勝利后仍然對少數民族實行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和同化政策。中國共產黨鑒于國共合作的現實和革命發(fā)展的需要,對民族自決的問題表述得微妙委婉。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提出“中國民族”,而沒有具體指國內的哪些民族,在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中再次表明了堅持民主政治的決心,提出了邊疆少數民族和中國本部的關系由各民族自決。這不僅維護了國共合作的大局,又體現出國共兩黨在民族政策主張上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三) 大革命失敗后,黨在民族自決的表述上呈激進之勢
1927 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分別在上海和武漢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反革命政變,使大批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遭到了血腥屠殺。大革命失敗后,處在極度危難中的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各族人民加入到黨領導下的革命陣營,以挽救中國革命的危局,在解決民族問題的主張上更加堅定民族自決,并呈激進之勢。1927年11月,黨中央在上海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中國共產黨認為必須宣言承認內蒙古民族有自決的權利”,半年之后,黨又提出:“統(tǒng)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接著又在《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明確指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問題……對于革命有重大的意義。”1929年1 月,黨在《中國共產黨紅四軍軍黨部“共產黨宣言”》 中提出“統(tǒng)一中國,承認滿、蒙、回、藏、苗、瑤各民族的自決權。”顯然與黨在六大上提出的革命宣傳口號“統(tǒng)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有著很大不同,賦予了南方少數民族民族自決權。雖然這一時期黨在民族自決的表述上呈激進之勢,在某種意義上,這只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統(tǒng)治對抗的一種策略性口號宣傳,《中共中央給云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地處云南的苗族同胞正和云南的工農群眾一起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侵略壓迫,現在黨對云南的革命宣傳口號只能是民族自決。可見,我們黨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針對任何民族都提倡民族自決權,每一次提出都是基于中國革命發(fā)展和各民族利益的綜合考量。
(四) 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初步嘗試
1933 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qū)發(fā)起了第五次“圍剿”。國民黨因軍事上的絕對優(yōu)勢,以及黨中央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對紅軍錯誤的軍事指揮,致使黨的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于1934 年10月被迫撤出了中央蘇區(qū)根據地,實行戰(zhàn)略轉移,踏上了長征之路。在長征過程中,黨和紅軍與南方少數民族有了充分接觸,不僅宣傳了黨的民族政策,而且還嘗試性地實施了黨的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第一,建立了兩個藏族革命政權。1935 年5月,紅四方面軍進入了四川西部的藏、彝等少數民族聚居區(qū),為了保障藏族同胞的民主權利,黨在蘇聯民族政策的影響下,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建立了兩個藏族革命政權,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民族區(qū)域自治性質的地方政權。雖然這兩個革命政權都是我們黨對列寧民族自決權的一次摸索,與中國國情不符合,解決不了中國的民族問題,但為今后黨的民族工作開展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第二,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1936年10月,由紅十五軍團和中共陜甘寧省委共同籌建的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成立,該政府機關人員不僅通過民主選舉產生,而且基本上都是由回族人民自己來擔任,真正實現了回族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治訴求。從行政隸屬來看,該政府是在陜甘寧省委領導下的一個縣級地方自治區(qū)域,因而它“是中國共產黨探索以民族區(qū)域自治方式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一次重要嘗試”,為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qū)推行民族區(qū)域自治積累了寶貴經驗。
二、全面抗戰(zhàn)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區(qū)域自治的進一步嘗試和深化(1937—1945)
“七七”事變爆發(fā)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在亡國滅種面前,全體中國人民深深地體會到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的民族危機感。因此,我們黨提出了只有國內各個民族團結起來共同御敵,才能保證抗戰(zhàn)取得最后的勝利。該時期黨并沒有完全放棄民族自決和聯邦制主張,而是在民族戰(zhàn)爭的形勢下,民族自決應以維護國家統(tǒng)一為前提,即使該時期黨提到民族自決,對內是不包含民族獨立的自決,對外是中華民族對帝國主義的自決。我們雖然承認民族自決權,但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滅亡中國之際,若一再地強調民族自決,其結果只能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削弱中國革命力量。因此,當時只能是在建立統(tǒng)一國家的條件下,實行民族自治,才有利于全中國。
全面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進一步鞏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民族區(qū)域自治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之下,只有少數民族與漢族聯合建立統(tǒng)一的國家,在統(tǒng)一的國家內各少數民族享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利,這樣不僅滿足了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愿望,更有利于形成全民族抗戰(zhàn)的合力。同時要求地方政府對少數民族和漢族雜居的地方在設置少數民族委員會和省縣政府委員會中要有少數民族的位置,以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實施。可見,該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則,在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內以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形式來保障少數民族的權益。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無論在政策的制定上還是宣傳上,更加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和國家的統(tǒng)一性。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這個國家不是由漢族一個民族組成,而是由中國境內的多個民族結合而成。這不僅為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提供了理論支撐,同時奠定了抗戰(zhàn)勝利的基礎。在此認識的基礎上,黨的民族政策也進行了重要的調整,主要體現在《建設回民自治區(qū)》這一重要的黨史文獻中,該文獻在黨的民族區(qū)域自治發(fā)展演變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從文獻內容來看,這是中國共產黨比較全面具體地論述黨的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專題性文件,不僅深化了黨對民族區(qū)域自治的認識,而且為陜甘寧邊區(qū)進一步實施黨的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導和參考。首先,關于回民自治區(qū)的性質問題,文獻的第一部分指出:“回民自治區(qū)是民族平等政策在今天中國的具體應用,它的任務是團結抗戰(zhàn),實現民族平等,因此它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自治區(qū)。其政權是回民族各階級各階層聯合的政權——‘三三制’的政權。”體現的政權性質為新民主主義。其次,從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內涵來看,文件揭示了地方自治政權與國家不可分離的關系以及民族區(qū)域自治的職權范圍。文件明確指出:在陜甘寧邊區(qū)實行的回民自治區(qū)域從領土歸屬來看仍然屬于邊區(qū)領土的一部分。文件又從法律的角度對民族區(qū)域自治的職權范圍給予解釋。文件指出:民族自治區(qū)在邊區(qū)的范圍內雖然有權制定符合本民族特點的單行法規(guī)和條例,但對于邊區(qū)的一切政治方針和法令制度也必須毫無條件地遵照和執(zhí)行。再次,強調了建設回民自治區(qū)的重要性。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共產黨愈發(fā)地重視民族政策的調整和完善,以滿足全民族抗戰(zhàn)的需要。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報》 社論指出:“必須允許國內各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有平等權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則下……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區(qū)”。可見,建設民族自治區(qū),已被黨視為團結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必需條件。1942年春夏之際,陜甘寧邊區(qū)建立了2 個自治區(qū)、3個自治鄉(xiāng)、1個自治委員會。這些基層民族自治政權的建立,實現了自治地區(qū)民族當家作主的愿望,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三、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實踐與確立(1946—1949)
抗戰(zhàn)勝利后,內蒙古地區(qū)因突出的戰(zhàn)略位置,使國共兩黨對其展開了激烈爭奪。1945年10月23日,黨中央在《關于內蒙工作方針給晉察冀中央局的指示》 中明確指出:“在目前我黨控制熱、察、發(fā)展東北、取得華北優(yōu)勢的方針下,內蒙在戰(zhàn)略上具有極重要的地位,適當地解決內蒙民族問題,不僅關系內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夠建立我黨我軍鞏固的后方及和蘇、蒙軍取得直接連系的有利地位。”因此,黨非常重視內蒙古地區(qū)的民族工作。那么,如何將蒙古族人民從反動派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真正地實現蒙古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愿望,成為中國共產黨抗戰(zhàn)勝利后亟需解決的一項重要歷史任務。對此,黨指出:“對內蒙的基本方針,在目前是實行區(qū)域自治。”在這一方針的指示下,黨中央委派蒙古族共產黨員烏蘭夫等去解決問題。鑒于此,晉察冀中央局與烏蘭夫多次研究商議,對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提出分兩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成立一個具有政府咨詢機關性質的半政權、半群眾團體的統(tǒng)戰(zhàn)機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在它的統(tǒng)一領導下開展內蒙古自治運動。第二步,由該自治運動聯合會對內蒙古地區(qū)各盟旗的蒙古族上層實施統(tǒng)戰(zhàn),極力團結蒙古族中的王公、知識分子。待各方面工作有了一定基礎時,再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該商議決定后,晉察冀中央局將結果上報給黨中央,中央立即回電批準了所呈報的內容,并同意烏蘭夫同志繼續(xù)留在內蒙古地區(qū)主持工作。
接到黨中央的指示后,烏蘭夫等人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經過三次籌備會議的精心準備,最終于1945年11月26日在張家口正式成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功地解決了“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的問題。關于“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的問題,黨中央指示:“在今天整個國內國際形勢下,成立這種自治共和國式的政府仍然是過左的……東蒙今天應依和平建國綱領第三節(jié)第六條實行地方自治……而不應與中國形成所謂宗主國與類似自治共和國的關系。”1946年3月,烏蘭夫到達承德與東蒙代表團就內蒙古東西盟統(tǒng)一問題進行協商洽談。烏蘭夫等人認真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對東蒙代表團提出“獨立自治”會嚴重損害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應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區(qū)域自治”和“平等自治”的方針,以此來實現內蒙古人民的解放。經過五次預備會議和會下的討論協商,雙方代表決定于1946 年4月3日,在承德正式舉行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統(tǒng)一會議,即著名的“四三會議”。“四三會議”的召開,標志著300年來一直處于分裂局面的東西蒙統(tǒng)一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蒙古族人民的解放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成立,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對內蒙古地區(qū)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的領導地位,為內蒙古地區(qū)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46 年6月,國民黨徹底打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發(fā)動了全面內戰(zhàn),在對各個解放區(qū)發(fā)動猛烈軍事進攻的同時,對邊疆少數民族仍然推行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并在內蒙古地區(qū)有所策動。對此,黨中央指出:“為了團結內蒙人民共同抵抗蔣介石的軍事進攻與政治經濟壓迫,現在即可聯合東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避免采取獨立國形式。”1947年春,隨著全國解放戰(zhàn)爭局部反攻序幕的拉開,以及內蒙古自治運動在黨的領導下經過一年時間的發(fā)展呈現出了明顯變化,一些王公、喇嘛等蒙古上層分子,思想發(fā)生了根本改變,主動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自治運動中。廣大農牧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顯著提高,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因此,他們更加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7 年3月23日,黨中央再次對“內蒙古自治問題”發(fā)出了指示,中央指出:“內蒙民族自治政府與中國的關系問題,在大會宣言中應確定內蒙自治政府非獨立政府,它承認內蒙民族自治區(qū)仍屬中國版圖,并愿為中國真正民主聯合政府之一部分”。在黨中央的指示下,1947年4月3日—21 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在王爺廟召開了執(zhí)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安排部署召開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及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相關事宜。4月23 日召開了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撤銷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并討論通過了《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1947年5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第一個省級自治政權——內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它的誕生加強了自治區(qū)內各族之間的團結,有力地支援了全國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1949 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第一次會議正式將民族區(qū)域自治確立為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
總之,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在艱難的民族民主革命實踐中,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指導下,經過長期摸索和反復比較才得以確立的一項基本民族政策,符合中國國情,能夠解決中國民族問題。如今,“經過幾十年的發(fā)展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已經成為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民族政策、基本法律的‘三位一體’,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一大支柱、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一大特色、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大方略,必須毫不動搖地繼續(xù)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