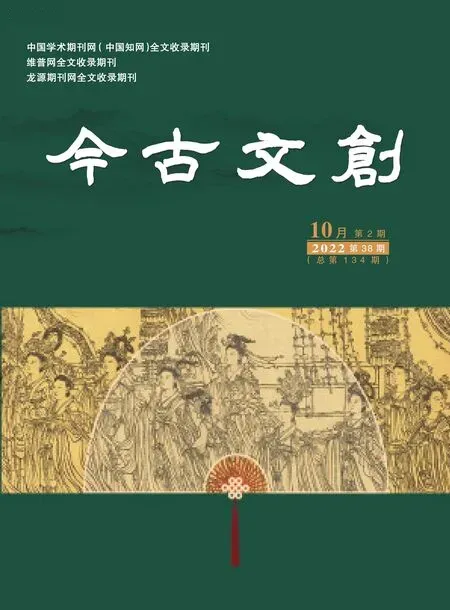嚴復論培根的科學觀
◎吉春曉
(福建師范大學 社會歷史學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一、培根科學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西方科學傳入中國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是時利瑪竇等一批耶穌會士以移植宗教思想為目的譯書著說,在客觀上散播了西方科學。近代以來尤其甲午之后,中西沖突背景下的社會變遷呈現不可逆轉之勢,身處時代困境中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僅有器物之變的不足,隨即將目光轉向了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學思想,并渴望從中覓得救國良策。這一過程中,國人對西方科學思想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而嚴復正是催化這一轉變的學者之一,他將“西學格致”視為“開民智”和“救亡”的不二法門,并以此為據開始翻譯西方科學著作。這一背景之下,培根逐漸走進嚴復的視野。
學界對嚴復科學思想的研究成果豐碩,多數學者從嚴復的“四篇文章”和“八大譯著”出發,進而著手分析嚴復的科學進化論、科學概念和科學方法論。培根雖和赫胥黎、穆勒等人同被稱為西方近代科學的先驅,但其并未在嚴復著作中得到系統引介,這也導致學界對嚴復和培根科學觀的研究屈指可數。《培根及其哲學》一書的附錄提及嚴復與培根,其作者余麗嫦認為“嚴復是自覺地把培根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沈國威在《嚴復與科學》一書依照文本的順序解讀了嚴復譯著中所蘊含的“科學”,其間摻雜對嚴復從培根處得到的科學啟示的討論。李玉通過分析嚴復認知中的培根知識學思想,進一步解釋了其“會通中西”的學術理念。此外,多數研究培根學說東漸的論著在介紹嚴復時僅是走馬觀花,大半討論嚴復科學觀形成的論說提到培根亦止步蜻蜓點水。所以探討嚴復之前培根學說在晚清的傳播,以及嚴復又是如何將培根的思想糅合在自己論說中的,對全面地認識嚴復科學觀仍有相當意義。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的一位全才巨擘,在哲學、科學、法學和文學等領域成就斐然。培根生活的時代正值中國的明中晚期,然而直至19世紀下半葉培根的相關學說才得以傳入中國。據張江華考證,我國最早介紹培根事跡的是王韜《甕牖余談》一書。該書由王韜所著,以傳書的形式對培根做了簡要介紹。值得注意的是,王韜在為培根立傳時,關注到了他的學術創新精神,認為培根為學務在“自有所發明”、立言力求“已所獨創”。”此外,王韜還概括了培根《新工具》的思想主旨,他將《新工具》譯為“格物窮理新法”,認為該書蘊涵著西方科學“物以合理”“實事求是”的精神。
培根科學思想在近代的傳播除了有王韜式的西學先鋒效力外,傳教士群體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格致新法》的作者英國傳教士慕維廉即是代表之一。慕維廉認為培根突破了亞里士多德以來“溺于無用之辯論、虛空之解說”的學術風氣,并贊同其“推從六合凡有實事,并到一處”的科學歸納方法。在論及翻譯《新工具》的目的時,慕維廉認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一直采取躲避的姿態,但他們所不敢直面的,正是“今日所謂急務者也”。他指出“格致”對時務之重要意義,同時批評國人泥古不化,對新知畏難生懼。培根學說在中國數年的傳播,或多或少地引起了正從事翻譯工作的嚴復的注意,這顯露于嚴復譯著中對培根科學觀三大內涵的闡發。
二、嚴復對培根科學觀三大內涵的闡發
費正清認為近代來中西沖突的本質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費氏的“沖擊——反應”模式如今雖存爭議,但其中至少可以看出近代知識分子面對“世變之亟”的種種反應。以嚴復為例,以往先進知識分子探索西學的經驗和其留英經歷使他逐漸意識到了此前所效行西法不過是“淮橘為枳”,這樣下來“民智既不足與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舉其事故也”,因此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而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所帶來的存亡危機,嚴復將目光瞥向了西方科學思想,他認為西方富強的本質在“學術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屈私以為公而已”。于是寄希望于“西學格致”來啟發民智,此后便不斷譯書立說,致力傳播科學。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培根的科學思想經由嚴復得到進一步散播。
(一)“追求真理”的途徑
《天演論》譯自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對培根“求真”理念的關注也在該作品中有所體現。《天演論》卷下首節嚴復提到“道每下而愈況,雖在至微,盡其性而萬物之性盡,窮其理而萬物之理窮”。該句按語中嚴復提及培根,他肯定了培根“首為此言”,并提出真理由科學而生,是國人所應關注。“道每下而愈況”語出《莊子·知北游》,意即越是往低微處探尋,越是能理解何為“道”,這里嚴復附會莊子來解釋培根的科學思想,認為培根的觀點是一切客觀事物無論貴賤都應有其價值,都值得被“盡其性”“窮其理”,如此方能成“格致之事”。
嚴復此番論調并非空穴來風,《新工具》中亦有相關論調:“凡值得存在的東西就值得知道,因為知識乃是存在的表象;而卑賤事物和華貴事物則同樣存在”培根將一切自然事物都納入自己觀察和研究的領域,這一點正是近代科學精神的開端。嚴復以其獨到的眼光將培根這種思想歸結為“求真”二字,并在其同時期另一篇著作中進行充分解釋:“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民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受培根的影響,此時的嚴復已然認定只有從客觀事物中才能獲得真知。
“論三 教源”中嚴復再次提到培根:“善夫柏庚之言曰:‘學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真;教者何?所以求言行之是’。”其后嚴復從培根的話中總結道,學者的首要任務就在于求真,而那些“孜孜于天人之際者”只是內心荒蕪,難得真知。嚴復此言并非毫無緣由,儒學傳統浸染下的士子們“一切皆資于耳食,但服膺于古人之成訓,或同時流俗所傳言,而未嘗親為觀察調查”。泥古不化、無意求真同樣也是中國傳統學者的一類通病。嚴復借培根所言一則表達了對此類學者的不滿,另外從側面暗示了求真觀念之于當時中國社會的普遍意義。
(二)“開發民智”的利器
甲午之后,嚴復“覺一時胸中有物,格格欲吐”,遂寫成時論“西學三篇”。《論世變之亟》一文中嚴復深刻分析了中西方對“古今”態度的差異以及此種差異造就的不同結果,他認為中國人“好古而忽今”,把盛衰交替視為天道使然,而西方人“力今以勝古”,在學術等方面不斷追求進步。”在此基礎上,嚴復進一步總結道,若要學習西方圖求富強,必須把握“西學命脈”——“學術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屈私以為公而已”,直言即是學術上的科學,政治上的民主。
嚴復在天津《直報》上先后兩次刊載《原強》,文中嚴復將“格致之學”提到至關重要的位置。嚴復著重強調了“格致之學”對“去偏僻之情”的先決性作用,而“去偏僻之情”正是“開民智”的關鍵一步。在科學的認識論問題上,培根也曾提出著名的“四假象說”。培根認為只有“以真正的歸納法來形成概念和原理,無疑是排除和肅清假象的對癥良藥。”嚴復在《原強》中的強調“去偏僻之情”的觀點正是與之不謀而合。
細究嚴復“西學三篇”,便可一窺其在危機背景下的救國思維邏輯:獲得太平的第一要義是國家富強,而富強之基則要靠學習群學才能達到,學習群學又要先了解西方物理格致之法,影響西方格致之術普及的首要障礙則是“八股取士”,所以學習“西方格致”作為中間環節既承擔著橋梁作用,又被嚴復當作“廢八股”“開民智”的關鍵手段。“西學三篇”中培根的科學思想雖處處顯露,但培根本人卻直到《原強修訂稿》才被嚴復正式提及。
《原強修訂稿》本是嚴復受梁啟超所托補齊的未完之作,嚴復也想借此機會“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發明富強之事”。《原強修訂稿》的關注點在于如何提高民智民力和民德。嚴復在文中指出民智、民力,民德關乎“一種之所以強,一群之所以立”,而“格致新理”對西方來說啟發了民智、增長了民力、改進了民德。嚴復進而總結歸納到:“(西方)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為稱首……故曰:民智者,富強之原。”在這里,嚴復不僅明示了培根之于“西學格致”的意義,還通過分析得出了民智乃富強之源的結論。
(三)對“歸納科學”的詮釋
17世紀早期,實驗科學的進步呼吁著新的邏輯方法的問世,而在此節點上出現的培根科學歸納法則為當時實驗科學提供了邏輯工具。西方自然科學的進步讓嚴復意識到了邏輯之于中國社會的關鍵性。《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于1903年書成,嚴復在其中將名學列入“應譯外國通行教科書”中,同時還提到名學是確立思想和語言的法則。《穆勒名學》的按語中,嚴復認為名學之所以被稱為邏輯,正因培根所說:“是學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即邏輯是一切學問都要用到的工具和方法。培根所言出自《學術的進展》,書中認為“邏輯乃研究理性的藝術”“一切藝術之藝術”。嚴復受培根等人影響,極為重視邏輯學的作用,在他的八大譯著中,單邏輯學就占兩部。
嚴復在其譯著中通過附會培根學說,解釋了獲取新知需要經歷的邏輯途徑。其第一階段為“考訂”;第二階段為“貫通”,也即是“類異觀同,道通為一”,這一階段是中間環節,強調通過分類觀察事物以發現其背后的本質規律;第三階段為“實驗”,嚴復認為“實驗愈周,理愈靠實”。嚴復所提到的這三個階段對外可以形成一個完整閉環,對啟發人們有效獲取新知可謂意義非凡。嚴復的“三階段論”脫胎于培根“三表法”,“三表法”在內容上“既包括歸納推理,也包括演繹推理、還包括了整理經驗材料的方法”,它主要用于補進自然科學發展下簡單枚舉歸納法的缺陷。“三表法”為嚴復知識論的形成提供了參考模型,但嚴復并沒有原封不動地照搬培根的觀點,而是在表述時采用了國人更容易接納的論調,而嚴復此舉也無疑促進了培根科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
三、嚴復影響下培根科學思想的傳播
嚴復持“會通中西”的理念譯介西方科學著作,客觀上促進了培根科學思想中國的傳播,推動了培根倡導的歸納邏輯在中國的研究與發展。由于嚴復留學英國的經歷和對培根、穆勒的推崇,《穆勒名學》成為嚴復的首本邏輯學譯書。嚴復通過譯著、教學、演講等途徑,致力傳播培根以來的西方近代科學思想,對激勵后來者進一步認識培根科學思想起到了相當作用。
辛亥前后,培根及其科學思想傳播范圍已不再局限于當時的文化中心。由王延直編撰而成的《普通應用論理學》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培根和穆勒的歸納法,該書在云南印刷,于貴陽發行,一定程度上也從側面說明了培根及其科學歸納法在相對偏遠的西南地區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傳播。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新文學、新教育的需要促使著邏輯學研究走向縱深。許多學者在引介培根學說的同時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金岳霖《歸納總則與將來》、謝幼偉的《培根之方法論》等。培根的主要著作《新工具》《崇學論》等從1935年起先后在我國正式翻譯出版。章士釗在其《邏輯指要》一書“例言”中就曾說道:“為國人開示邏輯舉途徑,侯官嚴氏允稱巨子。本編譯名泰半宗之,譯文間亦有取,用示景仰前賢之意。”由此不難得見,嚴復在其譯著中對邏輯學的介紹推進了我國邏輯科學的發展。同樣,在此過程中,蘊于其中的培根科學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四、結語
嚴復的科學思想是其啟蒙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培根的學說又在嚴復科學觀中起到了關鍵的支撐作用。嚴復對培根科學思想的引介與闡發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轉型,他推崇實驗與科學歸納法,堅持去偽存真的科學精神,對于革新國人的思維方式具有奠基性意義。嚴復對西方文化并不是全盤接收,而是根據現實的需求進行甄別,有針對性地借鑒。這其中凝結著嚴復對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與思考,不僅對新時期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還提醒著我們在各種知識觀念紛雜的今天,文化甄別能力和信息過濾機制也要有相應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