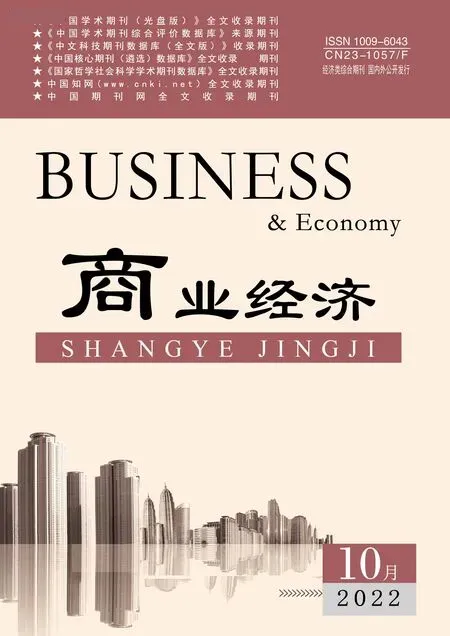國際區域治理的概念與實踐:文獻綜述
鞏浩宇,周帝言
(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 山東 威海 264209)
一、治理與區域的概念
“治理”(governance)一詞源自于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中“掌舵”一詞,原意是操作,控制和引導。受全球化進程的影響,“治理”一詞逐漸進入國際關系領域。國際政治中的治理概念是在1989 年世界銀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問題的報告》首次提出的,即“為了發展而在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資源的管理中運用權力的方法”。羅西瑙對“治理”的概念進行了更為清晰深刻地界定,他認為治理是“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治理是被社會普遍接受的規則體系,包含傳統的政府機制與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兩方面的實踐活動。
治理行為發生的場域也隨著人類活動的拓展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斷變化,安德魯·庫珀認為區域將日益成為對全球問題進行治理合作的場域。而對于區域的內涵,學界也有諸多論述。劉宏認為區域具有獨特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是“關系性的存在、互聯互通的節點和立體的空間結構”。區域的自然屬性正如巴里·布贊所論及的,區域都必須由地理意義上的一組單位聚合而成。而社會屬性則主要體現在實踐性,政治性和歷史性。實踐性上,張乃和指出,同一地域的人們可以在習俗、習慣、規范和法律等共有文化的作用下結成價值共享與互動的文明單元,從而通過實踐建構區域這一共同體。在歷史性上,張云(2019)區域是一種非國家的社會歷史單元,通過地域文化、共同的歷史記憶們將地理上相鄰的行為體凝聚在一起。而在區域的政治屬性上,阿查亞(2014)指出,區域不僅是固定的地理或文化實體,而是社會和政治身份的動態構造。同時,由于區域是多元行為主體的聚合,區域內的權力結構也是政治性的主要體現,正如王學玉(2013)指出,權力結構在區域中是最重要的,在正式的法律意義上,地區處于無政府原則下,由各種等級制的權力結構與關系共同塑造。
區域治理的概念,根據讓·高丹(1988)的研究,最早出現于17 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的論述當中,指一種區域性的政治協調與制度安排。且在政治安排中,區域觀念的等級排序處在國家觀念之先,這是因為當時的歐洲仍處在教權與王權共同統治的格局下。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冷戰的結束使得全球化的發展進入到新的階段,在越來越多國際組織的推動下,對于區域治理的研究也迅速增多。對于區域治理的概念,學界較為共識的是郭樹勇(2014),澤德爾鮑姆(2015)等所主張的“是指某一國際區域內的主權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其他國際關系行為體對區域事務的共同管理。”而從這一概念不同的性質出發,學界對其的再詮釋也較為多元。加里·戈茨、凱斯·鮑爾斯(2014)則強調了區域治理的制度定義,認為它由規則、規范和原則等一系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構成,建立在此智商低特定的管理機構、決策機構和爭端解決機制凸顯了區域治理活動的組織性。而另一些學者,則試圖構建以區域為治理單元的本體論概念,張云(2019)認為,區域治理是人類基于區域場域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以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文明傳承和族群分布為特征,在整個地區范圍內將存在、認識與實踐進行三維整合。
二、區域治理的實踐與發展
功能主義者認為,形式源自功能,跨國性治理行為的出現是為解決某一特定領域的共同問題,并以此作為推動一體化的驅動力。世界面臨著技術問題不斷增加的發展前景,這些問題只有通過跨國合作才能解決,由于現代經濟、技術和其他領域的發展使得國家之間的跨國交流不斷增加,這種互動帶來的外溢效益將為國家之間選擇某一功能性領域開展合作帶來可能。而對于區域治理的興起,張蘊嶺(2019)指出,區域性問題是治理的內因,這類問題范圍廣泛,包括經濟、社會、安全等領域,超出一國能力范圍,需要區域層面的治理。邵鵬(2010)提出,區域治理進程的興起是以區域一體化作為條件的,區域的一體化伴隨著其內部的某種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興起,地區內主要成員間因勢力均衡的共存并協調發展。同時,在一體化進程中,各國進行分工協作,創造并提供公共產品,并在不斷交往中增進主體間的互適性和彼此行為的可預測性,從而推動區域內合作機制的產生。
蘭格(2019)認為,治理的實踐涉及到多層次的互動進程。邵鵬(2010)提到,區域治理是一種多中心的治理主體模式,這主要表現在:政府之間的關系以及區域政府的競爭力是區域治理的主要內容,政府與民間組織、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互動關系也是區域治理的重要內容,區域治理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企業和社會的行為方式。而季劍軍(2017)對作為重要治理主體的區域大國較為重視,大國是區域權力結構中的關鍵變量,在國家組群長期互動中可以保持自身穩定并決定區域走勢的力量;大國擁有較為成熟的國家治理經驗,單邊和多邊的地理和資源優勢,能保證區域治理的領導力,從而引領制度建設和治理框架體系不斷完善。張云(2019)、馬銀福(2020)則肯定了區域組織的作用,他們認為區域政府間組織的組織化、正式化機制的日趨完善,各種組織架構健全。這些組織是協調和溝通區域事務的平臺,也是多重權力交匯的治理機構,構成了區域為主體的框架結構和治理網絡。而區域治理的實踐層次也在不斷發展,俞正梁(2001)、張蘊嶺(2019)、鄭先武(2020)認為,當前區域的治理層次主要有大區域的治理,即以洲為治理單元的治理模式;跨區域的治理,它既是區域化、區域政治與區域治理的強力擴張,又是對全球化、全球政治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補充;以及正在蓬勃發展的次區域治理模式,這些地區的共性更為明顯,更易形成合作與規范的內化。
區域治理的合作進程是學者們對區域治理的實踐發展關注的重點,季劍軍(2017)認為,區域治理合作是成員國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領域中的主權讓渡推動國家治理走向共同治理。張蘊嶺(2019)認為,區域治理的實現有賴于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主要有區域性政治間組織為載體的制度形態、非正式的對話、論壇形式的磋商機制、國家雙邊或多邊的合作等。幾乎所有觀點都認為,歐盟的實踐發展是目前最為成熟的區域合作治理機制,諾爾特(2016)認為歐盟的治理實踐是“以經濟合作為主軸的區域一體化逐漸向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的綜合性治理的過渡”。亨克·奧弗比克(2013)認為,歐盟已經實現了基礎設施建設,各類物質要素流動的區域連接,建立政府間的政治體制,實現了超國家的區域構建。哈貝馬斯(2001)認為歐盟的區域化治理行為遵循政治置于市場之前的邏輯,通過建立政治統一體和跨民族的政權,在確保民族國家的各項功能的基礎上實現超國家民主的合法程序。
亞洲地區的治理實踐在冷戰后愈發受到學界重視。俞正梁(2001)指出,冷戰結束以后,區域性的政治合作和治理實踐加快發展,一種更為開放的區域組織聯系凸顯,最典型的是亞太經合組織,它整合了亞洲地區內基本所有主要國家作為成員國,在政治合作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政治間網絡及多種有關組織,其目的是確立一種開放性與多邊性的制度化論壇,而非進行域內國家的整合,體現了富有東方特色的“開放的地區主義”。張勝軍(2017)認為,西方自由主義語境的治理觀導致全球治理制度和規則碎片化并陷入能力不足的困境,而隨著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和新興國家的蓬勃發展,國際社會中正在逐漸出現“東南主義”的跨區域治理范式,通過其獨有的敘事邏輯和概念性理論構建應對更為緊迫、更為重要和更為廣泛的目標和利益。鄭先武(2020)在亞洲地區區域治理的實踐基礎上總結了三種國際區域治理的行為路徑。
三、區域與全球的關系
而目前學界對于區域與全球的關系存在一定的共識,比較典型的是鄭先武(2020)在拉姆什·塔庫爾(2006)的研究基礎上所總結的:區域是治理單元,在國際關系中有存在的實體,形成了介于全球和國家之間的重要的新型互動層次。因其具有治理所需的特定的區域規則體系和跨國管理機制,與全球治理的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旨在解決國家層次和全球層次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兩者之間架起一座互通的橋梁,因而成為興起中的全球治理的一種重要的補充性層次。可以說,在目前的各項研究成果中,將區域的治理行動較多視作全球治理的補充,或者是赫爾德(2001)所言的“全球治理的中間層次”。
在全球治理與區域治理的互動關系上,霍斯蒂(1992)的研究發現,區域治理的實踐遠遠早于全球性的治理發展,當前全球性的治理實踐和規范有著明顯的區域淵源,區域治理的發展更為深遠。此外對于區域治理對全球治理的促進作用與二者的協同發展,學界也多有論述,俞正梁(2001)認為區域治理與全球治理在本質上是相互依存、相互補促、相互制約、同步進行的,兩者是矛盾的統一體。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可以通過協調與合作并行不悖地發展下去,并實現共同的健康發展。邵鵬(2014)就此問題做了更詳細的闡述,區域治理不僅是一個多邊合作的過程,同時也是上述各種當代合作問題暴露、處理和演進的過程。區域治理能促進國際治理格局多極化和民主化發展的積極態勢,客觀上可以約束全球治理進程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為全球化提供必要的規范。
百年大變變局的到來使國際體系中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在全球層次應對跨國問題的復雜性帶來的較低的可操作性,由此部分學者對于區域化的治理合作前景有著積極的預期。例如,李博一(2020)認為,區域內的國家由于地域的相鄰性,有著更多的相同點和共同利益,從而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基礎。區域一體化可以使它們共同對付外部挑戰,在國際機制或談判中協調它們的區域立場,促進共同收益和價值,解決共同問題。
四、結語
目前對于區域治理的研究,仍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多數研究者將區域作為全球治理的一個部分或一個層次進行研究,而區域作為地理,歷史,與社會實踐的聚合行為體,有著獨立的本體地位,目前對于以區域為本體的理論體系尚未構建。同時,目前學界對于地域經驗的挖掘較為失衡,目前的理論仍是在西方話語主導下對歐洲經驗的挖掘,對于來自亞洲、拉美地區、非洲的治理實踐仍需更深層次的研究,因此,為了構建更具普適性的理論體系,研究案例的來源應當注重多樣化。隨著次區域治理實踐的不斷興起,次區域的區域特性更為明顯,治理合作的形式更為多樣化,對于次區域的研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此外,由于區域長期被視為一個治理的層次,對于區域內部的結構研究仍處于較為空白的狀態,而這對區域治理的本體論地位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對于區域研究的方法論仍處于長期相互割裂的情況,學界尚未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