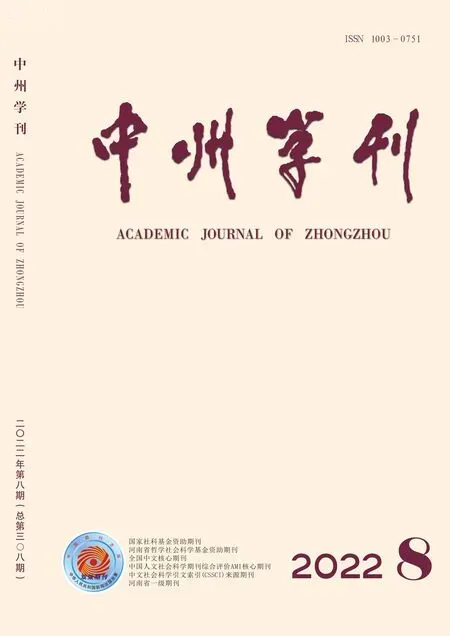明代過繼規則的民間文書表達*
徐 嘉 露
明代戶絕家庭的“過繼”行為無論在國家制定法或是在民間生活層面都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宗法繼承制度,為傳統社會祖先祭祀和財產繼承制度體系增加了開放、多元的“過繼”內容。關于明代民間家庭“過繼”研究,學術界依據明代地方司法官吏留下的判例判牘材料,從案件的具體事實角度對民間“過繼”行為進行了諸多法律與道德評價,但是對約定俗成的民間“過繼”習慣性規則,學術界的研究卻涉及甚少。為多角度挖掘和利用明代社會史料對明代民間社會中的家庭“過繼”現象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以明代民間“過繼”文書為基礎,對明代民間“過繼”行為的內容、方式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民間“過繼”規則進行探討,以期對明代民間“過繼”行為的完整意義有一個新的認識。
一、“過繼”的概念及其相關研究
1.
在中國傳統社會,民間私法的權利繼承稱之為“承繼”,具有現代民法意義上的“繼承”出現于清末變法時期。中國傳統社會的“承繼”和現代民法的“繼承”不只是書寫的不同,其內涵也有明顯區別。中國傳統社會的“承繼”包括公法意義的“承繼”和私法意義的“承繼”。所謂公法“承繼”,是指對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權身份的繼承,如王位的繼承和爵位、封賜的世襲以及政治特權身份的享有。私法意義的“承繼”不僅包括財產權利的獲得,還包括對被繼承人的人身權的承受,同時還包括對被繼承人的義務的承擔。傳統社會的私法“承繼”分家庭內部的“承繼”和家庭之間的“承繼”。在傳統社會,家庭的法律概念是指“同居共財”的社會主體,因此,家庭內部的“承繼”是指“同居共財”人之間的父子、父女相繼,一般為父母尊長以遺囑、分書的方式進行。家庭之間的“承繼”則是同宗或同族內部的非“同居共財”人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承繼”,又稱為“過繼”,明代民間社會常簡稱為“繼”。明代的“過繼”包括家庭之間的同宗繼子“承繼”和異姓養子、養老女婿的“承分”。關于同宗繼子“承繼”的當事人,被立為繼子的同宗侄輩稱為“出繼”,被繼承之家則稱為“入繼”,“自幼哺乳者曰‘養繼’”。明代的“過繼”與“收養”的概念是不同的。《大明令》規定:“凡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侄承繼。”“并不許乞養異姓為嗣,以亂宗族。”即立同宗之侄、孫為嗣稱為“繼”或“承繼”,而收異姓男為養子為“養”或“乞養”,因此明代的“繼”與“養”分別代表不同的“過繼”內容。現代民法的“繼承”一般只包括對被繼承人的財產的取得和債務的有限承擔。所以,傳統社會的“承繼”包括現代社會的“繼承”,如果將現代社會“繼承”的內涵放置于傳統社會“承繼”的概念體系中,“繼承”則是“承繼”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社會,無子家庭不僅指未生育子男的家庭,而且還包括生育有女兒的家庭。在家庭層面,這些家庭因未生育子男而使祖先陷于絕祀境地;在國家層面,這些家庭因無子承擔賦役而導致了作為社會民事主體的“戶”的消失,故稱之為“戶絕”。為了準確把握傳統社會的民間私法語境,筆者在本文擬沿用欒成顯等學者的做法,仍將明代戶絕家庭的“承繼”行為稱為“過繼”,以體現傳統社會的時代特色。
2.
學術界對明代民間家庭私權承繼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借鑒的觀點。美國學者白凱認為,由于征收賦稅的需要,強制侄子繼嗣的立法致使戶絕家庭的女兒們逐漸減少取得娘家財產的機會。汪慶元將徽州民間收養“義男”分為三類,即官宦之家為役使勞作而收養的“義男”為奴隸,庶民地主之家為幫工耕作而收養的“義男”為“雇工人”,自耕農、佃農家庭收養的“義男”與養父彼此“相為依倚”,一般具有互助性質,這些“義男”可以對“義父”繼受財產、承當門戶并入籍當差,應按家庭成員的子孫看待。日本學者臼井佐知子認為,明清時期的承繼規范是以“承宗”和“繼產”展開的,現實目的主要是為繼受家產和承擔戶役,出現了一男在多戶繼產、承戶、養老現象。張萍認為,明清戶絕家庭承繼的方式主要是立嗣與招婿,嗣子多為戶絕家庭的胞侄宗親,因此其地位比招贅女婿高,而為了規范族內“過繼”行為,減少“過繼”糾紛,徽州民間通過制定家法族規和簽訂契約文書的方式干預族內的“過繼”行為。程維榮認為,明代開始允許民間立繼可以“擇賢”“擇愛”。邢鐵認為,明代宗族與戶絕家庭選定的嗣子不一致時,還出現了兩子并立的“并繼”現象。由于多數學者對明代民間“過繼”行為的研究所依據的史料以明代判例判牘為主,而對于能夠反映民間“過繼”個案詳細內容的民間文書參考較少,致使一些研究結論與明代民間“過繼”的實際情況存在一定的誤差。如程維榮認為,明代民間立嗣文書必須到官府辦理手續,家父尊長寫立遺囑安排財產繼承問題也應當“經官給據”等,為此程氏還特地將明代判牘《盟水齋存牘》“爭繼馮明敬”中的“已經糧廳審定”一語認定為民間“過繼”到官辦理戶籍變更的實例。筆者認為,明初民間立嗣將家子出繼到他人家為繼子,可能存在以人丁為對象的徭役負擔即“人去稅存”問題,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一條鞭法”等賦役制度的改革,人身徭役負擔已經改為政府出銀雇役,嗣子出繼須到官辦理戶口遷移以過割役銀已經沒有實質意義,這也許是在明代民間立嗣文書中已經找不到關于“經官附除”約定的原因。因此《盟水齋存牘》中的“糧廳審定”,其審定內容應當是“馮鳴敬”的兒子“南芝”是否符合“過繼”條件,而不是須“經官給據”才可以過繼。在宋、元時期,出于國家稅收的需要,官府明令民間私產轉移必須到官辦理準予交易手續,即“經官給據”,否則,交易財產一半沒官,處罰十分嚴厲。而到明代,典賣田宅文書以及遺囑等民間處分財產文書必須“經官給據”的做法已經逐漸廢除,民間交易可以自由進行,所以在所見到的明代遺囑承繼文書中無法找到“經官給據”的約定內容。
二、明代民間文書中戶絕家庭的“過繼”實踐
1
明代民間戶絕之家“過繼”文書主要有遺囑“立繼”文書、“出繼”文書、贈與文書、遺贈撫養文書、招婿養老文書等。各種文書因“過繼”方式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格式。
一是遺囑“立繼”文書。明代的戶絕“立繼”有戶絕家長遺囑“立繼”、戶絕遺孀“立繼”、戶絕夫婦俱亡的族眾共議“命繼”等,其中常見的是家長遺囑“立繼”。遺囑“立繼”是在戶絕之家由戶絕家長生前寫立的“過繼”文書,此類“過繼”文書常見的稱呼為“遺書”或“遺囑”。遺囑“立繼”是明代民間社會最常見的“過繼”方式,此“過繼”行為多以寫立文書的方式實施。在明代判牘中,司法官吏常在判斷案情時提到戶絕家長的“遺書”。如前引《盟水齋存牘》“亂繼李衍庚”案中的梁逢南去世后,由其侄衍祚入繼,逢南妻陳氏偏愛其女婿李衍庚,欲將繼子逐出,將家產盡歸其婿。為維護正常的承繼秩序,梁氏族長便拿出逢南生前所書“遺書”一紙,按照該“遺書”的安排,對繼子、女婿以及陳氏的養老資費進行重新明確,維護了遺囑文書的權威。明代遺囑“立繼”文書在契約文書匯編中多有收存,現取一件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金世貞所立“遺書”如下。
立遺囑父金世貞同妻汪氏,自因無子,先年搬宥子佛成娶親完聚,不幸身病危篤,有弟世盛所生三子,今立次子佛壽繼嗣,當憑親族將身屋宇田園等業眼同分扒明白,有舊老土庫一所與侄佛祐等兩半均業,又新造土庫一所用銀二百五十兩與侄佛祐等兩半均業,仍有余屋田園并地等業注簿逐一開明,待妻汪氏及妾進喜、眷喜食用終身、買辦衣棺殯葬訖,余剩俱與成、壽二子均分,眾議成、壽二子遞年均納無辭,自立遺書之后,二子早晚勤心孝順,不得冒犯違逆等情,如違,聽母送公懲治,以作不孝而論,今恐人心難憑,立此遺書一樣二張付二子各執一張永遠照。
萬歷四十四年六月初一日 立遺書父:金世貞。同妻:汪氏
(以下財產清單略)
此“遺書”即是一件由戶絕家長寫立的遺囑文書。可以看出,此類“過繼”文書的格式由五部分構成:一是立繼的原因;二是遺產情況;三是遺產的分配;四是繼子的義務;五是違約責任。此文書中兩子的共同義務是贍養繼母及繼父的兩個小妾,并為之買辦衣棺送葬,其權利的不同之處是養子“佛成”只能參與“均分”財產,繼子“佛壽”不僅參與“均分”財產,而且還要對繼父“繼嗣”承宗。
二是“出繼”文書。“出繼”文書是“過繼”文書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由繼子的父母出面寫立“出繼”文書將子男“出繼”他人。“過繼”行為一般由戶絕之家男性尊長出面主持,但是在男性尊長已經去世的家庭,也可以由家庭主婦主持“立繼”活動。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祁門謝得興過繼書”,就是由家庭主婦主持所立。
在城謝阿黃氏觀音娘有二男,長男富興,次男得興。曾于洪武十年間將長男富興出繼十都叔謝翊先為子。為因長子不應,回宗了畢,未曾過戶。后叔翊先自生親男淮安,至十九年,次叔文先病故無后,有翊先體兄弟之情,與族眾商議,再來凂說,今黃氏愿將次男得興,戶名謝□出繼文先為子,實乃昭穆相應。自過門之后,務要承順翊先夫婦訓育,管干戶門家務等事,不許私自還宗。其文先戶內應有田山陸地、孳畜彩物并聽繼人得興管業,家外人不許侵占。所是翊先原摘(同擇)長男富興文書,比先系太姑本汪仲達收執,一時撿尋未見,不及繳付,日后賚出,不在行用。今恐人心無憑,立此文書為用。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黃氏觀音娘(押)
見人 謝曙先(押) 汪景原(押)
此件出繼文書與金世貞立繼文書的“遺書”相比,其承繼內容的人身、財產權利基本相同,其不同之處是寫立文書的是出繼之家的家庭尊長,而不是被繼承之家的父祖,故稱之為“出繼”。
三是具有贈與性質的“過繼”文書。明代民間社會的贈與行為是戶絕之家財產繼承的一種比較特殊的“過繼”行為,其文書在徽州地區被稱為“批契”。此類“過繼”行為的特點是贈與文書當事人在民事法律行為中一般只體現單方的權利行使和義務承擔,即贈與人只承擔給付財產的義務,不享有契約權利,而被贈與人只享有取得財產的權利,而無給付義務。如永樂二十年(1422年)“祁門縣胡仕批山契”。
岳父胡原承祖買受山二號,一號買受汪真五,字號坐落東都四保,土名木瓜塢,系經理二千五百六十號;又一號買受方通,字號土名郭公坑,系經理二千一百七十號。其山二號畝步四至自有經理可照。今前二號山因管業不便,自情愿批與女婿洪寬名下永遠為業,本家子孫日后即無家外人異言爭論。今恐無憑,立此批約為照。
永樂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立批契人 胡仕
奉 書 男 胡陰周 見人 曹天得 鄭伯善
此件“批契”顯示的明代民間贈與文書的格式有以下四部分,一是雙方當事人情況;二是贈與財產的情況;三是贈與的原因;四是違約責任。此類財產贈與行為的文書中雖然沒有約定受贈人對贈與人的人身或財產義務,但是從內容看,贈與人所贈財產應當是其財產的一部分,且在立契之時贈與人尚無晚年無依的境況,因此此類贈與或許是換取其晚年養老的可期待利益。贈與文書雖然在徽州地區被稱為“批契”,但是明代署名“批契”的民間財產文書并不局限于民間贈與行為文書。“批契”在明代民間使用范圍比較廣泛,有的表示“遺囑”,有的代表“贈與”等。“批”在明代民間契約文書中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文字,其基本含義有兩種:一是作為動詞使用,有“書寫”或“簽字”之意,常見的有“再批”“又批”等;二是作為名詞使用,相當于“文約”“文書”等。
四是遺贈撫養“過繼”文書。明代民間遺贈撫養契約文書一般出現在晚年無子家庭以自身財產附條件贈與他人以換取晚年生養死葬的養老領域。其基本內容是,戶絕老人寫立文書將自己遺下家產贈給對自己依法不應當承擔贍養義務的人,贈與的對價是約定由該受贈人對贈與人承擔生養死葬的義務。該類文書在明代徽州地區也被稱為“批契”。如洪武二十年“祁門縣王寄保批產契”。
五都王寄保娶妻陳氏,生育子女,不幸俱已夭亡。今身夫婦年老病疾,慮恐無常,思無結果,同妻商議將吾分下承祖王祥孫、王德龍經理名目產土,盡數批與侄婿洪均祥、侄女寄奴娘承業,管顧吾夫妻生侍送終殯葬之資。承祀侄婿子女,毋得違文背棄。如違,甘當不孝情罪毋詞。自批之后,一聽均祥己業,毋許家外非故異詞爭奪。今恐人心無憑,立此批契,永遠為照。
洪武二十年九月初八日 立批契人 王寄保
中 見 人 謝 寧 王志保
此“批契”約定受贈與人要承擔對其家庭“承祀”祭祖和照顧晚年生活以及送終殯葬的義務,可見與前述的“過繼”行為的內容基本相同。此“批契”顯示的明代民間遺贈撫養契約文書格式由以下五部分組成:一是贈與人的家庭情況;二是贈與財產的原因;三是贈與財產名目;四是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五是當事人的違約責任和權益保障。
五是招婿“過繼”文書。明代前期的法律規定,民間戶絕之家招養老女婿養老的,必須另立繼子以承宗,家庭財產由養老女婿與繼子均分。但是在民間實踐中,一些戶絕家庭招養老女婿以繼承財產,翁、婿相處融洽,不欲再另行立繼,直接將承宗祭祀義務交給養老女婿,這樣的入贅養老方式實際上等同于“過繼”。如洪武元年“李仲德入贅文書”。
十都李仲德,年二十九歲,未曾婚娶。有汾士云宅長女蜀娘未曾出事。今憑親眷汾元熙為媒,招仲德到汾士云宅為養老婿。隨即告稟親房族長,以蒙先可。今自過門合親之后,自當侍奉舅姑二尊,及管干公私門戶等事,務在精勤,毋致怠惰。二親存日,決不擅自回家。百年之后倘要回宗,聽從自便。如違,一任經公陳治,仍以此文為用。今恐無憑,立此文書為用者。
洪武元年四月初八日 李仲德(花押)文書
族伯 李子奇(花押) 族兄 李慶夫(花押) 主媒 汾元熙(花押)
此件贅婿“過繼”文書格式分五部分:一是當事人情況,男“未曾婚娶”,女“未曾出事”;二是中間人參與情況;三是為告稟“以蒙先可”,即招養老女婿應征得親族的認可;四是入贅婿應履行的義務,侍奉二老、支掌門戶、“務在精勤”、不得擅自回宗等;五是違約責任。此文書中的“管干公私門戶”就是繼受財產、當家承戶,與民間過繼的內容極其相同。
2
關于民間文書所反映的明代“過繼”內容,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祁門李云寄承繼合同民間文書”可見一斑:
十西都李興戶原有戶丁李四保,于上年間出繼同都汪周付為婿以為養老,原立摘繼文書。今因李四保生子云寄,又摘李興戶丁李法,本年大造,是李興戶內人朦朧又將云寄名目填注李興首狀內。四保岳母細囝訐告本縣,蒙批里老查處。李興、四保不愿煩官,遵奉孫爺教錄,憑中立文:云寄仍承汪周付戶籍奉祀、繼產、當差,李法仍承李興戶役,各自管辦。所有李興將云寄名目收入首狀,李興自行改正,云寄仍在汪戶當差。自立合同之后,二家各無悔異,如違,以自呈官理治無詞,仍以此文為始。今恐無憑,立此合同文書為照。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初八日
立合同人戶丁李長互(押)
同立文人:李夏(押)李四保(押)、汪三春(押)
里 長:謝錄(押)、謝公春(押)
代書中見人:李滿(押)
此文書囊括了明代民間諸多“過繼”內容,首先是以養老女婿“過繼”。戶主李興以其戶丁李四保入贅到“同都汪周付”家為養老女婿,這種以“出繼”的方式將過繼子作為養老女婿的過繼方式在明代民間實不多見。其次是以“過繼”子“奉祀”在異姓之間進行。“四保”以及其子“云寄”皆姓李,按照法律規定作為異姓入贅女婿只可以“承分”財產,不可以對岳父承宗奉祀,但是汪周付不僅招贅李四保為繼,并且在四保回到原主家后,又留李四保之子李云寄以外孫身份承應其戶籍,并“奉祀”“繼產”“當差”,出現了外孫承外祖父之宗現象。最后是招贅行為有良賤為婚之嫌。出繼人四保為李興戶丁,從文書內“李興、四保不愿煩官”、愿意托請“中人”調解并立約可知,四保作為訴訟案件的當事人,與李興不是父子關系,應為李興的家仆之類,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凡人”,而接受其做養老女婿并“承汪周付戶籍”的汪周付應當是具有“凡人”身份,且四保所娶之妻是汪家女兒而不是汪家的奴婢。汪周付擇立沒有人身自由的戶丁為入贅女婿進行入繼并托付其“奉祀”,形成了事實上的良賤為婚。上述“李云寄承繼合同”所顯示的過繼行為曲折、格式完備,是一件頗能代表明代民間過繼行為真實情況的文書。
該文書所顯示出的明代民間過繼內容基本為“奉祀”“繼產”“當差”三個方面:一是“奉祀”承宗。在被繼之家,招嗣子承繼的目的就是使本宗祖先有人祭祀,為達到此目的,戶絕之家必須以家產的給付為對價,沒有財產的給付,“宗祧”繼承很難實現。當然過繼子也必須履行對被繼承人家廟的祭祀義務,否則就很難取得被繼承人的財產,即使入繼取得財產,也可能被逐出而另立繼子。二是“繼產”。財產繼承是“過繼”的核心。當然,“過繼”的財產承繼為概括性承繼,既包括財產的承受,也包括戶絕家庭對外所負債務的承擔,即承繼人對被繼承人在承繼行為發生前對外負擔的債務也應予以償還。如祁彪佳天啟年間在莆陽任職時審理的一起“過繼”糾紛案,就摻雜著被繼承人殯葬債務償還問題,祁彪佳就是按照民間習慣明確判令“過繼”子償還被繼承人的棺殮之費。三是“當差”,又稱“承戶”,就是對被繼承人家庭的賦稅、勞役義務的承擔,如上述“李云寄出繼合同”文書關于出繼人的權利義務部分就把“當差”作為入繼人的義務。
3
由于明代民間“過繼”參與人身份的多樣性,致使民間“過繼”方式呈現出復雜性特征。筆者現圍繞明代“過繼”權利義務的三個核心內容,將明代民間“過繼”方式歸納為四類。
一是權利義務概括承繼類“過繼”。權利義務的概括承繼是明代最基本的“過繼”方式。如前述“李云寄承繼合同”中的李云寄對其外祖父的繼承就是“奉祀、繼產、當差”,明顯是全部權利義務的承繼。二是養老“承分”不承宗的“過繼”。就是繼子在承受繼父財產的情況下只履行對繼父的養老送終的義務,而無承擔奉祀承宗的責任。此類“過繼”方式多發生在收養義子和“招夫養子”的家庭。如萬歷二十一年“程祜一投贅應役文約”。
十六都程祜一,今因無妻,空身托媒投贅房東鄭臣五公焦坑口莊人鄭五孫媳吳氏為妻,撫育子女成人,養鄭五年老,及承種山地、管照山場,永遠應付。自投贅之后,務要小心伏侍,毋得言語抵觸,私自回祖。如違,聽自房東理治,納還財禮銀一十五兩整。今恐無憑,立此存照。
萬歷二十一年六月廿日 立投約人 程祜一(押) 代書媒人 鮑志(押)
此件“投贅應役文約”約定對鄭家的義務為“撫育子女成人、養鄭五年老、應付”差役等,其權利是“承種山地、管照山場”,其間并沒有關于承宗祭祀的約定。雖然此類“養子”“接腳夫”、贅婿等對入繼之家的財產權享有“承分”的權利,當然也包括被繼承人的社會義務的承擔,但是由于這些人多為身份貧賤的異姓之人,往往不被入繼之家賦予祭祀祖先的權利,因此其對入繼之家的權利義務的內容不具有完全性。三是以養老換取繼產的“過繼”。此類“過繼”的方式由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的財產,作為契約對價,繼承人應對被繼承人承擔生養死葬的義務,但是此類“過繼”的權利取得是在被繼承人去世之后才開始,而“過繼”開始前對戶絕老人的贍養行為只是“過繼”的前置義務,因此在整個契約履行過程中既不涉及對被繼承人家庭祖先的祭祀承宗的內容,也不涉及對被繼承人的社會義務的承擔。此種“過繼”方式多以簽訂遺贈撫養協議而產生。如前述“祁門縣王寄保批產契”,作為侄女婿,洪均祥既不是其法定繼承人,也不是王姓宗支,故在雙方的契約中只涉及繼產養老,不涉及奉祀承宗、當戶承差。四是只繼產不養老不承宗的“過繼”。即財產承受人只享有承繼被繼承人的財產權利,既不承擔被繼承人的宗祧祭祀義務,也不承擔對被繼承人的養老送終和承戶當差等義務。此類契約的當事人一般是具有血親或姻親關系的特殊主體,其贈與的目的一般具有富裕之家對相對貧弱之家的近親照顧或者將來幫扶利益的期待。前述的“祁門縣胡仕批山契”就屬于此類性質。
三、明代民間戶絕家庭“過繼”規則的發展與創新
明代民間“過繼”不僅對之前各歷史時期的“過繼”內容進行了全面的繼承和發展,同時也有明顯的創新。
1
綜合分析明代“過繼”文書所顯示的明代民間“立繼”規則,與唐宋時期相比已經出現諸多變化。一是立嗣的形式有所增加。明代以前的立繼形式主要有“立繼”和“命繼”。“立繼”就是按照法律規定確立嗣子;“命繼”就是在戶絕夫婦皆去世時由同宗房長族眾議立。到明代,為了減少民間矛盾,充分尊重戶絕之家的意愿,在同時存在數人符合立繼條件的情況下,通常的做法是由戶絕夫婦按照自己好惡和應繼者的品行賢否進行選擇,此種立繼方式被稱為“擇繼”。二是立嗣對象由“昭穆相當”向親及疏發展。雖然明代法律仍規定立嗣要“昭穆相當”,但是民間立嗣行為開始向多元化發展,不斷出現不立胞侄卻選擇遠房族侄甚至招養老女婿、收養義子為繼子的情形,在已招有養老女婿的戶絕家庭,多直接由養老女婿“過繼”承祀,不再強行要求另立嗣子與養老女婿均分遺產。三是打破了“一子不可承兩宗”的限制,確立了“兼祧”制度(詳見下文)。四是不再堅持“良賤有別”。在明代“過繼”文書中開始出現了以賤承良現象。如“李云寄出繼合同”中的李四保就是以“戶丁”身份出繼凡人汪周付為養老女婿,后又留下其子云寄承宗。五是立嗣必須經宗族認可的現象已有改變。明代戶絕之家按照自己的意思獨立選擇繼子可以發生法律效力,不再必須經過宗族同意。六是立嗣“經官附除”已經廢除。由于明代政府對民間不動產交易行為的管理政策發生了變化,致使唐、宋、元時期盛行的民間立嗣必須“經官除附”的硬性規定也隨之不再行用。七是繼子不得擅自歸宗的限制也有突破。明代民間文書顯示,一些已經過門的嗣子可以自由歸宗,只要另行補充相應人承繼即可。如前文所述的“李云寄出繼合同”中的李四保就是留下兒子承祀自己回到原主家生活。
2
“兼祧”就是同宗兩房以上家庭中只有一家生育有一個子男,另一房無子,由宗內兩房唯一的兒子同時作為兩房的繼承人,這種一子承祀兩房的做法就是“兼祧”。“兼祧”現象最早在南宋民間已經出現,因不合宗法禮教而被政府官員否決。對于如何解決這種民間社會因無法找到合適的過繼子而可能出現絕祀的現實問題,在國家制定法沒有現實答案的情況下,明代民間則創制了“兼祧”這種特殊的宗法繼承方式,以民間智慧彌補了國家法律的不足,為解決無嗣家庭老人生養死葬、傳宗接代提供了兩全的現實方案。但限于史料視野,筆者所見到的明代承繼文書中尚未見反映明代“兼祧”承繼的內容,因此有學者稱“兼祧”“繼承習慣在明清的農村十分流行”,顯然有溢美之嫌。但是在刊刻于明天啟年間的馮夢龍小說《醒世恒言》以及明末清初講述明代松江府民間故事的《飛花詠》等小說中都曾顯示一子“兼祧”承繼兩家甚至三家煙火的故事,可知“兼祧”現象在明末民間社會確實已經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在民間實踐中,“兼祧”承繼規則的實行必須同時符合四個條件。一是繼子的選擇范圍一般是同姓“同宗”,“不許乞養異姓為嗣,以亂宗族”,是謂“異姓不養”。二是繼子必須在輩數上與承繼之家“昭穆相當”,不能紊亂被繼承人的宗法支脈。三是出繼之家與入繼之家必須是兩家只有一子,若有兩子,則只能過繼,不能“兼祧”。四是承繼人必須一人承擔兩家祭祀祖先和傳宗接代的義務,并且兩家應分別為“兼祧”子各娶一妻室以生子。但是這種一子兩祧的做法,從其產生之日起便與傳統社會宗法禮教以及國家法律相沖突。在禮教方面,“兼祧”是一個子男承繼兩家香火,與“孤枝不立”的傳統承繼觀念不同;在法律方面,“兼祧”子在本家和承繼之家各娶一妻,與國家法律規定的一夫一妻制度不符。為了做到“禮”“法”兩全,民間社會進行了技術性操作:即在禮教層面,將“兼祧”子的本生與過繼兩種身份分開看待。在本生父母家內,其是本生子,按正常家庭規則娶妻生子,祭祀承宗;在出繼之家,其以過繼子身份出現,稱被承繼人為父母,按過繼規則娶妻生子,為承繼之家祭祀承宗,兩不相擾。在法律層面,其兩房妻子各自獨立生活,彼此互不以宗法嫡庶、尊卑區分。當兩房妻子彼此發生沖突需要追究法律責任時,法官則依據婚娶時間或宗房長幼規則以妻、妾名分區別對待,從法律層面解決了一夫兩妻現象的現實矛盾。
3
明代的遺贈撫養就是戶絕之家以財產換取養老的民事習慣性規則。從契約文書看,中國傳統社會具有現代民法意義的以財產換取養老的民間規則最早出現在明代。雖然按照政府規定,明代戶絕老人可以住進專門養老機構“養濟院”,由政府養老,但是民間社會仍然是以居家養老為主,一些膝下無子的老人如果不采取“過繼”方法,依然處于老無所依的境地。為了解決戶絕老人的養老困難,明代民間社會存在一種以家產換取養老的“遺贈撫養”性質的民間“過繼”養老形式。如前引“洪武二十年祁門王寄保批產契”所顯示的民間“過繼”規則與現代民法中的“遺贈撫養協議”并無二致。可見,在明代政府對戶絕家庭的養老問題無法進行有效解決的情況下,民間社會則自發地創制了解決孤寡老人晚年生養死葬難題的習慣性契約規則,彌補了明代國家制定法的缺憾。
4
關于財產繼承問題,明代前期的法律明令禁止家庭財產繼承中的異姓承繼,即明代的養子沒有法定財產繼承權。但是在民間承繼實踐中,個別地區則出現異姓養子承繼養父家庭財產的現象。如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中收錄的一件“嘉靖三十九年謝弘等賣養子文書”顯示:立賣養子人謝弘的繼母李氏收養“謝生兒”為“義男”,已為其娶妻生子“六乞”,“生兒”死后,其妻“妙秀”改嫁馮淮西,“六乞”即隨母生活在馮家,后為馮家“過繼”承宗。
在明代晚期,這種異姓養子對養父承宗養老的現象不僅在民間文書中多有出現,而且在地方政府的判牘中也有一定存在。如在祁彪佳《莆陽讞牘》中,有一莆陽民方啟寅膝下無子,其妾黃梅花抱養一螟蛉子名方瓊。依照法定繼承,啟寅應立其弟啟休子尾仔為繼子,依啟寅遺囑,又立同宗方武珍為繼子。啟寅死后,遺下土地十畝。方家諸繼子、養子就繼承問題爭執到官,其妾黃氏堅持將家產留給養子,不情愿由“過繼”承嗣的侄子尾仔承繼。判官祁彪佳斟酌情法認為:“螟子無預繼事,方瓊只量給田地三畝,其七畝著尾仔與武珍均分,歲時蒸嘗(祭祀)二子共之。”就其財產分配看,養子所得僅少于繼子半畝,每年祭祀費用還要由繼子承擔,基本等于均分。因此祁彪佳自稱其判為“存繼之名不計繼之實”,從判決上承認了養子的財產繼承權。
上述諸案例表明,明代異姓“過繼”現象在法律層面雖然不被認可,但是在民間社會卻廣泛存在并逐漸形成規則,大量的社會存在倒推了地方政府的司法認可并產生了一系列可供參照執行的典型案例,在民間習慣與司法實踐方面為傳統社會民間“過繼”的實務操作提供了規則性依據。
結 論
綜上所述,通過民間“過繼”文書可以看出:明代民間戶絕家庭“過繼”養老制度體系已經初步完備。其內容是在無子家庭擇立嗣子以祭祀祖先、養老送終、傳宗接代。無嗣子可立或兩房一子的,則以養老女婿、養子或“兼祧”子為養老送終人。無養老女婿、養子或無子可“兼祧”的,則以遺贈撫養的方式作為生養死葬的依靠。有法定或契約義務不履行的,在官,對孤寡老人“應收養而不收養”或“剋扣衣糧”的,依《大明律》“收養孤老”條予以處罰;在民,繼子不贍養老人或“奉養有缺”的,“以不孝論”,送官糾治,即按國家法律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明代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尚未形成,民間養老基本依靠居家養老為主,因此戶絕家庭的養老只有依靠讓渡遺產的“過繼”和遺贈撫養等方式來換取。民間文書顯示,明代民間以“過繼”方式對戶絕老人進行養老的規則已經形成體系,“過繼”養老已經成為明代民間養老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深入研究明代民間戶絕家庭“過繼”養老制度規則對全面把握明代社會史以及家庭法律制度史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在本文構思過程中,得到了明史學者徐曉莊先生在寫作素材等方面的熱心幫助,特此感謝。
①影印件為“翊先”,據文書分析,“次叔文先病故無后”,翊先已生子“淮安”,應承順文先遺婦訓育。②筆者在《敦煌資料》中見到一件唐代的稱之為“唯書”的文書,其內容是當事人“尼靈惠”將“家生”奴婢“威娘”的人身權交于其侄女“潘娘”使喚以換取對自己的“葬送營辦”,但是其以家婢人身勞動換取履行喪葬義務的做法,與現代民法的以財產換取生養死葬有實質的區別。參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年,第430頁。